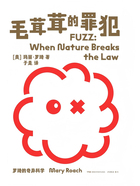
第1章
袭击案探警
犯罪现场取证:鉴定非人类凶犯
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美洲狮把你咬死的概率和你被文件柜砸死的概率差不多。在加拿大,除雪机致死人数是灰熊致死人数的2倍。北美人被北美野生哺乳动物杀死的情况极为罕见,这种事发生后,调查工作都由本州或本县专管钓鱼、打猎的警员和督察员负责,其隶属的机构叫作“鱼类及捕猎管理局”(或“鱼类及野生动物管理局”,因为像我所在的州已很少有打猎的状况,机构就重新命名了)。由于这类事件罕见,管理局只有极少数人有这方面的经验。他们常常处理的是偷猎案件。一旦局势逆转,嫌疑犯变成动物时,他们就需要另一种截然不同的犯罪现场鉴定和取证方法。
没有这套方法,就会犯大错。1995年,一个年轻人死在山间小路上,脖子上有刺伤,人们通常推测是美洲狮干的,而真正的凶手,却得以逃脱。2015年,人们又错误地判定某个男人是被一头狼从睡袋里拖出来再咬死的。这类案件就是设立“野生动物人类攻击案特训班”的原因之一(WHART创始者们开玩笑说,由首字母缩写而成的简称WHART“太不搭了”[2])。特训班为期五天,一部分课程是课堂讲座,另一部分是实地培训,教员们来自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自然环境保护署[3]。
因为加拿大人在这方面很有经验。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美洲狮袭击事件比北美其他州或省都要多。那儿有15万头黑熊(阿拉斯加只有10万头),还有1.7万头灰熊,以及60名掠食动物攻击专家,其中14名(专家,不是熊)从加拿大赴美,担任WHART特训班教官。2018年的特训班由内华达州野生动物管理局承办,其总部设在里诺(Reno),也就是博彩业的发源地之一,这个背景资料有助于我们理解一点——为什么野生动物专业人员的特训会在一家大赌场里进行?常驻于此的野生动物只有Betti the Yetti[4]老虎机上毛茸茸的拟人动物,以及导致游泳池关闭一天的某种“有危害性”的未知生物。本周,似乎只有WHART特训班预订了赌场的会展中心。赌场内部管理人员就在我们隔壁的会议厅里玩宾果游戏。
本期特训班的学员共有八十余人,分成了几个小组,所有的组长都由掠食动物攻击专家担当。和许多加拿大人一样,他们和美国白人看起来没什么差别,只能从口音上加以区分。我在此特指的是北方人用乡土气息浓郁的反问句式来收尾的习惯。这种方言习惯挺讨喜的,听来十分亲切,但就当下的主题而言却很容易出戏。“吃得真不少呢,嗯哼?”“只剩两三根筋连着,你明白不?”
我们的会议厅名叫“黄松厅”,有一个讲台和用于播放幻灯片和视频的大屏幕,这部分属于标配。不属于标配的是5只很大的动物头骨,在房间最前面的长桌上摆成一排,俨如要发言的与会者。屏幕上,一只灰熊正在攻击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克兰布鲁克市的维尔夫·劳埃德。这段录像是讲座的辅助内容,讲座题为:“掠食动物进行人身攻击时的击毙战术讲析。”维尔夫的女婿试图射杀熊,又不想伤到人,教官总结了他当时面临的难题:“你能看到熊的全身,时不时才能看见维尔夫的一条胳膊或一条腿。”结果,这位女婿救了维尔夫的命,但也射伤了他的腿。
另一个挑战在于:受肾上腺素影响,枪法会失准。精细运动技能会瞬间消失。教官告诉我们,此时该做的是“直接跑到那头野兽面前,抓稳枪管,向上方开枪”,以避免击中正在受到攻击的人。哪怕你要冒着“攻击转向”的风险——这种术语听上去挺镇定的,但说白了就是野兽撂下手头的受害者,转头朝你扑来。
第二段视频说明了身处猛兽攻击的混乱局面时,保持秩序和纪律非常重要。视频中的那头雄狮正在向一个猎人发起攻击。同行猎人像无头苍蝇一样乱跑。教官在好几个瞬间按下暂停键,我们可以看到有支步枪指向狮子的同时,也瞄准了它身后的某个猎人。我们得到的建议是“按兵不动,并保持沟通”。稍后,我们将去赌场下面特拉基河边的灌木丛里进行沉浸式野外实地培训。
光标再次滑向“播放键”,狮子继续攻击。我以前在动物园工作过,每到喂食时段,狮子馆里的咆哮宛如上帝发声,听得我胆战心惊。而那不过是狮子们用餐时的闲聊罢了。这段视频中的狮子可是要吓破你的胆、要你的命。玩宾果游戏的那群人肯定很想知道在黄松厅里的我们到底在干什么。
又听了一场讲座,我们进入午休时段。预先订购的三明治已备好,等着我们去赌场另一头的小餐馆自取。排队等候的时候,我们这群人吸引了不少好奇的目光。确实不同寻常,我心想:你在赌场里肯定不太会看到这么多穿制服的执法人员。我取走自己的午餐袋,跟在几个保护署官员后面,走向外面的草坪。他们的皮革登山靴走起路来咯吱作响。“她看了看后视镜,”有个人在说,“结果看到后座上有一只熊,正在吃爆米花。”监管野生动物的官员们聚集一堂时必定三句不离本行。比如昨晚我踏进电梯时,有个人正说道:“有没有对麋鹿用过电击枪?”
趁我们午休的时候,教官们把椅子靠墙摞好,在桌上摆好了训练用的人体模型,每组一个,模型有分男女,触感柔软。有些制造者颇有艺术天赋,根据照片,逼真地仿造出了实际案例中的伤口,除了用到油漆,显然还动用了钢锯。用“伤口”这个词来形容利齿和兽爪所能达到的效果,未免太平淡了点。
我们小组的模型是女性,尽管仅凭脸部残余的部分很难确定性别,贴在桌上的标签也无甚帮助——标签上写的是“百威(BUD)”。后来,我去洗手间时沿途看到了被严重暴击的“拉巴特(LABATT)”和没有脑袋的“摩森(MOLSON)”。摆放人体模型的工作台都没有编号,贴的标签上写的都是啤酒品牌。我视其为一种非常加拿大的做法,很能让人放轻松。
我们的首要任务是运用刚刚学到的法医学知识,鉴定造成这些伤害的是什么动物。我们现在查看的是负责攻击案的法医们所说的“受害者证据”:身体和衣物遭受的损害。就我们这具模型来说,最严重的可见损伤在肩头(她只剩一条胳膊了)。她的一部分颈部皮肤已被剥离,一小块头皮像剥落的墙皮耷拉下来。眼睑、鼻子、嘴唇都不见了。我们一致同意:这不像是智人的杰作。人类很少去吃同类。如果谋杀犯要移除某些身体局部,通常都会选择手或头,不让警方通过指纹或牙科记录比对来确认身份。少数情况下,谋杀犯会带走一件战利品,但通常不太会选择肩头或嘴唇。
我们一致认为,她是被熊处决的。熊的主要武器是牙齿,其软肋是毛发不那么旺盛的脸。熊攻击人类时所用的战术就是它们互斗时用的那一套。“它们都是咬来咬去的,对吧?所以它们出于本能,就会直奔你的脸而去。”我们的组长乔尔·克莱恩是个直率的年轻教官,担任过十宗熊袭人案件的调查员。“它们扑向你,下一秒,你的脸上就会有这样惨重的伤。”乔尔的脸上——听他说话时,那就是我们目光的焦点——有一双毫无瑕疵、清澈水灵的蓝眼睛。我费了不少心力,不让自己去想这张脸在那种状况下的模样。
成为杀人犯的熊与优雅无缘,有一部分原因在于它们是杂食动物。熊不需要为了捕食而频繁杀戮,进化也为它们带来了相应的改变。它们会吃坚果、浆果、水果和草,它们也会吃垃圾和腐肉。相比之下,美洲狮堪称真正的肉食动物,以其捕杀的猎物的鲜肉为生,因此,它的杀伤力极强。美洲狮会跟踪猎物,巧妙地隐蔽自己,然后瞅准时机,从后方猛扑过来,冲着后脖颈咬下去——真正的“咬杀”。美洲狮的臼齿可以像剪刀刃那样合拢,干净利落地咬开肉体。而熊的嘴巴是为粉碎和研磨而进化的,臼齿的表面很平坦,下巴既能上下移动,也能左右移动。熊齿造成的伤口会比较粗线条。
而且,熊咬痕的数量极多。“熊就是喜欢咬、咬、咬。”乔尔说,被咬的人通常都像我们的人体模型这样“咬得一塌糊涂。”
我再去看周围别的模型,不仅有咬伤和抓伤,还有大范围的头皮剥离和皮肤剥落。乔尔解释了其中的力学原理。人类头骨太大、太圆,无论是熊或美洲狮都没办法在咬住人头时使上劲儿,下颚发不出压碎头骨所需的杠杆力。因此,当它咬合牙齿时,牙齿就会从头骨上滑下去,撕开皮肤,啃下头皮。你可以试想一下:咬开熟透的李子时,李子皮会怎样被扯下来。
鹿,是美洲狮喜欢的主菜。鹿的脖子比人类长,脖子上的肌肉也比我们的多。美洲狮想在人类身上使出它们的咬杀绝技时,狮牙很可能在通常有肉的地方咬到骨头。“它们会试图用犬齿咬下去,把上下牙齿咬合起来,咬开皮肉再扯下来。”特训班的联合创始人凯文·凡·达姆在名为“美洲狮攻击行为”的讲座中这样说道。凡·达姆长得像宇航员,洪亮的声音不用麦克风就能传到黄松厅的最后一排。有一次,我打开手机上的分贝测试程序,惊讶地发现他的声音达到了79分贝,和垃圾处理机的音量差不多。
我们小组的模拟受害者身上的爪痕表明美洲狮不可能是嫌疑犯。与犬类不同,猫科动物的爪子在抓取猎物时会留下一串三角形的穿刺伤。熊的攻击更可能留下平行的疤痕,也就是呈现在我们眼前的爪痕状况。
乔尔向前走了一步,靠近人体模型的头部。“凯,这儿还有什么迹象?缺了鼻子、嘴唇,对吗?所以,我们之后要考虑去哪儿寻找这些……?”
“熊的胃。”我们小组的几个人高声答道。
“胃容物[5],对极了。”乔尔经常说“对极了”。事后写这个章节时,我总觉得他的口头禅是“宾果”,但那很可能是从墙的另一边渗透过来的记忆。
整个会议厅里,没有哪具人体模型的躯干是敞开的。没有凡·达姆所说的“吃内脏”的情况。我的第一反应还挺惊讶的。之前做调研时,我从某本书上得知食肉动物往往会直接撕开猎物的腹部,取食内脏——也就是最有营养的部分。我们的教官说,在人类受害者身上不太能看到这种情况,有一种可能是因为人穿着衣服。熊和美洲狮在猎食或吃尸体时都会避开有衣服的地方。也许它们不喜欢衣服的触感和味道,或者它们搞不明白,不知道衣服下面就是肉。
乔尔指了指脖子和肩上的一组伤口。“我们要考虑死前还是死后?”换句话说,我们的受害者遭到这些损伤时是还活着、还是已经死了?搞清楚这一点很重要,否则,在尸体身上找东西吃的熊就可能背上杀人的罪名。根据穿刺伤口周围的淤斑,我们判定这是死前留下的伤。死人不流血,也不会有淤青,淤青就是皮肤表层下的血管破裂。如果心脏不再输送血液,血液就不会再流动。
乔尔给我们讲了一个故事:有人在树林里发现了一具被啃咬过的尸体,尸体紧挨着死者的车,有一部分被掩埋在树叶下面。看起来像是熊咬的,于是,人们在附近捕获了一只熊,但死者的身上和身边没太多血迹。调查员们在该男子的脚趾缝里发现了针眼,并在汽车地板上发现了一支用过的注射器。尸检证实了该男子死于吸毒过量。正如乔尔所说,那只熊只是“逮到了一个可以吃到高脂肪、高热量美餐的好机会”,就把他从车里拖了出来,吃了一顿,再把尸体藏起来,留着下顿再吃,那只熊得以无罪释放。
乔尔把我们的人体模型翻过来,露出背部的另外一两处死前遭受的重伤。我指出两小块被抓扯下来的皮肉,它们贴着脊柱边,没有紫色淤斑或红色血迹。昨天我们看过一张幻灯片,显示了啮齿动物造成的死后损伤,我据此大胆猜测:可能有某只森林里的小动物啃食了我们的尸体。乔尔和我们小组的一位成员交换了一个眼神,对方是来自科罗拉多的野生动物生物学家。
“玛丽,那些是喷射成型留下的印记。”他的意思是,这是人体模型的制造工艺所致。假如我前几天没出过大糗,这也不至于让我太尴尬——前几天的练习中,我作为小组记录员负责记录牙齿造成的伤口测量结果,但我记下的是厘米,而非毫米的缩写,导致本组的证据是自侏罗纪时代以来闻所未闻的上下犬齿间距。
说完了“受害者证据”,我们现在开始探讨“动物证据”——在攻击现场被射杀,或在附近被捕获的“嫌疑犯”体表或体内的证据。乔尔举例说,你可以在动物(记得先把它固定好)的牙龈囊里找到受害者的皮肉。熊吃人也会塞牙,这样想来总觉得怪怪的,但确实一找一个准。
乔尔补充说,换作是美洲狮的话,有时可以从爪子深处的缝隙里找到受害者的血液或皮肉。“你得把它们——那些可以伸缩的爪子——全部推出来,才可能在爪子下面找到证据,对吧?”
但在估算攻击动物的爪子大小的时候,爪痕却可能导致误判。动物踏出一步将重心转移到脚上时,那只脚的爪趾就会张开,脚印看起来就会更大一点。调查员在测量衣服上的爪孔或牙孔时也必须警惕这一点,因为布料在被爪子刺穿时很可能起皱或折叠起来了。
“好了,还有什么是我们该查看的?”
“毛皮上有没有受害者的血迹?”有人问道。
“是的,对极了。”乔尔还提醒我们注意:如果这只熊是在袭击现场被射杀的(而不是在事发后被围捕的),熊和受害人的血可能混在一起,使DNA测试结果含糊不清。“那我们该如何预防这种情况呢?”
“堵住伤口!”这就是不列颠哥伦比亚省自然环境保护署的男性探员们的车里会有一盒卫生棉条的原因。
我们要查找的——这所有细节的终点——是关联:将凶手和受害者联系起来的犯罪现场证据。乔尔走到会议室的前面,从桌上拿起一只头骨。他把上排牙齿扣在人体模型肩头的一排伤口上。这就是实锤落下的时刻。上排犬齿和门齿是否刚好契合模型肩上的咬痕?如果是,下排牙齿是否与模型背面的咬痕相匹配?
确实匹配。“压力和……”乔尔把下颚骨嵌在人体模型背面的伤口中。“反作用力。这就是你们要的铁证如山。”
我在本章开头提到过一个死于登山小道的男人,脖子上有穿刺伤。虽然没有一组上下匹配的齿痕证据,调查人员仍然认为这是美洲狮攻击所致。事实证明,那些伤不是任何野兽的牙齿造成的,而是用冰锥刺出来的。凶手逍遥法外,直到十二年后犯了别的案入狱,和狱友自吹自擂时才说出了这件事。
相反的情况也时不时发生:某人被误判有罪,但杀人的其实是野兽。最著名的莫过于澳大利亚的琳迪·张伯伦,1980年,她和家人在艾尔斯岩附近露营,她尖叫着说她看到一只澳洲野狗叼着她的孩子跑了。我们的教官之一,掠食动物攻击专家(也是幸存者)本·比特斯通在一次讲座中解说了此案。因为澳大利亚的调查人员没有找到尸体,也没有逮到野狗,所以无法像我们现在这样探查究竟。他们无法将受害者证据与动物证据关联起来。没有关联,庭审只能靠假设(比如:一只野狗不可能或不太会叼走一个10磅[6]重的婴儿)、人为的错误和媒体的狂轰滥炸来煽动公众舆论。张伯伦被定罪后大约三年,有一支搜寻攀岩者遗体的搜索队发现了一个澳洲野狗巢穴,洞里有些婴儿衣物的残片。张伯伦被宣告无罪释放——她的小孩真的是被野狗吃了。
时至今日,我们通常使用DNA匹配法来建立关联。被捕获(或被杀)的嫌疑犯的DNA是否匹配受害者指甲下的头发或皮肤的DNA?动物的DNA是否匹配在受害者身上找到的唾液中的DNA?就动物攻击案而言,食腐动物会让这一流程变得复杂。比方说,受害者外套上的齿痕周围的唾液很可能是动物攻击时留下的,但从受害者皮肤上拭取的唾液却可能是事后来吃尸体的动物留下的。
加拿大的北方荒野里会有很多熊,所以,务必要建立确凿的关联。凡·达姆给我们讲了一个故事: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利洛厄特(Lillooet),有一个女人死于自家后院的熊掌之下。凡·达姆的团队设置了陷阱,对两头“很有嫌疑的熊”进行了DNA检测,但最终是在第三头熊身上得到了匹配结果。前两只无辜的熊都得以释放。
啤酒时段到了(在加拿大意味着下午5点)。教官们正在整理桌子,把人体模型搬到会议厅后面,堆在茶水桌旁的地板上。你想续最后一杯咖啡的话,必须先跨过一具尸体。我拦下了一位组员,自然环境保护署育空分部的亚伦·考斯·杨,请他简述WHART特训班不会涉及的一个问题:“在受到动物攻击或只是偶然撞见野兽的情况下,人们应该怎么做?”亚伦很爽快地答应了。他和乔尔同龄,都有端正的五官,举止很有教养。
你可能听说过一句谚语:看到黑的就反击,看到棕的就趴下。这话的意思是,棕熊(灰熊的一个亚种)对看似死人的对象多半没兴趣。但要这么说,问题来了——棕熊的毛色也可能是黑色的,而一些黑熊看起来却是偏棕色。要想区分这二者,更靠谱的方法是看爪子的长度和弧度,但等你离得够近、能看清这些细节并做出判断时,光有这方面的知识也不能解决眼前的危机。亚伦说:要考虑的重点并非是你面对哪种熊,而是哪种攻击。是掠食性的还是防御性的?大多数熊的攻击是出于防御。它们不是真的要击倒你,而是在吓唬你——你惊动了它,或是离它太近了,所以它希望你能乖乖地离开。“它会让你觉得它很大只、很吓人。它的耳朵会朝上竖,而不是往后贴着脑袋。”亚伦停了一下,擤了擤鼻子。他得了热伤风,挺可怜的。“它可能会用力地捶地面,喘粗气。”也就是跺跺脚或咬牙切齿。(但不会咆哮或低声怒吼,电影里才那么拍。)
亚伦把纸巾团一团,塞进羊毛衫口袋里。“它只想把你吓得屁滚尿流。”相比于黑熊,灰熊的进化是在更开阔、林木更少的地带完成的。黑熊受惊后的典型做法就是迅速消失在树丛中,但灰熊通常做不到。所以,它们决定让你逃跑。
对于这种虚张声势的建议是:你要尽可能做出不具威胁性的反应——慢慢地往后退,用平静的音调与那只熊说话。那就可能万事大吉,哪怕你面对的是一只带着幼崽的母熊。要说母熊的保护意识有多强,坊间传言都很夸张,但就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所有的熊,以及人和熊的所有偶遇来说,只发生过一次护崽母熊致命攻击案。(那是只灰熊。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至今尚无带着幼崽的雌性黑熊杀人事件。)
至于掠食性攻击,生存策略则完全相反。熊的掠食性攻击很罕见,开始时是悄无声息的,目标明确。往往是黑熊,而不是灰熊,这也和通常的假设正好相反。(尽管就两个物种来说,掠食性攻击都很罕见。)那头熊可能会隔着一段距离尾随你,在附近转来转去,一会儿消失,一会儿又冒出来。如果一头熊冲过来时耳朵是朝后平贴在脑袋上的,需要虚张声势的一方就该是你了——敞开你的外套,使自己块头看起来更大。如果你身在一群人中,那就让大家聚在一起大喊大叫,好让你们看起来像一个又庞大、又响亮的生物。“要试着发出这样的信号:‘我决不会不战而退,”亚伦说,“跺脚,扔石头。”
用这个策略应对美洲狮的攻击也很正确。堪萨斯州的先驱N.C.范彻的经验倒是可以给我们一点启示,1871年春天,他站在一头水牛的尸体边察看时,发现有只美洲狮正盯着他看。《堪萨斯州先锋史》(Pioneer History of Kansas)是这样描述的:范彻把一只脚踹进死水牛的双角间,用脑袋猛撞水牛的大腿骨,还上蹿下跳,“拼命地吼叫”。那头美洲狮就走了,说真的,谁看到这一幕不会赶紧溜呢。
如果那头美洲狮没被吓跑,而是冲过来并发动攻击呢?亚伦回答:“做你能做的任何事,去反击。”如果是熊,就攻击它的脸。亚伦指了指他的鼻子以示方向,那只红彤彤的鼻子都被擦破了。“不要装死。”如果你在这个节骨眼装死,有可能,你很快就不用装了。
如果掠食性猛兽执意要进攻,无论是什么情况,你转身就跑莫过于最糟糕的事。尤其是面对美洲狮这样的肉食性猎手的时候,因为逃跑(或骑山地车)会引发“捕手—猎物反应机制”,好比按下了开关,一旦开启了,就会保持很长一段时间,直到捕杀完成。
特训班的教官之一本·比特斯通亲身体验过美洲狮的攻击,深知它们在进攻模式中有何等的决心和毅力。他是不列颠哥伦比亚省西库特尼山区保护署的警员,接到过不少动物攻击案件的救援电话——大多数都是遇到熊,有了轻伤。几年前,他接到了一通很不寻常的电话。一头瘦弱的美洲狮鬼鬼祟祟地在一对老夫妇家的周边出没。比特斯通在昨天的讲座中讲述了这段体验。他告诉我们,他下了车,没有携带武器,走向门口,敲门,全程都没有意识到那头美洲狮此时此刻正隔着玻璃窗紧跟着那对老夫妇。“只要那个男人离开这个房间,走进另一个房间,美洲狮就会去那个房间的窗边,”他对我们说,“玻璃上有爪印。”
突然,那个男人关上了门。比特斯通一转身看到了美洲狮,就在五英尺[7]开外,后腿蹲着,耳朵紧贴脑袋,尾巴摆来摆去。“我大喊大叫,冲着它踢腿,我们告知公众要做的那些动作我都做了,都没用。”美洲狮扑到了比特斯通身上,他试图掐住它的脖子,但它扭开了,再一扭头,狠狠咬进了他的工作靴。他抓起靠在墙上的一把扫帚,奋力抽打美洲狮,但它没有松口。他设法将扫帚柄塞进它的嘴,往喉咙里推。这时候,躲在屋内的那对夫妇只是透过窗户往外看。比特斯通一边用廉价的锡柄扫帚拖延美洲狮的进攻,一边大喊:“嘿!嘿!”
“那个老男人总算打开门,问了一句:‘你要怎样?’我就说,‘我需要一把刀!’”老男人就去了厨房,想找出某把特定的刀,结果发现它在洗碗机里。等他终于找到那把刀、再交给比特斯通后,比特斯通“手刃”了美洲狮。(尸体解剖显示,跑鞋的碎片卡在了那只美洲狮的胃囊口,堵住了胃部,导致它饥肠辘辘。)
亚伦和我收拾东西离开会议厅时,宾果游戏也散场了。当凯文·凡·达姆用胳膊夹着一个血淋淋的半裸人体模型走过走廊时,有个敏捷但有点驼背的玩家正向男厕所走去。凡·达姆走起路来大步流星,目不斜视,气宇轩昂。那位宾果玩家停了下来。“不好意思。”凡·达姆说了一句,没作任何解释。
赌场停车场距离特拉基河仅有四分之一英里[8],这条路上鲜有汽车经过。今天走这条路将乐趣多多,因为一路上有好多个黄色警戒带封起来的犯罪现场。穿着制服和“动物攻击反应小组”荧光绿马甲的男男女女带着步枪和尸体袋走来走去。今天是WHART实地特训日。
我们小组的犯罪现场介于道路护栏和陡峭的碎石堤坝基底之间。昨天晚上,反应小组收到了一份攻击事件报告,这当然是事先安排好的。我们据此得知,有个年轻人和未婚妻吵了一架,之后离开了两人当作居所的温尼贝戈房车,用睡袋在户外睡觉。凌晨四点,警长接到未婚妻的电话,她说他失踪了,警长就开车出去找了一圈。他找到了空瘪的睡袋,看到了一头狼,就开枪打死了它。之后,他把调查报告发到动物攻击反应小组,也就是我们。
我们的首要任务是保护案发现场,以确保没有大型动物潜伏于此。美洲狮和熊有时会掩藏受害者的尸体,用树叶和灌木枝将其浅浅地掩埋起来,留着以后回来再吃。对反应小组来说,这会让“犯罪现场”存在潜在的危险。
一个年轻女子走到我们小组中担任行动负责人的男人面前。“我哥哥在哪里?”她问道,“出了什么事?”我愣了片刻才反应过来:她在扮演妹妹的角色。她问出这句话时没有丝毫焦虑感。更像是在说“嘿,你们好啊”。与此同时,我们还能听到从路面的模拟场景中传来N.C.范彻那种撕心裂肺的吼叫。“你们必须找到他!他只是个12岁的小男孩!”这就是实地培训设置的场景感:有一个阿尔·帕西诺[9]在飙戏,别人都在看有线电视读书频道。
我们组的行动负责人把手搭在那位妹妹的肩头。“是这样的,我们接到报告,这个地区有野兽。”
“什么样的野兽?”说得好像她会回去拿望远镜似的。她抬起一只脚,跨过警戒线,“我要下去找他。”
行动负责人轻轻地按住她的胳膊。“听着,你现在下去可能受伤,我们不希望发生那种状况。我们的战术小组正在下面做菱形安全扫荡。”
我们之前练习过菱形扫荡。四个人背靠背,同步前进,武器待命。简而言之,就是带枪的人形章鱼组。每个人都要负责检查自己面对的象限区(四个区以钟面时间命名:12点区、3点区、6点区和9点区),如果没有看到危险,就要口头报告“安全”。右侧区域的人也要继续汇报“安全”。如此这般一个接一个,周而复始。这样做不仅可以全方位监察四周环境,还很安全,不会有人无意中把武器指向别人。只要有人发现有险情,就要当即喊出来,两边的人就可以迅速到位,守护两侧。这时,就会有三支步枪待命,随时可以瞄准开火,还有一个人负责照看后方。我们之前练习时,乔尔扮演带来危险的动物。我曾一度期待看到一些表演性的动作,甚至会有道具服装,但他只是走到我们面前说了一声“我是熊”。
我们小组的四个队友保持菱形组合在灌木丛中移动。亚伦爬上一块大石头,负责“制高掩护”,本该是一枪致命的制高形象,却因为他在托着步枪的掌心里塞满了纸巾而有损威仪。我再一次负责现场记录(因为“你是个作家”)。
“熊,3点钟方向!”这只熊不是乔尔,而是栩栩如生的假熊模型,给射箭选手练习瞄准用的那种硬泡沫道具。6点区和12点区的队员迅速聚拢在3点区组员的两侧,他们不用看着地面,脚步在粗糙的地面上滑动,各就各位。他们不约而同地举起武器,有点像跳芭蕾,更像是花样游泳混搭步枪射击,我们能不能把它发展成一个奥运体育项目?
飞快地数完“一二三”,假装向塑料熊开枪。有人高喊需要卫生棉条,激动人心的场面就这样结束了。
警长昨晚射杀的那头狼是个无辜的路人,还是误导我们错失真凶的一种干扰?现在,我们的职责就是厘清这一点。这就是一部野外侦探剧。
本该在睡袋里的受害者——由昨天我们用过的某个人体模型扮演——很快就在山下被发现了,他倒在一片灌木丛中。一个队员假装快速地拍完“尸体”的照片,因为乔尔扮演的那位平易近人的验尸官想赶在中午升温前把“尸体”移走。我们还有机会在停尸房(黄松厅)仔细检查它。
现场一旦被保护起来,就进入收集证据的阶段。各类证据被统称为“证物”,我们在警匪片的固定流程里已能学到这类知识。尸体、睡袋、脚印、爪印、拖曳的痕迹——这些都可作为呈堂证物。要送往实验室的物品被一一编号,先拍照,再放入证物袋中。在发现该物证的地方,会插上印有相应数字的记号旗。我的任务就是在《证物报告》文件中把这一切动作记录下来——对物品的简短描述、编号及其位置——我的字迹难以辨认,可能还会填错地方。
泥地中的动物足迹是熊的。不错,因为我们还没在讲座中学过狼的攻击是怎样的。(因为这种事几乎从未发生过。)
现在,队员们手脚并用,搜寻动物的毛发和血迹。这活儿干起来很不舒服——又热,又乏味,但非常重要。犯罪现场的血迹可以让我们掌握很多信息。血滴在地面上呈圆形,表明符合“重力模式”:血液因其自身的重量从伤口滴落下来。重力模式的血滴呈椭圆形,表明血滴下来时,受害者在奔跑。尾巴像彗星一样被拉长的血迹属于“暴力相关模式”——血是在受到重压的情况下喷出来的,比方说,大动脉受到爪子的挥击或猛力打击。这叫喷溅,而非滴血。
有人发现了一连串的滴血痕迹。乔尔叫我们仔细观察血滴的尺寸。假如沿着这条血迹看下去,血滴越来越小,那就可能不是从伤口滴落的。而可能是从动物的皮毛或是凶手的刀上滴下来的。如果血滴的大小前后一致——“持续失血痕迹”——那可能是“正在失血的人”留下的。血迹模糊表示有一种“接触模式”,也许是在受害者跌倒或放下沾了血的手的地方。
当我们确定自己已经把所有能找到的线索找出来后,乔尔伸出手,把一片叶子翻了过来,原来叶子背面有很小的一滴血。我们漏掉了这个细节。其实我们还漏掉了很多——石头上、植物上、地上的血迹。“泼溅模式。”有人自以为是地说道。
乔尔点点头,但又轻轻地补了一句:“是喷溅,不是泼溅。”
血迹和泥地上的痕迹一起讲述了这次攻击事件的全过程。睡袋上的唾液和血迹是刚刚被咬时留下的痕迹。熊把这名男子从睡袋中拖出来、拉进灌木丛中时,留下了拖曳和持续失血的痕迹。当该男子试图逃脱时,泥地上留下了摩擦的痕迹和血迹,接着,植物和岩石上出现了喷溅血迹,也许是熊为了阻止他而下了狠手。如果人死后停置很久,尸体腐烂时产生的化学物质会留下最后的证据,一片污迹,或是植被上发黑的区域,这被称作“分解岛”。这种岛上没有美丽的海滩。
乔尔说,这位受害者受的伤都已复制在一具人体模型上了。模型不在实训现场,但我们会在明天上午的课程上试图建立关联时再细细查看。
就这样,又到了啤酒时段。乔尔把各种道具、证物旗和硬塑料熊归拢好,我们一起沿路返回,各自回酒店房间换衣服。等我换好下楼的时候,我们小组的成员都已聚在二十一点牌桌后面的小酒吧里了,那儿可以看体育比赛直播。他们只想看冰球,埃德蒙顿油人队对多伦多枫叶队的比赛。
“嘿,”我试着寒暄,“多伦多枫叶队(Maple Leafs)的‘枫叶’不该拼写成Leaves吗?”事实证明,我没法和冰球迷们讨论语法问题,所以我决定出去散步。最后,我走到了一家坎贝拉猎人户外装备店。我不打猎,但我很喜欢动物标本。这家店里有一个相当出色的山区立体模型,更衣室门框顶部还有一只麝牛头。竟然还有一个“枪支图书馆”,我发现里面都是二手枪,而不是书。
柜台后面的男人在等我开口。我就问,这图书馆要不要办张借阅证?“你不能借这些枪,”他说,“都是卖的。”
“这么说的话,根本不算什么图书馆,不是吗?”我看今晚的天都被我聊死了,到此为止吧。
这次,来自犯罪现场的人体模型有些额外的附件。乔尔刚刚把一袋胃容物倒在桌面上——那只胃袋是用泥塑模制的,非常逼真——包括一只耳朵、一只眼睛和一小条带着头发的头皮,头发的款式也很明显:莫西干头。我们在小组中传阅了这些东西。一大清早就干这个活儿,未免太早了。甜甜圈都没人去动。
胃容物与我们这具人体模型的头部缺失的内容相吻合,这表明攻击者确实是熊,而不是狼。莫西干头看似花招儿,但事实证明并不是。乔尔道出原委:我们昨天实地训练的情景是基于真实的攻击事件扮演的——熊是真的,人是真的,莫西干头也是真的。乔尔在2015年调查过这个案件。事实上,WHART特训班里的所有人体模型不仅模拟了真实伤痕,也都有相应的真实受害者原型。
乔尔带来了一些真实的攻击事件的现场照片。有一张拍的是受害者的后背。最大的伤口在臀部,赫赫然、乱糟糟的一大口生猛的咬痕。这名男子睡觉时穿着连身长睡裤,乔尔说,熊拖动他的时候,屁股口袋的翻盖肯定被掀开了。“所以就在那个部位咬了一口。”过了一会儿,乔尔补充道:“你们知道有熊爪图案的那种睡衣裤吗?印在屁股口袋上?”在加拿大,那显然是一种常见的家居服,因为好几个组员都点了点头。“他穿的就是那种睡裤。”
在人体模型的肩膀上有一组清晰的咬痕。从上下犬齿印的位置可知,这人在受到攻击时是仰卧的。据乔尔推测,那头熊凑近了这个熟睡的人,也许舔了他皮肤上的盐分。那人醒了过来,可能发出了一些声音。“所以熊心想,行吧,要么一不做二不休,要么只能逃跑。熊选择了就地了结。”
与此同时,我们还有另一个嫌疑犯,也就是警长到达现场时射杀的那只狼,狼的肚子里有什么呢?口香糖包装纸和锡纸,没有人体组织或衣物。结案,不需要再进行DNA分析了。
取证完成,确定了是哪种掠食性动物,接下来该干什么?假如人们没有在攻击现场附近射杀这头熊,它的命运又将会怎样?后来,凯文·凡·达姆在一次讲座中谈到了这个问题。监狱就不要考虑了。加拿大的动物园不会收留年龄在三个月以上的熊,因为熊总要走来走去,也因为动物园通常都有足够多的熊了。等待它的只能是死刑。“如果一头熊把人当作食物,以后就会再犯,”凡·达姆说,“我当了26年的掠食动物攻击专家。我知道你们中的一些人不同意我的观点,但如果它伤害了一个人,它就只有死路一条。”
正如任何犯罪学家会跟你说的一样,预防胜于惩罚。对两个物种来说,最安全的做法终究是井水不犯河水。别让熊学会把人类和容易得到的食物联系起来。要求有熊出没的地区的居民管好他们的垃圾。告诉他们别再喂鸟,别把狗食放在门廊上。穿连身睡裤的那个男人住在树林里——垃圾车去不到的地方。垃圾可能都堆积在他的拖车外面。狼肚子里的锡箔纸和口香糖包装纸表明,在这片区域,野生动物已经习惯捡垃圾吃了。垃圾本身就是杀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