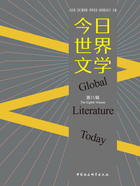
理论旅行的流通机制与世界文学的诗学问题
李孟奇[1]
【摘要】在世界文学研究中,世界文学理论的流通与接受机制往往很少受到相关学者的关注。结合萨义德的理论旅行概念,对理论旅行的过程、应用、变异、抵抗、经典化、本土化等多个方面进行分析,可以发现作为全球化进程产物的世界文学理论畅想,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非西方文学的全球流通,但是在涉及世界文学的理论构建与文学经典的评价标准等问题上却依然具有西方中心主义的倾向。同时,针对世界文学理论的东方旅行,对从泰戈尔、郑振铎到当代中国学界的理论接受情况及相关学者的世界文学观念构建进行宏观性的考查,则可以得出结论:非西方世界的世界文学研究只有在诗学层面上能够达到与西方世界分庭抗礼的程度,才能够真正摆脱西方中心主义的束缚。
【关键词】萨义德;理论旅行;世界文学;世界诗学;郑振铎
The Circulation Mechanism of Traveling Theory and the Poetics of World Literature
Mengqi Li
Abstract:In the study of world literature,the circulation and acceptance mechanism of world literature theory has often received little attention from relevant scholars.Combining Said's concept of traveling theory and analyzing its process,application,variation,resistance,canonization and localization,we can find that although the theoretical conception of world literature as a product of the globalization process has promoted the global circulation of non-Western literature to a certain extent,it still tends to be Western-centric in issues related to the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of world literature and the evaluation criteria of literary classics.At the same time,with regard to the oriental travel of world literature theory,by examining macroscopically how Tagore,Zheng Zhenduo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academy accept it and what world literature concepts relevant scholars construct,we can conclude that the shackles of Western-centrism can be rid of only if the poetics put froward in the study of world literature in the non-Western world can stand up to that from the Western world.
Key words:Edward Said;Traveling theory;World literature;World poetics;Zhenduo Zheng
一 理论旅行的流通机制
虽然《旅行中的理论》(“Traveling Theory”,1982)被收录至达姆罗什主编的《世界文学理论》(World Literature in Theory,2014),但是目前学界关于理论旅行的世界文学维度分析还缺少针对性,这或许和理论旅行只涉及诗学层面的流通机制,却缺少对文学文本流通的分析不无关系。同时,在世界文学理论层面的相关探讨中,也确实存在只关注非西方文学书写,却鲜少涉及非西方文学理论这一现象,正如瑞易瓦兹·克里希纳斯瓦米(Revathi Krishnaswamy)指出:“一个普遍的假设是,理论是独特的西方哲学传统的产物。从这个角度来看,非西方可能是异域文化生产的来源,但不可能是理论的场所。我们被告知,即使非西方产生的理论——后殖民主义理论——也只是对西方的一种回应。”[2]可见,即便是非西方世界拥有《舞论》《朵伽比亚姆》《文心雕龙》《沧浪诗话》等丰厚的文论遗产,却并不代表东西文化交流之间具有平等的理论阐释空间,就连以反抗性著称的后殖民理论也主要是以西方理论来反对西方的文化霸权,却无法在东方文论的资源中形成和西方理论双峰并峙的文化思潮。为了改变这种不平等的理论交流机制,关于理论流通的问题应该与文学文本的流通机制一样,引起一定的重视。
如果说在文学研究中,萨义德以世俗批评的境况性分析来代替以新批评为代表的封闭式阅读,那么萨义德对理论旅行的理解则主要反对以封闭的视野看待理论,并强调在对理论进行评述时要将理论传播的社会、政治、历史等境况性因素考虑在内。可见,在《旅行中的理论》中萨义德已经将文学批评与接受的现世性维度上升至跨文化理论阐释层面的情境性考量,这种分析模式与萨义德在《东方学》中所论述的西方中心视域下的东方主义观念一脉相承。萨义德将理论旅行主要限定于四个步骤:首先是观念产生的条件与境况;其次是理论从甲地到乙地的时间与空间转换中所要经过的不同语境;再次是包含着赞同与抵抗的特定接受条件;最后是在新的地点与时间被接受与使用的理论,必然要涉及对理论的挪用与再阐释。[3]然而,在文学批评领域却一直存在着方法论上的分歧,为理论旅行设置了障碍,一种是以文本性为基础的文学内部研究,另一种是包括社会历史等因素在内的文学外部研究。当文学研究局限于文本内部,文学批评就成了一种充满稳定性与专业性的阐释领域,而原本与文学研究关系密切的思想史等交叉学科也在新的学科空间中变得泾渭分明,不再干涉文学批评,这样,广义上的文学概念与文学研究就被狭义的文本研究取代,关于经典性的问题也会在此基础上退居为保守主义的建制派倾向。萨义德认为,只有当这种文本性与经典性的权威被打破之时,同质性的阐释空间才能够包容异质性的他异因素,从而赋予理论旅行完整的意义,并在境况性的文本阐释背景中加以分析。
为论述理论旅行在不同历史与社会境况中的意义阐释、应用界限、理论接受等问题,萨义德以卢卡奇(György Lukács)的《历史与阶级意识》(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1923)为例,论证了卢卡奇在不同时空中的理论接受情况。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卢卡奇在马克思关于商品拜物教分析的基础上,对物化现象进行了详尽的解释。卢卡奇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的劳动分工一方面使劳动成为一种高度机械化与重复性的工作,另一方面使时间量化为可以被计算的劳动定额,这致使心灵与人格被彻底地客体化,以便在商品经济中归入计算的法则。同时,人在这一劳动过程中并不表现为劳动的支配者,而是作为被机械化这一整体支配的一部分服务于这一生产流程。于是,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法则下,物就成为人的主宰,而“主体日益退隐为消极的、私人化的观照,并且渐渐地、愈益脱离了现代工业生活那势不可当的碎片化现实……从而进入了终极消极状态”。[4]萨义德认为,卢卡奇的目的在于对资本主义物化世界进行描绘的基础上以阶级意识锻造反抗性的可能,从而在政治上对资产阶级赖以生存的物化世界进行颠覆性的打击,这样理论就被赋予了带有革命色彩的现世性特征,而“无产阶级是他笔下的一个形象,它代表着意识挑战物化、心智维护其驾驭物质的权力、意识宣称它假定在只有客体的世界之外的一个美好世界的理论权利”。[5]
然而,卢卡奇的门徒吕西安·戈德曼(Lucien Goldmann)在《隐蔽的上帝》(The Hidden God,1955)中对卢卡奇进行引证的过程中,阶级意识却成了“世界图景”,从而失去了反抗性的维度。萨义德认为,造成这种理解偏差的原因在于卢卡奇与戈德曼迥异的境况性处境。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是为1919年匈牙利无产阶级革命而作,而戈德曼只是索邦大学的一名教授,正是这种写作情境的差异使戈德曼将卢卡奇的反抗意识与战斗热情转变为相对温和的理论阐释。可见,理论是对情境的一种回应,而理论的旅行则是一个使理论在流通中进行变异的一个过程。当然,萨义德并不认为一切对理论的解读都是一种误读,这样的理解既引起了对理论的盲目照搬,又否认了批评家的职能,相反萨义德重在透过理论旅行的过程强调对历史、社会等因素进行批判性的考量。
在卢卡奇物化观念的理论旅行问题上,萨义德尤为看重雷蒙·威廉斯(Raymond Henry Williams)对戈德曼与卢卡奇的分析。威廉斯在《唯物主义与文化问题》(Problems in Materialism and Culture,1980)中一方面使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恢复了革命性的批判锋芒;另一方面则针对卢卡奇物化理论的总体性困境对理论接受问题进行了批评性的反思。在威廉斯看来,从总体性的角度思考问题其悖论性在于著述者本身也是总体性的一部分,这使得任何关于理论的反思都处于内在的方法论困境之中,即便这种理论本身是一种具有创造性的实践。在卢卡奇的《小说理论》中,这种困境得到了集中的显现,致使卢卡奇在书中失去了《历史与阶级意识》的批判锋芒。出于对戈德曼的尊敬,《唯物主义与文化问题》并没有对戈德曼的卢卡奇接受进行直接的批判,而是在字里行间表明理论的阐释并不是一种不加批判与节制的重复,正如萨义德指出:“某种观念一旦由于它的显而易见的有效性和强大作用,而开始广泛传播开来,那么,在其流布过程中,它就完全有可能被还原、被编码化、被体制化。”[6]在对卢卡奇物化理论的接受问题上,萨义德的看法与威廉斯一致,一方面对卢卡奇的批判精神表示认可;另一方面认为物化与总体化并不能主宰一切,这恰恰表明理论的旅行是一种有限度的阐释与接受。正是在此基础上,萨义德认为对于人类智识空间的阐释既需要理论本身与理论旅行,又要认识到没有任何理论能够囊括一切境况性因素,所以对理论的运用形成批判性的认识就变得尤为必要。
针对理论旅行的诸多问题,萨义德提出了颇具建设性的反思性意见,具体可以归纳为以下五个方面:一是理论接受的前提在于认识到理论本身的不完备性;二是理论的解读并非客观中立,而是某种立场的产物;三是理论必须置身于理论起源的时间、地点等情境中才能得到明确的把握;四是批判意识既是对理论的一种抵抗,也是使理论得以“向着历史现实、向着人类需要和利益开放”的一种方式[7];五是理论的封闭[8]既会使批判性的意识丧失殆尽,也会使理论的阐释因缺乏多维度的审视而走向贫瘠。值得指出的是,正是认识到了理论的局限性与对理论进行抵抗与重塑的重要性,萨义德在《旅行中的理论》中认为福柯(Michel Foucault)的知识与权力分析过于强调权力的支配性,致使其论述缺乏反抗性的精神,忽视了对于权力进行抵抗的可能性,而这样的理论建构一旦被学院派加以权威化,其弊端在于理论“可以轻易地变成独断的教条……它们不断孳生的危害则在于,它们起初的源头——即它们的对抗的、对立的派生理论的历史——就会使批判意识变得麻木迟钝,使这种意识相信,原来是叛逆的理论对于历史依然是叛逆的、生动的、敏感的”[9]。回顾《东方学》一书,萨义德在对福柯的理论加以运用的基础上确实忽略了对东方主义进行抵抗的可能性分析。从这个意义上讲,《旅行中的理论》标志着萨义德超越了知识与权力结构的固有局限,并在后续的《文化与帝国主义》、《关于流亡的反思及其它文章》(Reflections on Exile and Other Essays)、《人文主义与民主批评》等多部著作中强调对位式的政治与文化反抗。在《理论旅行再思考》(“Traveling Theory Reconsidered”,1994)中,萨义德再次重点强调理论旅行在新的环境中可以使理论获得新的生命力与批判性的阐释空间,并继续以卢卡奇的理论旅行为例论述法兰克福学派领军人物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 Wiesengrund Adorno)《新音乐的哲学》(Philosophy of New Music,1949)及后殖民理论先驱弗朗茨·法农(Frantz Omar Fanon)《全世界受苦的人》(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1961)对卢卡奇的批判性继承。这表明,正是通过理论的旅行与对理论的批判性继承,理论的优势与局限得以同时暴露,并在新的境况性阐释中收获超越本土的价值与意义,从而启迪新的理论创建。
二 世界文学理论旅行的诗学问题
萨义德的《旅行中的理论》涉及理论旅行的过程、应用、变异、抵抗、经典化、本土化等多个方面,为学界考察世界文学的理论接受及其诗学问题提供了有益启示。针对世界文学的理论旅行,王宁指出:
“世界文学”本身就是一个旅行的概念,但是这种旅行并非率先从西方到东方,而是其基因从一开始就来自东方,之后在西方逐步形成一个理论概念后又旅行到东方乃至整个世界。因此它不同于赛义德所谓的“理论旅行”,因为后者一开始就是从西方旅行到东方,并在旅行的过程中发生了某种形式的变异,最终在另一民族文化的土壤里产生了新的变体。应该承认,理论的旅行很少体现为双向的旅行,然而世界文学的旅行却是个例外。[10]
借助萨义德的理论旅行概念,王宁的论述强调了世界文学观念产生的东方背景。正是在中国传奇的启发下,歌德提出了世界文学这一概念。可见,世界文学的双向旅行可以理解为以下四个阶段:首先,发轫于东方作品在西方的广泛传播;其次,歌德与马克思、恩格斯将这一文学文本的流通与接受现象概念化为世界文学;再次,后世学者将世界文学这一概念进行不断深化;最后,作为西方产物的世界文学观念又经由理论的旅行传播至非西方世界。可是,这种从东方及至西方的双向文化传播并非理论的双向旅行。从东西文学交流的角度看,只有文学的交流是双向的,而文学理论的旅行往往只是单向的。这样,西方在世界文学的问题上就仍然牢牢掌握着理论的话语权,卡萨诺瓦、达姆罗什、莫莱蒂等学者则成了永远无法越过的学术高峰,而非西方世界的作用往往只体现在推动西方理论的经典化。这表明,文学研究的去中心化倘若无法上升至诗学层面的平等对话,那么这股关于世界文学的理论热潮是强化还是削弱西方中心就仍然是一个值得玩味的问题。针对这一问题,张隆溪在《结语:世界文学观念的变化》(“Epilogue:The Changing Concept of World Literature”,2014)中针对世界文学的诗学问题提出了极具建设性的分析。在张隆溪看来,从歌德、马克思、卡萨诺瓦到达姆罗什的世界文学观念主要是西方观念的产物,这说明世界文学要超越欧洲中心主义与种族中心主义的局限,就不能仅仅通过阅读非西方文学来实现,而是要在理论层面上打破东西界限。因此,在世界文学的理论问题上张隆溪认为:
我们需要建立一个将西方与东方视为平等贡献者的公平竞争环境,世界文学的诗学应该是一组探究语言与表达的本质、意义与理解、阐释与审美价值、诗歌与文学的起源、艺术与自然的关系等问题。在不同的文学传统中,这些问题被提出和回答的方式肯定是不同的,但正是这样的基本问题及其答案构成了世界文学中的文学理论,不同的例子和批评的表述丰富了宝贵的见解。[11]
张隆溪的阐释提出了世界文学研究中往往被忽视的理论问题,也充分表明如果世界文学仅仅关注文学文本的流通、翻译与阅读等问题,却忽视在理论层面上构建东方与西方的平等对话机制,那么世界文学的多元文化畅想将只是实践意义上的空中楼阁。倘若无法在观念上打破西方文化与理论的支配地位,那么非西方文学资本将仅仅是世界文学舞台上的异域风格装饰,却无法撼动西方中心的话语根基。在此基础上,张隆溪指出世界文学的诗学同样涉及萨义德的理论旅行问题,即“对位并置”(contrapuntal juxtaposition)层面上的文学创作与文化实践。通过阅读《旅行中的理论》,张隆溪认为萨义德的理论旅行与世界文学的诗学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相关性:一是全球化时代的理论旅行不再遵循中心与边缘的单一结构划分;二是理论的域外传播与应用是一个适应与归化的实践过程;三是任何世界文学选集与理论的全球视角都无法做到绝对的价值中立,所以“世界文学在实践中总是本土化的,选择不同的作品进行研究和批判性的评论,以不同的文化和理论视角处理不同的问题,并具有不同的兴趣”。[12]可见,世界文学的理论畅想作为全球化进程不同阶段的产物,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非西方文学作品的全球流通,但是在涉及世界文学的理论构建与文学经典的评价标准等问题上依然是一种西方话语的角力场。在这场没有硝烟的理论论争中,非西方学者既要通过西方话语来迎合西方中心的学术思维,又要承担边缘话语与非西方文论资源难以进入西方主流学界的尴尬境遇。从这个意义上讲,世界文学的理论旅行及其诗学问题事关东方与西方能否在理论的争鸣与文学经典的构建中创立平等的话语机制,这也表明对非西方学者关于世界文学话语的代表性文献进行宏观性的把握是极其必要的。
三 世界文学理论的域外旅行
回顾世界文学观念发展的不同阶段,来自非西方世界的理论创建在不同程度上推动了世界文学的诗学构建。在东方世界,最早对世界文学观念进行回应的学者很可能为泰戈尔(Rabindranath Tagore)。据斯皮瓦克(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考证,泰戈尔在《世界文学》(“World Literature”,1907)中出于孟加拉语的语境考量把英语“比较文学”翻译成孟加拉语“世界文学”[13],这种误译或许也从侧面说明了比较文学的发展方向即是世界文学的理论畅想。泰戈尔从人类心灵的角度出发论述了文学对于重塑精神世界、展现人性光辉、塑造完美人格的重要意义。与歌德的世界文学观念类似,泰戈尔认为文学的重要意义就在于其非功利化的实践目的与普遍性人性的共通性表达,而出于功利化目的撰写的文学文本则只会在历史的淘洗中被淘汰。作为以“沟通东西方文化的桥梁”著称于世的东方作家,泰戈尔强调作家的世界意识,即“只有当作者的内心意识到人类的思想并在作品中表达人性的痛苦时,其作品才能被置于文学的殿堂”[14]。可见,泰戈尔的世界文学观念并不致力于讨论文本流通的过程性,而是主要抓住了文学文本自身的普遍性特质。在随后的散文随笔中,泰戈尔则以具体的实例论述了民族文学何以成为世界文学。在《爪哇通讯》(1927)中,泰戈尔认为穆门辛格县的民间诗歌之所以能够跻身世界文学,就在于这些诗歌表达了具有人类共通性的快乐与痛苦。[15]在《东方和西方》中,泰戈尔指出孟加拉文学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并出现了以般吉姆·钱德拉为代表的伟大作家,原因就在于孟加拉文学打破了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的界限,能够“毫不困难地吸取西方文化与思想的精华,为己所用”[16]。可见,泰戈尔世界文学观念的核心要义就在于在表达人类共通情感的基础上推动不同民族文学间的相互交流与借鉴。
在中国,世界文学的观念旅行已逾百年。据刘珂考证,在中国“世界文学”一词最早由黄人于《中国文学史》(1907)中提出[17]。然而,从引起广泛影响的层面讲,郑振铎的《文学的统一观》(1922)无疑对于理解中国的世界文学观念与实践具有先导性意义。在文中,郑振铎对文学研究中以国别划分研究界限的现象表示不满,认为应该以“文学的统一观”来整合全球范围内的文学资源。相较于分散的国别文学研究,文学的统一观可以有效地探求民族文学之间的相互影响与共同起源,把握不同民族的普遍人性与精神特质,并在方法论上形成对文学发展与进化的整体观念。同时,为解决文学的统一观在文学研究的语言、体量、翻译、鉴赏等层面面临的方法论困境,郑振铎一方面承认文学作品的可译性;另一方面认为文学研究的最高境界并非为文学鉴赏,而是以进化的视角审视全部文学作品的起源、渊源、情感等诸方面。在对西方世界文学观念的接受上,郑振铎所受到的直接影响来源于理查德·格林·莫尔顿(Richard Green Moulton)《世界文学及其在一般文化中的位置》(World Literature and Its Place in General Culture,1911)。经过跨越东西的理论旅行后,郑振铎并没有盲从于莫尔顿的世界文学观念,而是以文学的统一观对莫尔顿在文学研究中以一国文学为出发点的做法予以驳斥。这样,郑振铎就在理论旅行的批判性反思中形成了自身的世界文学观念建构。值得指出的是,郑振铎对于世界文学的热情不仅体现在观念层面的讨论,还见诸实践意义上以文学的统一观撰写《文学大纲》与主编《世界文库》,为推动中国的世界文学研究贡献了不世之功。
进入21世纪,世界文学的理论复兴也带动了中国学界的世界文学研究。但是,相较于西方学界对于理论建构的热情,中国学界关于世界文学的研究主要停留在以下三个层面:一是对卡萨诺瓦、达姆罗什、莫莱蒂等学者的理论研究;二是以中国文学海外传播为代表的文学文本流通研究;三是世界文学与相关交叉学科及学术概念的关系探析。关于世界文学的诗学建构则是少之又少。这其中,王宁作为佼佼者做出了重要贡献。在《“世界文学”:从乌托邦想象到审美现实》(2010)中,王宁根据达姆罗什的世界文学定义与中国文学的发展历程提出了自己的世界文学概念。他指出:
(1)世界文学是东西方各国优秀文学的经典之汇总;
(2)世界文学是我们的文学研究、评价和批评所依据的全球性和跨文化视角和比较的视野;
(3)世界文学是通过不同语言的文学的生产、流通、翻译以及批评性选择的一种文学历史演化。[18]
与达姆罗什的世界文学概念不同,王宁的世界文学定义既强调了文学文本在跨界流通中所衍化的文化现象,又对世界文学的经典性特质与文学研究的全球视角予以重视。同时,在判断一部文学作品能否成为世界文学的标准中,王宁的见解无疑也比达姆罗什的跨国文本流通更具系统性。他指出:“一,它是否把握了特定的时代精神;二,它的影响是否超越了本民族或本语言的界限;三,它是否收入后来的研究者编选的文学经典选集;四,它是否能够进入大学课堂成为教科书;五,它是否在另一语境下受到批评性的讨论和研究。”[19]面对欧洲中心主义的桎梏,王宁承认文学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其评价标准带有一定的相对性,这造成任何基于普适意义的考量都无法平衡不同民族在文化、历史、地理等诸方面的巨大差异。所以,在王宁看来世界文学标准的第三与第四个定义并不具备普遍性,反而带有一定的人为干预因素。从王宁的世界文学定义到世界文学的评价标准分析,似乎都预示着世界文学的讨论必然要上升至东西诗学层面的平等对话才能够摆脱文学研究的知识与权力话语,而王宁正是在有鉴于以中国为代表的诗学体系难以在世界文学的诗学舞台上施加重要影响力的前提下提出“世界诗学”这一概念。在《世界诗学的构想》(2015)中,王宁认为世界诗学首先要建立在东西方诗学的相互比较之上,并在认知诗学的基础上形成普适性的理论构建。从王宁对孟而康(Earl Miner)与鲁文·楚尔(Reuven Tsur)的批判性继承来看,王宁的世界诗学理论重在强调文学研究从文化批评向文本研究的回归,这表明王宁有意在文化理论衰落的后理论时代以世界文学为契机调和文化批评与文本研究的结构性矛盾,并以世界诗学的理论畅想整合东西方的文学理论资源,从而使世界文学的诗学能够以跨语言、跨边界、跨学科的视角走出西方中心主义的泥淖。
除王宁外,刘洪涛在分析中国的外国文学教材在结构与观念演变的基础上提出了“‘同心圆’的世界文学观”。刘洪涛的世界文学观念强调以中国为中心,具体表现在其主编的《世界文学作品选》中并没有中国文学作品入选,然而中国“却是这个同心圆关系结构的枢纽、标准、尺度,因此它又无处不在”。[20]在选集的编选上,刘洪涛强调以洲际文学为单位,同时兼顾国籍与民族属性存在混杂性的流散、族裔、语系文学,而在选集分册的顺序上则以中国与其他洲际文学关联与影响的先后强弱关系为基础,分为“亚洲文学卷”“欧洲文学卷”“美洲文学卷”“非洲、大洋洲文学卷”“流散、族裔、语系文学卷”。[21]刘洪涛的贡献在于将世界文学研究从理论反思与重建的基础上提升至文学选集的编选与实践,同时在编选结构上打破达姆罗什主编《朗文世界文学作品选》时的历史分期体例,带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时至今日,世界文学的理论旅行在世界范围内已经引起了广泛的回应与学术争鸣,而从泰戈尔到中国学者的世界文学阐释与反思则代表了非西方学者为打破东西文化隔阂,推动全球文学交流与重建世界文学经典秩序所做出的努力。然而,非西方世界对世界文学话题的讨论尚没有形成足以与西方进行分庭抗礼的诗学体系,正如达姆罗什在论述理论旅行时指出:“受后殖民研究的启发,理论向西方以外的世界开放已经进行了几十年,但它仍然是一个不完整的项目,尤其是因为‘理论’仍然主要来源于欧洲和北美……就像古老的伟大经典一样,理论经典赋予欧美理论全球适用的特权,而非西方理论主要用于讨论其文化起源。”[22]在中国,一个尴尬之处在于中国学界虽早已经将达姆罗什等的理论建构加以经典化与权威化,却缺少实质性的批判性反思与理论重构。这样,世界文学的理论旅行就面临与萨义德所论述的福柯理论接受相似的风险,即一个立足于批判性与反思性的理论构建由于在理论的域外接受过程中缺少了批判性继承的维度,致使原著原有的批判性锋芒在域外经典化的过程中被消耗殆尽。综上所述,世界文学的诗学构建确实具有现实的指导与实践意义,当然这样的工作并非一朝一夕能够完成,只有经过时间的淬炼与不断的打磨推敲才能够铸就“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理论构建。不过,正如张隆溪指出:“我们有前辈学者为榜样,有他们已经取得的成就为基础,加之我们自己的使命和抱负,只要不断努力,就总能够在问学的道路上,向前迈进一步,对普遍性的诗学和文艺理论,做出我们的贡献。”[23]在治学的道路上,经过前辈学者的开疆拓土与学术后浪的薪火相传,中国学界在不久的将来于世界文学领域足以形成独具特色的理论构建。
[1] 【作者简介】李孟奇,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主要研究领域为后殖民理论、世界文学理论。
[2] Revathi Krishnaswamy,“Toward World Literary Knowledges:Theory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in David Damrosch,ed.,World Literature in Theory,Oxford:Wiley Blackwell,2014,p.135.
[3] [美]萨义德:《世界·文本·批评家》,李自修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401页。
[4] [美]萨义德:《世界·文本·批评家》,李自修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408页。
[5] [美]萨义德:《世界·文本·批评家》,李自修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412页。
[6] [美]萨义德:《世界·文本·批评家》,李自修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419页。
[7] [美]萨义德:《世界·文本·批评家》,李自修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424页。
[8] 具体例证为新批评封闭式阅读。
[9] [美]萨义德:《世界·文本·批评家》,李自修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431页。
[10] 王宁:《比较文学、世界文学与翻译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60页。
[11] Zhang,Longxi,“Epilogue:The Changing Concept of World Literature”,in David Damrosch,ed.,World Literature in Theory,Oxford:Wiley Blackwell,2014,p.521.
[12] Zhang,Longxi,“Epilogue:The Changing Concept of World Literature”,in David Damrosch,ed.,World Literature in Theory,Oxford:Wiley Blackwell,2014,p.522.
[13] 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An Aesthetic Education in the Era of Globalization,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2,p.464.
[14] [印]泰戈尔:《世界文学》,王国礼译,载大卫·达姆罗什、刘洪涛、尹星主编《世界文学理论读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62页。
[15] [印]泰戈尔:《爪哇通讯》,白开元译,载刘安武、倪培耕、白开元主编《泰戈尔全集:第二十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76页。
[16] [印]泰戈尔:《东方和西方》,潘小珠译,载刘安武、倪培耕、白开元主编《泰戈尔全集:第二十三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46页。
[17] 刘珂:《中国的“世界文学”观念与实践研究:1895—1949》,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44页。
[18] 王宁:《比较文学、世界文学与翻译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08页。
[19] 王宁:《比较文学、世界文学与翻译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09页。
[20] 刘洪涛主编:《世界文学作品选》第一册,高等教育出版社2021年版,第2页。
[21] 刘洪涛主编:《世界文学作品选》第一册,高等教育出版社2021年版,第3页。
[22] David Damrosch,Comparing the Literatures:Literary Studies in a Global Age,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20,p.145.
[23] 张隆溪:《什么是世界文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年版,第19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