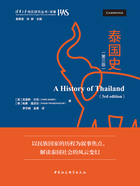
沿海地区称雄
贸易带来的财富对地缘政治产生了更为持久的影响。随着造船业的发展,海上贸易不断增长。从13世纪开始,阿瑜陀耶向南袭击马来半岛,并北上突入内陆地区,以控制产地,满足中国对于异域热带雨林产品,如香料、象牙、犀牛角和绚丽鸟羽的巨大需求。通过积极参与中国的朝贡体系,阿瑜陀耶成为中国亲密的贸易伙伴。随后,在15世纪后期,阿瑜陀耶又控制了横跨马来半岛颈部的运输路线,在东西方之间建立了新的贸易联系,避开了通过马六甲海峡的路线,后者路途更遥远且海盗猖獗。阿瑜陀耶因其贸易中心地位而繁盛起来,东方(中国)、西方(印度和阿拉伯)和南方(马来群岛)都在此进行货物交易。16世纪初到来的葡萄牙人将阿瑜陀耶视为亚洲三大强国之一,与中国和印度的维查耶纳伽尔帝国并列。
在15—16世纪,阿瑜陀耶一直在向北方诸城扩张势力。但这并不是简单的征服和兼并,而是一种更微妙的传统融合。财富和贸易联系给阿瑜陀耶带来了军事上的优势,它可以得到葡萄牙的枪支和雇佣兵的供给。但是北方诸城却可能拥有更多可供征募的人力,以及更强悍的尚武传统。一些北方人是被强行掳到崛起的港口都城的,但其他人可能是为了能够分享城市的繁荣而自愿迁去的。北方城市的统治家族也通过联姻与阿瑜陀耶王朝紧密相连。北方的战士成为阿瑜陀耶军队的将军。北方的贵族在港口都城定居,并融入统治精英阶层。阿瑜陀耶逐渐吸收了北方邻国的行政体制、建筑风格、宗教习俗,甚至可能还包括日常用语。由于阿瑜陀耶在贸易上具有地理位置的优越性,它也成为这个壮大了的联邦的都城。北方的彭世洛城因其对抗兰那的战略地位而成为第二都城(葡萄牙人有时候描述它们是双子城)。最终,来自北方的贵族成为阿瑜陀耶的王位决定者(king-maker)。1559年,他们终于驱逐了旧王系,独揽大权。
与此同时,贸易也引发了来自东边和西边的竞争。湄南河流域人口和权力的南移与这两边的情况相吻合。在西边的伊洛瓦底江流域,勃固(Pegu)取代旧的缅甸中心阿瓦(Ava)成为统治中心。在东边,高棉人放弃了王都吴哥,转而选择了湄公河三角洲一带的洛韦—乌栋(Lawaek-Udong)。勃固、阿瑜陀耶和洛韦—乌栋这三个港口都城相互竞争,以争夺与中国贸易所需的林产品等内陆资源的控制权。
他们的统治者们同样在竞争至尊的地位。这些地方的统治者通过贸易利润储备国库,从内地招募新兵充军,用外国雇佣兵充当私人卫队,用从被征服的邻国掠夺来的佛像和黄金装饰寺庙,他们把自己想象成转轮王(cakkavatin),即《三界经》(Traiphum)等佛教经典里描述的独一无二的征服了世界的帝王。在这场东—西竞争中,西边占据了优势,可能是因为那个方向是葡萄牙雇佣兵和大炮的来源。暹罗派兵击垮了高棉的都城,并立顺从的王子为高棉国王。勃固要求暹罗接受类似的朝贡地位,然后联合北方的贵族于1569年包围并攻占了阿瑜陀耶城。勃固掳走了大量人口、工匠、佛像和战利品;缴获了珍贵的大象作为标志性的贡品;并将阿瑜陀耶统治家族的成员带走作为妻子和人质。
但是,由于距离遥远,还需要跨越文化差异的巨大障碍,“套盒”就更加难以维持了。当越南在高棉的另一侧形成了抗衡势力之后,暹罗对柬埔寨的控制就衰落了。同样地,当入质勃固的暹罗王子纳黎萱(Naresuan)逃脱之后,他废除了与勃固的朝贡关系,并在其15年的统治期间(1590—1605年)花去大部分时间南征北战,对抗缅甸的侵犯,并重新确立了阿瑜陀耶在湄南河流域下游地区的统治地位。
到17世纪初,战争年代已难以持续。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大多数横贯东南亚大陆的统治中心都遭受过一次甚至多次洗劫。人们开始更有效地抵制仅仅为了皇家自尊而进行的屠戮。16世纪60年代,在被带到阿瓦的战俘中间爆发了一场大规模的暴动。其他形式的反抗虽然不及它壮烈,但是同样有效。人们会贿赂招兵人员、混入僧侣之中或逃进森林。统治者们竭力招兵,希望能维持先前的规模。城市投资修筑砖墙、拓宽护城河、安置防御性的大炮,这些足以抵消围攻者的优势。在16世纪90年代和17世纪初期,一系列围攻都以失败而告终,叛逃的士兵都散失于乡野之中。

图1-2 早期的政治地理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