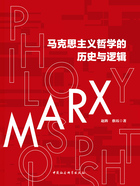
第一节 哲学是认识改造世界的世界观方法论
哲学是什么?这个问题古今中外很多学者和哲学家都在追问,但是并没有确切的答案。有一位哲学家曾说过,对于一位哲学家来说,最恶毒的问题就是问他什么是哲学。如果说有一千个读者就会有一千个哈姆雷特,那么有一千个哲学家就会有一千个关于哲学是什么的答案。古今中外不计其数的学者都以哲学家自诩,不同的学术流派都称自己的学问为哲学,但是他们的思想观点却大相径庭,而且千差万别、各有千秋的哲学学说却又能够共存于世。“我们必须讲明白:哲学系统的分歧和多样性,不仅对哲学本身或哲学的可能性没有妨碍,而且对于哲学这门科学的存在,在过去和现在都是绝对必要的,并且是本质的。”[1]
一 哲学是起源于惊异的人类智慧
在汉语中,“哲”是指聪明、智慧之意。在《尚书·皋陶谟》中记载有:“知人者哲,能官人,安民则惠,黎民怀之。”这里所说的“哲”即是智慧,而在中国哲学传统中,哲之智慧主要体现在伦理、政治活动之中。哲学所追求的智慧并不回答和解决各种具体问题,而力图为人类社会的生存和发展、个人的安身立命提供指引。古希腊文philosophia由philo(爱、追求)和sophia(智慧)构成,意思是爱智慧或追求智慧。哲学家并不是所谓的“智者”,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把智者看成是歪曲真理的诡辩论者,而真正的哲学家是“爱智者”,是追求智慧之人。
从逻辑上而言,哲学起源于人类对宇宙或人生方面的根本性问题的好奇以及沉思。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详细解释了哲学起源问题:“就从早期哲学家的历史来看,也可以明白,这类学术不是一门制造学术。古今来人们开始哲理探索,都应起于对自然万物的惊异;他们先是惊异于种种迷惑的现象,逐渐积累一点一滴的解释,对一些较重大的问题,例如日月与星的运行以及宇宙之创生,作成说明。一个有所迷惑与惊异的人,每自愧愚蠢(因此神话所编录的全是怪异,凡爱好神话的人也是爱好智慧的人);他们探索哲理只是为想脱出愚蠢,显然,他们为求知而从事学术,并无任何实用的目的。这个可由事实为之证明:这类学术研究的开始,都在人生的必需品以及使人快乐安适的种种事物几乎全都获得了以后。这样,显然,我们不为任何其它利益而找寻智慧;只因人本自由,为自己的生存而生存,不为别人的生存而生存,所以我们认取哲学为唯一的自由学术而深加探索,这正是为学术自身而成立的唯一学术。”[2]
追求世界的智慧本身就体现着人的智慧,《列子》中的杞人担心天崩地坠不是哲学而是庸人自扰,他出于自身安危而对自然现象产生恐惧而去探究问题,当他人帮其解开心结后也就不再追问天地之状。人们在现实生活中要能够“不疑人之所疑,而疑人之所不疑”,去探讨研究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的万事万物,使人类从无知过渡到有知。哲学所探讨解决的问题具有超越性特征,它通常超越现实的功利甚至是纯粹兴趣使然。古希腊哲学家毕达哥拉斯在谈到哲学时,曾以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人的不同动机为例,来解释哲学的特性。第一种人是奔奖牌而来的,志在取得好的成绩,第二种人尚无夺得奖牌的实力,但是抱着学习和积累经验的目的来参加比赛,第三种人并无功利动机,他们来此的目的仅仅是处于好奇,想对有关的东西弄个究竟。毕达哥拉斯认为,只有第三种人才属于我们所说的哲学家。
正因为起源于个人兴趣而对世界万事万物进行智慧求证,哲学展现出了千变万化的形态特征。中国古代庄子的哲学力图“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司马迁的历史哲学“究天人之际,穷古今之变”,张载的哲学所实现的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西方哲学家的哲学主题也各不相同,毕达哥拉斯立志求索“万物本原”,亚里士多德分析“存在是什么”,费希特则希望“提供一切知识的基础”,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提出哲学的问题是:我能够知道什么?我应当做什么?我可以希望什么?
罗素在《西方哲学史》中写道:“哲学,就我对这个词的理解来说,乃是某种介乎神学与科学之间的东西。它和神学一样,包含着人类对于那些迄今仍为确切的知识所不能肯定的事物的思考;但是它又像科学一样是诉之于人类的理性而不是诉之于权威的,不管是传统的权威还是启示的权威。一切确切的知识——我是这样主张的——都属于科学;一切涉及超乎确切知识之外的教条都属于神学。但是介乎神学与科学之间还有一片受到双方攻击的无人之域;这片无人之域就是哲学。思辨的心灵所最感兴趣的一切问题,几乎都是科学所不能回答的问题;而神学家们的信心百倍的答案,也已不再像它们在过去的世纪里那么令人信服了。世界是分为心和物吗?如果是这样,那么心是什么?物又是什么?心是从属于物的吗?还是它具有独立的能力呢?宇宙有没有任何的统一性或者目的呢?它是不是朝着某一个目标演进的呢?究竟有没有自然规律呢?还是我们信仰自然规律仅仅是出于我们爱好秩序的天性呢?……对于这些问题,在实验室里是找不到答案的。各派神学都曾宣称能够做出极其确切的答案,但正是他们的这种确切性才使近代人满腹狐疑地去观察他们。对于这些问题的研究——如果不是对于它们的解答的话,——就是哲学的业务了。”[3]
每个哲学家都会就自己的哲学主题给出答案,这些哲学思想就成为人类思想宝库中的瑰宝,并成为后世学者探索惊异世界的精神养分。一方面,哲学是一种历史性理论,任何哲学都是建立在特定历史条件和人类认识发展阶段基础之上的,而不能把哲学看作超历史的先验规定;另一方面,哲学思想又具有穿越性特征,在新的历史境遇中通过与现实的碰撞又能够产生极具时代感的认知。
哲学总是在不断实现超越和自我超越,它不满足于既有的结论,不受已有的思想框架的束缚,总是在反思、批判和突破。哲学通过提炼人类所面临的那些最深刻、最普遍、最具有长远意义的问题、经验和感受,形成新的理念和方法,以实现人的精神的发展与超越。这也就意味着哲学永远不会终结,它始终面临社会现实,处在不断深化、拓展、超越和自我发展的过程之中,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深刻、最具思想代表性的科学。
二 哲学是一种理论形态的世界观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过去的哲学以及现代西方哲学的区别与联系是什么,它们有没有共同之处,既然都叫“哲学”,那就说明它们之间是有联系的,那么它们的区别又体现在哪里呢?既然是哲学,就是研究整体世界及其一般规律的科学,一切哲学之所以称为哲学是因为它包含了本体论,一切哲学家的哲学思想又都包含有关于世界本原的本体论思想。
本体论一词起源于17世纪的经院哲学,通常是指在现象背后或现象以外寻求世界的本原,甚至是把某种神秘、抽象的东西当作世界的本原,它是关于世界存在的理论(ontology),也有学者将其翻译成存在论。西方哲学中对世界本原或基质进行探究的古希腊罗马哲学、莱布尼茨的形而上学和黑格尔的绝对理念等都属于本体论哲学。另外,中国古代哲学的道学、玄学、理学等实际上也是本体论。从根本上而言,本体论就是关于整个世界及其一般规律的理论,即这个世界到底是什么。世界到底是什么首先取决于世界本身,但是这个世界并不是一个完全独立的世界,而是人生活于其中、在人的活动影响塑造下形成的世界,是人眼中的世界。
世界观(world view)是指人对世界的经验性感知,即人的“世界观点”。世界观是人们关于世界的根本看法。从广义上而言,世界观有多种存在形态。常识世界观的本质特征是经验性;宗教世界观的本质特征是对神的信仰;作为人类把握世界的审美方式,艺术通过具体生动的形象来反映社会生活以及人与世界之间的丰富关系,也是世界观;科学是人类运用理论思维实证地把握世界的一种基本方式,也可以成为世界观。
人们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必然形成关于世界各种事物的看法,进而形成关于世界的总体理解和根本看法。同时,一旦拥有了某种世界观,这种世界观就会对人们如何理解世界、如何采取行动发挥基本的作用。也就是说世界观可以在人的自发行动中形成,也可以通过主体积极学习实践活动进行培育树立,实际上二者是辩证统一的,外部世界观理论必须转化为主体的认知才能成为真正的世界观,而主体只有接受科学世界观理论并结合自身实践进行转化才能树立正确的世界观。
在日常生活中,人们通常会把世界观等同于哲学,这是因为世界观这一术语本身起源于哲学。事实上,马克思恩格斯经常用世界观代称哲学。例如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等作品及书信中,恩格斯就提出了“马克思的世界观”“新世界观”“唯物主义世界观”等用法,它们都共同指向我们今天所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尽管世界观和哲学关系密切,甚至对许多人来说,世界观就是哲学的婢女,但哲学仅仅是世界观的一种,常识、宗教、艺术、科学等都是或者包含世界观。
与其他世界观相比,反思性是哲学最突出的一个特点。由于哲学与其他世界观的关系错综复杂、难以厘清,因此,把哲学与其他世界观清晰地区分出来具有很大挑战。黑格尔进行了创造性探索,给出了一种至今仍有广泛影响的解答。他认为,“哲学的认识方式只是一种反思,——意指跟随在事实后面的反复思考”;哲学所跟随的“事实”不是感性的具体事实,而是“一种现存的知识”,因此,“反思以思想的本身为内容,力求思想自觉其为思想”。冯友兰认为,哲学就是对于人生的有系统的反思的思想,哲学家必须对人生反复地思考,然后系统地进行表达。李泽厚主张:“哲学既非职业,而乃思想,则常人皆可思想。此‘想’不一定高玄妙远、精密细致,而可以是家常生活,甚至白日梦呓。哲学维护的只是‘想’的权利。”[4]抓住反思性这个特点,人们不仅可以将哲学与神话(幻想)、宗教(信仰)、艺术(审美)、常识(经验)区分开来,还能够在哲学与科学之间找到一条切实可行的划界标准。
哲学是理论化、系统化的世界观,是通过一系列概念、范畴和系统逻辑论证而形成的思想体系。作为理论化的世界观,哲学需要经过系统的逻辑论证。不可否认,有的哲学作品并没有表现出系统化特征,如《论语》、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阿多诺的《否定的辩证法》和《美学理论》,但是《论语》采用的是语录体,《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采用的是格言体,它们的逻辑体系由于文体的原因而变得松散以至于难以直接把握,但是仍然存在系统化的思想。至于阿多诺的作品,它们基于哲学上的严肃思考而反对传统的逻辑,自觉采用了“反体系”“碎片化”的文体形式来表达自己抗拒性的哲学思想。实际上,哲学是一种利用思维来把握世界的科学,严密的逻辑体系是其内在本质要求,不具备理论化、系统化特征的学说也就根本不是哲学。
作为理论化、体系化的世界观,哲学既包括对自然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总体理解,又包括对历史以及人与历史关系的总体理解,还包括对人本身以及人生意义的总体理解。具体而言,哲学包括自然观、历史观和人生观等内容。从人这一主体角度来看,自然观和历史观最终都会体现于人生观之上,人生观是关于人生问题的根本观点,决定了人生存于世的基本立场和原则,决定了人的实践活动目标、人生道路方向和对待生活的态度。人生观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要解决主体与客观世界之间存在的问题,使得主体能够在客观世界中生存发展。希腊德尔菲神庙前有三句著名箴言,其中有一句是“认识你自己”。从古代时期开始,人们就认识到作为主体的人一定要处理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只有这样才能解决好主观与客观之间的矛盾,解决好自由与必然、理想与现实、有限与无限等一系列的矛盾。
人生观具有个性化特征,每一个个体都有自己的人生观,世界上并不存在任何两种完全相同的人生观,但是人生观中的基本价值取向却是相通的,以什么为最高价值追求是每个人都应该认真思考的。古希腊时期的第欧根尼是犬儒学派的代表人物,他认为除了自然的需要必须满足外,其他的任何东西,包括社会生活和文化生活都是不自然的、无足轻重的。他强调禁欲主义的自我满足,鼓励放弃舒适环境。作为一个苦行主义的身体力行者,他居住在一只木桶内,过着乞丐一样的生活。每天白天他都会打着灯笼在街上“寻找诚实的人”。有一天亚历山大大帝专门来访问他,表示非常愿意帮助他。第欧根尼回答道:“我希望你闪到一边去,不要遮住我的阳光。”在第欧根尼看来,自由是至高无上的第一追求,至于金钱、名誉等都毫无意义。作为亚历山大帝国的缔造者,亚历山大大帝深谙第欧根尼的人生追求,他曾感慨地说:“我若不是亚历山大,我愿是第欧根尼。”
在《中国哲学简史》中,冯友兰将人生境界划分为四个概括的等级,“从最低的说起,它们是: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5]。一个人做事只是顺着他的本能或其社会风俗习惯,所做之事对自身没有或者只有很少意义,就是自然境界。一个人可能意识到他自己,为自己做各种事情,对于他自身具有功利的意义,即是功利境界。还有的人了解到自己是社会的一员,他只是社会整体的一部分,从而为社会的利益做各种事情,所做各种事情都是符合道德意义的道德行为,也就达到了道德境界。“一个人还可能了解到超乎社会整体之上,还有一个更大的整体,即宇宙。”[6]他不仅是社会组织的公民,而且还是孟子所说的“天民”,从而为宇宙的利益做各种事情,也就达到了最高的人生境界,即天地境界。“这四种人生境界之中,自然境界、功利境界的人,是人现在就是的人;道德境界、天地境界的人,是人应该成为的人。前两者是自然的产物,后两者是精神的创造。”[7]冯友兰认为依照中国哲学的传统,哲学的任务就是帮助人们达到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特别是达到天地境界。只有通过哲学获得对宇宙的了解,觉解行动和生活中的道德原理,才能达到天地境界和道德境界。
在人生观问题上,古今中外的哲学家都格外重视精神境界的追求,这是因为人固然是生物性的人,但是人的本质在于其社会性,人的社会交往体现了人的本质,而人若要实现对生物性的超越成为万物之长,就必须在精神境界实现升华。
三 哲学是改造世界的方法论
世界观同时又是方法论。在形成的世界观的基础上,人们就会依照世界观的观点去解释现象、处理问题、改造世界。而此时,世界观作为指导人们观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基本原则,就表现为方法论。
人们认识、改造世界的方式、手段、原则和办法的总称即为方法,方法不过是对客观规律的自觉地运用。方法又具有不同的层次,包括个别方法、特殊方法、一般方法。方法论是关于方法的本质、特性的理论,即研究如何运用客观规律以便自觉地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理论,哲学方法论是一般方法的最高层次。世界观解决的是“是什么”的问题,方法论解决的是“怎么办”的问题,二者有区别,但却紧密相连,世界观转化为方法论,叫作“化理论为方法”。一般来说,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就会有什么样的方法论,世界观决定方法论,方法论包含和体现世界观。恩格斯认为:“我们的主观思维和客观世界遵循同一些规律,因而两者的结果最终不能互相矛盾,而必须彼此一致,这个事实绝对地支配着我们的整个理论思维。这个事实是我们理论思维的不以意识为转移的和无条件的前提。”[8]
在古希腊时期,苏格拉底作为哲学家从事哲学讲授、社会活动,他劝导、勉励每一个人,但却不是讲道、训诫或枯燥的道德说教。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中写道:“苏格拉底的谈话(这种方法)具有一种特点:(一)他一有机会就引导人去思索自己的责任,不管这机会是自然产生的还是苏格拉底故意造成的。……接着(二)他就引导他们离开这种特殊事例去思索普遍的原则,引导他们思索、确信并认识什么是确定的正当的东西,什么是普遍的原则,什么是自在自为的真和美。这种工作,他是用著名的苏格拉底方法来做的……这个方法主要地有两个方面:(一)从具体的事例发展到普遍的原则,并使潜在于人们意识中的概念明确呈现出来;(二)使一般的东西,通常被认定的、已固定的、在意识中直接接受了的观念或思想的规定瓦解,并通过其自身与具体的事例使之发生混乱。这些就是苏格拉底方法的一般。”[9]
苏格拉底就把自己关于世界、社会以及其与人的关系的认知转化为了行为方法,依照这种方法的行为实际上也就充分表达了他的世界观,表达了他深邃的哲学思想。实际上,真正的哲学并不仅仅是思想的表达,而是思想与行动的统一,用中国哲学语言表达是“既入世而又出世”,既是理想主义,又是现实主义,既实用但又不肤浅。
在《莱茵报》时期,马克思批判《科伦日报》编辑海尔梅斯的政论文章时曾这样阐述哲学:“哲学就其性质来说,从未打算把禁欲主义的教士长袍换成报纸的轻便服装。然而,哲学家并不像蘑菇那样是从地里冒出来的,他们是自己的时代、自己的人民的产物,人民的最美好、最珍贵、最隐蔽的精髓都汇集在哲学思想里。正是那种用工人的双手建筑铁路的精神,在哲学家的头脑中建立哲学体系。哲学不是在世界之外,就如同人脑虽然不在胃里,但也不在人体之外一样。当然,哲学在用双脚立地以前,先是用头脑立于世界的;而人类的其他许多领域在想到究竟是‘头脑’也属于这个世界,还是这个世界是头脑的世界以前,早就用双脚扎根大地,并用双手采摘世界的果实了。”
“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因此,必然会出现这样的时代:那时哲学不仅在内部通过自己的内容,而且在外部通过自己的表现,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那时,哲学不再是同其他各特定体系相对的特定体系,而变成面对世界的一般哲学,变成当代世界的哲学。各种外部表现证明,哲学正获得这样的意义,哲学正变成文化的活的灵魂,哲学正在世界化,而世界正在哲学化。”[10]
在马克思看来,哲学来自于现实世界,同时它又返回到世界以改变世界,这中间即经历了主体的世界观、认识论和方法论的转化,人们关于世界的观点和看法直接影响了他们对现实问题的求解方法。艾萨克·牛顿是世界著名的物理学家,曾担任英国皇家学会会长,他发现的万有引力定律和三大运动定律科学揭示了三维空间里天体的运行规律,但是他无法弄懂宇宙的起源问题,因此其后半生从事神学研究,希冀从上帝那里找到宇宙第一推动力。正如诗人亚历山大·波普(Alexander Pope)为牛顿写的墓志铭:自然与自然的定律,都隐藏在黑暗之中;上帝说“让牛顿来吧!”于是,一切变为光明。上帝在牛顿的世界观里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牛顿早在年轻时就开始研究神学,在他自己能解决的科学问题领域他自己加以解决,而一旦遇到无法解决的问题,上帝就成为他最终的依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