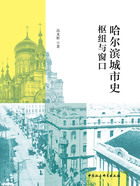
绪论
哈尔滨是我国东北[1]的一个枢纽性城市。哈尔滨是我国近代发展起来的一个年轻城市和新兴城市,没有经过从古代到近代的序列演进。这较多为一个历史发展的叙事,也是一个时间存在。时空交错造就了哈尔滨的历史演变与历史地位。哈尔滨曾经是东亚、东北亚甚至世界的经济中心之一,也是一座举世闻名的国际化大都市。作为中东铁路的枢纽,哈尔滨是连接欧亚的节点性城市。哈尔滨是中西文化传播与交流的窗口。哈尔滨在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和发展,以及新中国的成立与发展中做出了“共和国长子”的重要贡献。哈尔滨虽然年轻但是有故事,哈尔滨城市史研究应该具有跟北京、上海、天津、武汉、广州等城市史研究同等的地位和格局,因为哈尔滨具备这样的历史资源、历史记忆与历史地位。哈尔滨城市史不仅是一个区域史研究或城市史研究的个案,更是一部世界史或国际史研究的对象[2]。当然,这离不开中外学者的关注与书写。
关于哈尔滨城市史的相关研究多为“碎片化”的专题性或微观研究,较多是硕士研究生或博士研究生的毕业论文。“系统化”的整体性或宏观研究较少。本研究是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相结合、专题性研究和整体性研究相观照、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相关联的一种尝试。但这也是哈尔滨城市的一个“侧面”,而不是哈尔滨城市的“全貌”。哈尔滨城市史研究需要学人的培养、学术的积累与学林的滋养。这首先需要哈尔滨与黑龙江学者的推动与拓展。
一 哈尔滨:城市史、区域史与“哈尔滨学”
作为城市史的哈尔滨史研究,严格意义上是从改革开放以后肇始的。这最初并不是纯粹专业学者的学术研究,也不是学院派或学院式的叙事,而是部分专业学者发起、城市各基层参与的大讨论,其中《哈尔滨日报》《新晚报》《黑龙江日报》《生活报》与《晨报》等报纸发挥舆论宣传作用。基本上先后进行了三次相对集中的讨论,关涉名称、建城与纪元三个问题,即哈尔滨地名的由来、建城时间与城史纪元。
这三个问题都是哈尔滨城市史研究的节点性问题,并且是引起争论的话题。哈尔滨地名的由来至今还是一个悬而未决的议题,尽管目前基本趋向满语“渡口”一说。这一次大讨论是在全国文化热的大环境下,探索哈尔滨之名的渊薮。第二次大讨论与情感相交织,哈尔滨的城市发展没有经历从古代的城市到近代的城市的演进过程,是以水定城与因路兴城。中东铁路的修建与通车开启了哈尔滨的近代化。哈尔滨城市的形成与发展是殖民主义的“双重作用”的结果。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一些人不愿承认哈尔滨是俄国的铁路“附属地”和日本的殖民地,实际上哈尔滨现存的历史文化遗存就是一个不言而喻的佐证。第三个问题城史纪元有金源说、铁路说等不同标准,目前亦存在争议,但基本趋向于中东铁路的修筑与通车促成了哈尔滨城市的诞生与发展。
伴随着这三次大讨论,黑龙江大学、哈尔滨师范大学、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吉林大学、东北师范大学与吉林省社会科学院等专门研究机构,以及国内其他一些专业部门,首先是教师或研究者开始从事东北史或哈尔滨城市史的研究,后来就是数量日益增多的研究生群体的加入,逐渐形成了一个相对稳定、良性循环的发展态势,并且发表和出版了一些哈尔滨城市史的研究论文和专著[3]。与此同时,苏联(俄罗斯)、日本、美国、法国、德国、波兰等国学者,也利用自身的资料优势撰写关于哈尔滨城市史的论文和专著。
作为区域史的哈尔滨史研究。相对于城市史研究,区域史研究是一个更大的研究范围。与城市相对的是农村,农村与城市都是区域史研究的对象。城市史研究是区域史研究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区域是动态的、变化的。区域史多以区域社会史、区域经济史、区域文化史等呈现。区域史与城市史研究的领域或主题亦多有交叉。城市史与区域史在研究一个城市和区域所具有的共性时,多强调城市与区域的特性。哈尔滨城市史研究论证的是哈尔滨的多元、交互与共生的城市特质。
作为“哈尔滨学”的哈尔滨史研究。“哈尔滨学”是以哈尔滨城市为研究对象[4],以哈尔滨城市历史发展为研究主线,以哈尔滨城市历史的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相结合为研究支撑,以哈尔滨城市研究的微观、中观与宏观相观照为研究视角,以哈尔滨城市的空间维度、时间维度、文化维度等相参照为研究维度,进行历史学、地理学、城市学、政治学、社会学与文化学等相借鉴的跨学科研究或融学科探索。历史研究是“哈尔滨学”的主要内容、主要载体与主要凭借。研究目的是为哈尔滨城市建设与发展探寻规律性、借鉴性、指导性与引领性的知识路径,打造哈尔滨的城市“智库”,挖掘哈尔滨的发展潜力,提升城市的知名度。
二 哈尔滨城市史:史料的“田野”收集与研究的“视野”拓展
什么是历史?历史包括历史本身与历史研究两个部分。历史本身是客观的,属于本体论的范畴,也是科学的;历史研究即历史学是主观的,属于认识论的范畴,也是艺术的。人也就是研究者是历史本身与历史研究的媒介。“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是从主观到客观的一个探索过程。“历史学的理论与实践”的目的是寻找“历史的真相”。“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历史研究者的叙事与评判离不开其思想的主观判断。“历史的观念”是历史的必然性与偶然性的统一体。西方的历史理论[5]与我国的历史研究经验,是在各自的学术研究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不同总结,有着各自的发展路径。
20世纪和21世纪对整个世界影响最大的史学理论流派是法国的年鉴学派,在近100年的发展中经历了三四代的传承,仍然影响着各国的史学研究和史学实践。年鉴学派在史学理论与史学方法上,关注下层民众的“眼睛向下的革命”与重视研究主体的主体性,特别是“长时段”的研究理论,给我们的历史研究提供了一定的研究范式。打破史学研究与史学理论平行线的状态,实现两者的交叉,引进、消化与融合是一个长期的复杂过程。我们有自己的史学研究传统,西方史学理论与中国史学研究的具体实践有适应性、选择性与调和性。近代以来,我国的史学研究传统存在裂变、失衡与博弈的现象。但是,历史研究的基础是史料。
“历史学即史料学”,强调的是历史研究的条件,以史带论,而不是以论带史,最终是史论合璧。从史料到史料学,历史学、文学与哲学等都强调史料学在各自研究中的重要性,重回历史现场,让文本说话。从史料学到文本学,都需要史料的收集、整理与研究。年鉴学派重视史料的多样性与多元化。其中史料的收集是一项基础性工作,除了我们普遍认同的官方机构图书馆、档案馆等,民间和地方也有支撑历史研究的资源。[6]史料的“田野”收集是一个视角,也是一种方法。“田野”不仅需要“脑”,也需要“腿”。哈尔滨城市史研究不仅需要研究者在故纸堆里爬梳文献,也需要走街串巷踏查历史文化遗存,“登堂入室”拜访历史的见证者,口述历史的多彩绚丽画面,探赜哈尔滨城市史,从而拓展哈尔滨城市史研究的“视野”。
三 “哈尔滨学”:国际视野、微观研究、价值判断与现实关怀
在长期的历史研究中,笔者总结了“国际视野、微观研究、价值判断与现实关怀”16字的历史研究经验。从研究对象来看,哈尔滨城市史本来就是多元文化的融合体。哈尔滨这座城市具有世界性意义和国际性价值。国际视野是研究哈尔滨城市史应该具有的前提条件。笔者从硕士研究生到博士研究生从事的都是世界史相关问题的研究,也培养了一种使用世界眼光研究历史的习惯,这是一个主观的历史意识。哈尔滨城市史研究需要具备国际视野,国际视野是打开哈尔滨城市史研究的一把钥匙。
《哈尔滨城市史:枢纽与窗口》是一次关于哈尔滨城市史的专题性研究,既有宏观性的梳理,也有个案的微观研究,一定意义上是一项专题性微观研究的尝试。以国际视野为指引或指导,叙述哈尔滨城市史的一个个侧面,力求经过长期的研究,塑造一个较为全面的、整体的“镜像”。宏观与微观是相对的概念。微观研究需要宏观研究作参照。
价值判断关涉史学研究的立场,这与历史研究的客观性诉求并不矛盾,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哈尔滨城市史研究既要有客观的历史叙事,也需要有明确的历史立场,价值判断亦表达了研究者的立场。
为什么学历史?学历史有什么用?现实关怀是历史研究的一个重要使命。由于城市自信来自文化自信,文化自信又不可脱离历史的深度,因此,哈尔滨城市史研究是哈尔滨城市自信的重要支撑。
哈尔滨这座副省级城市需要和期待一部通史。[7]这需要时间的抉择,更需要时机的选择。哈尔滨作为一座城市从来就是优雅的,没有失落过,失落的只不过是人而已。
[1] “东北”这个概念,不管从行政区划,还是政治经济,以及社会文化等层面,都是一个变动或变化的动态名词。现在一些叙述中,多用“东北地区”来呈现。这是一个较为复杂的问题,但不是本研究的重点。笔者使用“东北”,而不是“东北地区”。
[2] 这不是“没有中国史的世界史不叫世界史”的简单解释。
[3] 即使有的研究生有较为浓厚的兴趣和强烈的意愿,但是基本不把地方史研究作为毕业论文的首选,因为这关系到未来工作的落实。
[4] 主要研究哈尔滨主城区的历史,今南岗、道里、道外、香坊、平房与松北区等。而不是现在哈尔滨行政区划下9区9县的研究。哈尔滨主城区是哈尔滨历史的主要承载体。
[5] 历史理论与历史哲学不是一个概念,历史哲学是一个独立的学术系统。
[6] 四川巴县档案的重要性,在于传统研究更多是自上而下的政令或政策的研究,缺乏自下而上的反映或反馈。巴县档案从一个区域提供了这种研究的可能性,尽管不具有整体性的意义。我国县级档案馆及其馆藏档案(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前)是一个需要引起重视的领域。
[7] 哈尔滨曾经在政府相关部门的主导下出版过通史性研究。王世华主编:《当代哈尔滨简史》,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