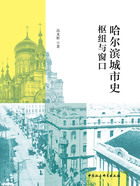
第一节 城与城市:哈尔滨城史纪元问题再探讨
关于哈尔滨城史纪元问题,“金源说”以金朝建国为基点(1115年正月初一)。“金源说”还涉及哈尔滨的名称由来。“设治说”以滨江关道的设立为标识,其中有以设治奏准(1905年10月31日)与设立办公(1906年5月11日)两种不同说法。“设治说”还关涉哈尔滨城史纪元的“开埠说”“铁路说”。以中东铁路开工(1898年6月9日)和开通(1903年7月14日)为节点,6月9日还以俄国“海兰泡”轮船带来最后一批中东铁路技术人员(俄历1898年5月28日)为标志。然而,“金源说”需要厘清现在的阿城区与哈尔滨主城区的历史与现实关系,说明哈尔滨主城区历史沿革;“设治说”需要梳理设治当时的管辖范围与哈尔滨的关系以及民族情感意识;“铁路说”需要解释中东铁路与哈尔滨近代化的关系,阐释殖民主义“双重性”的问题。同时,还要处理好民族情感与历史真相的关系。不同于长春(宽城子)和沈阳(奉天)由“城”到“城市”的发展脉络具有连续性和继承性,哈尔滨是一个随着中东铁路的修建和开通,作为中东铁路的枢纽,经过二三十年发展,而逐渐形成的国际化城市。哈尔滨的城史纪元没有一个确切的时期,而是从1898年开始“建设”城市。1948年,中共中央东北局的《东北日报》和《生活报》的哈尔滨建设五十周年纪念报道,也证明哈尔滨作为“城市”来“建设”始于1898年。
一 千年文脉:“金源说”、金朝建国与哈尔滨城史纪元
20世纪90年代,哈尔滨历史研究领域进行了第一次关于哈尔滨城史纪元的大讨论。核心问题是“金源说”的提出以及对此的商榷。王禹浪(时在哈尔滨市社会科学院)的《哈尔滨地名含义揭秘》[1]与《哈尔滨地名与城史纪元研究》[2](时在大连大学与黑河学院)、段光达(黑龙江大学历史系)的《关于哈尔滨城史纪元的几个问题》[3]和《哈尔滨早期城市特点刍议》[4]及纪凤辉(黑龙江省档案馆)的《哈尔滨寻根》[5]等是主要代表成果。当时在《哈尔滨日报》和《新晚报》等报刊开设了专栏,具有全民性讨论的性质,学院派与民间互动。王禹浪是“金源说”的肇始者。他最初以金代为节点,后来随着考古发现进一步以金代建国为起始。并且,哈尔滨市阿城区力推此观点。
王禹浪介绍:“1990年9月,我曾在《北方文物》第3期上发表了《哈尔滨城史纪元的初步研究》一文,认为哈尔滨城史纪元应始于金代。无论从当时哈尔滨地区的人口规模、古城性质和形态,还是城市手工业与商品经济的角度看,都说明了金代的哈尔滨已踏上了最初的城市历程,已经形成了具有古代都市文明规模及其城市功能的城市,哈尔滨地区的古代城市文明在金代已经形成,这就是哈尔滨的城史纪元。作为城市形态的代表,位于哈尔滨香坊区的莫力街古城和位于哈尔滨市东郊阿什河畔的小城子古城的建置年代,就是哈尔滨古代城史纪元的实物遗存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天,当年的阿城市已经成为哈尔滨市的阿城区,坐落在阿城区的金上京会宁府的都城,实际上就是哈尔滨城史纪元最重要、最真实的历史标志。”[6]
2015年5月10日,在哈尔滨市阿城区召开的“2015年哈尔滨城史纪元学术研讨会”[7]上,王禹浪指出:“作为哈尔滨地名语源的‘阿勒锦’(霭建)村的地名,早在穆宗统治时期即公元10世纪末期,就已经出现在《金史》中。特别是‘塞北马王堆’完颜晏夫妇墓的发现,印证了今阿城区巨源乡的小城子村古城正是金建国前的阿勒锦村。在古代行政区划上,哈尔滨一直受金上京城会宁府和清代阿勒楚喀副都统衙门管辖,只是中东铁路修建后把哈尔滨作为中东铁路管理局的所在地,哈尔滨才脱离了阿勒楚喀的行政管辖范围。因此,现在的哈尔滨与阿城区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现实中均属同一行政区划。除此之外,哈尔滨地名的区域化在清末也已经形成,以哈尔滨、大哈尔滨、小哈尔滨地名为村屯的区域称谓在阿什河下游及与松花江汇合处附近已经具有特殊的地域范围,这也进一步说明阿什河流域的阿城地区与哈尔滨实为同一地域的文化区域。”[8]
王禹浪进一步提出:“完颜阿骨打建立大金帝国之日(公元1115年正月初一,笔者注)应作为哈尔滨都市文明城史纪元的标志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这一点得到了与会学者的一致认可,研讨会后学者们联合撰写了鉴定意见书,对我在二十多年前提出的哈尔滨城史纪元应从金代开始的观点给予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并以此作为定论。我的家乡哈尔滨的城史纪元也将有望提前至数百年,并期待能够步入中国古都行列。”[9]
此次会议达成共识,“金上京会宁府的出现是今天哈尔滨地区的区域文明的源头,城史的开始”。因为,“哈尔滨的城史纪元与金源文化密不可分,金源文化是哈尔滨城市发展中最为重要的一个阶段。有金一代国度的建立,其规模、功能也都是在当时的城市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所以金上京会宁府这座都城作为哈尔滨城史纪元的重要基础应当是毫无疑问的。金上京会宁府就是今天哈尔滨城市之源头,将金上京的创建时间定为哈尔滨建城的时间是科学的、确切的,这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10]。并且会议强调,“根据哈尔滨市阿城区所保存的金代上京会宁府遗址的事实,确定了哈尔滨的城史纪元应该起始于金代的观点,从而改变了以往哈尔滨城史纪元起始于近代中东铁路设置的观点,为哈尔滨城史纪元寻到了根脉”[11]。需要指明的是,这次会议没有哈尔滨主流历史学者如李述笑、石方等的参与。这样的共识是否具有意义?
20世纪90年代,毕业于吉林大学历史系的段光达和纪凤辉指出:“在史学界,有关哈尔滨城史纪元问题争论了很长时间,已趋共识的就是金代古城堡与近代哈尔滨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不可混为一谈。在争论之初,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哈尔滨城史纪元应该始于金代,迄今已有800多年的城市历史。”[12]
但是,哈尔滨的城史纪元绝非在金代。“首先,这些古城堡都有自己的城堡名称,与今哈尔滨城名不同,名不正,则言不顺。很难想象,在金代连哈尔滨这个地名都没有产生,何谈哈尔滨城的城史纪元?第二,这些城堡的位置与哈尔滨的位置不同,莫力街、四方台古城堡均在城郊,而白城古城堡遗址更远在30公里开外。区域概念是很重要的,事实上,金代哈尔滨还未形成地域概念,它只不过是金上京会宁府会宁县的边荒,莫力街、四方台也只不过是金上京城延伸出的城堡而已。清末哈尔滨范围只局限在‘西起正阳河,东至马家沟河下口,南达田家烧锅,北靠松花江这一三角地带’,并不包括莫力街、四方台、白城古城。因此,近代兴起的哈尔滨城,与后来才成为哈尔滨辖区内的古城堡是两回事。况且白城古城一直归阿勒楚喀所辖,无论如何‘张冠李戴’,也戴不到哈尔滨的‘头’上。”[13]
他们强调:“哈尔滨地区的城市发展史起源可以追溯至辽金代或更久远的年代,但哈尔滨这座城市本身的城史纪元却不能从辽金代或更久远的年代算起,而只能从近代算起。”因为“确定城史纪元,不仅需要进行共时态的横向比较,即搞清城乡差别,而且还要进行历时态的纵向考察,即明确自身的发展轨迹。无论是以辽金古城堡为起点的顺向延伸,还是以近代哈尔滨城为起点的逆向上溯,都可以发现二者之间的非连续性的断裂关系是十分明显的”。这些“金代古城堡早就以其遗址为自身的历史画上了句号,完成了它自身的生命周期,与近代哈尔滨并不存在任何遗传的‘血缘关系’”[14]。并且,“哈尔滨地区的金代古城堡,与近代哈尔滨城具有完全不同的文化形态。产生这种差异的原因就在于二者形成于完全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哈尔滨是作为近代意义上的城市而问世的,它不像其他一些中国城市那样,是在传统形态的基础上开始其近代化过程的,而是由强行介入的西方文明,把哈尔滨推上了城市发展之路。中东铁路的枢纽作用,从根本上改变了它与附近地区经济社会的原有结构,掀起了以工商业为主体的城市近代化运动,与近代古城堡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15]。还有,“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金毓黻先生在所著《东北通史》一书中,曾经论及东北和内蒙古地区历史上的‘四大古都’,上京会宁府是其中之一。这里的‘四大古都’皆未发展成近现代的大城市”[16]。
“哈尔滨城史纪元,犹如城市历史的定盘星,它不仅关系到对哈尔滨历史研究的总体把握,也涉及对具体历史问题的再认识。人造城市,城市造人,人和城市造就着城市文化。哈尔滨城市沿革史,有别于哈尔滨地区的发展史。社会发展史可以追溯到该地名出现的最早时间和该地区最早人类活动;而城市沿革史则不然。从严格意义上来讲,甚至该地区最早出现的村落、堡寨的年代,也不是城市沿革史的开端。哈尔滨城市沿革史,有别于哈尔滨地区城市发展史。作为地区城市发展史,它可以包括这个地区的若干古代城市兴衰和若干现代城市发展史。而哈尔滨城市沿革史则不然,从严格意义上来讲,它只能指现今的这座城市的兴起与发展史。哈尔滨城史纪元,有别于哈尔滨城市沿革史。作为城市沿革史,它包括这个城市本身的兴起、形成、发展,以及未来趋势的整个过程,而城史纪元则不然,仅仅指这个城市本身的开端、起点或起步。”[17]
针对2015年5月10日在哈尔滨市阿城区召开的“2015年哈尔滨城史纪元学术研讨会”(在此基础上,哈尔滨市计划召开哈尔滨建城900年大会,后取消),黑龙江省哈尔滨历史文化研究会与李述笑会长给哈尔滨市相关部门“建言献策”,李述笑还在《新晚报》刊发《哈尔滨历史误读误释考订》[18]一文,对相关问题特别是城史纪元问题进行了澄清。
“金源说”与哈尔滨城史纪元讨论涉及哈尔滨地名的由来,如关成和的“阿勒锦说”[19]、王禹浪的“天鹅说”“晒网场说”“大坟墓说”“渡口说”等,与女真语、满语[20]、蒙语、俄语等有关联。实际上,20世纪上半叶出版的书籍如《哈尔滨指南》《北满与东省铁路》《北满农业》《滨江尘嚣录》等早有提及。据《哈尔滨四十年回顾史》介绍:“哈尔滨于俄人筑路前,距今约三十年,固一篇荒野场,其命名之来源,于汉义,绝无讲解。哈尔滨三个字,原系满洲之语,有谓晒鱼网之义,惜不佞不谙满语,不敢率然决定,但敢证其确为满语也。”[21]孟烈和李述笑在《名城与城名》[22]一文中也明确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此外,有的学者认为,哈尔滨“建城纪元为1097年”[23]。不过,“关成和先生所考证的1097年阿勒锦村的始见时间实际上是对哈尔滨名称的始见时间的确定,而并非城史纪元的初始时间”[24]。但是,笔者认为,《金史》中的“阿勒锦村”的始见,不能等同于“哈尔滨”这个地名的始见。并且,“《金史》中关于阿勒锦的记载,始知金史原文为‘霭建’,后用满语标音为阿勒锦”[25]。
值得一提的是,王禹浪后来提出了“哈尔滨城史纪元的远端与近端”的说法。“2015年夏季,哈尔滨市委宣传部与哈尔滨市阿城区政府组织召开了哈尔滨城史纪元专家论证会”[26],他提出:“‘哈尔滨城史纪元的远端就是金代上京城建立之时’,而‘哈尔滨城史纪元的近端就是中东铁路建设之日’。”在《哈尔滨城史纪元再研究》中,他指出:“哈尔滨市的阿城区金代上京城会宁府遗址,实际上就是哈尔滨城市发展史的远端,而近代随着中俄密约签订后中东铁路局设定在哈尔滨的开埠之日,则是哈尔滨城市发展史中的近端。”并且,“哈尔滨城史纪元是哈尔滨城市发展历史全过程中的开端,而伴随着中东铁路出现的哈尔滨市,则仅仅是近代工业文明的城市诞生日或叫开埠日”[27]。因为“主张哈尔滨城史纪元起始于金代的学者,是在追寻这座城市发展史全过程的远端,而主张哈尔滨城市纪元起始于近代的学者的观点,则是在强调这座城市的历史近端”,从而,“求证的是哈尔滨城市发展史的城史纪元而不是哈尔滨筑城的纪元”[28]。但是,笔者认为,哈尔滨的城市发展史的特殊性是没有经过从古代的“城”到近代的“城市”的连续发展,哈尔滨没有筑城的历史。“近端”和“远端”的提法还是在强调哈尔滨城史纪元的“金源说”。“千年文脉、百年设治”,是哈尔滨市政府在城市发展和变化的基础上提出的一个较为合理和清晰的说法,尽管不提中东铁路与哈尔滨的历史关系。
二 百年设治:“设治说”、滨江关道与哈尔滨城史纪元
随着21世纪初期(2005)哈尔滨道台府的发现与修复,出现了关于哈尔滨城史纪元的第二次大讨论。这次的主题是“设治说”与哈尔滨城史纪元。李兴盛(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柳成栋(黑龙江省地方志办公室)与曾一智(《黑龙江日报》)等参与研讨、保护和报道。《黑龙江晨报》与《黑龙江日报》(《城与人》专栏)给予宣传。
关于哈尔滨关道设治,《清实录》卷550载:光绪三十一年十月癸卯(初四)“添设哈尔滨道员一缺,从署吉林将军达桂、署黑龙江将军程德全请也”[29]。滨江道奏准于光绪三十一年十月初四,即1905年10月31日;设立于光绪三十二年四月十八日,即1906年5月11日。[30]
曾一智在《保护滨江关道衙门行动》一文中介绍:“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清政府在哈尔滨设滨江关道,道台为杜学瀛(正四品)。哈尔滨自此开埠。杜学瀛为由皇帝任用的第一个也是最高级别的哈尔滨地方行政长官,而1906年建成的滨江关道衙门也就是哈尔滨最早和最高的行政机构。”“滨江关道衙门建于1906年,是哈尔滨的第一个最高级别的行政机关机构。”[31]刘延年进一步解释:“1906年5月11日,在哈尔滨傅家甸(今道外)正式设治办公并启用‘滨江关道兼吉江交涉事宜关防’,这是哈尔滨地区历史上第一次由政府批准设立的行政机构。机构当初的任务很明确,就是专办与中东铁路公司交涉事宜,并督征关税。这个关道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地方政府机关,因滨江关道没有辖区也没有管理地方事务的职能,以致出现‘专管华洋交涉案件,俄国人不承认其职权,而所辖区不足十里,殊难成治’的现象。”[32]阿唐在《老街漫步》一书中讲过,“1905年,清朝在傅家店设置了只收税不管治安的衙门,史称‘滨江关道’”[33]。王哲的《国士无双伍连德》一书中也有涉及,“伍连德事先已经听施肇基介绍过,知道这就是朝廷在哈尔滨最高级别的官员”,“吉林西北路分巡兵备道道台于泗兴”(应是于驷兴,笔者注)[34]。然而,柳成栋在《哈尔滨设治及几个相关问题的再认识》中指出,“哈尔滨关道衙门的建立,并非是中国封建王朝设立的最后一个传统式衙门和清王朝最后在中国北方设立的权力机关”,并且,“哈尔滨关道设立的同时,哈尔滨吉江两省的铁路交涉局也随之裁撤”[35]。但是,《吉林公署政书》中关于《交涉司》一章中提到,“旋以俄议不协,总局未撤,故滨江道于征税外,犹兼总局会办”[36]。并且1917年11月27日《施道尹兼任交涉局总办》强调,“吉林铁路交涉局总办一席向滨江道尹兼任”[37]。
笔者认为,这些关于哈尔滨关道性质的说法不尽合理,并非学术意义上的探讨。“第一”“最高”“最早”等称谓失之偏颇。在一定历史时期,设治在道外的哈尔滨关道并不能管理现代意义上的哈尔滨(道外、道里、南岗、香坊),作为铁路“附属地”的哈尔滨由中东铁路管理局管理。随着中国收回路权的斗争的开展,哈尔滨关道道尹的权力有所变化,如董士恩兼任东省特别区管理局局长,但是权力实质有待研究。黑龙江省社科院研究员石方指出,一般意义上,道是“中华民国前期沿用清制而设立的省和县之间的一级行政建制,为省辖下的二级政区,所辖数县或设治局”。道官(观察使、道尹)“为一道之行政长官,其职权范围是依照法令执行辖区行政事务,接收上级行政长官委任监督财政及司法的执行情况,对所辖县份的人事任免、奖惩权力可报上级核办,对辖区内巡防警备队的调遣节制等”[38]。而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李述笑在《谈滨江关道设治的几个问题》中强调,“哈尔滨却有它自身的特殊性:她是一座借中东铁路的修筑和经营的机遇,由村镇聚落点向近代城市逐渐转化而形成的城市。第一,她没有建筑城垣的经历;第二,1905年滨江关道的设治又明显地滞后于哈尔滨城乡嬗变的开端”[39]。值得思考的是,哈尔滨关道道尹不同于其他地方的道尹的职能是,专办吉江交涉事宜及督征关税,还兼任外交部的交涉员、吉林铁路交涉局或黑龙江铁路交涉局总办等,哈尔滨关道道尹的工作重心是外交事务,特别是处理中俄关系。如施肇基所言,“哈尔滨关道交涉事项对俄者最烦,尤多主权之争。因凡在铁路附近地段,俄人皆认为有行使行政之权”[40]。
关于哈尔滨关道设治有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即哈尔滨设治与城史纪元问题的关系。关于设治说,柳成栋强调“奏准设立哈尔滨关道即哈尔滨设治,是哈尔滨近代城市建设的最权威的纪念日”。同时,他指出“中东铁路的修建,绝非只形成一个哈尔滨,导致城市(镇)的形成和发展主要在于其本身的内在因素即内因起作用”,“中东铁路是沙俄帝国主义侵略东北的产物,哈尔滨近代城市纪念日绝不能定在与帝国主义侵略相关的耻辱之日”[41]。笔者认为,我们应该承认历史事实和相关条约的客观结果,不能进行情绪化论述。关于哈尔滨的城史纪元,米大伟总结为,“作为现代城市功能和定位的哈尔滨,主体内容自然是哈尔滨作为城市的历史,它的发生、发展是中东铁路建设带来的,是一座借中东铁路的修筑和经营的机缘,由村镇聚落点迅速转化的现代城市”[42]。这些村镇聚落点主要是随着铁路建设形成的铁路村[43]。尽管铁路“附属地”和租界、租借地有所不同,但用殖民主义的双重性来解释它是有一定合理性的。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中讲道,“英国在印度要完成双重的使命:一个是破坏性的使命,即消灭旧的亚洲式的使命;另一个是重建性的使命,即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44]。作为铁路“附属地”的哈尔滨,俄苏等国建设性的结果不仅表现在物质方面,也表现在精神文化方面,从而形成了一个“洋华杂处、中西交融”的城市。也就是说,哈尔滨的城市化和近代化是一种后发现代化。
哈尔滨城史纪元的“设治说”关涉“开埠说”。学界目前以1907年1月 12日成立哈尔滨商埠公司为哈尔滨开埠的标志。更有学者提出:“开埠比设治还晚,更重要的是帝国主义强加有损于中国主权的条款,怎么能拿这个丧权辱国的条约作为哈尔滨的城史纪元呢?这实在是让人无法接受。”[45]但是笔者认为,哈尔滨是先开埠后设治。中东铁路的建设和开通,是哈尔滨开通商埠的历史前提[46]。1905年12月22日,中日在北京签订的《会议东三省事宜正约》(又称《满洲善后协约》)的《附约》第一条规定:“中国政府应允,俟日俄两国军队撤退后,从速将下列各地方自行开埠通商:奉天省内……;吉林省内之长春(即宽城子)、吉林省城、哈尔滨、法库门;黑龙江省内之齐齐哈尔、海拉尔、瑷珲、满洲里。”《哈尔滨市志》的《大事记》记载,1905年12月22日,“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条约》3条及附约12款在北京签约,清政府被迫承认《朴茨茅斯和约》中有损中国主权的条款,并允许哈尔滨等16个城镇开通商埠”;1907年1月12日,“根据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条约》,哈尔滨辟为商埠,设立哈尔滨商埠公司”[47]。一般来讲,近代中国一些城市的开埠分为条约开埠和自主开埠两种。哈尔滨“自行开通商埠”经历了一个过程。从“长时段”来看,哈尔滨的开埠早于滨江关道的设治。同时需要强调的是,哈尔滨开通商埠的区域是中国政权管辖的范围,而不是中东铁路“附属地”,也就是说不是现在的整个哈尔滨主城区;另外,研究者不能因民族感情或情绪而影响历史研究的客观性。
三 建设周年:“铁路说”、中东铁路与哈尔滨的城史纪元
第三次关于哈尔滨城史纪元的大讨论,肇始于2015年拟召开的哈尔滨建城900周年。黑龙江省哈尔滨历史文化研究会及李述笑等对“金源说”等问题进行了回应,并且提出“铁路说”与哈尔滨城史纪元的关系。1898年6月9日中东铁路的开建和1903年7月14日开通不应作为哈尔滨城史纪元的标识,同时“海兰泡”号到达哈尔滨的日期,也不该作为哈尔滨城史纪元的标志。关于“铁路说”还有一种时间提法,1928年波兰文版的《波兰人在远东》一书提到:“载着建设局工程师和官员的‘圣诺森号’与‘奥德赛号’轮船分别于5月13日、5月16日到达这里,他们的到达标志着哈尔滨城的正式建立。”[48]这里首先不讨论这个时间能否作为哈尔滨城市建立的标志,而存在一个问题是,时间是俄历还是公历?[49]哈尔滨因路而兴,是随着中东铁路建设与开通而逐渐“建设”而成的新兴近代城市。哈尔滨历史上的《远东报》《滨江时报》《盛京时报》《生活报》[50]《东北日报》等报刊都曾刊发过关于哈尔滨城史纪元的文章。《生活报》曾专门关于哈尔滨城市“建设”刊发《哈尔滨建设五十周年纪念特刊》。《新晚报》《哈尔滨日报》《生活报》与《黑龙江省广播电视报》等参与报道了这次大讨论。
关于这次哈尔滨城史纪元大讨论,2015年5月18日《新晚报》刊发《哈尔滨城史或提至900年前 有望进入中国古都之列》;然而,《黑龙江广播电视报》在2015年5月22日刊出《哈尔滨城史要沾阿城的光?荒唐》。《哈尔滨城史或提至900年前 有望进入中国古都之列》中的五大论据为:“1.《金史》中明确记载,公元1115年正月初一,女真首领完颜阿骨打在按出虎畔(今阿什河)建国立帝,国号大金;2.金上京会宁府遗址建于12世纪,至今仍像长龙一样横亘在阿城大地上,这是不可移动的标志性建筑遗址,它无言地述说着这里当年作为都城的辉煌,这是哈尔滨市古代城市文明形成的历史见证;3.2006年,阿城出土了一件金代铭文石尊,其铭文为‘承命建元收国·子曰典祀’,而金建国时的年号为收国,这件文物确凿地证明了金朝当年立国建都的事实;4.哈尔滨地名的语源来自《金史》中记载的‘阿勒锦’,其地理位置就是今天哈尔滨市道外区巨源镇城子村。专家考证,城子村古城是金初皇帝的春水捺钵行宫之地;5.哈尔滨古代历史的行政区划一直受金上京会宁府和清代阿勒楚喀副都统衙门管辖。不论历史上的阿城管辖哈尔滨区域,或是当下哈尔滨管辖阿城,都说明哈尔滨与阿城历史上就属于同一行政区划。”[51]
2015年5月24日下午,黑龙江省哈尔滨历史文化研究会在果戈里书店针对该问题进行了详细而严肃的讨论。其中,李述笑指出,在阿城召开的城史纪元研讨会,“五大论据不足为据”;“五大概念不可偷换”。文明的源头不等于城史纪元;上京会宁府不等于阿城;阿城区不等于哈尔滨市;城史纪元不等于建城时间;加入古都行列不等于增加城市竞争力。城史纪元,顾名思义,是城市历史的起算年代,其上限应从其最早形成村落,并有自己名字的年代起算。依据中外计算城史的规则和惯例,考察该村落最早形成的时间应以有文献记载或有文物可证的时间为准;建城时间,一般指开始建设城垣或城市行政设置的时间。我国的六大古都以及讨论中涉及的上海、齐齐哈尔和青岛均可据此确定建城时间。哈尔滨是特殊的,它既无建筑城垣的历史,城市设置的时间又远滞后于城市形成的时间。因此,它没有建城时间或建城纪念日可言,它是个随着中东铁路修筑和经营,逐渐形成的近代城市[52]。
哈尔滨城史纪元问题,在改革开放前没有被学者们意识到。这个问题是改革开放以后逐渐浮出水面的。“金源说”的相关“研究者”《盛京时报》的《滨江特刊》曾经介绍《哈尔滨特别市概况(一)》,“一八九八年,旧俄帝政时代之建设中东铁路,辄以此间为侵略远东政策根据地,自是厥后扶摇直上”[53]。在《生活报》的《哈尔滨建设五十周年纪念特刊》中,署名“一波”的人在《哈尔滨历史标志着人民胜利》一文里写道:“五月二十八日,是哈尔滨建设五十周年的日子。”并且强调,“帝俄为着侵略远东,用中国人民的血汗,把哈尔滨建设成一座现代的城市,这时,哈尔滨是半殖民地,不是属于人民的,它包含着耻辱和愤怒”[54]。王坪在《哈尔滨半世纪》中指出,“哈尔滨是满洲语,译成汉文是‘打渔泡’或‘晒网场’的意思。由此可知哈尔滨不过是松花江边一荒村。自从一八九八年(光绪二十四年)中东铁路兴筑以后,哈尔滨才慢慢地脱落原始本色,逐渐穿上时代新装而成为今天新中国第一个新都会”[55]。《生活报》的文章仅指出1898年5月28日这个纪念日,并未讲出具体的出处。1949年5月29日,《东北日报》刊发《哈尔滨各界欢度建设五十周年》的消息。“昨日哈尔滨建设五十周年纪念,全市国旗飘扬,在进一步支援战争建设人民城市的号召下,各界人民欢欣庆祝。”并且强调,“会中,李议长首述‘五二八’来历系因一八九八年的今天,从帝俄以‘海兰泡’号轮船,载来最后一批建路技术人才,兴筑中东路开始建设哈市”[56]。关于这个日子还有一种说法,“中东铁路开始施工以后,为了适应中东铁路建设指挥的需要,将中东铁路建设工程总局由海参崴迁到哈尔滨,一八九八年五月二十八日正式在香坊田家烧锅办公。这个日子可看作是哈尔滨城市创建的日期”[57]。
关于中东铁路的修建与哈尔滨的城市发展之间的关系,哈尔滨地方史专家、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石方分析:“哈尔滨被确定为中东铁路的中心枢纽后,使资本主义得以安身立命的蒸汽机、动力机械较早地出现在这里。‘外力’赋予的现代工业化因素使其从根本上改变了哈尔滨地方经济社会的原有格局。”中东铁路的修筑“实是在哈尔滨地方形成了一场巨大的‘社会革命’,使其能够在短短一二十年内便由一个以传统的分散的自然村落经济占主导地位的社区系统迅速崛起为现代城市。中东铁路修筑的本身就是现代工业的产物,而近十年来围绕着中东铁路的建设出现的为生产生活服务的工业企业把哈尔滨推上了高起点的发展之路”。随着中东铁路的建设,“哈尔滨已摆脱了传统文化氛围的束缚,显露出现代城市的雏形并日趋发展”[58]。在《关于哈尔滨城史纪元的几个问题》一文中,黑龙江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教授段光达指出:“哈尔滨作为中东铁路的中枢,是沙俄在华推广殖民主义侵略政策的产物,因而从形成之日起便带有相当浓厚的半殖民地色彩。由于它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受特殊的外力和诱导因素的作用,开始其特殊的城市形成过程的。”[59]
2018年4月29日,孟烈与李述笑进行了关于中东铁路与哈尔滨城史纪元的对谈。他们的共识为,哈尔滨是随着中东铁路的修筑而逐渐“建设”而成的城市。李述笑强调:“中东铁路的建筑与经营促进了哈尔滨由村屯聚落向铁路村镇的转化,促进了城市的形成和发展。但确定所谓建城时间或者建城纪念日,应是以开始建筑城垣或行政设置的时间为依据的。绝不是俄国人轮船一到,哈尔滨城市就正式建立了。”[60]
关于哈尔滨城史纪元问题,研究者需要从具体的史料出发,进行实事求是的探究,而不是对该问题进行过度阐释和过度消费。李述笑指出:“史料对于历史研究是重要的,没有史料基础的所谓研究是空洞无物的。我们应该相信既往的史料,因为前人比我们更接近于那个历史年代;同时,我们又不迷信既往的史料,因为任何史料都会因为时代的局限性、作者的片面性而有疏漏、讳忌和差错。”[61]哈尔滨城史纪元问题作为哈尔滨历史文化研究的节点问题,将会随着研究的日益深入而逐渐澄清和明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