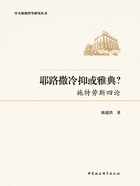
前言
1999年夏天,从北大外哲所硕士毕业,旋赴香港浸会大学宗哲系念书。那时,刘小枫教授还在香港。抵港不久,到他家中做客,趁机请教他,有哪几个比较厉害的思想(史)家值得阅读。如果记得没错,他提了三个名字,施特劳斯、沃格林和麦金太尔。我想现在,他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已经有所不同。当时,这三个人中,我最生疏的是沃格林这个名字。麦金太尔,算是读过他的几部中文译本。施特劳斯,知道河北人民出版社曾出过他主编的《政治哲学史》,另外,碰巧曾在北大图书馆处理外文书的时候,不小心花了16块钱买了施特劳斯的红皮市集本(Agora Edition)《论僭政》(On Tyranny),附布鲁姆所写简短前言。这类书通常会引起青年学生莫名其妙的兴趣,于是也就莫名其妙地买了,反正不是很贵。后来却发现,这本书题目这么热闹,原来不过是对一篇“生僻”的古代文章的“学究”解读以及相关争论。于是乎,束之高阁。
那时,刘小枫教授大约也明白我还不得其门而入。于是推荐我阅读潘格尔(Thomas L.Pangle)所编施特劳斯的入门文集《古典政治理性主义的再生》(The Rebirth of Classical Political Rationalism),作为引导。同时,也试着读了读沃格林的名作《政治的新科学》,然而并没有读懂。比较而言,也不能说更懂一些《古典政治理性主义的再生》中的篇章。不过,确实惊服施特劳斯解读文本的细腻功夫和不拘一格的思想方式。于是,开始阅读并偶尔搜罗一些他的作品。后来,因为个人原因中断了香港的念书生涯。随后到了比利时,在鲁汶大学哲学院念书。不久,收到刘教授的一封回邮,大意是说,施特劳斯是真正的方向。我想,他的意思不是说,要供奉施特劳斯的教诲,而是说,用心阅读施特劳斯,能够找到真正的思想方向。
本书收录四篇文章的顺序,既显示了写作时间的先后,也表现了研究思路的线索。在鲁汶完成硕士论文之后,开始考虑博士论文的题目。基本的想法是重点考察施特劳斯对一个现代哲学家的研究。现代哲学家中,施特劳斯用力最多的有三个人:斯宾诺莎、霍布斯和马基雅维利。迈尔所编《施特劳斯文集》凡六卷,其中三卷分别为施特劳斯论述这三位哲学家的文集。施特劳斯对迈蒙尼德、修昔底德和色诺芬的重视,在一定程度上要分别归功于他对三位现代哲学家的悉心研究。施特劳斯的读者都十分熟悉,他是古典政治哲学的拥护者和现代政治哲学的批评者。然而,施特劳斯并非纯粹为了厚古而薄今,或者纯粹为了薄今而厚古。他强调,没有通往古人的直截道路。只有深入琢磨现代政治哲学奠基者对古人的攻击及其如此攻击的意图,才为正确揣摩古人心意奠定可靠的基础。只有在今人与古人的断裂处,古人的心意即便受到猛烈地攻击也还栩栩如生。一旦这个断裂宣告胜利而后,一旦这个胜利被视作当然,古人的心意便在这个胜利宣告之下逐渐模糊,而后迹近销声匿迹。这也是为什么施特劳斯不断要追本溯源现代政治哲学的奠基处。
几经考量之后,决定以施特劳斯的霍布斯为方向,然后我的导师德斯蒙(William Desmond)教授建议同时考察施米特的霍布斯,以开阔论文的思路和视角。于是,基本上确定论题计划。要同时考察施特劳斯和施米特,迈尔(Heinrich Meier)的著作便是绕不开的文献。准备硕士论文的时候,已经尽可能地阅读和评述讨论施特劳斯的著作和文章。不过,刻意略过了迈尔的论述。当时对迈尔的论点虽不陌生,但感觉尚未很好地把握整体论述。而且,迈尔的论述值得单独考察。第三篇文章便是多次阅读迈尔尤其是《施米特、施特劳斯与〈政治的概念〉》的思考结果。最后一篇文章乃是应刘小枫教授之约,为施米特论霍布斯文集中文本所准备的导言。迈尔札记留下的问题,这篇文章试图做一个初步回答。如今回头再看头一篇论文,有些看法已经有所改变。最后一篇文章已经体现了一些关键想法的转变。但是,没有头一篇论文作为基础,后来的想法也没有可能。因此,将这四篇文章集在一起,作为几年来阅读施特劳斯的一些初步心得。谨将此书献给刘小枫教授,以表谢忱和敬意。其中牵强谫陋之处,则愿识者不吝指正。
2003年10月草于鲁汶
2004年11月补于鲁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