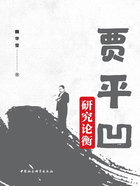
第五节 《浮躁》研究热潮
1987年,贾平凹的长篇小说《浮躁》发表在《收获》第1期,作家出版社同年出版单行本。在当时国内长篇较少的情况下,《浮躁》一出版就受到文学评论界的热议。之前贾平凹凭借商州系列,已经获得文坛的认可,对于长篇小说《浮躁》的出现,大家普遍期待。另外,《浮躁》和当时处于变革期的社会情绪有关,之前写改革的《鸡窝洼的人家》《腊月·正月》,贾平凹就已触动了时代变革的声音,新旧观念、生产方式的变革,通过较为偏僻的山乡生活反映出来。《浮躁》的出现,也被认为是贾平凹改革文学的集大成之作,作者有意以一部长篇总结之前的创作,很好地概括了变革时期的总体社会心理。以至于王富仁曾在文章中回忆,当时读到《浮躁》书名的时候,心里咯噔一下,觉得自己朦朦胧胧感觉到的东西被唤醒了。《浮躁》也为贾平凹赢得更大的社会声誉,经中国作协推荐获得美孚飞马文学奖,这也是新时期以来中国作家作品首次获得重要的国外奖项,《浮躁》旋即成为当时文学界的重要话题。对这部小说的评论、研究从1987年一直延续到1989年,在当代文学界形成了一个不小的研究热潮。
作品出版之后,陕西《小说评论》编辑部,以及作家出版社分别在西安和北京召开了作品研讨会。《小说评论》编辑部1987年7月21—22日在西安召开,以及陕西部分评论家、作家、编辑等30余人参加了会议。会议由时任《小说评论》主编王愚、副主编李星主持。与会者高度肯定了《浮躁》是从宏观上把握时代律动的重要作品,是贾平凹创作成熟的表现。《浮躁》的重要性在于,这是一部以对现实的同步思考为特征的,试图从宏观上全方位地把握时代律动的重要作品。作品既反映了时代的改革要求和改革给当代社会带来的活力,又尖锐地触及了在开放搞活以及发展城乡商品生产中出现的种种新问题与新矛盾。在研究者看来,《浮躁》最突出的特质在于对转型期社会整体上所做的对时代情绪以及文化心理的准确而集中的概括。同时,《浮躁》对于当下中国人的人性建构,以及对于转型期社会心理的挖掘,社会情绪的整体把握,达到了相当深广的深度。就贾平凹的创作而言,《浮躁》称得上是跃上了新的一级,“《浮躁》是贾平凹走向成熟的表现”[40]。
作家出版社于1987年11月24日在北京召开《浮躁》研讨会。关于贾平凹的新长篇小说,与会者普遍认为展现了改革时期五光十色的农村社会生活画卷。作者也拓展了之前的道德视角,尝试深入历史、文化、政治等多种层面,揭示了现阶段中国农村社会的现实问题与历史特征,特别是以权力、家族为中心的宗族文化在未经彻底蜕变之前,对中国社会各个领域的变革所起的巨大阻碍作用。《文汇报》在总结时专门指出:“要了解当前的中国社会,不可不读《浮躁》。它的出现,是近年来长篇小说创作中的一个重要成果。”《人民日报》在1987年12月1日,刊载《长篇小说〈浮躁〉讨论会》纪要。12月29日《人民日报》又刊发董子竹的评论文章《当代民族心态裂变的交响——评长篇小说〈浮躁〉》,探讨《浮躁》与时代转型的关系。
关于《浮躁》,涌现出大量评论文章。费秉勋《谈〈浮躁〉》(《新疆石油教育学院学报》1988年第1期),认为《浮躁》是贾平凹创作历程上一部非常重要的作品,是他创作的一个大综合。《浮躁》总体上看是现实主义的,但是是向《红楼梦》那种现实主义的回归。贾平凹在以前的作品中,大多有一个主要的生活原型,作为构创人物和故事的依据,相较而言,《浮躁》则突破了这一写法,没有制约全篇构架的生活原型,摆脱了以往写作程式的制约。周政保《〈浮躁〉:历史阵痛的悲哀与信念》(《小说评论》1987年第4期),指出当下的小说界尽管模式纷繁多样,但总体来说,贾平凹的小说方式,以及这种方式中所可能包含的富有自身生活特色的巨大思想容量走向却不能不认为是中国当代小说的一种卓越形态。并且重点分析了人物形象,认为金狗是一个近年来农村题材小说中具有典型意味的人物,他的全部命运际遇及心灵轨迹,都呈现出中国当代社会走向变革的繁难和艰巨,以及传统因袭的制约,农民在新的现实面前的改变与挣扎。就人物形象来说,金狗更具有时代性,同时具备民族与土地的深沉意味,当下时代感与人的观念意识相融合的审美价值及思考特质。
董子竹作为贾平凹的好友,曾指导《浮躁》的修改,对这部作品也给予很高肯定。在评论文章《成功地解剖特定时代的民族心态:贾平凹〈浮躁〉得失谈》(《小说评论》1987年第6期)中认为,《浮躁》的现实意义在于,作品人物形象的描写以及对于时代的整体性概括。虽然作品刻画出金狗作为一个倔强、聪明、有社会责任感的青年,但过分强调个人在改革社会进程中的作用。而悲剧的主要原因在于:他的改变、改革的行为是符合历史发展的要求,但是具体做法并没有完全跳出原有“文化大革命”式的思维,仍是突出斗争性,似乎为唯一通行的法则。在董子竹看来,《浮躁》所揭示的,正是这种“左”的思维方式和价值系统,如何不自觉地在人们的思想行为中起作用,以及所产生的悲剧结局。而贾平凹之所以把这部三十多万字的长篇小说定名为《浮躁》,其深意也是在于此。
李其纲《〈浮躁〉:时代情绪的一种概括》(《文学评论》1988年第2期)指出,《浮躁》是人文背景下民族心态的一个侧面,浮躁同时是原欲与超越。金狗在原欲的驱动下单枪匹马进入州城,但在这里找不到立足点,反而处处忍受着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折磨,以至于返回故土,再次回到生他养他的州河上。因此,金狗走过的是一条超越原欲、超越自我的道路。论者肯定金狗的浮躁史、奋斗史,认为他的气质已经逐渐坚忍沉着,也开始摒弃空谈玄思的幻想,回到崇尚务实的行为中去。在这个意义上,浮躁同时是历史进程的价值尺度。以小水们为代表的传统稳定结构来证明“浮躁”本身的价值内涵,也凸显出沉闷的土地急需变革的历史进程和发展态势。在评论家看来,《浮躁》的成功一方面很好地概括了改革时期的社会情绪,同时塑造了金狗这样一位改革者形象,在创造“新的人物”“新的世界”的20世纪80年代,金狗无疑具有改革者的诸多要素和意义。
《瞭望周刊》1988年第50期,在《浮躁》获得飞马文学奖之后更是请出评委谈论这部作品,刊载《浮躁》四人谈。包括刘再复《〈浮躁〉的成功之点》、唐达成《说〈浮躁〉》、汪曾祺《贾平凹其人》、萧乾《读〈浮躁〉》,参与者都是对这部作品做出肯定评价。在编者的策划中,提及《浮躁》所获的美孚公司设立的“飞马文学奖”。该文学奖的设立,是为促使那些较少被译成英文的国家的优秀作品能够通过翻译推介,走向世界,获得国际社会的承认。这对于长久处于封闭状态的中国文学来说,是难能可贵的。当年的“飞马文学奖”在中国作家的作品中评选,评委是萧乾、唐达成、刘再复、汪曾祺和茹志鹃。因此编者特意邀请四位在京评委撰文进行评价。在刘再复看来,《浮躁》不仅是贾平凹个人创作上的一部重要作品,而且在新时期小说的整体创作中,也是很优秀的一部。在当今改革的纷繁世态中,作者能够审视和摄取人们的文化心态特征,并且做出富有深切的忧患意识和批判精神的刻画。汪曾祺认为《浮躁》写的是一条并不存在的州河两岸土著居民在改革开放激变中的形形色色的文化心理嬗递,没有停留在河上的乡镇企业、商业的隆替上。他把这种心理状态概括为“浮躁”,是具有时代特点的。
唐达成则从纵深讨论贾平凹的作品,在他看来,贾平凹是有自己独特创作个性和审美特征的作家,也是在当代中国文坛享有盛誉的作家。《浮躁》无论在生活面的开阔宏大,还是在思想、文化内涵的深入挖掘方面,与贾平凹以前的作品相比较,都是一次较大的提升与超越。作品从时代的高度,以富有个性色彩的审美追求,以及独特的文化审美批判眼光,深刻地把握住当代农村改革背景之下的复杂脉络。在萧乾看来,贾平凹是当代一位对写作十分认真的青年作家,作品并不概念化,多是从生活实际出发。最重要的是小说使人感到这个乡镇在浮躁着、蠢动着,新生的和陈腐的势力在搏斗着。评委们对贾平凹一直以来的创作实绩和《浮躁》所代表的时代意义都给予较高的评价,也从不同方面解释了获奖的原因。
此外,还有评论文章对于作品艺术性的系列分析,包括李星《混沌世界中的信念和艺术秩序——〈浮躁〉论片》(《小说评论》1987年第6期)、徐明旭《说〈浮躁〉》(《文艺评论》1987年第6期)、金平《由〈浮躁〉衍生的话题——与贾平凹病榻谈》(《当代文坛》1987年第2期)、王彬彬《俯瞰和参与——〈古船〉和〈浮躁〉比较观》(《当代作家评论》1988年第1期)、刘思谦《不必为了理解——金狗、雷大空论》(《当代作家评论》1988年第1期)、陈骏涛《〈浮躁〉的联想》(《瞭望》1988年第13期)等。这些文章都从不同角度分析了《浮躁》所涵盖的时代情绪与转型期的社会问题。总体来说,关于《浮躁》,多是从肯定性和积极意义进行评价。费振钟认为贾平凹是“商州之子”,商州系列使他获得了商州历史的语言形式,以及领悟到商州的精神,确立了一种确定性的形式[41]。
在作品中的人物形象方面,刘火《金狗论——兼论贾平凹的创作心态》(《当代作家评论》1989年第4期),重点分析主人公金狗,认为是一个具有现代意识和反叛道德的形象。金狗作为一个具有现代意识的个体,他的个性特征不仅表现在社会功利性方面,还表现在与作品人物韩小水、田英英及石华的复杂情爱关系方面。金狗所代表的浮躁既是实现个体价值的动力又是阻力,所以故事会以悲剧告终。
这些评论大都从不同侧面解读了《浮躁》的创作意义和人物形象。贾平凹谈及自己创作《浮躁》的意图时说,关于人物形象,自己也长久思考这个问题。联想到鲁迅先生的《阿Q正传》和塞万提斯的《唐吉诃德》,为什么这两部作品中的人物形象能够典型地概括那个时代的特点?后来发现是作家能够从现实生活中抓住当时时代社会的特点,抓准了,抓得有力,涵盖面就大,就能代表一个时代。因此,在写《浮躁》的时候,就有意改变了创作方法,开始尝试不再从某一个人的视角或生活来看问题,不再是单纯地听到什么故事或者从具体的某一件事来写,而尝试着从许多人的心态中提炼出当前时代中的典型面,即那种浮躁情绪:“从这一点出发,去组合人物,展开事件,用的一些素材是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事情,但抓住的是弥漫其间的情绪。”[42]虽然这部作品获奖、社会评价也很高,但贾平凹本人对《浮躁》的写法并不满意,他在作品后记中提及散点透视的创作方法给他造成的痛苦,先后废过十五万字,后又翻来覆去改过三四遍,原稿完成后又根据《十月》编辑侯琪和评论家董子竹的意见做了修改。甚至一度怀疑写《浮躁》,作者亦是浮躁的心态。
当时,也有评论者撰文谈及对《浮躁》存在问题的异议,如邢小利《〈浮躁〉疵议》(《小说评论》1988年第2期)认为,贾平凹对州河上生活的人物和生活本身的描写是真实和深刻的,但是当他跳出人物和生活流程进行理性分析,并试图站在哲学高度进行把握时,就显得有些捉襟见肘。在他看来,贾平凹的问题在于创作中一方面依赖自己对生活的体验,另一方面过于依赖读书所得,以及惰性地认同周围他者的思想和看法。这也代表了主流之外的另一种看法,当然,从个人审美感受指出作家作品存在的问题也是无可厚非的。
1988年10月26日上午,中国作家协会与美孚石油公司在北京举行新闻发布会,正式宣布《浮躁》获得飞马文学奖。评委会主席介绍并宣读评委会委员们对作品的评价:在中国进行改革与开放的巨大浪潮中,长篇小说《浮躁》站在时代的高度上,把握住了当代改革中生活巨变的脉络,以及在政治、经济、文化、道德、心理等各方面所经历的复杂曲折的斗争,作品虽然描写的是偏远山区的农村生活,却相当典型地反映了具有传统文化氛围的中国现实。按照飞马文学奖的惯例,《浮躁》由美国方面组织安排将其翻译成英文版,推向世界。后由汉学家葛浩文先生翻译出英文版。在2018年评选“改革开放四十年最具影响力小说”时,《浮躁》获得最具影响力十五部长篇小说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