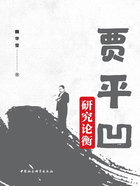
第三节 “笔耕”研讨会与《二月杏》风波
1979年5月,中断了十多年的陕西省作家协会开始恢复工作并开办了首期读书班。1980年夏天,在太白召开农村题材座谈会,贾平凹、陈忠实、路遥、李星、肖云儒、邹志安、京夫等都参与其中。1980年12月,由胡采担任顾问、王愚担任组长的“笔耕”文学研究组成立,意在团结西安地区的文学评论工作者,开展各种文学创作评论与研究活动。“笔耕”文学研究组是新时期伊始陕西文坛的重要评论力量,成员之间的文学批评观及批评风格虽然不尽相同,但能够出于本心,坦言直陈各自观点,基本保持了君子“和而不同”的批评风范[26]。1981年1月13日,“笔耕”文学研究组正式在西安开展第一次学术活动,具体讨论文艺的真实性和倾向性等问题。在80年代初意识形态相对严肃紧张的时期,其影响力和权威性使其成为陕西文坛最为重要的批评力量。
贾平凹的个人创作在这一时期却遇到波折,1981年,他在《长城》杂志第1期发表中篇小说《二月杏》,引发较大的读者舆论风波。“安徽省地质局宣传科向崇安说:‘作家把我们的地质队,简直描写成了乌七八糟的团伙’。”[27]“《二月杏》提供给人们的,乃是一幅被歪曲、丑化了的,色调灰暗的生活图画……在作者的笔下,看不见地质工人从事四化建设的蓬勃热情,看不见工人阶级崇高的生活理想和道德情操。”[28]各种投诉、压力,批评文章的不断出现,给年轻的贾平凹营造了一个非常“紧张的文学氛围”。
1982年2月10—13日,“笔耕”文学研究组在西安召开贾平凹的近作座谈会,认为《二月杏》连同贾平凹1981年前后发表的《生活》《沙地》《好了歌》《“厦屋婆”悼文》等色调灰暗的小说构成了贾平凹创作的“偏差”。众人对于贾平凹的创作状况也存在较大分歧,一部分意见认为贾平凹的思想和创作倾向确有偏离,从过去写美人美事美景,到写丑人丑事丑景、怪人怪事怪景,泯灭了是非之心,可以说基本上否定了贾平凹这一时期的创作。而费秉勋等人则持不同意见,认为应该意识到其创作的多面性与复杂性,并提出“贾平凹的思想不是出世而是入世”,“生活像一座大山,贾平凹过去写的是阳面,现在写的是阴面,合起来才是完整的”。根据《延河》杂志发表的会议纪要,可以看出当时对贾平凹多面的评价。
贾平凹同志,是我省一位勤奋而有才干的青年作家,他开始创作六、七年来,写下了小说、散文、诗歌等一百余万字,有着比较广泛的影响。我省文艺界和评论工作者对他的成长十分关心。“笔耕”文学研究组,于二月十日至十三日,召开了一次贾平凹近作讨论会。贾平凹本人以及西安、宝鸡少数同志应邀参加了会议。
一些同志在探讨贾平凹近作产生某些偏差的原因时指出:对艺术的探索,必须以对生活的探索为先导,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指针。这些方面,恰恰是平凹比较薄弱的环节。作者生活、思想修养与艺术修养不平衡,造成了作品的畸形发展。有同志说,贾平凹创作中出现的问题,既是我国当前社会生活复杂面貌在作品中的不正确反映,也可照见中国传统文化、历史中消极因素的影响。
持另一种意见的同志认为,贾平凹的思想不是出世而是入世。他近来反映的生活越来越广,越来越深,越来越复杂,他在思考生活,触及社会,探索人生,解剖灵魂,企图把生活的本来面目,真实地暴露在读者面前。
贾平凹表示,今年要系统地读点马列著作,历史著作,哲学、美学著作,想办法到生活中去。在艺术探索上力求做到有效限制,走出自己的路来[29]。
随后,《延河》杂志相继刊载关于贾平凹作品讨论的文章,1982年第5期刊载李星《评贾平凹的几篇小说近作》,批评了贾平凹1981年发表小说中的消极观点,并且指出:贾平凹创作中出现的问题和错误并不是偶然现象,它是当前我国社会复杂的生活面貌在作家创作中的错误反映。李星认为贾平凹的创作出现了很多并不积极,也不健康的倾向,这和他的艺术修养、生活修养、思想修养不够有关,并指出浓厚的群众生活根基才是一个作家健康的发展艺术才能的基础,呼唤贾平凹深入生活。费秉勋在《贾平凹一九八一年小说创作一瞥》中,则提出不同意见。在他看来,贾平凹的小说曾经在1980年发生过一个突变,从对山地青年美好心灵的摹写,转而对当代生活中病态部分的揭露和解剖。1981年,贾平凹小说又发生了另一个新变化,对于社会病态的揭露和解剖虽然仍在继续着,但作家的情绪和声音却有了不同的调子。这一时期,作家注重对于人生的探求,进而成为作品的重要内容。冷峻的调侃代之以情思的描写,艺术熔铸的功力更趋纯熟,文气更趋浑厚。冠勇的文章《染印着时代色泽的艺术花朵——也谈贾平凹近年的小说创作》,肯定了贾平凹近年的创作倾向,原因是和他前期作品一样,他依然抱着热爱生活、追求美好的愿望锲而不舍地创作着。
1982年第7期《延河》杂志刊载了畅广元的文章《作家应该具有透视力——读贾平凹几篇近作的感受》,作者批评了贾平凹创作的消极和缺陷,认为近作中的几个问题,表明他在对生活的思考和探索中迫切地需要敏锐的透视力。李健民《探索中的深化与不足——评贾平凹近期小说创作》,认为作家通过对人的复杂性格的揭示,在深入开掘生活上所做的努力是不应简单否定的。《延河》第8期,陈深的文章《把生活的井掘得更深——贾平凹小说创作直观录》,开篇直言贾平凹是一个有追求、有作为的青年作家。首先应该承认他有一定的生活基础,但也不能否认他这一时期存在相当多的作品比较消极,表现在如何理解和认真生活出现思想偏差,态度也不够正面准确。
这次会议和随之而来的评论文章给贾平凹造成极大的心理压力。因父亲在“文化大革命”时的不幸遭遇及对政治高压的历史恐惧,贾平凹一度担心自己无法写作,一向高产的他停顿半年时间寻找新的文学出路。甚至专门去陕西省地质局征求意见,宣传处的同志当面转达了地质职工对于小说《二月杏》的批评意见,贾平凹也专门认真地记录了下来,并 “表示要根据批评意见把《二月杏》好好修改一下,并争取将来写一点反映地质生活的作品”[30]。据友人马士琦回忆,自己当时初识贾平凹,向他提问:
“你已发表了200多篇作品,出了6本书,你认为力作是哪一篇?”
“《二月杏》。”
“《**日报》上不断地发大块文章,不是正在围攻《二月杏》吗?”我即联想到“文化大革命”中的“大批判”,特意用了“围攻”一词。
“年轻的母亲,把娃抱出,无论旁人说娃是美是丑,娃总是自己生的。”平凹并没有正面回答,他又深吸了一口烟。
沉默片刻。[31]
从这段回忆中可以发现贾平凹内心对自己创作风格的坚持,但20世纪80年代初的文学环境,尤其是刚刚经历“文化大革命”的遭遇,这一时期的文学批评和外部波动仍对其创作转向产生重要影响。贾平凹经过一段时间的心灵挣扎,面对“少年不知愁滋味,为赋新词强说愁”的评价,一向高产的他将创作停顿了下来[32],1982年下半年,仅仅写了些小散文,几乎连一篇小说也没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