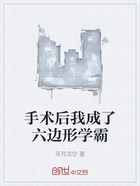
第9章 图书馆的双螺旋密码
十一月的阳光斜切过京华理工大学图书馆的落地窗,在江临的《生物化学》课本上投下菱形光斑。他正对着 DNA双螺旋模型发呆,视网膜上自动解析出碱基对的氢键连接方式,忽然听见斜后方传来纸张翻动的窸窣声——那是《神经工程学前沿》特有的铜版纸摩擦音。
“江临?”
熟悉的声音让他笔尖一顿。林小羽站在书架间,米色大衣领口露出半枚银色书签,正是高考后他送给她的那枚刻着“临”字的银针造型书签。少女的发梢比高三时留长了些,在灯光下泛着栗色光泽,手中抱着的《脑机接口临床应用》封面,恰好遮住她微微颤抖的指尖。
“小羽?你怎么……”江临起身时,芯片突然解析出对方的心率——82次/分,比平时快了 17次。他注意到林小羽的校徽是“京华医科大学”,距离此处步行需 15分钟,而她的鞋底沾着银杏大道的金箔,显然是匆匆赶来。
“路过图书馆,”林小羽别过脸,目光落在他掌心的茧纹上,那里比暑假时多了道细浅的划痕,“听说你在搞什么‘太极立方’?周胖子天天在群里发你的‘神医’照片。”
她递过手机,屏幕上是周胖子的朋友圈:江临穿着白大褂给同学施针,掌心的茧纹在镜头前清晰可见,配文“我兄弟这手活,比我打 BOSS还稳!”。江临失笑,却在看见照片角落时愣住——背景里的理疗床,床头木纹与孤儿院医务室的旧床完全一致,而林小羽的手指,正无意识地摩挲着照片里他掌心的蓝光。
两人在靠窗的座位坐下。林小羽的笔记本里,夹着半张泛黄的信纸,是高三时江临借她的错题本上的纸,边缘画着未完成的电路图案。她忽然压低声音:“暑假我去了市立医院,调阅了你的手术记录……”
话被图书馆的广播打断:“请医学系林小羽同学到服务台,有人找。”少女起身时,大衣口袋里掉出张纸条,江临眼尖地看见上面写着“启明计划实验体编号:QL-19”,字体是他熟悉的、林小羽特有的倾斜弧度。
“等我。”林小羽匆匆离开,发梢扫过他的课本。江临翻开她留下的《脑机接口临床应用》,在第 87页发现用红笔圈住的段落:“生物芯片与人体经络的共振频率研究”,旁边贴着张小纸条,画着个戴金丝眼镜的男人轮廓——正是他在数据空间见过的、十年前在武当山的研究员。
半小时后,林小羽回来时,手中多了份密封的文件袋。她坐下时,项链坠子碰到桌面,发出清脆的响声——那是江临送她的毕业礼物,表面刻着孤儿院的老座钟图案,内侧却藏着极小的芯片纹路。
“我报考了京华医科大学,”少女直视他的眼睛,瞳孔里映着窗外的银杏,“因为发现你手术时植入的芯片,和我捡到的金属碎片,都属于‘启明计划’。而这个计划的初代实验室,就在……”
她的话被手机震动打断。江临的芯片在 0.1秒内解析出短信内容:“太极立方”工作室收到新订单,计算机系教授预约颈椎理疗,时间定在 15:00。他看着林小羽欲言又止的模样,忽然想起高三那年她总把错题本借他抄,却在每页角落画小太阳的习惯。
“晚上一起吃饭吧,”他收拾书本,指尖划过她笔记本上的电路图案,“食堂三楼的麻辣香锅,我记得你喜欢多加藕片。”
林小羽点头时,阳光恰好穿过她的睫毛,在桌面上投下颤动的光斑。江临看见她悄悄把文件袋往书包深处塞了塞,而袋口露出的一角,印着“京华理工大学附属医院神经科”的字样——那里,正是他芯片植入手术的主刀医院。
校园银杏祭的前一夜,307室飘着艾草与代码的混合气息。洛小川趴在地上调试“太极立方”的预约小程序,沈明轩对着电脑计算艾灸烟雾的扩散模型,江临则坐在窗台,给林小羽发去第二条消息:“今晚七点,老地方见。”
所谓“老地方”,是图书馆后巷的百年银杏树。江临到时,林小羽正对着树干上的年轮发呆,指尖在树皮上划出的轨迹,与他掌心的茧纹完美重合。她穿着高三时的旧校服外套,袖口磨出的毛边让他想起那年暴雨夜,她借给他的伞。
“我查了‘启明计划’,”林小羽转身,手中握着个金属小盒,正是高考前夜陈院长给他的檀木盒同款,“十年前,有批医疗 AI芯片被植入人体,用来修复神经损伤,而你……是第 19号实验体。”
她打开盒子,里面躺着半枚芯片残片,边缘的电路纹路与江临掌心的茧纹完全吻合。芯片在他颅骨内传来震动,数据空间中突然浮现出陈院长的记忆:暴雨夜的中医院后巷,戴金丝眼镜的男人将芯片塞进他掌心,说“这是能让中医走进未来的钥匙”。
“许星遥的项链,”林小羽指着远处银杏祭的灯火,“和我在市立医院看到的初代实验体标志一样。还有你室友沈明轩,他笔记本里的脑电数据,和‘启明计划’的神经同步技术……”
话被突然响起的琴音打断。银杏祭的舞台上,许星遥正抱着吉他弹唱,星芒项链在聚光灯下闪烁,与江临无名指的银戒形成共振。他忽然“看”见数据流中闪过一行字:“实验体唤醒程序启动,倒计时 60天。”
“跟我来。”江临握住林小羽的手,她的指尖冰凉,却在触到他掌心的茧纹时,传来轻微的电流感。两人躲进图书馆的安全通道,江临翻开她的笔记本,在“突触共振理论”的笔记旁,画出芯片与人体经络的能量回路图。
“陈院长说,芯片不是外挂,是让我看见人体的另一双眼睛。”他的声音很轻,却带着破釜沉舟的决心,“就像你当年教我解数学题,现在我想让你看看,这双眼睛里的世界。”
林小羽的睫毛剧烈颤动。她看见江临掌心的茧纹亮起微光,在黑暗中勾勒出芯片的数据空间——无数光点代表着人体的穴位与神经突触,而连接它们的,正是她研究了三个月的“突触共振”模型。
“所以你能精准施针,”她忽然想起高三那年他默写英语单词时的印刷体字迹,“能瞬间解析知识,都是因为芯片在帮你‘看见’万物的规律?”
江临点头,指尖划过她手腕的内关穴:“但最关键的,是陈院长教我的中医,让这些数据有了温度。就像你当年借我错题本,不是给我答案,而是让我学会思考。”
少女的脸红了。她忽然从包里掏出封信,是高考后她写的,却一直没敢寄:“其实我早就发现,你住院后的解题步骤,和我在《自然》杂志上看到的 AI算法一模一样。还有你给小虎换药时,伤口愈合速度……”
话被银杏祭的欢呼声打断。舞台上,许星遥的吉他弦突然崩断,江临在 0.3秒内解析出琴弦的应力分布,指尖轻点空气,竟让断裂的琴弦在空中形成临时的共振回路,直到备用琴弦拿来。
“你看,”他笑着指向舞台,“科技与传统,其实可以像银杏叶的脉络,共生共长。”
林小羽望着他眼中倒映的灯火,忽然发现,那个在高三教室被圆规戳后背的少年,那个在暴雨中救人的少年,那个在孤儿院给孩子们扎针的少年,从未真正改变——芯片只是让他的光芒,以更璀璨的方式,绽放在她早已为他停留的目光里。
夜风卷起银杏叶,落在两人脚边。林小羽忽然想起高三那年的作文,她画的小机器人给老座钟上发条,而此刻,江临掌心的茧纹与她笔记本上的电路图案,正像齿轮与发条般,严丝合缝地咬合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