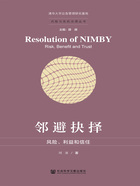
第一章 邻避问题的产生及对公共决策的挑战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不要建在我家后院
长期以来,危险设施选址(Hazardous Facility Siting)问题被视为一个纯粹的技术问题,由技术专家和政府官员根据地理条件、土地规划和成本-收益分析等技术原则进行决策,并没有进入公众视野。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一些垃圾处理设施选址方案在美国引发了一系列激烈的地方抗议活动,从此掀开了邻避运动的序幕。由于担心居住环境、生活品质、公共安全甚至是房屋价值受到影响,居民们反对政府或者发展商在自家附近兴建邻避设施,如垃圾填埋场、焚化炉、机场、监狱、收容所、精神康复中心、戒毒服务中心等。尽管公众都认为这些邻避设施对社会发展来说必不可少,却希望它们能够远离自己,落址他处,而“不要建在我家后院”(Not-in-my-backyard,缩写为“NIMBY”,中文音译为“邻避”)。在邻避运动的压力下,邻避设施选址频频受阻,1980~1987年间,美国试图选址的81个垃圾处理设施中仅有6个正式投入运行,其余的均因地方抗议而被迫终止或缓建(New York Legislative Commision on Toxic Substances and Hazardous Wastes,1987)。《纽约时报》将整个20世纪80年代称作不折不扣的“邻避时代”(Glaberson,1988)。同时期,有关核废料储存库的选址问题在英国、瑞典、荷兰等欧洲国家逐渐成为公众议题,并不同程度地受到地方的邻避抗议和更广义的环境运动的挑战。进入90年代,邻避运动开始在日本、韩国及中国台湾等亚洲国家或地区出现,邻避运动俨然扩散到全球不同体制、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和地区。基于“命令-控制”、工程分析、共识机制等不同方法的选址程序在遭遇本地抵抗时都不幸搁浅,哪怕发展这些设施的全国范围的政治意愿很强烈的时候也是如此。
我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展开,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张力表现突出。在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的大背景下,我国的邻避设施选址问题也浮出水面。2003年,我国的一部分环保人士、记者以及非政府组织通过新闻报道、政协提案、联名上书等形式成功阻止了在云南怒江建设水电站,也引发了持续将近10年的怒江开发之争。这可以被视为我国邻避设施选址冲突的早期案例。但是以大规模公众参与为特征的邻避运动的发端是以2007年厦门PX事件为标志的。2007年6月,厦门市民为反对具有潜在危险的石油炼化PX项目落址厦门而走上街头“和平散步”。事发之后,政府与公众进行了充分沟通和良性互动,最终决定倾听民意取消该项目的建设计划,并由政府对开发商提供部分赔偿。但是PX项目的选址难题并未结束,随后大连、成都、宁波、昆明、茂名等地爆发了类似的群体性事件,并通过网络舆论在全国引起了广泛关注。PX项目成为一个人所共知的敏感词,无论在何处动议PX项目的选址计划都会引起当地居民的高度紧张。除此之外,四川什邡的钼铜项目、广东鹤山的核燃料生产项目等都是近年来由邻避设施选址引发公众抗议的代表性案例。其他如北京市民抗议京沈铁路临近居民区、广东番禺市民反对垃圾处理设施的建设等具有地方性影响的邻避运动在近些年中更是不胜枚举。
可见,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公众的环保意识和权利意识也大幅提高。诸多工业投资项目被当地民众否决的事件表明,中国已经进入了邻避运动高发期。邻避现象的出现可以被看成一种社会进步,公众抗议爆发之后,各地对新项目的审批、环境影响评估越发严格,有利于环境保护和产业健康发展。从各国的发展来看,邻避现象似乎已经是一个国家工业化、现代化过程中必须面对的困境。一方面,当公众生活水平达到一定高度后,价值观念开始发生变化,人们对生存权的追求已从物质层面提升到更高的环境层面;另一方面,这也是对高速工业化的集体反思。改革开放以来在我国的高速经济发展中,不知道有多少工业项目肆意向天空、河流和地下排放各种污染物,给生态环境和公众身体健康造成无法弥补的影响(薛澜,2013)。
在我国维护社会稳定的总体要求下,频繁爆发的邻避事件大多以官方向民意妥协而告终。这样的结局看起来似乎是民意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但严格说来没有赢家,给经济社会的长远发展埋下隐患。首先,对大部分已经筹建或开工的项目来说,项目停建必然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这些损失的很大部分是由政府来埋单的,换句话说,没有得到公众支持的选址方案导致了高昂的决策成本。其次,从长远来看,我国经济发展中迫切需求的产业项目、公共设施得不到有效满足,一些紧缺的工业原料大量依赖进口。最后,更为严重的是,邻避项目的最终放弃一次次印证了“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的公众预期,哪怕是最温和的抗议行为也会腐蚀公众信任,不仅不能化解社会矛盾,还会进一步加深中国社会阶层之间的裂痕和对抗。随着社交媒体的广泛普及,地方性的邻避冲突极有可能借助互联网技术引发全国性的公共舆情和抗议,对我国的社会秩序造成不良影响。可见,邻避设施选址问题的政策困境远未破解,其对经济发展和环境安全的权衡将成为今后较长时期内不可回避的重要政策问题。相关部门必须找到一种有效的决策模式,让决策能够最大限度实现科学化和民主化,让利益相关方的博弈不再以社会剧烈震动的方式进行,让妥协和理解不是在社会撕裂了之后再浮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