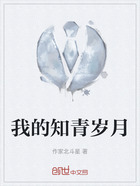
第1章 初见
一九七四年九月十日,一个让洪涛一生都记住的日子。年仅十八岁的洪涛响应国家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他不知道,眼下的行动会给他的一生带来什么……
豫阳市文化宫前的体育场院内,停放着数不清的解放牌汽车。每台汽车的鼻子上扎着纸制的大红花,车厢两侧帮子上插着彩旗。每辆汽车周围站着一些胸戴大红花的青年男女及送行的人们。
洪涛的家邻近体育场,这天早上八点来钟,洪涛的父亲用自行车驮着专为洪涛下乡准备好的木箱子,木箱子上面是按军人标准捆绑好的行李,自行车车把上挂着一个装有脸盆、水缸、饭盒等物件的网兜。洪涛的父亲在前面推着自行车车把,洪涛斜挎着绿书包在自行车后面扶着木箱子和行李。他们父子倆人在体育场院内,找到了23号解放牌汽车。此时,汽车周围已站了一些人。洪涛的父亲立好自行车,来回转头向两侧瞅着像是在找人。
“哎,老余,”洪涛父亲喊老余这个人,洪涛也认识,几天前洪涛随父亲去过他家,洪涛喊他余叔。余叔听到了洪涛父亲的喊声,笑容满面地走了过来,身后相随着一个扎着两条短辫子,皮肤白皙的姑娘。洪涛虽第一次见这个姑娘,但,他知道那是余叔的孩子,是余叔托付洪涛在乡下照顾的姑娘。余叔握着洪涛父亲的手,侧身回头对他身后的姑娘,说:“那是洪涛,你们认识一下。”
姑娘脸颊绯红,两手掐着胸前的挎包带,跨前一步,微笑着说:“你好”。
洪涛迎着她的微笑,点点头笑着说:“你好!”
上午九时,解放牌汽车在锣鼓声中,缓缓地驶出了体育场。车上的、车下的人们,都在尽情地挥动着他们的手臂,直到车子转弯看不见了。洪涛坐在木箱子上,脸颊凝重。
淡淡的白云,犹如棉絮点缀着碧蓝的天空,白云下面,大雁排成一行向南飞行。
汽车驶离了市区,彩旗哗哗作响。马路两侧的绿树,成排地向后倒去。
一个多小时后,汽车下了柏油马路,拐上乡间土道,七转八拐在村庄里的一处院落前停了下来。
洪涛父亲悄声对洪涛说:“青年点到了。”
随着汽车的鸣笛声,从房子里跑出来很多人,他们穿戴不一,红润的脸庞,健硕的身体,是他们共同的表征。新知青和送行的家长们下了车,老知青帮着新知青往青年点里搬箱子、拿行李……
时间已近正午,青年点里四间房八铺炕,每铺炕上摆着一张长方形木桌。桌子上面摆着两个脸盆,一个脸盆里是猪肉炖芸豆;另一个脸盆里是雪白的大米饭;还有四个白瓷饭碗、四双筷子。
饭后,新知青与送行的家长告别,女知青大多是哭鼻子抹着眼泪与亲人恋恋不舍地惜别着。洪涛送他的父亲上了车,汽车再次鸣笛驶离了青年点。汽车拐弯,驶出了他的视线。
接下来,洪涛里里外外地看看他的新家。五间正房,红砖照面,稻草扇顶。房檐下麻雀飞起飞落,叽叽喳喳地吟唱着,像似在迎接着新来的家人们。五间房正中间一间是厨房,四角有四个大号灶台。厨房正中间开门,门两侧各有一扇向外开的玻璃窗户。另外四间房,男生在东屋;女生在西屋。
每间屋里有南北窗户,上下结构,下面是木框里镶嵌着玻璃,上面是一扇向外推开的白纸糊的木愣格窗户。屋内:黄泥新抹平的墙面;花格纸新糊的屋棚。
正门前有一米多宽的过道通向村里,过道两侧是一米多高的土墙围起来的栏子,栏子里种着适季的蔬菜,蜻蜓,蝴蝶飞起飞落,麻雀儿打闹着。
两个房山头,各埋一口头号大缸,大缸上面摆放着两块一脚宽的木板。东房山头是男厕所,西房山头是女厕所。厕所围墙一米多高,是用黑泥土加稻草跺起来的。房子后院,是土墙围起来的菜栏子。
夕阳西下,老知青收工回来。吃过晚饭的青年男女们聚集在房前,弹吉他的,拉小堤琴的……一位身材窈窕面相娇好的女生,随着音乐唱起了俄罗斯民歌。她是潘莉莉,七一届知青。
新知青刚来,农活不忙,生产队给了几天假。洪涛围着村子看个遍,一条土道由北向南穿过柳家村,往北八里路是柳家房公社所在地,往南四里路是红旗铺大队。村里两条土道与通往公社和红旗铺大队的土道相穿插。柳家村大队三百多户人家,分五个自然屯,按自然屯分成五个小队。
一小队队部在村东北角,五间红砖瓦房坐北朝南,四周是红砖墙,大门朝南。东西厢房是牲口棚,院内有六挂木制胶皮轱辘大马车。
这天徬晚,老知青段鹏举领着洪涛去一小队队长杜保国家串门。杜队长四十来岁,圆脸黑胡茬,身披一件半新不旧的卷着衣领的蓝涤卡上衣,背着手站在地中间。洪涛从上衣兜里掏出纸烟,递给杜队长一支,“你自己抽吧,”杜队长摆摆手,粗声粗气地说道。
“杜队长不抽烟,”段鹏举接着杜队长的话说道。
“你抽不?”“我也不抽,”段鹏举笑着回答道。
杜队长的媳妇,穿一件白色短袖旧的发了黄的圆领汗衫,肥硕的奶袋子在她胸前颠来颠去。
“灰子,你去把猪喂了。”杜队长的媳妇叫着她家的大小子。灰子,圆头圆脸,十三四岁的样子,他跑出屋子喂猪去了。……洪涛和段鹏举走出杜队长的屋子,在厨房门口与一个脸颊俊俏的姑娘走个顶头碰。姑娘侧过身,让过洪涛和段鹏举,然后,走进了西屋。
段鹏举说:“她是杜队长的二女儿,在县城读高中呢。”
洪涛问:“杜队长几个孩子呀?”
段鹏举接话说:“四个孩子,大女儿在县里上班;还有个小儿子,十了岁吧。”
几天后的一个下午,天空乌云密布,下起了不大不小的雨。
“一小队的全体社员到村东头地块收苞米喽!”喊话的是杜队长。
老知青听到杜队长的喊话声,分别从自己的箱子里翻找出来白色的塑料布披在身上,走出了青年点的房门。洪涛知道自己没有塑料布,稍微犹豫过后,他毅然决然地走出屋门,淹没在风雨中。
洪涛到了地头,见地头散放着一些空麻袋。杜队长背着手站在地头,大声吆喝着先到的社员进苞米地,把先前掰下来还堆在地里的苞米棒子,用麻袋装上扛到地东头来。地头已有马车在等着。
洪涛从地上拎起一条麻袋,瞧了瞧看不到深处,也不知道边缘在哪里的苞米地,一头扎了进去。
苞米杆上已经枯黄、卷了边的叶子,蔫头巴脑地随着风雨凄凉地摇晃着。
湿漉漉的麻袋,装上大半袋子被雨水浸泡过的苞米棒子,大约也有百十来斤重吧。洪涛将麻袋扛在肩上,踩着泥泞的垄沟,深一脚浅一脚的往返着。雨还在下着,洪涛肩上的麻袋往下滴着水流,从脖颈到脊梁再到脚下。
抢收完了苞米棒子,洪涛拖着疲惫的湿漉漉的身子,回到了青年点。
“半天就给六七个工分,”崔建华用嘲讽的口吻说道。
这让洪涛心中生厌,说:“哪是工分的事啊!你不去,也没必要嘲讽别人好不好。”
“刚来就积极表现没用的,等老知青抽调完了才能轮到咱们呢。”崔建华说完,扬着下巴颏转身走了。
豫阳市河东区旺民里,有二十多趟平房。洪涛家住18栋2号,崔建华家住13栋1号。
洪涛与崔建华有着共同的爱好——练武术。十四五岁的年纪,想着练好武术,防身抓流氓,长大了当解放军。
旺民里东南角有一片杨树林,树林中间被练武术的人平整出一块块场地,一年四季都有人在那里活动。舞枪弄棒的,打拳踢腿的……洪涛和崔建华看得着了迷。他俩也学着那些人的样子,先压腿再练骑马蹲档式,用手掌击树,用脚踢树,用背靠树。日久天长,他俩练得手掌又宽又厚,一掌出去就能将人击倒。夏日里,他俩穿着跨栏背心,挺着胸脯,露出大块的肌肉,横着走路。
洪涛与崔建华是同学还是邻居,一起练武术,一起下乡插队,又被分在同一个生产队。按理说,他俩应多亲多近才对呀,可是,洪涛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崔建华冷嘲热讽他,这让洪涛的心怎能不憋屈呢。
北方的十月,是金秋的季节。黄灿灿、沉甸甸的稻穗弯下了腰,低下了头。
杜队长站在地头,将手中的镰刀在空中挥了挥,高喊一声:“开割喽!”
一年一度的秋收会战正式拉开了序幕。每个人把着六条垄,崔建华与洪涛并排往前割。下乡的头一年,又是第一次割稻子,洪涛学着老农的样子,用左手拢住稻草杆,右手挥动镰刀,一下一下地割着。唰唰的声响,犹如优美的旋律回响在洪涛的耳畔。
晴空万里,天高气爽。农村社员有说有笑地往前割着,他们手中的镰刀,仿佛是战士手中的冲锋枪,成片的水稻在他们的枪口下倒下。农村社员先到了地头,坐下歇晌。洪涛和崔建华被农村社员落下半条垄。农村社员坐在地头抽着烟,看着他俩一前一后的忙碌着。崔建华先到了地头,他将镰刀头往地下一扎,伸开两臂,叉开双腿,仰面朝天地躺在地上。洪涛到了地头,伸了伸将要折断了的腰,扭了扭似乎裂开了的胯骨轴子。之后,他坐在草地上,擦了擦脸颊上的汗水,脱下被汗水浸透了的背心,拧出了汗水再穿上。秋风习习,背心湿凉,那是怎样的一番心境。打头的社员又开了新垄,洪涛站起身拿起镰刀,拉胯着脚步跟了上去。
再到地头,洪涛的背心上满是盐霜。他哈趴在地头的水泡子旁边,也不管水中游动着的小生物了,张开大嘴巴,咚咚咚地灌着水。有社员喊道:“慢点喝,别炸了肺!”
中午歇晌,洪涛蹒跚着脚步回到了青年点,没吃一口饭就一头扎倒在炕上了。
“上工了,”杜队长的吆喝声……洪涛双手撑着炕面坐起身子,双腿从炕沿顺到地上,弯腰拿起立在墙边的镰刀,拉胯着脚步走出屋门,上工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