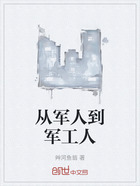
第2章 儿时的快乐很简单
我出生在三年困难时期,那时的居民凭“一本两证许多票”实行票证购物。其中“一本”是《户口簿》,“两证”是《市镇居民粮食供应证》和《购物证》,“许多票”泛指“粮票、油票、肉票、煤票”等,一般按户口簿核定人数在年底统一发放两证和林林总总的各种票证。
城镇家庭的普通居民每月粮食定量为27斤,这在当时,是经过精细考量后定下的额度,用以维持日常生活所需。工人阶级,作为时代发展的中流砥柱,每日从事着重体力劳动,体力消耗巨大,因而在粮食分配上有所倾斜,每月定量为32斤。而正处在成长关键期的大、中学生们,承载着国家的期望,为助力他们茁壮成长,同样给予32斤粮食的供应保障。这般不同群体间各有差异却又合情合理的粮食配给安排,印刻着岁月的痕迹,也从侧面让我更加懂得粮食的珍贵,将父母的教诲铭记于心。
那时的人非常纯朴,工作态度端正,正常上班时间很少请假办私事,晚上也经常加班,一般的小家庭有了小孩后,都需要请人带。听老一辈讲,那时大家都穷,小孩送出去带,口粮被克扣的情况也时有发生。
在我上幼儿园之前,也是白天请人带,晚上父母下班后接回家。据说父母从牙缝里省下的一点口粮,也或多或少存在上述的情况,并没有全部成为我的食物,所以我小时候营养不良。久而久之,父母有所发现,便另外找了一个自己没有幼儿的老大娘带我。
在这种情况下,父母有点好吃的,便尽量晚上下班了接我回家后,再拿出来喂我。那时全家供应的肉、白糖等,父母舍不得吃,都给我一个人吃。那时候没有电冰箱,天气炙热时怕肉坏了,又不放心带我的人喂,所以每次买来肉,就尽量一、两次喂完,经常造成消化不良,反而伤了肠胃。
还有一次,父母晚上加班开会,参加单位组织的学习。把我接回家时,已经深夜11点左右了,非常疲倦。当时我还小,不懂事,闹着肚子饿。那时烧火炉,为了节约煤,一般是早晨发火,晚上火早就灭了,母亲拿出一把干面,让父亲重新发火,但等把面下好,我又睡着了。那时买挂面要细粮票,父母自己坚持吃粗粮当顿,舍不得吃面,第二天早晨又热了给我吃了。
记得小时候,父母偶尔发了几毛钱加班费,就会在星期天带我们小孩子进城购物。那时的重庆城市规模比现在小得多,主要的商业中心和大商场都在两江环抱的渝中半岛的城里头。江北和南岸隔着长江和嘉陵江,当时江上没有桥梁,要进城必须乘坐轮渡过江。处于半岛西北部的沙坪坝要乘坐2路电车到上清寺才算进城。而同样处于半岛西南部的九龙坡杨家坪,也是先花1角4分钱乘坐3路电车,到终点站两路口下车,就算到了重庆城了。
父母一般带我们乘坐早班电车进城,在两路口下电车后,通常先步行到上清寺的“九园”餐厅去吃早餐,那里的八宝粥和小笼包子很有名。早餐后再换乘1路电车到解放碑。
到解放碑,基本上是以一上午的时间逛百货公司或五金商店等等,按事先的计划采购物品。这时候,父母经常会用糖票或点心票称几两水果糖或买一包糕点给我们,我们对他们要买的东西多半不感兴趣。父母办他们的正事,我们跟在后面吃零食,互不打扰。
中午,父母便带我们去吃重庆小吃“打顿牙祭”。印象中经常光顾的有解放碑的“颐之时”吃豆芽肉片汤;八一路的“吴抄手”去吃水煮抄手和锅贴饺子;到小什字的“老四川”吃灯影牛肉;还有“陆稿荐”的卤心舌和卤拱嘴;“正东”的担担面;“丘二馆”的炖鸡面;“小滨楼”的凉面和川北凉粉;“一四一”的老火锅等等。
我们小时候的重庆火锅吃法简单,几乎所有能吃的东西,像平时不太常用的食材比如毛肚、鸭肠、黄喉、郡花、脑花等等都能拿到火锅里面去烫,这些食材的腥味因为油厚和麻辣味重被压住,很有地方特色。那时吃火锅也不讲究,冬天戴着围巾吃,夏天光着膀子吃。
父母开始只让我们小孩子吃清汤火锅,稍大才吃又辣又麻的红汤火锅,每一次吃完,辣得我们满头大汗,大人便在火锅馆打一碗灏水(点豆花后的余水)来让我们喝,给我们降火解渴,巴适得很。
那时重庆小吃味道独特且价格相因,一般人也消费得起。即便如此,父母还是经常舍不得吃,看着小孩子吃,给我们吃顿好的补充营养,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而他们经常吃的是豆花饭,豆花饭经济实惠,既好吃又吃得饱。那些年在重庆,寻常百姓家常常以“推豆花”来招待客人,所以豆花也被称为“素肉”。
总之,品尝名特小吃成了我的一个习惯。后来习惯成自然,我因工作原因经常到全国各地出差,每到一地安顿下来后,第一件事便是外出寻觅当地的风味小吃和名胜古迹,想方设法品味一番美味佳肴和浏览风景名胜。
进城的下午时间则以休闲为主,或逛逛新华书店,或到七星岗、观音岩逛街,有时也到人民公园或少年宫游玩。然后开心地坐电车回家。
在我儿时的记忆里,父母极为重视节约粮食方面的教导。当我稍稍长大,懵懂间便能吟诵那首“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古诗,虽那时年幼,尚未能全然领会诗中深意,却也在日复一日的诵读里,知晓了粮食来之不易。
那时,供应给居民的粮票并非单一指向大米、白面这类精细食粮,玉米、饭豆、红苕等粗粮也被纳入城市口粮配给范畴,用以保障大家的基本饮食需求。大致的配给比例是,细粮占七成,粗粮占三成,力求均衡。众人不分彼此,手中所领的粮票也相应地细分为细粮票与粗粮票。而且,粗粮与细粮之间存有一定兑换规则,需五斤粗粮票方能换取一斤细粮票。
粗粮偶尔尝上几顿,权当换换口味,倒也还能接受,可要是长期以其作为主食顿顿食用,那粗粝的口感实在令人难以下咽。但单纯依靠细粮,又难以填饱一家人的肚子,于是父母只能在粗粮的精细烹饪上费心思、花功夫,变着法儿让家人吃得顺口些。
我的印象里,粮站里的粗粮是根据季节的变换而不断变化:有时供应的是玉米(俗称苞谷米),买来后父亲就带我们用背兜背到土坝子的九龙公社磨房去磨成苞谷粉。一般在早晨将苞谷粉烙成苞谷饼下稀饭咸菜;或是将苞谷粉加在大米中蒸成苞谷饭晚上吃;有时供应的是饭豆,母亲就煮饭豆稀饭与南瓜汤混合吃;有时是红苕,红苕不是一斤粗粮票买一斤,而是一斤粗粮票可买5斤红苕。母亲经常箜红苕饭或者煮红苕稀饭,我们小孩子最不喜欢吃红苕,印象中父母亲常常在红苕饭里专挑红苕,尽量多留一些米饭让孩子吃。
那时的小孩子普遍比较喜欢吃面。原因好像是平时油水少,下面要放猪油,加上油辣子、胡椒粉和葱花、大蒜等佐料,感觉特别香。父母于是买来干面,为我们两兄弟订了牛奶,早晨就给我们每人吃半磅牛奶,煮一个鸡蛋,再下一碗干面,而他们却经常吃玉米粥或煮红苕。
父母坚持勤俭持家,注重少花钱多办事。为弥补粮食的不足,经常采取经济实惠的办法,把粮食与蔬菜搭配,早晨煮江豆稀饭,中午箜四季豆饭,煮南瓜饭,土豆饭,晚上经常煮面块菜汤或用剩饭剩菜煮一锅烫饭一家人将就吃。
与粮票同时供应的还有油票和肉票,因为肉食定量,所以不像现在这样每天都可以吃肉的。父母便偶尔到自由市场买条鱼或称几斤黄鳝和鱼鳅,节假日则买只鸡或鸭,煲一锅当归、黄芪鸡汤,或酸萝卜老鸭汤,以弥补餐桌上荤菜的不足。母亲做的砂锅鱼头豆腐汤也是一绝,汤色奶白,清淡利口,味道特别鲜,我特别喜欢吃。
蔬菜水果虽然卖相差,但很少耍称,童叟无欺。稍大一点,我记得有时母亲带我上街买菜,几角钱的蔬菜,能装满两个菜篮,提都提不动。
那时我们楼上的邻居们,有很多是饮食公司各个餐厅的厨师或服务员,由于经常有附近生产队的菜农给他们送鸡鸭鱼和蔬菜,知道副食蔬菜的销售渠道,了解周边区县往往是半夜用船把鸡鸭鱼和蔬菜运到九龙坡黄家码头,然后在凌晨挑到蔬菜公司和供销社供应市民。所以,当有时令新鲜蔬菜上市时,左邻右舍的大人们常常聚在一起商量,统一意见后,便在半夜三更赶到河边,截住送菜菜农,用稍高于他们买给蔬菜公司和供销社的价格,收购一批新鲜蔬菜和土鸡土鸭,当几个菜农挑着箩筐送到后,人们便在公用厨房用大杆称来平分,欢声笑语,热闹非凡。父亲经常在分鸡鸭鱼和蔬菜时,主动把好的、大的让给邻居,孬的、小的留给自己。父亲的善良之举给我上了关于人性的最初一课。
那时大家煮饭炒菜烧的是煤炭。各家各户每个月都要买一次煤球(后来是蜂窝煤),挑煤的箩筐是几个邻居共同出资购买的,大家轮流共用。挑煤那天,往往早晨天不亮我就要起床,到杨家坪兴盛路的煤店帮父亲排轮子。买一次煤需要排两次轮子,一般父亲手持煤票排缴钱开票的那一队,我在制煤机房那边排挑煤的那一队,我这一队大家都是用箩筐排队,排轮子的人不停地移动自己的箩筐。一般情况下,要到中午,有时要到下午才能买到煤,父亲挑回家里再整整齐齐地码好备用,有时挑煤的人太多甚至要耽搁一天时间。
那时的工资水平差别不是很大,大家的收入比较平均。大人小孩穿的衣服裤子,很少买成品,一般棉被和棉袄先称回棉花,请走街串巷的匠人弹棉被;毛衣是买回毛线自己织;一家人穿的衣服,是大人们扯来布以后拿到裁缝铺量身定做,一般的棉织品比较便宜,但颜色品种非常单调。记得当年的确凉才上市时,因为结实耐磨、色彩鲜亮,又不要布票,大家蜂拥而至,居然把百货商场的柜台都挤垮了。
那时的人普遍节约,大都“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改革开放初期,父母买来缝纫机,自己扯布裁剪一家人的衣服,节约了不少的开支。
那时国家实行统购统销政策,城市居民几乎所有的生活用品都被纳入到全民所有制性质的配给体系,吃的穿的用的无一例外都在国营商店购买,所以排轮子司空见惯。每月领了工资,母亲便仔细地做出安排,我们小孩子也经常被父母差遣去排轮子购物。
那些年《户口簿》是公民的身份证,《购粮证》是居民的命根子,《购物证》和各种票证是购买吃穿杂物的通行证,这些都缺一不可。
每年底按街道的通知,凭户口簿领来厚厚一本一家人全年的各种票证,母亲便开始筹划一家人全年的生活。在开年后的第一个节日春节放假前,一般要用布票买来布料,给大人小孩做一身新衣服;在冬至前后,买肉做好腊肉香肠,挂在灶头上通风的地方,一年四季都可食用;还要用全年节约的肉票,买来边油,熬制一罐香喷喷的猪油供全年食用。
为了应对蔬菜淡季时经常缺菜,家家户户都时兴做咸菜和泡菜。那时的每个家庭,都有几个腌菜的陶缸和泡菜的坛子。每年冬春时节,大家按照祖先传下来的古老方法,用寻常的天然食材,通过洗、晒、晾、切、腌、泡等等程序,忙活好多天,做出各式各样的物美价廉的咸菜和泡菜,想方设法丰富日常的餐桌。
在这方面,母亲也是个行家里手。做得比较多的大众化品种是:将萝卜洗净、切丝、凉干做成萝卜线;将江豆洗净、晒干制成干江豆;买来青菜,菜叶做成水盐菜,菜头做成大头菜;买来胡豆和黄豆,用近似的程序分别做水胡豆办、豆食和豆腐乳;用辣椒、仔姜、江豆、萝卜等制成泡菜。母亲做的咸菜和泡菜,味道非常好,脆而不绵,辣而不燥,清香扑鼻,是我们一年到头餐桌上佐餐的美味佳肴。
每个年代都有它独特的历史烙印,那时虽然物资供应紧张,但实行公费医疗,很少听说如今相当普遍的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之类的富贵病。平时患感冒等头疼脑热的小病或受点磕磕碰碰小外伤,去医院一般花几分钱最多几角钱就能治好,多的费用由国家报销。那时实行义务教育,上中小学仅交点学杂费,学龄儿童都上得起学,也没有课外学习教材和校外培训班需要花冤枉钱。凡是国营单位就业的人,都会按政策受到组织的善待。工作调动服从分配,住房也按岗位性质和工龄长短由单位提供,虽然简陋但通水通电,租金也低得离谱。也没有听说过克扣工资的情况,到了发薪关饷的日子,微薄的薪水都能发到手里,从不拖欠,职工无后顾之忧,基本生活有保障。
回首往昔,那些旧时光里,童年的生活虽然清苦,却有着别样的安稳。那时候,餐桌上的饭菜虽简单质朴,可大自然馈赠的清新空气,是如今难以企及的滋养;身体虽还未长成,力气尚小,精神头儿却格外饱满,满心都是对生活的热忱与憧憬。工资水平普遍不高,好在物价亲民,柴米油盐维持在能接受的花销,物资虽称不上充裕,靠着各类票据的精细分配,倒也保障了一家老小的基本生计。
那时的市场上别有一番风味,摊位上摆放的尽是无农药、无激素、无添加剂的绿色果蔬,粮油也都是纯天然,吃得安心、放心,舌尖上萦绕的都是食物本真的味道。普通百姓的日子过得平实,大家的生活条件相差无几,没有悬殊的贫富差距,平等在日常点滴间尽显。工厂、单位就像温暖的大家庭,不存在压榨与剥削,兢兢业业工作,不必忧心失业的阴霾,同事间真诚交往,遇困难搭把手,彼此的情谊在互助中升温;邻里街坊更是亲近,一声问候、一个微笑,互敬互爱,鸡犬相闻间满是和睦。
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后,物资供应逐渐丰富了起来。到90年代中期,票证被取消。彼时年幼的我们还无法体悟那些年的生活压力,但我们的父母,那些勤劳善良的长辈们,用双手与汗水,精心呵护我们长大成人,让生活的希望在艰辛岁月里生根发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