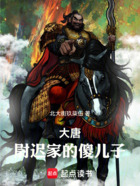
第25章 宵禁
唐朝的宵禁制度其实很严格,尤其是初唐时期。长安因为实行的是里坊制度,坊门是有专人看守的,如果过了时间,没有回到自己的坊市,那么你就需要自求多福了。
古人一般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唐朝外廓城的宵禁,一般是从傍晚时分开始敲闭门鼓,二更时分(晚9点到晚11点)各坊门就紧闭了。然后,冬夜五更三点,夏夜五更二点(古代将一夜分为五更,一更又分为五点),太极宫正门承天门的城楼上,第一声报晓鼓敲响,各条南北向大街上的鼓楼依次跟进。随着鼓声从长安由北及南,响起,皇宫的各大门、皇城的各大门和各个里坊的坊门,依次开启。
因为这一情况,导致长安城北贵南贱。参加朝会的大臣,必须拂晓前赶到太极殿,所以一般大臣府邸,都坐落在长安北城。
唐朝的左右金吾卫,就是来负责宵禁的执行和管理的。二更时分,是宵禁最严的时候,左右金吾卫会骑着马一队一队的到处巡逻抓人,还有处于暗处的武侯,也会抓人。过了二更,到了三更及以后时分,虽然宵禁仍然有效,但相对宽松。
《唐律疏议》上,明确记载着:“犯夜者,笞二十。”也就是违反宵禁的人,将会被鞭挞20下。当然,像碰到尉迟宝琪这类人,左右金吾卫和武侯,就会睁只眼闭只眼。但如果御史得知这一情况,那弹劾,就免不了了。
六街鼓歇行人绝,九衢茫茫空有月。说的便是唐朝宵禁后,长安城内的情况,长安宵禁后,整个长安显得空荡荡的,再配合着呼啸而过的金吾卫巡逻人员,便跟身处边境的军镇一般。
但你要是认为唐朝人没有夜生活了,那就大错特错了。唐朝宵禁,是禁止人在大街上停留,但在自己坊内,是可以行动的。坊内有很多的“苍蝇小馆”,完全能满足你的需求。
唐朝长安城,一年都是这样吗?不,有特殊的时候,就是上元节的时候。史载,“正月十五日夜,敕金吾弛禁,前后各一日以看灯。”,意思就是上元节的前后三天,宵禁制度松弛,人们可以整夜在城中游玩,整个长安便成了一座不夜城。这也是唐朝诗词中,一提到上元节,便往往会和夜色、夜景联系到一起的原因。
上元节的时候,约束了人们一整年的宵禁,放开了。人们爆发出极大的热情,寻亲唤友,一起领略这巍峨的长安城。
火树银花合,星桥铁锁开。暗尘随马去,明月逐人来。游伎皆秾李,行歌尽落梅。金吾不禁夜,玉漏莫相催。这首唐诗人苏味道,著名的《正月十五夜》,描述的便是唐朝上元节的盛景。
尉迟宝琪回到长安尉迟家府邸,洗漱完后,便躺下修息了。
这时,甘露殿殿内,张达正在朝长孙皇后汇报着,“东市酒楼,今日入账二万五千余贯,西市酒楼稍微差点,但也入账一万五千余贯。”
“怎么会这么多?以前这两座酒楼,一个月,也不会入账这么吧?四万贯呀。”
“是。老奴听泾阳县男说,我们之前的酒楼,做的……做的……”
“说。我到要听听从他嘴里,能吐出什么歪理。”
“诺。他说我们之前做的如更衣(古代屎的雅称)一般。臭不可闻。”张达说完,低着的头没听见其它声音,便大着胆子继续说道:“泾阳县男说,做酒楼,就是‘人无我有,人有我精’这样酒楼才能脱颖而出。而且,酒楼外等待入席的食客,也会让东市的其它食客,跟着想进入我们的酒楼。泾阳县男说,这是人们的‘从众心理’,就像只要有热闹,外面就会围着一群人一样。”
“还有,泾阳县男,说我们以前没有目标群体。像他这样,一开始便选定官宦子弟出身的国子监学子,是因为科考马上降临,长安很多人都在关注着他们,且他们有的身价不菲,还有就是他们年轻,能接受新鲜事物,‘玉液’酒原来只在大臣们的口中传播,但明天一定会名满长安。”
这时李二陛下从殿后,走了出来。示意张达不用行礼了,继续说。
“老奴听钱顺说,泾阳县男的那副上联,根本不是他喝了酒之后做的。泾阳县男之后喝了酒,老奴等他送完各家子弟,问过他。他说,那上联就是个噱头,为了多卖酒,搞出来的噱头。”
“噗呲。”长孙皇后看了一眼,脸色变差的李二陛下,赶紧将头扭到一边。李二陛下为什么已经过了子时了,还未休息?还不是从下午百骑那得知,尉迟宝琪以文会友,出了一个上联,“客上天然居,居然天上客。”李二陛下自诩也是“学富五车”之人,他便忍不住,想要对出下联。
当张达说出,自己想了一个晚上,没有想出下联的上联,是尉迟宝琪仅仅为了卖酒,而搞出的噱头后,他的心情能好,才是“真见鬼”。
等张达下去后,李二陛下已经恢复过来,他轻声、温柔的对长孙皇后说道:“观音婢,苦了你了。”李二陛下明白,现在这个锱铢必较的长孙皇后,是生生让自己逼的。李二陛下在军中威望为什么那么高?不仅是因为他确实能打胜仗,还因为他将赏赐全部给了麾下的将军和士兵,他还定期的给之前因跟随自己而受伤、牺牲的府兵家内,赏赐;而且他作为陇西李氏的大家长,还需要照顾族人;现在又有新的宫殿要建。这些大大小小的事,都是需要花钱的,而李二陛下仅朝廷的事,就让他忙的焦头烂额,所以后宫的大大小小事情,全部落在长孙皇后头上。
贞观初年,太极宫内放归了3000宫女,李二陛下令之“任求伉俪”。意思就是三千人宫女一起被遣送出宫,让其自行婚配,圣旨下达之日,朝野为之震动,宫女们及其亲人无不山呼万岁,视为旷古未有之善举。
“三千怨女放出宫,四百死囚来归狱。”贞观四年,全国判处死刑的囚犯只有9人。而到了贞观六年,死刑犯增至390人。这一年的岁末,唐太宗李世民准许他们回家办理后事,秋天再回来服刑。
由于经过隋末的动荡,全国人口锐减。李二陛下励精图治,是非常注重死刑的批复的。对于执行死刑的日期,李二陛下规定:阴雨天、下雪天不能杀,冬天春天夏天不能杀,只有在秋后才能对犯人执行死刑。每年秋后,在死刑犯即将命赴黄泉之前,他还会亲自去狱中看望死囚,凡喊冤的案件必须重审,这样,也就避免了许多冤假错案的产生。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贞观七年九月,390名囚犯全部回还,无一逃亡。刑部官员上奏李二陛下,李二陛下大喜,“并皆赦之”。这件事记录在《资治通鉴》的第197卷,“帝亲录系囚,见应死者,闵之,纵使归家,期以来秋来就死。仍敕天下死囚,皆纵遣,使至期来诣京师。”
李二陛下能光耀千古、名留史册,从这两件事上,可见一斑。
这两件事,就连身处现代的我们,也觉得是李二陛下做的确实是善举。但大文学家欧阳修他不同意,他曾写过一篇有名的史论文章《纵囚论》,他说,唐太宗释放囚犯的做法,有悖人情,违反法度,是沽名钓誉的一种手段。所谓“是可为天下之常法乎?不可为常者,其圣人之法乎?是以尧、舜、三王之治,必本于人情,不立异以为高,不逆情以干誉”。
其实欧阳修这么贬低这件事,我也能理解。北宋“崇文抑武”,他作为文坛领袖,是绝对不会让武将发展起来的,而“盛唐”的万邦来朝,是武将们灭突厥、灭吐谷浑、灭高句丽等等,生生打出来的。你说他怎么可能不抹黑李二陛下呢?
还有就是,欧阳修早年,被宋仁宗赵祯任命监修《新唐书》时,他是反对佛教的,甚至经常诽谤佛教。而在唐朝,佛教却是得到了大力发展,这也是为什么,《新唐书》内,一代高僧辩机,会成了一个淫僧。欧阳修在编撰《新唐书》时,完全是以个人之好恶替代历史的真相,是典型的夹带私货的表现。从他居然评价千古一帝李二陛下,是“中材庸主之常为”,便可见一斑。
而欧阳修晚年,他却开始崇佛了,他甚至皈依了佛门,潜心学佛参禅,因佛门戒律而屏却酒色,还自号“六一居士”,将自己书集取名为《居士集》。这个时期的他,开始修撰《新五代史》了,后周世宗柴荣的灭佛运动,被他一笔带过。而柴荣作为五代十国最英明的皇帝,他灭佛是因为此时的寺院拥有不需要缴纳各种税收、不需要服兵役和徭役等政策特权,而导致各地纷纷私立寺庙,大量的铜钱被铸成佛像,寺庙更是囤积了大量的土地,有些寺庙居然私藏犯人,给民间带来了极大的灾难。
柴荣灭佛,在佛教内部被称为“法难”。私立的三万余所佛教寺院被拆除,大量没有度牒的僧人还俗,大量的铜制佛像和祭祀器物,被柴荣下令铸钱,用以充实国库。柴荣也因此,和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北周武帝宇文邕、唐武宗李炎,一并被称为“三武一宗”。
如此重大的历史事件,欧阳修仅仅一句,“甲戌,大毁佛寺,禁民亲无侍养而为僧尼及私自度者。”便一笔带过。所以欧阳修文学家之名很大,但史学家之名,很少有人知道,他可是修撰了《新唐书》、《新五代史》等一系列史书的。
贞观初年,李二陛下修养生息,实行“仁”政,放出了3000宫女,但这也是他的无奈之举。宫中的内库,确实是没有多少积蓄了。
长孙皇后她的能力再怎么突出,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所以,长孙皇后是真的为李二陛下付出了很多。
第二天,尉迟宝琪迎着从东方天际喷薄而出的朝阳,在尉迟府内跑步。
等尉迟宝琪坐下吃早饭的时候,尉迟宝琳便神色匆匆的,进入到尉迟宝琪的小院。
“二郎,今天平康坊聚会,你也来呗?”尉迟宝琳刚走进大厅,便朝着坐在桌子旁矮凳上的尉迟宝琪说道。
“不去。我要去看着酒楼。”尉迟宝琪刚喝一口粥,被尉迟宝琳这突然的说话声,吓的差点呛着,于是他没好气的回答道。
“那酒楼昨天你不是已经告诉他们怎么做了吗?你还用一直看着?你要学会用人呀。”
“大兄。你说这么多,到底是什么原因让我去平康坊?以前你可不是这样。”
一听这话,尉迟宝琳就知道,自己急了,应该先和宝琪聊会儿天,再将自己真实意图说出,得,自己又被自家二郎上了一课。
他便“破罐子破摔”道:“平康坊南曲有位都知,众人都入门不得,所以……”
“不去,我的诗都是有感而发。”尉迟宝琪说得理(臭)直(不)气(要)壮(脸)。“还有,我有那么大名气吗?这时间的平康坊都知,不是非‘蟾宫折桂’者,不可入吗?”
尉迟宝琳看着一脸疑惑,问出这问题的尉迟宝琪,不由无语,真是“旱的旱死、涝的涝死”,自己还在为出文名而努力,而尉迟宝琪这位名满长安的却不知道自己到底闯下了多大名声。尉迟宝琪在国子监的言论,经过虞世南润色后,那是极为出彩,尉迟敬德得到虞世南的手稿后,可是专门大开祠堂,在祠堂内待了良久。
于是尉迟宝琳将长安城内对尉迟宝琪的评价一一说出。尉迟宝琪越听越惊讶,不是,我本来想“初啼黄莺试新声”,怎么到了最后,反而成了“一石激起千层浪”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