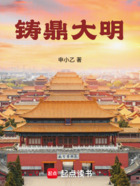
第145章 收集资料
在冯校长走后这段时间,周显庸也没闲着,跑到宫里,先是把他要办报纸,劝说冯无畏那一套,和太子和二皇子又事无巨细全说了一遍,等他们兴趣全上来后,又鼓动起两位皇子,和他一起,到典籍馆里,找来大明所有的律例,觉的非常重要的全部誊抄下来。又把近百年来颁行的政令,按时间、事件的顺序整理出来。
通过这次整理政令、律法,太子反倒比周显庸学到更多知识,总结了更多经验。
太子已经十三岁,进入半参政状态,虽然这两三年,皇上对太子横挑鼻子竖挑眼,三不五时给点难堪,挤兑一下,但始终没有明确表示想要废太子的意图,时间久了,太子反倒没有起初那么惊惧。他总结出一点,只要脸皮厚,少说话,多听,多总结,自己心里有数即可。
故这次在誊抄这些政令、律法时,他只是把自己不认同或者存疑的全部抄下来,打算有机会请教太师或者他认为可以完整解读的人。太子不再像过去那么鲁莽,贸然把自己认为不妥的观点直接上奏皇上,而是先记下,然后翻阅其他朝代有关这方面的条例,然后先行对比、思考,综合估量,如果仍有不懂,再去请教老师,老师不能给出合理或者让他信服的解释,他就先存疑。
太子不急,他还太年轻,知道许多人解决许多事出于理智考量,但还有出于情绪操控,没有什么事必须有对错和选择!法家讲对错容易矫枉过;儒家讲中庸容易包容烂疮;道家讲无为而治容易泥沙俱下失去重心。
没有谁的理论比别家更高深,有的只是所站的立场所处的角度所求所期许,求仁得戾,求同各异,大家不过都在尽可能地用自己理解的最佳方式表达自己!那他又有什么权利去对父皇的行为失望什么?他现在应该做的难道不是一个明辨一个积累吗?
太子朱见深在这为期十多天的典籍整理过程中,豁然开朗!
周显庸不知道太子千回百转的心思,他只是努力小心地在办他的报纸时候,尽量摘抄一些皇帝愿意推广到天下黔首中的政令与律法条文,他现在的嘴还没长出来,不能说,只能如同蚂蚁一般一个个掏洞打穴,而这些洞穴都是大人物眼里几乎看不到的,这就足够了。
继续花几天功夫搜集了三期科举真题,并简单摘录了几位当世理学名家和大儒们对真题的简单诠释。
周显庸觉得头几期报纸的第一、二版面基本搞定,接下来的一些民间百科和有关农、商、技术类的小窍门小方法,他都传达给了那名招聘来的编辑,让他去搜集有关内容。剩下的版面除了小说连载就剩下诗词鉴赏了,诗词鉴赏是冯校长的专栏,他既不擅长又不懂品鉴。
周显庸不确定冯无畏能不能顺利找到罗贯中,他觉得自己还得做两手准备,万一找不到罗贯中,得不到他的手稿,他还能连载哪一部集影响力和趣味性于一体的小说,水浒肯定不行,思想太叛逆,连载这个哪天皇帝一个不开心,不光封了他报馆,轻者他被训斥一顿,重者收监甚至掉脑袋。
他这命老值钱了,从现代幸福的家庭中,不可逆转地被推入到中国封建历史上最为黑暗的白色恐怖年代,他与现代年轻人的主流思想有所隔阂,在二十一世纪青年人均龙傲天,我命由我不由天的时代,他信奉宿命感,这大概是他之所以跟随大学同学在内蒙古那达慕大会上,骑马坠亡,突然穿越到这里的原因所在。
于是他坚信自己能为这个时代做点什么,能成就一个独特的完全释放自己意志和思想的“独我”。他谨小慎微甚至憋屈窝囊地在时代的夹缝里拼命拓宽人们的生存空间。他一直在参与,没有袖手旁观,任由这个时代的缔造者们,集体驾驭一列脱轨的火车,无限驰进不可逆转的万丈深渊,他做了那个钣道工。
周显庸不知道为什么这些生硬的政令能让他感怀良多,在这个春花开到荼靡的午后,他带着这种亦喜亦忧的心情收到了朱骁的第二封信。
朱骁每到一个新地方就会给他写一封信,这封信是告诉周显庸,他已经从天津启程准备下一站到应天府。
朱骁从正月离开京城到现在,过去了两个半月时间,这封信是半个月前写的,到他收到这封信的时候,估计朱骁已经到了应天府。他详细介绍了在天津设计站点的过程,没什么难度,就是琐碎,他在天津待了足足五十天,才把一切搞定。
周显庸还是比较欣慰的,天津不是一个太平的地方,各种民间势力交错复杂,需要花大把时间理顺这些关系,达到一个相对平衡的位置,对于原来没有任何经验的朱骁,确实应该算很大一个挑战。他用了五十天时间,和官府、商户、地方势力疏通好关系,站住脚,招募了驻站点的人员,已经很不错了。
以后随着经验逐渐丰富,周显庸能预料到他会越来越得心应手。
这两个来月,来自商会的成员越来越多地搭乘周显庸的船南下考察市场,已经达到每十天返航的船上,都会有三到四个商户代表,有北京的、有山西的、陕西的、北直隶的,开封府的。
几乎每一位过来拜会侯爷请求跟船出行的商户,都会给帝国理工大学捐一千两银子,以至于似乎这是个心照不宣、约定俗成的惯例了。
周显庸都会让学堂新招聘的专门负责财务的人员,每一笔都清楚地记录在册。他和这些捐款的人彼此都心知肚明,单单只是搭船南下一两个商人去南方,哪怕包趟专门的小船出行,来回十遍都用不了这么多银子。
大家为的不是买路费,为的是买通与侯爷的关系,为的是买通将来商路上一路平安保驾护航的一个招牌。甚而至于打通与皇上那里的直接通道,有机会晋升为皇商的第一步。于此来说,这一千两银子太值了,体面地捐助,落个善人的好名声,快乐地接受,把学堂真正的经济负担转移到社会中去,周显庸何乐不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