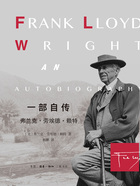
Sunday
星期天
星期天,是对刚刚过去的六天里“汗水,更多汗水”的救赎。
家族的小教堂里,舅舅们、姨妈们、他们的妻子或者丈夫们,有些头发花白,有些满头银发,在围着布道坛为他们摆好的老式摇椅上坐下。那本紫色布面的家族《圣经》摆在讲台上。星期天的布道坛通常会被孩子们采来的野花盖满。
当然,城里来的小“帮工”也坐在下面。
有时候,附近的农户们也加入进来。
每逢詹金舅舅布道,人们不再吝惜宝贵的泪水。伴随着摇椅的轻轻晃动,泪水悄然涌满他们的眼眶,又顺着面颊悄然流淌。全家人都随着詹金舅舅的布道而情绪激昂,正如他们听到超验主义的经典或者孩子们的歌声那样。所有人都笔直地站起,满怀尊严和信仰齐声歌唱他们心爱的诗篇:“自从时间肇始,我们看到人类一步步坚定地向前。”[42]这时候,城里来的少年又一次看到泪水。他目送着真声和假声混合的歌声在屋顶下萦绕,然后飞出窗外,消失在远处的山林间。他们真诚地拜服在宗教的激情之中。他们心中挚爱的诗篇化作歌声,让所有人眼中都涌满泪水。
托马斯舅舅是家族中的诗人。他在小教堂旁边栽下了一丛杉树,为日后星期天的家族野餐投下阴凉。
木瓦墙面的小教堂有一个别致的钟塔。小教堂东边的家族墓园里,有一座朴素的白色大理石方尖墓碑。碑身上用威尔士语刻着“Ein Tad”(父亲)和“Ein Mam”(母亲)。
围绕着修长的方尖墓碑,是家族其他成员的坟墓。
在那几个春天和夏天的每一个星期天里(直到九月五日之前),这个少年都会穿上他城里的衣服,端坐在小教堂里的一把椅子上。
装饰布道坛是他的职责。
星期天的早晨还透着几分凉意,几个表弟跟着他,按照他的筹划去采摘原料。大路两旁的花草树木让人眼花缭乱,只要一伸手就能摘到。他们跑几步,停一停,再跑几步,停一停,直到马车上堆起一座小山。
星期天的布道坛和讲台披上了优雅的盛装。一簇簇鲜花和枝叶被自由地混杂摆放着,就像它们在阳光下的模样,只不过更自然一些。
岁月流逝,小教堂一直得到精心的修葺维护。托马斯舅舅种下的杉树葱郁繁茂,已经快要将它遮住。每当树下摆开一排松木长桌,就是大家族聚餐的时候。劳埃德-琼斯家的十个兄弟姐妹,加上各自的妻子和丈夫,一共十八个人。再加上他们的孩子,一共四十个人。算上附近的邻居和帮工,大约七十五个人。假如有特殊的场合,比如詹金舅舅布道,或者是婚礼、葬礼、露营聚会,那就更加热闹,住在远近乡间的人都会聚在这里。
山谷里的这个小部落聚在朴素的小教堂里,膜拜他们饱含对上帝的爱创造出来的圣像。反过来,上帝在他们自己的想象中影响着大家的生活。这些欢快的宗教聚会其实是家族部落的欢聚。
仲夏季节来访的牧师客人们,让这些聚会变成真正的神学狂欢。威廉·甘尼特、亨利·西蒙斯、桑德兰德[43],还有从芝加哥来的托马斯博士,都是家里喜欢邀请的贵客。这些牧师通常利用假期来访,迎接他们的将是露营聚会、野餐和生日宴会。
托马斯舅舅总是以他一贯轻柔低沉的嗓音,召集大家野餐。
“来吧,姑娘们,”他对妹妹们说,“咱们去野餐吧。根本不用费心,带上一些格雷姆面包、一点儿奶酪和一罐子牛奶就可以了——大伙儿都去。”
大家纷纷开始准备。孩子们全都被叫来帮忙。不一会儿,“格雷姆面包、一点儿奶酪和一罐子牛奶”就扩充成了烤猪肉和烤火鸡。还有包着叶子烤的新鲜玉米、填了料的烤鸡、煎鸡排、煮火腿、煮鸡蛋、甜面包圈、玉米饼、饼干、黑面包和黄油、新鲜的番茄和黄瓜。整根黄瓜削了皮,拿在手里像香蕉一样,蘸一点儿盐吃。各种三明治和泡菜、青苹果做的馅饼和南瓜饼、绿奶酪、蜂蜜和高粱糖饴。还有从草莓到西瓜皮的各种蜜饯,和自家秘制的五花八门的腌菜。也少不了各家拿手的糖霜蛋糕或者素蛋糕、点心和姜糖饼。枝头多的是李子和野莓子,任你随手摘来。牛奶放在泉水里冰镇,咖啡用野餐时点起的火堆现煮。凡是劳埃德-琼斯家的人能够想到的美食应有尽有,丰盛无比。
毫无疑问,埃及法老的盛宴也难以与之媲美。
所有这些都塞进几个篮子里,然后各家带着自家的篮子和孩子们,穿上特意准备的衣服坐上马车。第一辆准备停当的马车会等待其他马车,然后庞大的队伍一起出发。料想古时候为某个先知——甚至摩西本人——送葬的队伍也不过如此。
而这只是劳埃德-琼斯家的一次野餐。
野餐选择的地点,通常是树荫下一片凉爽的绿草地,能靠近一条溪水或者一股泉水更好。铺起颜色亮丽的野餐布,将准备好的一切琳琅满目地摆开,孩子们在树下装好的秋千上玩耍。享用完美味之后,孩子们唱歌或者朗诵。城里少年的父亲拉起小提琴,为舅舅和姨妈们领唱他们熟悉的歌曲。长者中有人唱起他们儿时在威尔士唱过的歌,重现故乡古老的节日场面。“现代”的城里少年为大家朗诵《单驾马车》[44]和《戴瑞斯和他的飞行器》[45]。无论是成年人还是孩子,每个人或者朗诵,或者唱歌,都要有所表现。除了詹金舅舅的讲道,齐唱赞美诗无疑是一整天活动的高潮。所有人都加入合唱,那一刻他们洒落的是最热诚的泪水。
远处传来另一种音乐,那是雇工小伙子们在溪水旁一边走一边吹着口琴和口弦,雇工姑娘们陪在他们身边。他们不像劳埃德-琼斯家那样懂得享受布道和唱赞美诗的快乐。
理查德·劳埃德-琼斯的儿女们,在他们父亲的山谷里,像这个威尔士拓荒者希望的那样生活着。这个大家族拥有自己的教堂、自己的磨坊(约翰舅舅的)。山谷里的每一寸土地,都留下了他们耕种和放牧的印迹。
劳埃德-琼斯家族的生活,在幸福和坎坷中向前流淌。
从十一岁起的连续五个春天和夏天,这个少年都是在山谷里度过的。每年的九月,他回到麦迪逊那座湖畔的小木屋里,回到母亲、父亲、简和麦琪奈尔身边,在城市里度过秋天和冬天。
麦迪逊是一座美丽的城市。门多塔湖和莫诺纳湖这两片蔚蓝的水面,夹着一座平缓的小山丘。无论远处或近处,都能看到山丘上州议会大厦白色的穹顶在阳光下闪亮。另外两个小一些也不那么清澈的湖——温格拉湖和沃柏萨湖——陪护在山丘的一侧。
威斯康星大学坐落在市郊属于它自己的小山丘上。组成校园的是一群面孔模糊、毫无特征的建筑。
山顶上也有一座金色的穹顶。
这两座穹顶的性命,都是向米开朗琪罗借债的结果。正如众人所见,它们尽力而为,没有辱没前辈大师的声誉。几年后,这个年轻的学生将会目睹两座穹顶的毁灭。由于世人犯下的过错,时间这位债主(并非米开朗琪罗)剥夺了它们赎回性命的权利。
麦迪逊的城市格局像一个车轮,主干道是从议会大厦辐射出的八根辐条。其中一根辐条直通到大学的穹顶下面。
麦迪逊是一座具有自我意识的城市,但是它却比绝大多数村庄更为闭塞。大学给城市带来一股学者精英的氛围,可惜这种过度教育的氛围远远超出了这座城市的接受能力。
城里有零星几座不错的住宅散落在湖边——相对那个时代而言。维拉斯[46]家的住宅是其中最好的。除此之外,这座城市只是威斯康星州五千个村庄中最普通的一个,仅仅是规模大了一些。
知识阶层理所当然地统治着麦迪逊。那所大学是一枚徽章,象征着他们短暂的权威。一年一度,雄心勃勃的立法者们从全州的各个市镇云集于此,为了留下不朽的功业而制定一些法律,更多的“法律”。然后,云散回到各自的角落。
那座巍峨的议会大厦夺去了大学的荣耀。
“市民与大学”的较量始终存在,但是从未激化到引来众人的关注。
井底之蛙式的尊重才智,给这座城市箍上了一层自视颇高的外壳,幸而有大大小小的几面湖水,它和它的居民才得以在极端的沉闷中稍作喘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