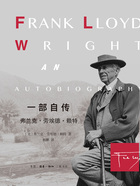
Truth against the world
与世界对立的真理
韦茅斯的这个牧师职位日渐不济。父亲原本是一个浸礼会[30]教徒,然而在他与母亲相识的地方,那里却信仰唯一神派,空气中弥漫着唯一神派的气息。在家里,母亲奉行着比浸礼会更丰富多彩的唯一神派教义。最终,父亲辞掉了韦茅斯的职位,成了唯一神派的又一个信徒。
对于母亲而言,她早已习惯了昂首阔步地走在自由的乡间。如今,却被一丝不苟的正义包围着,必须小心地恪守她作为牧师妻子的身份。狭隘的浸礼会缩在“神圣”的硬壳里,滋生出种种卑鄙和龌龊。几乎每一次“捐献餐会”都导致她与丈夫争辩,要不要回家——“去西部”?
牧师的报酬少得可怜,倒也适合让家里实现教义中清贫的生活理想,保持不容异议的完美无瑕。
劳埃德-琼斯家信奉的唯一神派,蕴含着更博大的内容。在当时混乱纷纭的教义解说中,它宣扬生活是上天所赐的礼物,只有一个至上全能的主宰,世间万物都因“他”而合为一体。
“统一”是他们的咒语。万物的统一!这正是母亲始终追求的理想。然而,对立的善恶依旧困扰着母亲和她的亲人们。当他们把万物统一的准则用于身边的生活,古老的善恶观念总是带给他们困惑和挫折。但是,他们的信仰没有失掉盐的滋味,他们怀有追求真理的热情。真理将拨开迷雾——“与世界对立的真理”。真理所蕴含的美!这足以让任何一个家族不得安宁。劳埃德-琼斯家的人,对美所蕴含的真理感到陌生。这些住在山谷里的人惧怕美,视之为疏忽的脚步可能会踏进的陷阱。美,会让他们在雪地里走出笔直的脚印,在年少轻狂的心中失去威信。
安娜姐姐和她的“牧师”捎回老家山谷里的超验主义,影响着劳埃德-琼斯家唯一神派的信念。他们逐渐认识了康科德[31]那一群内心敏感的思想者:惠蒂埃、洛厄尔、朗费罗,还有爱默生[32]。梭罗[33]?对他们而言,梭罗似乎过于聪明,让他们感到不舒服。
诗意的超验主义[34]思想,与他们对万物更博大、更坚定的敏感融合在一起,结出了可见的果实。
劳埃德-琼斯家的奢侈品不是笑声,而是泪水。
只有让他们眼含泪水的那一刻,你才真正感动了他们。
他们敏锐地体会人世间的渴求、悲伤和苦难。人世间高尚的行为总是令他们激动。在韦茅斯这间冰冷破败的小屋里,牧师家的生活日益穷困潦倒。若不是母亲有她的孩子们,父亲有他的音乐,这个家庭早已崩溃。虚弱瘦小的麦琪奈尔降生在这段艰难的日子里。她出生后的头几个月里,母亲把她放在枕头上,连着几个小时给她做抚触按摩,独自一人悉心地照料她。母亲把自己身体里的活力注入了这个小生命。
小女儿的到来,给牧师的肩头又添了一份负担。
母亲的寄托何在?在家里教育她的儿子,繁忙的家务之余一起摆弄那些“礼物”。还有给山谷里的老家写信和寄书,捎去康科德的超验主义:钱宁[35]、爱默生和西奥多·帕克[36]写的书。是的,还有梭罗。
父亲生活的支柱呢?是那些来波士顿演出的音乐家。其中有一个长得像帕格尼尼的意大利音乐家,还有鼻子和眼睛都生得诡异的雷梅尼[37]。搬到麦迪逊之后,吸引他的是风度翩翩的奥勒·布尔[38]。当然,他总是可以在空荡无人的教堂里求助于他的管风琴。
终于,牧师父亲和教师母亲回到了西部。在离老家的山谷大约四十英里的麦迪逊市,门多塔湖畔一幢朴素的房子是他们的新家。此时,儿子的教育成了当务之急。
将要挽救这个孩子的,不是聆听智者在讲坛上诵读“上帝的教诲”,而恰恰是远离那些被人自作主张地当作真理写成的圣书。他将在自然界的每一种生命、每一次呼吸之中,领悟“花必凋残,草必枯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