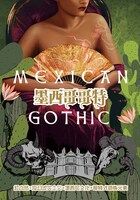
第3章
娜奥米还是个小女孩时,卡塔莉娜曾给她读过一些童话故事,它们常常会提起“森林”,在那里,汉塞尔和葛丽特撒下面包屑,小红帽遇到大灰狼。但娜奥米在大城市里居住,因此很久之后她才意识到,森林其实是真实存在的,在地图上就能找得到。她的家人在韦拉克鲁斯度假时,住的也是她祖母的海边别墅,看不到高大的树木。甚至到她长大成人之后,森林在她的脑海中的印象依然是她孩提时在故事书里瞥见的一张画,它有着木炭笔画的轮廓,明亮的色彩洒在画面正中。
因此,此时她花了好一阵才意识到自己正在进入一座森林,这是因为埃尔特里温弗就位于陡峭的高山之间,山上满是五彩斑斓的野花和浓密的松树和橡树。娜奥米看到绵羊慢悠悠地四处乱转,山羊勇敢地冲向岩墙,而后转向。银矿给了这片地区财富,但还需要从这些动物身上提取的油脂来照亮矿坑,并且它们的数量众多。一切看来十分美好。
不过,当火车往更高处去,越接近埃尔特里温弗,这些田园牧歌式的风景便改变得越多,娜奥米也改变了对它的看法。土地上满是深深的沟壑,崎岖的山脊在车窗外若隐若现。原本迷人的小溪变成了汹涌而喷薄的大河,任何落入洪流的人,都注定在劫难逃。山脚下的农民们照料的是果园和苜蓿田,但到这里后再没有任何这样的作物,只有山羊在岩间上下跳跃。土地将它的财富隐匿在黑暗之中,没有任何果树能生根发芽。
随着火车一路奋力攀登,空气逐渐稀薄,直到最后,火车突突作响地停了下来。
娜奥米抓起她的手提箱。她带了两只箱子,本来还打算带上她最喜欢的那只行李箱,不过最后还是认为它太笨重了。尽管做出了这样的让步,她随身携带的手提箱也依然很大很沉。
火车站并不繁忙,甚至很难被称为车站,不过是一座孤零零的方形建筑,以及一个在售票处后半睡半醒的女人。三个小男孩绕着这座车站你追我赶,玩着捉人游戏,她给了他们几枚硬币,让他们帮她把手提箱拖到车站外。他们愉快地照做了。他们看起来营养不良,如今矿场已经关闭,仅有山羊能提供些许贸易的机会,她不知道这座镇子上的居民要如何维生。
娜奥米为山间的严寒做好了准备,因此那天下午迎接她的薄雾便成了意料之外的元素。她好奇地看着这场雾,调整了她那顶装饰着黄色长羽毛的蓝绿色无边圆顶帽,又看向街上那辆接她的车。她几乎不可能认错,因为车站前只停了一辆汽车。那是一辆大得荒唐的车,让她想起二三十年前流行的默片明星——就是那种她的父亲年轻时可能会开出来炫耀财富的老式轿车。
但她面前的这辆汽车肮脏陈旧,需要重新上漆,因此并不真是当年的电影明星开过的汽车,而更像是遗物,曾被随意地丢弃积灰,如今又被拖回街上。
她本以为司机应该和这辆车一个样,原想方向盘后或许是个老头,结果车上走下来的却是个和她差不多年纪的年轻人。他身穿灯芯绒外套,发色很浅,皮肤苍白——她从未见过任何人能苍白到这种程度;天哪,他是从没在阳光下散过步吗?——他的双眼游移不定,他的嘴竭力挤出了微笑或致意的表情。
娜奥米给替她拖行李的男孩付了钱,向前走出几步,伸出一只手。
“我是娜奥米·塔波阿达,是多伊尔先生派你来的吗?”她问。
“是的,霍华德叔祖父让我来接你,”他回答道,有气无力地与她握了一下手,“我是弗朗西斯。旅途可还愉快?这都是你的东西吗,塔波阿达小姐?要我帮忙搬它们吗?”他迅速问出一连串问题,给人的感觉就像他更喜欢让所有句子都以问号结束,而不是说出明确的陈述句。
“你可以叫我娜奥米,塔波阿达小姐这叫法听起来太讲究了。这里就是我的所有行李,另外,没错,我很乐意有人帮我。”
他提起她的两只手提箱,将它们放上后备箱,接着绕过车子,替她开了门。透过前窗她看到这座镇子上满是蜿蜒的街道,有窗口摆着花钵的彩色屋子,一扇扇坚实的木门,长长的阶梯,一座教堂,以及在任何一本旅游指南里通常都会被评价为“古雅”的一切细节。
尽管如此,可以肯定的是,埃尔特里温弗不在任何一本旅游指南里。空气中有一股衰败之地的霉味。屋子是彩色的,没错,但色彩已从绝大部分墙上剥落,一些大门上有污损,花钵中的花朵一半已经枯萎,整个镇子鲜有人活动的迹象。
这倒没什么不同寻常。独立战争爆发后,不少在过去殖民时期采集金银的兴旺矿区立刻停止了活动。后来,在平静的波菲里奥时期,英国人和法国人受到欢迎,他们的口袋都因丰富的矿产而鼓胀。但革命结束了这第二次繁荣[1]。在不少埃尔特里温弗这样的小村里,你都可以瞥见钱财与人口富集时建造的精美小礼拜堂,但在这样的地方,大地母亲的子宫再也不会流溢出财富。
然而在其他许多人早已离开的时候,多伊尔家还徘徊在这片土地上。她想,或许他们已经学会了如何去爱它,尽管它没能给她留下多少好印象,因为这不过就只是一片陡峭而唐突的风景罢了。它看起来不像她童年故事书中的任何一座高山,在那些书里,树木似乎都很可爱,花朵会在路边生长;它也与卡塔莉娜描述中的她即将生活的迷人地方全然不同。就像那辆来接娜奥米的老爷车,这座镇子紧紧攥住不放的是往日荣光的渣滓。
弗朗西斯沿着一条狭窄的道路向群山更深处攀登,空气变得更为粗粝,雾气则更为浓厚。她搓了搓双手。
“还很远吗?”她问。
他又露出了不确定的表情。“也没有那么远,”弗朗西斯慢慢说道,语气仿佛在讨论一桩需要慎重考量的重大事务,“路不好,不然我还能开得再快点儿。以前挺好的,很早以前,当时矿场还开着,这附近的路都状况良好,就是在上高地附近也一样。”
“上高地?”
“那是我们的叫法,就是指我们住的屋子。我们家屋子后面,是英国公墓。”
“真的很英国风吗?”她说着,露出微笑。
“是的。”他说话的同时双手紧握方向盘,他握手时有气无力,她很难想象他究竟是从哪儿来的这股力气。
“哦?”她等待着下文。
“你会亲眼看到的。一切都很英国风。嗯,这就是霍华德叔祖父想要的,一小片英国的飞地。他甚至还把欧洲的泥土带到这儿来。”
“你觉得他有很强烈的乡愁?”
“没错。我还可以告诉你,我们在上高地不说西班牙语。我的伯公一个西班牙字也不识,弗吉尔只会一点,我的母亲则完全拼不出完整的句子。你……你的英语好吗?”
“从六岁开始每天上课,”她说着,从西班牙语换到了英语,“我相信自己没问题。”
树林更为浓密,它们的枝丫下阴暗沉郁。她不是个热爱自然的人,至少不爱真正的自然。上一次她到勉强算是森林的地方,还是在一场去洛斯莱昂斯狮子沙漠的短途旅行中,当时他们骑着马,她的哥哥和她的朋友们想拿锡铁罐练习射击。那已经是两年前,或许是三年前的事了。这地方与那儿完全不能比。这里要更蛮荒得多。
她发现自己警惕地估算着树木的高度和峡谷的深度。二者都相当可观。迷雾浓重,这让她有些畏惧,唯恐他们转错了弯儿,便会半途落下山里。有多少热切地掘取金银的矿工曾摔下悬崖?群山提供矿产财富,也提供利落的死亡。不过弗朗西斯似乎对自己的开车技术很有信心,尽管他说话时有些支支吾吾。总体来说,她不喜欢害羞的男人——他们让她心烦——但这有什么关系呢。她既不是来见他,也不是来见这个家族里的任何一名其他成员的。
“总之,你是谁?”她想让自己的思绪从这峡谷以及汽车可能会撞上看不见的树木上移开,便问道。
“弗朗西斯。”
“好吧,是,但你是弗吉尔的侄子吗?他是你失散已久的叔叔?又一个我得了解的家族败类?”
她用了她喜欢的取笑口气,那是她在鸡尾酒会上常用的,它似乎总能让她与人拉近关系,正如她所料,他回答时,脸上就带了一点点微笑。
“我和他差一辈,他是我的堂舅舅。他的年纪比我稍大一点。”
“我从来弄不明白这一套。一辈,两辈,三辈。到底是谁一直在记录这样的事?我始终觉得,会来参加我生日会的人一定是我的亲戚,就这样,根本不需要掏出家谱。”
“那一定很方便。”他说。此时他的微笑开始发自内心了。
“你算是好堂兄吗?我小时候可恨我的堂兄弟了。他们老在我的生日会上把我的脑袋按进蛋糕里,即使我根本就不想接受贿赂。”
“贿赂?”
“对。本来在切蛋糕之前,你能先拿到一小块的,但总有人会把你的脑袋推进蛋糕里。我猜你们在上高地不用忍受这种事。”
“上高地没办过多少舞会。”
“那儿一定地如其名。”她喃喃道,因为他们还在继续向上。这条路是没有尽头吗?车轮嘎吱嘎吱地碾过了一根又一根倒在地上的树杈。
“是的。”
“我还从没进过任何一栋有自己名字的屋子。如今还有谁会这么做?”
“我们比较传统。”他咕哝道。
娜奥米怀疑地看了这个年轻人一眼。她的母亲会说他需要补铁,还得好好吃肉。从他那细瘦的手指看,他就像是靠吃露水和花蜜过活的,他说话的声音也总是轻如耳语。在她的印象里,弗吉尔看起来比这个小伙子健康许多,也更现代。另外,正如弗朗西斯所说,弗吉尔的年纪更大。他三十好几了,但她忘了他的确切年龄。
他们撞上了路中间的一块石头,要不就是别的什么隆起的东西。娜奥米发出了一声不快的“哎哟”。
“抱歉。”弗朗西斯说道。
“我觉得这不是你的错。这里一直这样吗?”她问,“感觉就像在装满牛奶的碗里开车。”
“这算不上什么。”他说着咯咯笑了一声。好吧,至少他现在放松下来了。
接着,突然之间,他们到了,进入一片空地,那座屋子从迷雾之中蹦了出来,展开渴望的双臂迎接了他们。这实在是个古怪的地方!它看起来完全像是一座维多利亚时代的建筑,破碎的木瓦,煞费苦心的装饰,肮脏的凸窗。她从未亲眼见过这样的东西,它与她家时髦的大宅、她朋友的公寓,或是有着红色特宗特尔岩石[2]外立面的殖民时代房屋都截然不同。
这座屋子在他们头顶耸然出现,仿佛一只巨大而沉静的石像鬼。它原本可能会是个不祥之兆,让人想起鬼魂和闹鬼之地,但实际上它看起来却如此疲惫,几扇百叶窗缺了百叶,当他们踏上通往大门的阶梯时,乌木门廊嘎吱作响。大门上装有一个银质门环,它的形状如同挂在圈上的拳头。
这就是个废弃了的蜗牛壳,她心里想着。说到蜗牛,她联想到了童年时在院子里玩耍的事,她会将一盆盆植物搬开,看着那些胖乎乎的软体动物匆忙蠕动,四处躲藏。她会不顾母亲的警告,拿方糖喂蚂蚁。还有那只温和的虎斑猫,它总是睡在九重葛下,任孩子们抚摸个不停。但她没法想象他们在这座屋子里养猫的情景,就算是她平时会在晨间喂食的金丝雀也不会在笼子里愉快地啁鸣。
弗朗西斯拿出一把钥匙,打开了沉重的大门。娜奥米走进门厅,一眼看到一道由桃花心木和橡木建成的巨大楼梯,还有二楼楼梯平台上的一扇圆形彩色玻璃窗。那扇窗子往一块褪色的绿色地毯上投下红、蓝、黄的阴影,两座宁芙仙女的雕像静静地守着这座屋子,一座摆在这螺旋楼梯底部的中柱旁,另一座则位于窗边。入口墙上曾经悬挂过一张画,或是一面镜子,墙纸上仍然能看出它的椭圆形轮廓,就像一个残留在犯罪现场的孤零零的指纹。他们头顶上悬挂着一盏九臂枝形吊灯,它的水晶已因为年代久远而浑浊。
一个女人从楼梯上走了下来,她的左手滑下栏杆。她有些许白发,不过不算上了年纪,她那笔直的脊梁和敏捷的身姿不属于年迈之人。但她的穿着又很严肃,双目中带有严厉的神色,这给她增添了几分不属于她这个年纪的老气。
“母亲,这位是娜奥米·塔波阿达。”弗朗西斯说着,拿起娜奥米的手提箱走上楼梯。
娜奥米跟着他,面带微笑向这位女性伸出手,后者看着她的表情就像她手里拿着一条死了一个礼拜的鱼。女人没有与她握手,反而转身向楼梯上方走去。
“很高兴见到你,”女人背对娜奥米说道,“我是弗洛伦丝,多伊尔先生的侄女。”
娜奥米想出声嘲讽,却忍住了,只是快步走到弗洛伦丝身旁,与她保持了同样的速度。
“谢谢您。”
“我负责照管上高地,因此,你有任何需要都应该来找我。在这里我们有固定的行事方式,我们希望你能守规矩。”
“什么规矩?”她问。
他们经过了那扇彩色玻璃窗,娜奥米注意到它呈现出明亮的、非写实风格的花朵图案。花瓣的蓝色靠氧化钴呈现。她了解这些事。就像她父亲一样,颜料生意让她知道了各种化学现象,尽管大部分她都会无视,然而它们还是会自动跃入她的脑海,就像一首恼人的歌。
“最重要的规矩在于,我们是安静而注重隐私的群体,”弗洛伦丝说道,“我的叔叔霍华德·多伊尔年事已高,大部分时间都待在自己的卧室里。你不能去打扰他。其次,现在负责看护你堂姐的人是我。她现在需要大量时间来休养,因此如非必要,你也不能打扰她。不要独自离开屋子瞎转悠,很容易迷路,而且这片地区有很多山谷。”
“还有吗?”
“我们不常去镇上。如果你有事要去那儿,一定要来找我,我会让查理开车带你去。”
“查理是谁?”
“我们雇用的仆人之一。近来我们雇的人很少了,只有三名。他们已为这个家服务了很多年。”
他们沿着一条铺有地毯的走廊前进,墙上装饰着椭圆框和长方框的油画肖像。早已故去的多伊尔家家族成员的脸隔着时空凝视娜奥米。女人们头戴软帽,身穿沉重的裙子,男人们则头戴高顶大礼帽,配手套,表情阴沉。是那种会自称有权获得家族纹章的人。皮肤苍白,发色暗淡,就像弗朗西斯和他的母亲。那一张张面孔混杂在一起。即使凑近了看,她也没法分别认出这些人。
“这里是你的房间,”他们来到一扇饰有水晶门把手的门前,弗洛伦丝立刻说道,“我要提醒你,在这栋屋子里禁止吸烟,假使你有这种恶习的话。”她补充了一句,眼睛看着娜奥米时尚的手提包,仿佛她的视线能穿透它,看到娜奥米放在里面的那包烟。
恶习,娜奥米想,她回想起了监督她受教育的嬷嬷们。她就是在喃喃念诵玫瑰经的过程中学会了叛逆的。
娜奥米步入卧室,凝视古老的四柱床,它看起来就像是从哥特小说里蹦出来的;它甚至还有幕帘,你可以把它们放下来,将自己包裹成茧,远离这个世界。弗朗西斯将手提箱放在一扇窄窗旁——这扇窗没有颜色,夸张奢侈的彩色玻璃窗没有延伸到私人的生活区域中——弗洛伦丝则指着大衣橱和里面存放的多余的毯子。
“我们在山上高处。这儿很冷,”她说,“我希望你带了毛衣。”
“我有一条雷博佐披肩[3]。”
女人打开床脚的小柜子,拿出一些蜡烛和一个娜奥米毕生所见最丑的枝形大烛台,它通体银质,底部雕刻了一个向上伸出双手的小天使。接着她关上柜门,将这些找出来的东西放在了柜子顶上。
“1909年时我们这儿安装了照明电气,就在革命前,但自此之后的四十年里没有太多改善。我们有台发电机,能够制造足够的电力来使用电冰箱,或是点亮几个小灯泡。但它完全没法给整座屋子照明。因此,我们依靠的是蜡烛和油灯。”
“我都不知道你们是怎么用油灯的,”娜奥米说着咯咯笑了一声,“露营的时候我都没法得心应手地使用它。”
“就算是傻子都能明白最基本的原理,”弗洛伦丝说道,而后她继续说了下去,没有给娜奥米回嘴的机会,“热水锅炉有时候会有些小问题,但不管怎么说年轻人不该用太烫的水洗澡;温水正适合你。这个房间里没有壁炉,不过楼下有一个大壁炉。我还有什么遗漏的吗,弗朗西斯?没有,很好。”
女人看着她的儿子,但同样没有给他任何回答的机会。娜奥米怀疑在她身边有多少人能有机会说上一个字。
“我想和卡塔莉娜说话。”娜奥米说道。
想必弗洛伦丝本以为谈话结束了,此时她已将一只手放在门把手上。
“今天?”女人问道。
“对。”
“已经快到她吃药的时间了。她吃完后就要睡了。”
“我只想和她待几分钟。”
“母亲,她大老远来的。”弗朗西斯说道。
他突然插嘴似乎让这女人有些措手不及。她朝这年轻男子挑起一边的眉毛,而后双手合握。
“好吧,我猜你们大城市来的人时间观念和我们不一样,你们总是东忙西忙地赶时间,”她说,“如果你一定要立刻见到她,那最好和我一起来。弗朗西斯,你为什么不去问问霍华德叔父,他今晚是否会和我们一起用晚餐呢?我可不希望碰上意外。”
弗洛伦丝领着娜奥米走上另一条长长的走廊,来到一个房间里,那儿同样也有一张四柱床,还有一张带三折镜面的梳妆台,以及一只大到足以容纳小型军队的大衣柜。这里的墙纸是浅蓝色的,带有花卉图案。墙上装饰着小小的风景画,有高耸悬崖和无人海滩的沿海景色,但没有本地的风光。这些很有可能是用油画和银画框保存下来的英格兰。
窗边摆着一把椅子,卡塔莉娜坐在上面。她正望着窗外,两个女人踏入房内也没能惊动她。她那头茶褐色的头发束在后颈。娜奥米原本已经硬起心肠来面对一个备受疾病折磨的陌生人,但此时看来,卡塔莉娜似乎与她在墨西哥城生活时没什么两样。或许周遭的装饰放大了她那种梦幻的特质,但她身上的改变也就仅此而已。
“五分钟后她就该吃药了。”弗洛伦丝说着,看了一眼腕表确认。
“那这五分钟归我。”
年长的女人似乎并不高兴,不过她还是离开了。娜奥米靠近了她的堂姐。年轻的女人仍未看她一眼,她沉静得古怪。
“卡塔莉娜?是我,娜奥米。”
她伸出一只手轻轻地放在堂姐的肩头,直到此时,卡塔莉娜才看向娜奥米。她慢慢露出微笑。
“娜奥米,你来了。”
她站在卡塔莉娜身前点了点头。“是的,父亲派我来看看你的情况。你现在觉得怎么样?有什么不舒服的吗?”
“坏透了。我得了一场热病,娜奥米。肺结核让我病得很重,但现在已经好多了。”
“你给我们写了一封信,你还记得吗?你在信上说了些奇怪的话。”
“我记不清自己写的那些话了,”卡塔莉娜说道,“我当时烧得厉害。”
卡塔莉娜比娜奥米年长五岁。这不算太大的年龄差,但已足以让卡塔莉娜在两人幼时承担母亲般的角色。娜奥米还记得她与卡塔莉娜一起度过的许多个午后,她俩一起做小手工,给纸娃娃剪裙子,看电影,听她编童话。而现在,看到她这样无精打采的,要依靠从前曾依赖她的他人生活,这种感觉实在有些奇怪。娜奥米一点也不喜欢这样。
“那封信让我父亲紧张极了。”娜奥米说道。
“我真的很抱歉,亲爱的。我不该写信的。你本来在城里可能有好多事要做。你的朋友们,你要上的课,但现在你出现在这儿,就因为我随手写了一页没头没脑的话。”
“别担心了,是我自己想来看你的。我们已经很久没见了。老实说,我本来以为现在这会儿你该来拜访我们了。”
“是的,”卡塔莉娜说道,“是的,我原本也这么想。但要离开这座屋子是不可能的。”
卡塔莉娜陷入沉思。她的双眼如同两摊褐色的死水,在此时变得更为迟钝,她张开了嘴,像是准备要说什么,却没有说出一个字。相反她吸了一口气,屏住,而后转过头,咳嗽起来。
“卡塔莉娜?”
“你该吃药了。”弗洛伦丝说着走进房间,手中拿着一只放有汤匙的玻璃碗。“现在喝。”
卡塔莉娜顺服地喝下一汤匙药水,接着弗洛伦丝扶她躺到床上,将被子拉到她的下巴。
“我们走吧,”弗洛伦丝说道,“她需要休息。你们可以明天再谈。”
卡塔莉娜点点头。弗洛伦丝带着娜奥米走回她的房间,一路上给她简单描述了这座屋子——厨房在那个方向,书房在另一边——并告诉她,他们会在七点接她用晚餐。娜奥米拿出行李,把衣服放进大衣柜,接着去洗手间梳洗。洗手间里有一只古老的浴缸,一个浴室柜,天花板上有发霉的痕迹。浴缸周围的不少瓷砖龟裂了,不过三角凳上摆了干净的毛巾,挂在钩子上的浴袍看起来也是干净的。
她试了试墙上的电灯开关,照明设备没有反应。回到房间里,娜奥米根本找不到任何一盏装有电灯泡的电灯,尽管确实有一个电器插座。弗洛伦丝说他们靠蜡烛和油灯,她估计这不是玩笑。
她打开手提包,翻找了一番,直到找到香烟。床头柜上有个以半裸的丘比特为装饰的小杯子,正好充作临时烟灰缸。吸了几口后,她漫步到窗前,以防弗洛伦丝抱怨有烟味。但窗户根本打不开。
她站着,看向窗外的迷雾。
注释
[1]墨西哥独立战争爆发于1810年,是墨西哥人民与西班牙殖民当局之间的一系列武装冲突,直到1821年阿古斯汀·德·伊图尔维德与各派系结成紧密联盟,宣布墨西哥独立。波菲里奥时期指墨西哥总统波菲里奥·迪亚斯统治的时期,具体为1876—1911年间,迪亚斯推行现代化项目,引进外国的先进技术和大量外国资金,兴建铁路,开设工厂,但长期独裁仍引起人民不满,最终引发了墨西哥革命(1910—1920)。
[2]一种火山的火成岩,海绵状,多孔,重量轻而耐腐蚀,在墨西哥东西部都有广泛分布,因此自玛雅文明和阿兹特克文明时期便广泛用于建筑。由于含有二氧化铁而微微发红。
[3]雷博佐是墨西哥女性传统服饰,通常是一块介于披风和披肩之间的布,用以包裹头部和肩部,可御寒、遮挡阳光,特征为复杂的编织流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