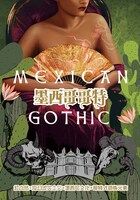
第2章
图农家的晚宴总是结束得特别迟,这家的主人们又特别喜欢变装舞会,因此见到穿传统裙装、头上系丝带的普埃布拉中国女孩[1]与小丑或牛仔相携出现,也不是什么非同寻常的事。宾客们的司机不愿在图农家门外干等,夜间也总有安排。他们会去街角的大排档吃玉米卷,或去拜访附近某家的女仆,展开一段堪比维多利亚时代情景剧般的精致求爱。另有一些司机会聚在一起,分享香烟,说些传闻故事。还有人会打个盹儿。毕竟,他们都很清楚,在凌晨一点之前,没有人会放弃舞会。
于是当两人在夜间十点踏出舞会,便打破了惯例。更糟的是,男人的司机离开吃饭去了,根本找不着人。这个年轻男子看起来很紧张,不知该如何是好。为了参加舞会,他戴了一个纸糊的马头,这个选择让他此时十分困扰,因为他们不得不带着这个累赘的道具穿过整座城市。娜奥米此前提醒过他,说自己想在变装比赛上拔得头筹,赢过劳拉·奎泽达和她那些拥趸,为此他努力了一番,只是如今看来这番气力用错了地方,因为他的同伴根本没有按照说的那么穿。
娜奥米·塔波阿达号称会租赛马骑师的装备,一整套,带马鞭。这本是个聪明的选择,还带点儿暧昧的意味,因为她听说劳拉准备打扮成夏娃,甚至会在头颈盘一条蛇。不过最后娜奥米改了主意。骑师的服装看上去挺丑,又蹭得她皮肤难受。于是她改穿了有白色贴花的绿色长袍,却懒得将这一改动告知她的约会对象。
“现在怎么办?”
“三个街区外有条大街。我们可以在那儿叫辆出租车,”她对雨果说道,“好啦,你有烟吗?”
“香烟?我都不知道自己把钱包放哪儿了,”雨果说着单手拍外套,“再说了,你的包里不总是有烟的吗?要不是我了解你,甚至会以为你这是小气的表现,自己买不起香烟。”
“让绅士给女士敬烟可不是更有趣。”
“今晚我连薄荷糖都敬不起。你觉得我是不是把钱包落在那间屋子里了?”
她没有回答。雨果将马头夹在腋下,艰难地走了一段。当他们抵达大街时,他差点就要把它扔掉了。娜奥米抬起纤细的胳膊,叫了一辆出租车。他们一进入车内,雨果便将马头放在了座位上。
“你明明可以提前告诉我,那我根本不用带这玩意儿。”他低声说着,注意到司机的脸上露出了微笑,估计是被他这倒霉事逗乐了。
“你发怒的样子真可爱。”她回答,同时打开手提袋,找到了烟。
雨果看起来也有些像年轻时的佩德罗·因凡特[2],这是他的一大魅力来源。至于其余部分,比如人格、社会地位、智慧等等,娜奥米压根懒得多想。如果她想要某样东西,那很简单,她就只是想要它,而最近这段时间里她想要的是雨果,不过既然现在他的注意力已经集中在她身上,那她也就没那么上心了。
他们到她家门口时,雨果抓住了她的手。
“给我一个晚安吻吧。”
“我累了,不过还是能让你尝点儿我的口红。”她取下香烟,将烟嘴塞进他的嘴里,回答道。
雨果将身子探出车窗外,皱眉望着娜奥米匆匆进入家中,穿过内庭,直接走向她父亲的办公室。就像这幢屋子的其余部分一样,他的办公室也以现代风格作为装饰,这似乎正彰显了户主所赚之钱的簇新程度。娜奥米的父亲从未经受过贫穷,不过他将一门小小的化工染料生意经营成了一笔巨大的财富。他知道自己喜欢什么,也不惧于将其显露在外:粗野的色彩和清晰的线条。他的椅子都装上了鲜红的垫子,每一个房间都用繁茂的植物装点着绿色。
办公室的门开着,娜奥米懒得敲门,快步走了进去,高跟鞋在硬木地板上踩得哒哒作响。她用指尖拂开发丝上的一朵兰花,在她父亲书桌前的椅子上坐下,大声地叹了口气,将手包扔在地板上。她也很清楚她自己喜欢什么,而且她一点也不喜欢早早地就被叫回家。
她进门时,父亲朝她挥了挥手——她的高跟鞋踩出的动静之大,与任何打招呼的语言无异,完全能清楚地作为她到来的标志——但没有抬头看她,因为他正忙于检查一份文件。
“我真没法相信,你竟然会打电话去图农家叫我,”她说着扯下白手套,“我知道你不怎么高兴,因为雨果——”
“此事与雨果无关。”父亲打断了她的话头。
娜奥米皱起眉头。右手握着一只手套。“不是吗?”
她提前问过父亲,得到了参加舞会的许可,不过她没有特意指出自己会和雨果·杜阿尔特一起去,她知道父亲对他有想法。父亲担心的是雨果可能会向她求婚,而她会接受。娜奥米并不想嫁给雨果,也向父母说过这一点,只是父亲不相信她。
与每一位优秀的社会名流一样,娜奥米在“铁皇宫”[3]购物,用伊丽莎白·雅顿的口红,拥有两件上好的皮草,能娴熟使用英语,由蒙塞拉特——自然,这是一所私立学校——的嬷嬷们教养长大,本该将她的时间花在娱乐与寻觅良婿这两大追求上。因此,在她的父亲看来,任何休闲活动都该同样具备寻觅配偶的目的。也就是说,她永远都不该为开心而寻开心,只能将此作为获得丈夫的途径。假如父亲确实喜欢雨果,那这思路倒也还不错,然而雨果不过只是初级建筑师,娜奥米应该有更高的追求。
“不,不过我们晚点儿也得谈谈这事。”父亲这么说道,娜奥米一头雾水。
当时她正在跳慢舞,一名仆人过来拍了拍她的肩膀,问她是否愿意去工作间里接个电话,与塔波阿达先生谈谈,这便毁了她的整个夜晚。她本来很确信,觉得是父亲发现自己与雨果一起外出,想将他从她的怀里挖出来,于是给她送来了这番告诫。但假如这不是他的目的,那这般大惊小怪又是为了什么?
“没发生什么坏事,对吧?”她问道,语调出现了变化。生气的时候她的音调会变高,听起来更像少女,与她近年来熟练掌握的调整过的音调并不相同。
“我不知道。接下来我要告诉你的事,你不能向其他人重复。不能告诉你母亲,不能告诉你哥哥,不能告诉任何朋友,明白了吗?”她的父亲边说边盯着她,直到娜奥米点了点头。
他向后靠上椅背,双手捂住脸,最后也朝她点了点头。
“几周前,我收到了你的堂姐卡塔莉娜写来的一封信。她在信中说了不少与她丈夫有关的疯话。于是我给弗吉尔写信,想弄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弗吉尔回信说,这段时间以来卡塔莉娜一直行为古怪,叫人烦恼,不过他觉得她正在好转。我们来回通了几封信,我坚持表示,如果卡塔莉娜真如他所说,表现得叫人烦恼,那最好带她到墨西哥城来,让专家看看。他回说这么做毫无必要。”
娜奥米脱下了另一只手套,将它放在膝头。
“我们僵持不下。我本来觉得他不会改变想法,不过今天晚上我接到了一份电报。就是这个,你自己读。”
她的父亲抓起书桌上的一张纸,递给娜奥米。那是封邀请函,请她前去拜访卡塔莉娜。火车不是每天都会经过他们镇子,不过周一会去,他们会在火车到达之时派一名司机去火车站接她。
“我希望你去,娜奥米。弗吉尔说她一直想见你。另外,我觉得这事儿最好由女人来处理。可能最后会发现,不过是夸大其词了的夫妻婚姻问题。毕竟你的堂姐一直有点情绪化。可能只是场为了引人关注而起的闹剧。”
“如果是这样,那卡塔莉娜的婚姻问题或她是不是情绪化,又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她问道,尽管她觉得父亲认为卡塔莉娜情绪化的说法并不公平。卡塔莉娜幼时便失去了双亲。你完全可以想象,自此之后她的生活又发生过多少动荡。
“卡塔莉娜的信很古怪。她声称她的丈夫对她下毒,她说她看到了幻象。我不是说自己是个医学专家,但这已足够让我去向镇上的好精神科医生们打听了。”
“你还有那封信吗?”
“有,给你。”
娜奥米读得很艰难,要弄懂句子的含义更艰难。信上的字迹似乎带着颤抖,写得十分潦草。
……他正在尝试对我下毒。这座屋子病了,它在腐烂,带着朽败的臭味,充盈着邪恶和残酷的情绪。我已试过坚守自己的神志以驱离这种邪秽,但我做不到,我发现自己正在丧失时间和思维的概念。求求你。求求你。他们残忍、苛刻,而且不会放过我。我用棒子抵住了门,但他们依然能进来,夜复一夜他们不停低语,我害怕这些躁动不休的死者,这些幽灵,这些没有血肉的东西。衔尾蛇,我们脚下污秽的土地,错误的脸孔和错误的口音,蜘蛛行经时会让丝线随之而颤抖的网。我是卡塔莉娜,卡塔莉娜·塔波阿达。卡塔莉娜。卡塔,卡塔登台表演。我想念娜奥米。我祈祷自己能再见到你。你得来找我,娜奥米。你得救我。我没法像我希望的那样拯救我自己,我被关了起来,铁一般的线穿过我的头脑、我的皮肤,而它在这儿。在墙里。它没有松开我,所以我必须请求你放我出来,从我身上切断它,现在来阻止它们。看在上帝的分上……
快来,
卡塔莉娜
在这封信的空白处,她的堂姐还潦草地填上了更多字句和数字,画了好几个圈。看起来令人不安。
娜奥米上一次和卡塔莉娜说话是在什么时候?一定已经有好几个月了,可能接近一年。那对夫妻在帕丘卡度的蜜月,卡塔莉娜给她打了电话,又寄来一些明信片,但在此之后就没什么消息了,只有电报会适时抵达,祝家庭成员生日快乐。她肯定还寄过圣诞节的信,因为他们收到了圣诞节礼物。不过也有可能,其实是弗吉尔写了圣诞信?不管怎么说,那只是一封平淡的格式信函罢了。
原本他们都以为卡塔莉娜正在享受新婚时光,不乐意多写。另外她的新家没有电话,这在乡间也不是什么非同寻常的事,而且卡塔莉娜本来就不太爱写信。娜奥米则忙于她的社交义务和学业,只觉得卡塔莉娜和她的丈夫迟早会来墨西哥城拜访。
也正因此,她手上拿着的这封信便与她能想到的任何一点卡塔莉娜的特征都不吻合。这是一封手写的信件,而卡塔莉娜更偏爱打字机;信上的字迹潦草,卡塔莉娜在书写时却总是很简洁。
“非常古怪。”娜奥米承认。原本她以为她的父亲在夸大其词,要不就是想让她将注意力从杜阿尔特身上转开,顺手利用了这个事件,但现在看来,这两种猜测似乎都不成立。
“至少可以这么说。你看到它,应该就能明白我为什么会给弗吉尔写信,叫他说明清楚。而当他立刻控诉我、说我制造了麻烦时,我又是多么惊讶。”
“你具体给他写了什么?”她问道,她担心父亲表现得太过粗野失礼。他是个严肃的人,可能会因为他那无意为之的唐突之举而与人产生不该有的摩擦。
“你得明白,我并不乐于把我的侄女送进卡斯达聂达这样的地方——”
“你是这么说的吗?说你要送她进精神病院?”
“我只是提出了这么一种可能性而已。”她的父亲回答,同时伸出一只手。娜奥米将信还给他。“也不是只有这么一种选择,不过我认得卡斯达聂达那里的人。她可能需要专业的护理,那可是她在乡下得不到的。另外,我恐怕我们才是会尽可能地保证她的利益的人。”
“你不信任弗吉尔。”
她的父亲干巴巴地轻笑一声。“你的堂姐这婚结得太快了,娜奥米,而且,我们可以说,结得有欠考虑。现在,我会先承认弗吉尔·多伊尔似乎确实富有魅力,但谁知道他到底靠不靠得住呢。”
他说的自有道理。卡塔莉娜订婚的过程仓促得几乎难称体面,他们也没有得到什么与新郎说话的机会。娜奥米甚至不清楚这对夫妻是怎么相遇的,只知道没过几周卡塔莉娜便送出了婚礼邀请函。在那之前,娜奥米甚至都不知道她的堂姐有了意中人。要不是娜奥米受邀去民事法庭做见证人,她怀疑自己甚至根本不会知道卡塔莉娜结了婚。
如此保密匆忙,自然让娜奥米的父亲很不高兴。他给这对新人举办了婚礼早餐会,但娜奥米知道,卡塔莉娜的行为让他自觉受到了冒犯。而这又是另一个理由,让娜奥米为卡塔莉娜甚少联络家里而担心。他们之间的关系在当时有些降温。不过娜奥米本来觉得,情况过几个月就会缓和,到十一月,卡塔莉娜或许便会带着圣诞节的购物计划抵达墨西哥城,然后大家都会开心。时间,不过只是时间的问题。
“你一定觉得她说的是真话,而他虐待了她。”她总结道,同时设法回忆自己对那位新郎的印象。英俊,彬彬有礼,她的脑海中跳出来的是这两个词,但随后能想起来的就不过只是一两句话而已了。
“在那封信里,她不仅声称他给她下毒,还说有鬼魂穿墙而过。告诉我,这听起来像是精神正常的人说的话吗?”
她的父亲站起身,走到窗边,双手抱胸,看向窗外。从办公室能看到她母亲那宝贵的九重葛树林,但此时,花朵的艳丽色彩隐匿在了黑暗之中。
“她状态不好,我知道的是这一点。我还知道,如果弗吉尔和卡塔莉娜离婚,那他将身无分文。很清楚的是,他俩结婚时他家的钱已经用光了。但只要他们还是夫妻,他便有权使用她的银行存款。能让卡塔莉娜一直留在家中对他有利,哪怕她可能最好还是进城里去,或是和我们一起住。”
“你觉得他是图财?将财产问题看得重于妻子的幸福?”
“我不了解他,娜奥米。我们没有一个人了解他。这就是问题所在。他是个陌生人。他说她得到了精心照顾,正在康复,但我只知道卡塔莉娜正被绑在床上,以稀粥为食。”
“那你还说她情绪化?”娜奥米问道,她检查着胸前的兰花装饰,叹了口气。
“我知道生病的亲戚会表现成什么样。我自己的母亲得过中风,在床上困了好些年。我也时不时会听说有些家庭没能处理好这样的事。”
“那么,你要我做什么?”她优雅地将双手摆在膝头,问道。
“评估形势。确定她是否真的应该被送到城里,如果确实如此,那就说服弗吉尔这是最好的选择。”
“我怎么能做得到这样的事?”
她的父亲笑了起来。从这得意的笑容,还有两双聪明的深色眼睛里,可以看到孩子和她的父亲彼此之间极为相似。“你心性不定。对所有事,任何事,总是主意改变个不停。一开始你想研究历史,接着是戏剧,现在则是人类学。你在所有你能想得到的运动上兜兜转转,最后没有一种坚持下来。你和一个男孩约会两次,到第三次就再也不给他回电话了。”
“这和我的问题没有任何关系。”
“我正要说到这一点。你心性不定,但你对所有错误的事都表现得很顽固。现在,是时候用你的顽固和精力来完成一项有用的任务了。目前为止,除了钢琴课之外,还没有任何事能让你尽心尽力去做呢。”
“还有英语课。”娜奥米回嘴说,但她没有否认这些责备中的其余部分,因为她确实常常周旋在不同的追求者之间,还完全能在一天里换四套衣装。
但这不等于你必须在二十二岁的年纪下定决心去做所有事,她想。不过将这想法告诉父亲毫无意义。父亲接管家族生意时十九岁。按照他的标准,她正以缓慢的速度向着一事无成而去。娜奥米的父亲严厉地看了她一眼,她叹了口气。“好吧,我愿意在几周内就去拜访——”
“周一,娜奥米。所以我才会从舞会半途把你叫回来。我们需要做些安排,好让你能搭上周一早上去埃尔特里温弗的头班火车。”
“但独奏会就要开了。”她回答说。
这是个薄弱无力的借口,他俩都知道这一点。她从七岁开始上钢琴课,每年都会举办两次小型独奏会。如今可不是娜奥米母亲那时代了,社会名流已不再必须能演奏乐器,不过,在她的社交圈子里,这仍是个会受到欣赏的美好小兴趣之一。此外,她也喜欢钢琴。
“独奏会。更像是你已经计划好了要和雨果·杜阿尔特一起出席,好让他别和其他女人约会,要么就是你不想放弃穿一套新裙子的机会。这不好,我们这边的事更重要。”
“我会让你知道的,我根本就没有买新裙子。我要穿的是我之前去参加格雷塔家鸡尾酒会的那条,”娜奥米说道,这话半真半假,因为她确实计划和雨果一起出席,“这么说吧,实际上我主要关心的不是独奏会。几天后我就得开始上课了,我不能就这么离开。他们会对我失望的。”她补充了一句。
“那就让他们对你失望。你可以下次再去上课。”
她正准备出声反对这种轻巧的说法,她的父亲转过身来,盯着她。
“娜奥米,你一直吵着要去国立自治大学。如果你干这事,我就允许你去报名。”
娜奥米的双亲同意让她去上墨西哥城的女子大学,但当她表示自己想在毕业后继续深造时,他们却反对了。她想获得人类学的硕士学位,这需要她去国立自治大学报名。她的父亲觉得这既浪费时间又不合适,那儿的所有年轻男子都无所事事,只会往女士们的脑袋里塞些傻气又下流的念头。
娜奥米的父亲同样对她那些现代的观念没有兴趣。女孩就应该遵循简单的生活轨迹,进入上流社交界,结婚生子。继续深造意味着将延迟这一轨迹,始终只做个茧子里的蝶蛹。为此他们争执过五六次,她的母亲狡猾地表示,得由娜奥米的父亲来做最后的决定,而她的父亲则似乎完全不准备这么做。
也正因此,她父亲的这句话让她震惊,给了她一个意料之外的机会。“你是认真的?”娜奥米小心地问道。
“是的。这是件严肃的事。我不希望报纸上刊登出他们离婚的消息,但我同样不能允许有人利用我们的家庭。而且,我们正在谈的是卡塔莉娜,”她的父亲说着,和缓了语气,“她已受够了不幸,可能极需要看到支持她的人。也可能,到最后,我们会发现她需要的就只是这一点。”
卡塔莉娜已深深受到多次不幸的伤害。首先是她父亲去世,接着是母亲再嫁,继父常让她流泪不止。卡塔莉娜的母亲在两年后去世,这个女孩住到了娜奥米家里,此时她的继父已经离开了她。尽管有塔波阿达一家人的温暖拥抱,亲人的死亡仍深深地影响了她。在此之后她还有过一段失败的婚约,这也产生了许多争吵,伤害了大家的感情。
有个相当愚蠢的年轻男子曾经向卡塔莉娜献过好几个月的殷勤,她似乎相当喜欢这家伙。但娜奥米的父亲不为所动,把他赶走了。在这段无疾而终的恋情之后,卡塔莉娜一定学到了教训,因为她和弗吉尔·多伊尔的关系便堪称谨慎的典范。也或许,更狡猾的人是弗吉尔,是他一直劝卡塔莉娜对两人的关系保持沉默,一直拖到再也没有任何事能破坏这次结合。
“我想我能告诉别人,接下来我会出几天门。”她说。
“可以。我们会给弗吉尔回电报,让他们知道你上路了。小心谨慎,我需要的是这些。毕竟他是卡塔莉娜的丈夫,有权为了她好而做出决定,但假如他不管不顾,我们也不能放任不管。”
“我觉得应该让你写下来,关于上大学的那点事。”
她的父亲坐回了桌子后面。“说得好像我会说话不作数似的。现在,把你头上的花摘下来,去准备行装。我知道要你决定穿什么简直得等到天荒地老。顺便问,你今天这是打扮成了谁?”她的父亲问道,显然对她裙子的剪裁,还有她露在外面的肩膀很不满意。
“我扮的是春神。”她回答道。
“那儿很冷。如果你打算穿得像这样在那儿四处走,最好带件毛衣。”他干巴巴地说道。
通常她会回上两句俏皮的反击,不过这次,她保持了不同寻常的沉默。在答应了这场冒险旅行之后,娜奥米想到,她对自己即将前去的地方及她将遇到的人,都知之甚少。这可不是一趟愉快的度假之旅。但她很快又让自己放心下来,父亲已经选择了她来执行这项任务,而她也将顺利完成。心性不定?呸。她会向父亲展示他想在她身上看到的倾尽全力。或许,在她成功之后——这么说是因为她完全没法想象自己失败的场景——父亲会认为她比他印象中的更值得托付,也更成熟。
注释
[1]传说普埃布拉中国女孩是17世纪时的一位亚洲出身、在普埃布拉居住的女奴,她创制的传统服饰是一种色彩艳丽的钟形长裙,19世纪前半时在墨西哥中部地区极为流行,到20世纪后逐渐退出了日常生活,但至今依然是墨西哥各种节庆时的代表服饰之一。
[2]佩德罗·因凡特(Pedro Infante,1917—1957),墨西哥最受欢迎的演员和歌手,在16年间拍摄过53部影片,是墨西哥电影黄金时代的象征,《寻梦环游记》中歌神德拉库斯的原型。
[3]墨西哥最大的高档连锁百货商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