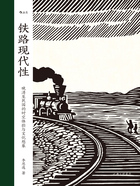
铁路研究的路径之二:作为决定现代性的技术
就铁路与现代性的综合思考而言,首推德国文化史学者希弗尔布施关于19世纪铁路旅行的原创性研究。他考察了铁路作为一种“机器集成”(machine ensemble)在工业化过程中对人们的时空认知演变和现代主体的形成所施予的多方面影响。铁路以其物质形态和机械速度清除了地理障碍,缩短了距离,真正实现了“时空的湮灭”(the annihilation of time and space)。铁路旅行将乘客个体从原有在地的自然环境中剥离出来,抛入一种全景式的(panoramic)视觉速度体验中,成为与外部观看对象区别的观看者。同时,铁路旅行也是一种最早的现代震惊体验,涉及车厢隔离引发的焦虑与尴尬、机械运动唤起的神经衰弱等现代心理病症,与现代文化的各种典型症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11]铁路在希弗尔布施的呈现中仿佛成了决定19世纪现代性文化的决定性技术——虽然他本意是想遵循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和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的思路。如果没有铁路的出现,我们根本无法想象以时间、速度和个体自我为显著特征的现代主义文学艺术还有诞生的可能。
法国思想家塞尔托(Michel de Certeau)从日常生活角度分析了铁路对现代经验的形塑及与现代主体之间的互动。他将铁路视为一间划分权力的圆形监狱、一个规训主体的禁闭空间、一组构建现代经验的句法规则,孕育了现代性的两大基本原理。其一是通过火车的玻璃窗去观看,让我们获得一种“全景视域”(panoramic view);其二是经由铁轨的线路产生的运动过程,区隔出空间的内部、外部以及观看者和被观看的对象。铁路这一现代性的宰制机器看似绝对,但塞尔托并未放弃乘客个体对此加以抵抗和改变的可能。因为悖论在于,这些机械之物、遥远之物自身的沉默让乘客的记忆能够言说、秘密的梦境得以显现。在塞尔托看来,一种精神性的、思想的东西恰恰在这种最为物质和技术性的状态下回归,并且坐落于机械秩序的核心——铁路于是成了“技术和梦境的结合”。[12]
新的文化表征与新的身体经验总是伴随着技术创新应运而生,这在视觉研究领域几乎已成为老生常谈。乔纳森·克拉里(Jonathan Crary)论证以视觉性为主导的现代文化和作为观察者的现代主体是如何由不同的知识、体制、技术、器物建构出来的。他提出视觉领域中原本占据统治地位的古典模型——暗箱(camera obscura)于19世纪瓦解,这使得视域从固定不变的关系中解放出来进入流变与运动的状态,促使了观看主体的转变,也奠定了现代视觉性与移动经验之间的共生关系。[13]也难怪汤姆·冈宁(Tom Gunning)会认为早在电影发明之前,铁路借助自身对实时性的掌控、距离的缩短以及速度的规训作用,成为第一个触发经验从传统向现代转变的技术装置。[14]琳恩·柯比(Lynne Kirby)则注意到铁路和早期无声电影在经验生产以及意识形态上的同构与互补,从视觉认知、性别认同、都市消费、民族身份等方面详细考察了两者之间的紧密关联。她认为铁路和早期电影是一对平行又互补的现代性机制,共同形塑了现代生活和它那不稳定的主体——“观众/乘客”(the spectator passenger);铁路旅行为无声电影的观众提供了一种观看的模式,引导他们去消费视觉图像与运动快感,适应现代西方社会的范畴与规则。[15]
需要指出的是,这种看似中立的技术论调往往可能预设了西方白人主体的有色眼镜;因为对于所有非西方国家来说,铁路在带来速度和利益之前首先意味着暴力与侵略。玛丽安·阿吉亚尔(Marian Aguiar)立足于印度的近现代史,考察铁路带来的移动性文化与移民、后移民之间的张力变化。她通过梳理西方移民帝国和印度本土有关火车的意识形态争论,探讨铁路在印巴分治进程中如何从外来移民者的侵略工具演变为独立民族国家的象征,同时分析后移民/全球化时代下游记文学和宝莱坞电影对铁路的本土再现,凸显移动性的经验及表征与不同时期印度现代性的主导叙事,时而合作共谋,时而激烈对抗的过程。[16]
以上两种研究途径无疑从各个层面丰富了我们对铁路的认识,但也都存在着明显的局限性。在第一种模式中,技术与物永远都是现代性的一种修辞,服务整个宏大历史的进程,而铁路不过是其中的一个例证罢了。所以无论怎样书写铁路的历史,资本主义现代性发展之类的最终结论在一开始就被设定好了。落实在中国的语境里,就是铁路如何从西方帝国主义移民扩张的工具转变为民族国家追求独立富强的象征,而其对人们日常生活的影响不过是响应这一主旋律的伴奏。铁路在这种研究中成了一个空洞的能指,适用于铁路的论述也同样可以套在轮船、飞机、电报,乃至蔗糖、茶叶身上;因为物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物与技术背后的资本市场、移民帝国、权力关系等。所以物成了没有个性、没有自身历史的“死物”——从人的角度来看,它们似乎都没有什么区别。反过来,第二种研究模式则始终隐含了一种技术决定论的姿态——无论具体的研究者对此持什么意见,他们毕竟都默认一种新技术的出现改变了我们的经验、我们的观念,以及我们的文化。所以铁路这类的科技产物不仅重新塑造了我们的日常生活,还开启了工业化、资本主义全球化这一普遍进程。所有的现代文化表征都可以被归结为对现代科技的一种回应——有时是种共鸣,有时则体现为抵抗。[17]在这种技术决定论的框架下,现代科技就像复魅的魔法一样,深沉而内在地影响着日常生活、经济发展、历史事件——换句话说,技术和器物又被意识形态化了。曾几何时,我们倾向于诉诸无法说清的“大词”来作为各种问题的终极答案,比如资本、权力、历史规律等,现在我们又把物与技术加入这个词汇表中。
铁路研究中暴露出来的“空洞能指化”与“再意识形态化”实质上体现了物本身难以被把握——被排除在物之外的人永远无法给非人的物一个恰当的位置。而人与物的分裂又与现代哲学中主体与客体、自我和他者的二元对立是一脉相承的难题。即使求助于黑格尔的辩证法,开启这一扬弃过程的前提依然是作为主体的自我施加于自身的对象化(objectification)。[18]对象化本身蕴含着客体化,即非人化、物化的意思,以物的眼光出发去对待人貌似调和矛盾的基础,却是为了以人的权力统摄物的取巧手段。批判理论中经常使用“物化”这个词,但我们是否反思过自己真的理解“像物一样”是什么意思吗?又或我们真能做到以物的角度去理解世界吗?不过,对物的反思并不必然要在物与技术之内展开,就像人的问题常常是非人的因素造成的一样。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曾在一篇著名的文章中提醒我们:技术的本质并不必然是技术性的,对技术本质的反思,以及人与技术不可避免的相遇都是发生在技术以外的层面上。[19]而人与物的分裂恰好就发生在现代性显现之际,这又必然涉及现代性更为显著的另一对矛盾:理论与经验的对立。
现代性,可能是学术领域最具争议又最难被界定的术语之一。不过相对于以民族国家为单位、指涉政治经济发展过程的现代化这一概念,现代性更多强调人的历史经验与文化意义。为了便于读者理解,我在这里先简要梳理一下现代性的主要内涵。首先,它可能是指一种历史分期,一般从17—18世纪“启蒙、理性的时代”开始延伸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其次,它也指涉一种形式风格,比如现代主义文学中的意识流手法,又或现代艺术中的先锋运动(Avant-garde);再次,它与主体的普遍自觉密不可分,既是启蒙的产物,也蕴含着对启蒙的反思;最后,它在很多情况下都表示一种新的经验,特别是我们对于时间和空间有了不同以往的体验。当然这四重内涵远远没有穷尽有关现代性的言说,而它们彼此之间也可能存在冲突和重合。就此而言,我认为现代性的言说方式以及由此引发的思考远比某一个被采纳的定义更重要。所以我并不想在现代性的内容之中寻找矛盾与对立——这实在是太多了,而是关注研究者究竟以何种方式来言说现代性,他们不同的言说方式又是怎样与物的难题联系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