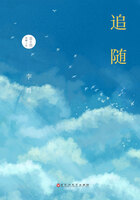
第2章 老舅(1)
老舅近来有些疲惫。
最让老舅困扰的是,最爱的儿子大学毕业已经两年了,依旧没有工作。老舅的儿子也算得上优秀,大学毕业的时候还是校级优秀毕业生,可儿子有一个后天缺陷——右手的无名指和小指残缺不全。
老舅和舅妈年轻的时候在外打工,把年幼的儿子留在家里,让姥姥照看。儿子好动,姥姥浑身是病,不能时刻跟在孙子后面。儿子经常跑到邻居木匠家看木匠叔叔做木活。有时候木匠叔叔忙起来,就让孩子搭把手,有一次,不小心把手伸到了木匠家轰鸣的电锯上,被锯掉了右手的无名指和小指。当时市里的医疗条件差,接肢手术只有省城能做,省城路途遥远,看着血流如注的手,老舅接受了医生的建议,直接缝合了伤口。几个月后,打开儿子手上的纱布,看着残缺不全的手指微微搐动,舅妈哭成了泪人。好心的医生打开一本伤残鉴定指南,指给舅妈看,示意给孩子做个残疾鉴定,申请政策补助。舅妈拿起书,扔在医生脸上,大骂道:“你才残疾呢!你们全家都是残疾!”意识到时机不对,好心办了坏事,医生忍着痛,默默低下头,不敢吭声。老舅把舅妈拽出了医院。
此后每隔一段时间,舅妈就要为此发一通牢骚。让舅妈没想到的是,儿子仅用剩下的三根手指依旧能写字,字迹刚劲有力。儿子的名声很快传遍了学校。学校里书法造诣很高的副校长主动把老舅的儿子收入门下,边指导边推荐他参加青少年书法比赛。手里捧着儿子拿回家的一个个奖励和证书,舅妈又哭成了泪人。老舅站在一旁,认真地看着儿子用三根手指写出的毛笔字,眼神中夹杂着些许迷惑。这是老舅万万没想到的。老舅的儿子在一阵又一阵的表扬声和赞许声中,完成了小学、初中、高中的学业,并顺利考入大学。
在大学担任了书画协会会长,年年拿下一等奖学金,还以最优异的成绩拿到了教师资格证的儿子,万万没想到毕业之后会面对如此惨淡的局面。
老舅的儿子大学毕业后,回了老家。面对不景气的经济,毕业就是失业的窘境,老舅的儿子既是随大流,也是顺老舅和舅妈的意愿,加入了“公考”大军。此时,手指缺陷的负面效应就渐渐浮现了。伴随着一次次充满希望的笔试入围和一次次欲哭无泪的体检不合格,儿子陷入了绝望的泥沼。
就这样,老舅的儿子待业在家两年了。
舅妈觉得,要是找不到工作,就先给儿子结婚得了,做父母的也算了却了一桩人生大事。老舅也不反对。老舅觉得自己还很年轻,甚至还从未有过当爷爷的想法,但是一旦想法在脑子里萌芽,就落地生根,有点欲罢不能、挥之不去了。想到抱孙子,老舅像是又回到第一次做父亲的时候,不由自主地陶醉在一把安乐椅旁边放着一个小摇篮的温馨想象中去了。可没想到的是,老舅的儿子在相亲场上也一次次碰壁,每一次失败的根源竟还是那两根残缺的手指。
老舅不明白了,儿子的学生时代,这残缺的手指带给儿子和家庭的都是身残志坚的赞许和特殊的关照,可一进入社会,这手指怎么就成了儿子头上的“紧箍咒”了呢?现在这不仅仅是儿子的“紧箍咒”,更是老舅全家人的“紧箍咒”了。回忆过去,老舅以为这缺陷是儿子因祸得福的宝贵收获,命定的收获。
这“收获”现在已成了儿子难以遮掩的伤疤、老婆抱怨的主题和家庭矛盾的焦点了。
矛盾是无法掩盖的。待业在家还只是悬浮在海面上的冰山。儿子渐渐自我封闭起来,时常带着情绪,这情绪像一片阴霾笼罩在老舅和舅妈头上。
老舅历来慈祥而威严,儿子的情绪表现在舅妈那边是大吵大嚷、疾风骤雨式的;在老舅这里则变成了沉默着的、闷着的,变成老舅嘴里的“不尊重”了。
“这兔崽子没良心了,不尊重他老子了!”老舅时常在舅妈面前这么抱怨。
这期间的某一天,大中午,老舅打开儿子的房间,窗帘紧拉着,屋子黑乎乎的,地窖一般,床上的被子没叠,几个月没换洗的旧衣服和袜子堆在床脚和床头柜上,散发出一股陈旧的酱油味。
老舅伸出食指,在书桌上轻轻一划,一指灰。转过身,看到垃圾桶里塞满了带着食物残渣的零食袋、纸屑和空饮料瓶。老舅在电脑桌后站了好一会儿。儿子注意到了老舅的身影,没理会,依旧自顾自盯着电脑,双方都在用沉默与无视和对方作对抗。冷暴力逐步升温,老舅打算给儿子一分钟。
五分钟后,老舅爆发了。老舅严厉斥责儿子的颓废和懒惰,儿子不转头,也不吭一声,老舅加重了语气,命令儿子把垃圾桶里的垃圾倒掉,依然没见儿子有任何回应。被浇了一盆又一盆冷水,老舅的脑袋气得冒烟,心凉到了极点。
物极必反。老舅一下火了,扯住儿子的衣领,抬起手。儿子猛地转过头,盯着老舅,目光里是热腾腾的岩浆。
时间模糊了,不知过了多久。面对始终默不作声的儿子,老舅反而害怕了,不由自主地松开了手。
老舅尴尬地退出卧室,垂头丧气地走到阳台,看了看自己的手掌,手掌还在颤抖。虽然没下手,可回想儿子刚才的眼神,老舅反而像是自己被儿子打了一巴掌,还要难受些。
老舅背靠着墙,全身僵硬,努力控制住颤抖着的手指,一口气连着点了四支烟。
老舅和儿子依旧同住一个屋檐下,但是相互躲闪着,竟有半个月真没碰到面。
与儿子的交流陷入困境,老舅束手无策。看着舅妈整天愁眉不展,老舅只好找来历来走得最近的五妹开导儿子。
五姨从小看着侄子长大,视如己出,儿子也很尊重五姨。五姨是市里一所重点初中的语文老师,成天琢磨怎么与青春期的孩子们打成一片,对揣摩年轻人的内心世界更有经验。当老舅和五姨谈到这件事时,五姨的态度像是早有预料。五姨一次次地把老舅和舅妈牢骚的腔调和抱怨的话语稀释、过滤、净化,变成爱和关心的词语,灌注进侄子的耳朵,结果收效甚微。侄子也是个有主意的人。经过几番交谈,五姨渐渐没了劝说的声音,只剩下默默倾听。几次试探后,五姨识趣地退场了。清官难断家务事,就算是五姨这样一个有二十年教龄的金牌老教师,面对一地鸡毛的家庭纠结,也只得独自叹息。感叹时光匆匆,物是人非。
老舅家的气氛,经历了潜伏期到爆发期的骤变后,再次进入潜伏期。
这场冲突后的第三天,老舅做了一个梦。这个梦,成了老舅此后一系列噩梦的开端。
老舅出生在骆城,骆城位于黄土高原与毛乌素沙漠交界地带。南部六县位于黄土高原地带,荒蛮贫瘠,人口稀薄;北部六县位于堪称“肥沃”的毛乌素沙地,地下水充足,庄户人家连年丰收,加之地下有“黑金”资源,富裕之名,远播全国。南北差距,形成了贫富差距的鲜明区划。老舅的老家,正好处在沟壑丛生的黄土高原最后几道山梁上。梦里的情节发生在老舅还很小的时候。
小时候的老舅总是背着一个和自己差不多高的粪筐,游荡在山路上,为公社的第二生产队拾粪。在那个人都吃不饱的时代,生产队的驴子大部分时候都只能吃树皮充饥。作为精华的自然肥料——驴子的粪便像金子一样难寻。梦中的那天是个大晴天,毒辣的太阳刚爬到万里无云的当空,到处都是光秃秃的山,没有阴凉可乘。万物的影子此时都聚合成小点,老舅把自己的影子踩在了脚底。刚刚爬过一条又长又陡的山梁,总算到了平坦开阔的山峁上,走了一整个上午,老舅累得汗流浃背,气喘吁吁,有气无力地拽了拽自己的破草帽,坐下来休息。还没等屁股坐实,突然传来一阵阵笑闹声。老舅抬起头,看到一群生产队的青年们都不干活,围成一圈,那场面像是集市,吵吵嚷嚷的。老舅走近人群,凑上去一瞧,才知道原来是一个凶神恶煞的青年正拿鞭子死命地抽打一头驴,那是一头高大的褐色母驴,毛发细腻柔亮,在烈日下闪着金光。
老舅努力踮起脚尖把头伸进去,看到母驴被拴在一棵瘦弱的小树上。母驴奋力挣扎着,可顶不住劈面而来的鞭打,瘦弱的小树也像是要被连根拔起。老舅从母驴湿润的鼻孔看出了它的虚弱,母驴的呼吸也越发沉重起来。看了一会儿老舅才发现,母驴微微浮肿的肚皮像是有了驴驹子。
“这是一头能生养的母驴啊!”老舅愤怒地喊了一声,“你们怎么忍心!”
围观的人群听到了老舅的呼喊,突然停住了,转过身来看着老舅。随后,那个鞭打母驴的年轻人也停住了。他往空中猛甩了一下鞭子,呼哧!鞭子发出了清脆的拍击声,随后收起鞭子,黑着脸朝老舅走过来。老舅胆怯地朝后退了几步。
他站在老舅面前,高大的身影遮住了老舅头上的阳光。
带鞭子的年轻人一边摇晃着鞭子,一边用要挟的口气说:“拾驴粪的小子,你管什么闲事!”
围观的年轻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其中几个人在相互传递眼神。突然,人群中跳出了三个强壮的青年,他们一哄而上,把老舅压倒在地上。老舅极力反抗,嘴里不住地用陕北土话扯出十八代祖宗咒骂那些年轻后生,骂得五花八门、色香味俱全。后生们实在听不下去了,使劲捂住老舅的嘴,想让老舅闭嘴,可老舅的嘴猛烈地张合着,锋利的牙齿不停地打战,像是一头浑身是劲的小驴驹,后生们看到老舅求生般的挣扎,吓得缩回了手。其中一个青年没放手,转溜着眼珠,突然灵光一现,咧起嘴对着老舅坏笑了一下,然后伸手抓了一把老舅身旁被打翻在地的粪筐里的粪,使劲塞到老舅嘴里,粪便顺着老舅的喉管往下钻,老舅瞪着眼睛,嘴里发出“扑哧、扑哧”的响声。
“驴粪小子!”年轻后生们一边大喊着,“你要是心疼,你就吃驴粪吧!”一边哄笑着散去了。
耳边再次传来鞭打母驴的声音。老舅的脸渐渐发紫,无法呼吸。
老舅被噎醒了,大呕了一声,伸手摸了一下额头,满是汗。
下了床,到厨房里接了杯水,看着窗外的夜色,枯黄一片,老舅渐渐镇定了下来。老舅隐约感到这不是个好兆头。
和儿子半个月没碰面,之后的几个月,偶尔见面,也不说一句话。老舅拉下脸主动示好,儿子似乎不太领情。
老舅是慈父,在老婆和儿子有分歧时,向来偏向儿子,与儿子站在同一条战线。面对这样疏离的局面,老舅心里膈应。可碍着做父亲的威严和对儿子不成器的失望,老舅不愿再让步了。僵局持续着……
现实却不容许老舅停留在这样的僵局里。
老舅一直不安地等待着那个不好的兆头,不好的兆头就真的来了。
没人知道姥姥是什么时候去世的。
五姨是最近一个去看姥姥的人,可那也是五个月前的事了。姥姥的遗容已然僵硬,也就是说,姥姥可能已经死了好几个月了。
那天正好大雨。老舅一如往常,骑着摩托车运送汽车配件,突然接到了村里邻居家打来的电话,便匆匆赶回老家。
大雨如注,模糊了视线。老舅的眼角满是水珠,不知多少是雨水,多少是泪水。唯一清晰的是,老舅那张雕塑般的面孔,没一丝变化,仿佛肌肉都凝固一般。
就在老舅冒雨前行时,我的母亲和四个姨也都接到了邻居家的通知。
他们差不多同时赶回村里,进了门,看到姥姥紧靠炕墙坐着,头垂到一边。老舅鼓起勇气,将姥姥的脸缓缓转过来。姥姥的下嘴唇已经被老鼠啃掉,露出了黑乎乎的牙齿。老舅慌忙松开手,姥姥的脸又垂了下去。老舅将姥姥放平,从旁边扯过来一条破枕巾,盖在姥姥脸上。
没有人见到姥姥的最后一面。姥姥养的三花猫,也不知所踪。据村里有经验的老人说,姥姥应该是两个月前死的。
“死了两个月的人差不多就是这种样子的。”村里的老人们平静地说。
姥姥死在了这个只剩下五个孤寡老人的村子里。自从姥爷死后,八年了,姥姥一个人住在农村老家。老舅是姥姥唯一的儿子,也是家中老大,身后还有五个妹妹。姥姥的所有孩子,我的母亲、老舅和四个姨,或是租房子,或是买了房子,总之,全都住在城里。
看到姥姥倚靠在土炕旁面目全非的样子时,五姨脸色苍白,怪叫一声。
“我早就知道妈会这么没的,我早知道会这样的,我早就知道!”五姨大哭着说道。
五姨双手捂着脸,跑了出去。
我的母亲和其他三个姨反应不一,但全都吓傻了,随后纷纷跑了出去,躲在门外。只有老舅留了下来。
老舅跪在地上,埋着头……
没人知道老舅当时在想什么。或许老舅什么也没想,只是在等待。面对躺在面前的母亲,老舅耐心等着,似乎母亲还会醒来,像小时候那样,告诉自己该怎么做,而自己只要照着吩咐去做,便一切如常了。老舅就这么一动不动地埋头等着。
如果没遭遇这样的惨剧,人们便会认为把姥姥一个人留在老家也无可厚非,毕竟现今这样的事太普遍了。可一旦发生了,问题的严肃性就前所未有地摊开了。
所有的谴责和批评都劈头盖脸而来,老舅自然就处在了这谴责声的旋涡中,不仅是村里的其他人,甚至是邻村的人也都或在明里暗里,严厉地谴责老舅。除了五姨,老舅的其他四个妹妹,也都不同程度地对哥哥心存怨气。
老舅始终默默承受着。老舅沉默,一根接一根地抽烟。在料理姥姥丧事的那些日子里,老舅仿佛自我作贱似的,在所有的事情上都亲力亲为。作为儿子,老舅夜夜守灵,在打坟、朝亡、抬棺送葬等一系列丧礼流程中也扑在前头,拼命干。料理丧事的前后,整整一周,老舅几乎没合过眼。村里人都知道老舅是个强人,但不管怎样强悍的人都经不起没日没夜的折腾,老舅的妹妹们也都看不下去了,纷纷劝说老舅,可老舅依旧一声不吭地拼命干。
老舅是想用葬礼为自己赎罪,大家都看在眼里,可又像是在赌气。老舅心里有委屈。老舅当然有委屈的理由。所有熟悉的目光都盯着他一个人,只因他是姥姥、姥爷唯一的儿子。葬礼俨然变成了大型道德演出,老舅被动地扮演着反派的角色。
老舅用肉体受折磨,来发泄心底的委屈和伤痛。
老舅是隐忍惯了的,即使是在姥姥灵前守灵的时候,也没人见老舅流过一滴泪。
一个星期后,丧事结束。大家一起乘坐大姨夫的车返城,紧张的一周后,大家如释重负,气氛也松快了许多。老舅默默地坐在后座靠窗处,不知不觉已泪流满面。老舅把脸伸向窗外,任凭泪水沿着下巴滴落,随风飘散。
一旁的大姨和三姨,原本还在他家长你家短地嚼着舌头,见老舅哭了,也都再不说话。
就这样,老舅用泪水与姥姥告别。老舅的痛、老舅的爱、老舅的委屈、老舅的赎罪,统统融入这无声的泪水,留在了故乡的土地上。
老舅唯一带走的,是噩梦。姥姥死后很长一段时间里,老舅每天夜里梦到姥姥,姥姥死去时可怕的惨相,永远留在了老舅的梦魇里。即便不做噩梦,只要一想起姥姥,老舅也时常心神恍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