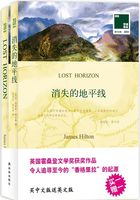
第2章
五月中旬的巴斯库尔,局势逐渐恶化。到了二十号,从白沙瓦安排到巴斯库尔疏散白人居民的空军飞机都已抵达。需要疏散的人约有八十个,大部分都安全地乘军用运输机飞过了群山。有几架式样不一的杂牌飞机也投入到此次护送任务之中,其中有一架小型客机,是印度禅达坡邦主借给空军使用的。上午十时左右,四位乘客登上了这架飞机,他们是:远东传教团的罗伯特·布林克罗小姐,美国人亨利·巴纳德,领事赫夫·康维和副领事查尔斯·马林森上尉。
后来,这几人的名字曾出现在印度和英国的报纸上。
康维,三十七岁,在巴斯库尔待了两年,他所从事的工作,从其经历看来,就像是赛马中下错了赌注,欲罢不能,而他的人生到此已告一段落。
本来,他在几个星期之后,或者回英国休几个月假之后,就会被派驻到另外一个地方,东京、德黑兰、马尼拉或马斯喀特中的一个。从事他这份职业的人永远不知道明天会怎样,他在领事馆已经工作了十来年,这十年已足够检验他的能力,也可以估得出自己还有多少机遇了。他清楚自己跟那些肥缺是沾不上边了,不过,这反倒让他感到心安,这并非是用“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的思想来说明自己并不喜欢那些美差。他更乐于做一些不太正式但有趣的工作,即便薪水不高,也不是常人眼中的好差事。无疑,这在别人看来是他处事不高明,而实际上,他自己感觉干得还满意,因为他这十年可以说过得愉快而充实。
他身材高大,古铜色的皮肤,一双灰蓝色的眼睛,棕色的头发剪得短短的。他不笑的时候看上去严肃而忧郁,但这样的时候并不多。笑起来时他又显得有些孩子气,工作过于紧张或者喝醉时,他的左眼附近会有点抽搐。在撤离前夜,他一直在捆扎和销毁文件,所以当他登上飞机时,已经精疲力竭,因而脸上的抽搐比平时更明显了。令他特别高兴的是,他被安排进一架专门为印度领主提供的豪华客机里,而不是拥挤不堪的军用运输机。当飞机升入高空时,他尽量让身体舒展一些。他是那种能适应艰苦条件的人,很少会去想要什么舒适的生活来做补偿。他的精神又振奋起来,心想尽管到撒马尔罕的这段旅程可能有些艰苦,但最后从伦敦到巴黎的这段可以舒适而安逸地在飞机上度过。
飞了一个多小时后,马林森说他觉得飞机并没有按直线飞行,然后立刻坐到了前排。他是个二十出头的小伙子,粉棕色的脸颊,看上去很聪明,但未受过良好的教育,这是公立学校的局限造成的,不过他也有自己的优点。他被派往巴斯库尔主要是因为一次未能通过的考试。他在巴斯库尔与康维相处了六个月,现在康维有些喜欢他了,可又不想费神与他闲聊,便懒洋洋地睁开眼睛说道:“飞哪一条航线,飞行员应该最清楚。”
又过了半小时,当疲倦和飞机马达的轰鸣使他昏昏欲睡的时候,马林森又来吵他:“我说,康维,我觉得不是费纳在驾驶飞机!”
“噢,不是他在驾驶飞机?”
“刚才那家伙转过头来,我发誓那不是费纳。”
“这不好说,隔着一层玻璃板。”
“在哪儿我都认得出费纳那张脸。”
“哦,那可能是其他人,这没什么大惊小怪的。”
“可之前,费纳肯定地告诉我是他来驾驶的呀。”
“那他们一定改变了计划,让他去开另外一架了吧。”
“那这人又是谁呢?”
“亲爱的小伙子,我怎么会知道?你以为每个空军上尉的脸我都能记得住吗?”
“他们中的很多人我都认识,可我不认识这家伙。”
“那他一定恰好是你不认识的某一个了。”康维笑了笑继续说,“我们很快就要到达白沙瓦了,到时你去和他认识一下,亲自问问不就得了。”
“这样下去,我们可根本到不了白沙瓦,飞机完全偏离了正常航线,又飞得那么高,根本看不清到了哪里。”
康维并不担心,他已经习惯了坐飞机旅行,所以对一切都想当然了。更何况,到白沙瓦之后,他没什么特别急于要做的事,也没有什么非常想见的人,所以,管它飞四个小时还是六个小时,他毫不在意。他还是单身,到了白沙瓦也不会有什么温馨接待。他倒是有些朋友,有几个也许会带他去夜总会喝喝酒,这是一种惬意的期待,但也还不足以让他特别渴望。
当他回顾过去那令人欣慰,却不完全让他满意的十年时光时,并没有那种怀旧式的叹息。一切变幻无常,短暂的空闲之后又是纷乱和不安定,这就是他对自己过去那段时间的最好总结,也是对世界局势的概括。他想起巴斯库尔、北平、澳门和其他一些他经常去的地方,最遥远的要数牛津,战后他曾回到那里教过几年书,讲授东方历史;在阳光充足的图书馆里查阅那些尘封的资料;推着自行车在校园漫步,这景象很吸引人,但他并不会为此而激动。他仍有一种感觉,感觉自己仍是过去的一部分。
一阵熟悉的倾斜,告诉他飞机就要降落。他本来很想拿马林森那副坐立不安的样子开涮,谁知那小子霍地站了起来,头“嘭”的一声撞到舱顶上,把正坐在过道另一边打瞌睡的美国人巴纳德弄醒了。“老天!”他惊叫起来,“快看下边。”
康维也凑过去看,可看到的确实不是他所预料得到的,如果说他真预料到了什么的话。他看到的不是按几何图案整齐排列的军营和巨型的长方形机库,呈现在他眼前的是一片茫茫的浓雾,浓雾下是一片广阔荒原,被太阳烤成了红褐色。虽然飞机在迅速下降,但仍然远远高出了普通的飞行高度。从他那个角度,隐约可以辨出一些长长的,呈波状起伏的山脉,这些山脉离云雾缭绕的山谷大概只有一英里,尽管康维以前从未从这种海拔高度观察过,但这确实是典型的边疆景色,给人一种怪异而深刻的印象。这让他感觉,白沙瓦肯定不在附近。“我看不出这到底是个什么地方。”他喃喃说着。然后悄声——他不想惊动别人——对马林森耳语道:“看样子你是对的,这飞行员迷失航向了。”
随着飞机以惊人的速度下降,空气变得越来越热,下面的土地灼热得就像是突然开膛的火炉。起伏绵延的山脉从地平线上隆起峻峭嶙峋的身影。飞机掠过高峰,沿着一条蜿蜒的山谷飞行,谷底干涸的河床上布满岩石,看上去就像撒满栗子壳的地板;飞机在气流中颠簸得十分剧烈,就像遇上了浪涛的小船,让人受不了。四位乘客都不得不紧紧抓住座位。
“看来他要着陆了!”美国人用嘶哑的声音大叫道。
“这不可能,”马林森反驳道,“除非他疯了,想让飞机坠毁,然后……”
然而,飞机果真着陆了。飞行员熟练地将飞机滑向一条溪谷旁的小空地,最后稳稳地停住了。此后发生的事情更让人疑惑和担忧。一群满脸络腮胡、包着头巾的土著人从四面八方冲过来,把飞机团团围住,除飞行员外不让任何人下飞机。那飞行员爬下飞机后和他们激烈地交谈着,很显然,他确实不是费纳,也不是英国人,甚至连欧洲人都不是。这时,那些人从附近的油料堆里拿来了几桶汽油,然后倒进容量超大的飞机油箱。被困在飞机里的四位乘客愤怒地喊叫着,那些人要么报以幸灾乐祸的笑容,要么干脆不予理睬。他们若试图下飞机,哪怕是最轻微的动作都会招来二十支枪的恐吓。康维懂一点当地的普什图语,便大声和这些人理论,但是什么作用也起不了。而当他试图用任何一种语言与飞行员交涉,那家伙只有一个反应,那就是举起他手中的左轮手枪,略带挑衅地向康维挥舞。正午的太阳火焰般在机舱顶部炙烤着,机舱内的空气闷热得令人窒息,再加上竭力的抗争,他们都快要昏过去了。然而他们最终毫无办法,因为在疏散撤离时一律不准携带武器。
终于,飞机加满了油,油箱盖也拧上了。一只装满温水的油桶从机窗口递了进来,尽管这群人好像并无敌意,可他们对任何问题都缄口不答。同那帮人又交谈了半天之后,飞行员回到机舱,一个普什图人笨拙地转动了一下螺旋桨,飞机又启动了。尽管是在这么个狭窄的地方,而且飞机还满载那么多汽油,可起飞似乎比降落还要灵巧熟练。飞机又高高地升入漫漫云雾之中,随后转向东方,似乎在调整航线。这时已是午后。
这一切真是非同寻常,而且又是多么令人迷惑!当凉爽的空气让他们清醒过来时,这些乘客几乎不能相信这事发生过。这样的恐怖事件,在动荡不安的前线所发生的各种混乱事件中也找不出先例。要是他们几个没有成为牺牲品倒会让人难以置信。怀疑之后便是愤怒,这是很自然的,而愤怒之后则是惶恐和焦虑。马林森给出了他的推测:他们被绑架了,有人要进行勒索。除此之外也没有更容易让大家接受的说法了。这种把戏太老套了,但所用的手段却颇为特别,而且十分高明。想到眼下他们的遭遇也不是没有发生过,大家心里多少舒坦了些。绑架案时有发生,而且多数也都以好的结局收场。这些土著人最多把你关进山洞,等政府付够了赎金,就把你放掉;你会受到客气的对待,而且那些赎金也不是你自己的,这种事最多有些令人难堪罢了。然后呢,空军部队就派出一队轰炸机,而你得以安全离开,余生便有一段精彩故事讲给大家听了。
马林森慌慌张张地讲述了自己的想法,巴纳德这个美国人却显得很滑稽:“先生们,我敢说在某些人看来,这可能的确是一种聪明的推测,可我看不出你们的空军到底有什么辉煌的战绩。你们英国人常拿芝加哥等地的劫机事件开玩笑,而我可想不起有过持枪歹徒驾着某架山姆大叔的飞机逃跑的先例。我还感到怀疑的是,这家伙是如何搞定原来那位飞行员的。我打赌他多半被塞进沙袋里了。”说罢,他打了个哈欠。他身材高大而肥胖,一张顽固的脸上刻着滑稽的皱纹,但这并不能抵消他略带悲观色彩的眼袋。在巴斯库尔,没人对他有更深的了解,只知道他来自波兰,有猜测说他做点与石油搭边的生意。
而这时康维正忙着一件更实际的事情。他把每个人身上的纸片收集起来,然后在上面用各种语言写上求救信息,每隔一会儿就朝地面扔几张。在这种人烟稀少的地方,虽然希望渺茫,但还是值得一试。
机上第四位乘客,布林克罗小姐这会儿紧绷身子坐着,双唇紧闭,一言不发。她是个弱小而坚韧的女人,带着一种被迫参加聚会,却对聚会上那套玩意儿不能苟同的神情。
康维没有另两位男士那么多话,因为把求救信息翻译成各种语言是一项需要集中精力的脑力活儿。不过,如果问到他,他仍会作出回答,他还对马林森的绑架说表示了模棱两可的赞同。马林森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同意巴纳德对空军的责难。“虽然不难发现,这事儿是怎么发生的:在一个骚乱的地区,那些身着飞行装备的人看起来都没什么两样,没有人会想到去怀疑这么个有着专业装备的人,况且他看起来还非常懂行。这家伙懂飞行信号之类的,而且很明显,他还知道怎么飞行……还有,我同意你的看法,这种事情肯定会有人倒霉,有人要惹麻烦的,你完全可以相信,尽管我怀疑不是他。”
“很好,先生,”巴纳德说道,“你能看到问题的两方面,我很佩服。无疑,这是最合适的态度,就算你被骗了也要这么有风度。”
康维心里很清楚,他们喜欢说些傲慢的话,但也不冒犯人,他客气地笑了笑,没有再说什么。他感到十分疲倦。那是一种知道随时可能遭遇不测,却又无法逃避的无可奈何的困倦。直到快傍晚的时候,巴纳德和马林森还在争论不休,其中有一两个看法,康维还听得进去,可当他俩向他征求意见时,却发现他已经睡着了。
“累坏了,”马林森说,“忙了几星期,也难怪。”
“你是他朋友?”巴纳德问。
“我和他在领事馆共过事,我也只是碰巧知道他已四天四夜没合眼了,实际上,我们真算是走运了,有他和咱们一起被困在这该死的机舱里。他除了会许多种语言,还自有一套与人打交道的办法,如果能够帮助我们摆脱困境的话,他会去做的,他处事总是很冷静。”
“好吧,那就让他好好睡吧!”巴纳德表示同意。
布林克罗小姐嘴里终于迸出一句话:“我倒觉得他像个勇敢的男人。”
康维反而不确信自己是个非常勇敢的人。他实在太疲倦了,他在闭目养神但并没有睡着,他能听到和感觉到飞机在空中的飞行,而且也听到马林森对自己的那一番称赞,他的心里虽感到得意但又有些忧虑。这会儿他感到有些反胃,他精神焦虑不安时就会有这种身体反应。以过去的经验,他很清楚,自己并不属于那种为冒险而冒险的人。虽然在某种程度上,这件事情让他也感到有一种冲动,那是一种让沮丧迟钝的内心世界得到净化、洗礼的冲动。但他绝不愿拿性命开玩笑。早在十二年前,他就开始对法国战壕里残酷的冒险深恶痛绝了,他好几次正是拒绝了毫无意义的无畏行动才免于一死。甚至他那准尉军衔的获得也并非是凭借勇气和胆量,而是靠某种很不容易才训练出来的耐性。自从开战以来,无论什么时候遇上危险,他都渐渐对它们失去了兴趣,除非是遇上那种让他感到极度刺激的危险。
他仍闭着眼睛,听到马林森刚才的话,他有所触动,乃至有些沮丧。命中注定,他的镇定总是与勇气相悖,而现在这种心态,实际上是缺乏男子汉气概的表现。在他看来,大家正处于一种糟糕透顶的尴尬处境,而他心里非但没有激起充分的胆量与勇气,反而对将要降临的任何麻烦都感到极度的厌恶。他预见到在某些情况下他必须按照推测来行动。比方说眼下这位布林克罗小姐,她是个女性,她要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在意这事,他担心在这种场面自己难免会做出不太合适的举动。
他装出一副刚刚醒来的样子,随后就同布林克罗小姐交谈起来。他发现她既不年轻也不漂亮——其人品也不敢恭维。不过,在这种困境中,这样的人却非常可靠,因为正是在这样的处境之中,他们会很快发现自己的优势并加以发挥。他同时也为她感到遗憾,因为他注意到马林森和那个美国人都不喜欢传教士,特别是女传教士。他本人倒没有什么成见,但是他却担心她对他的直率不太习惯,甚至觉得有点难为情。“看样子,我们好像是陷入困境了,”他对她轻声说道,“但是我很高兴你能如此冷静应付。况且我并不认为真的会大难临头。”
“如果你能阻止的话,那就肯定不会发生。”她的回答丝毫没有让他有所安慰。
“如果能做些什么让你轻松些,请务必告诉我们。”
巴纳德扯着嗓子打断了他们。“轻松?”他喊道,“这是什么意思?我们可不就是很轻松嘛。我们正在享受旅行的愉快,遗憾的是我们没有扑克——要不我们还可以玩上几局桥牌。”
康维不喜欢打桥牌,但他很欣赏这样的乐观态度。“我想布林克罗小姐不玩牌。”他笑着说。
可我们的传教士却轻轻转过身来反驳道:“我还真会打牌,而且,我从来没觉得打牌有什么害处,《圣经》里也没有任何反对打牌的教条。”
他们都笑起来,似乎是感激她给他们找到一个开脱罪行的理由。不管怎么说,康维并不认为她有任何歇斯底里的倾向。
整个下午,飞机一直在高空的薄雾中航行,由于飞得太高,他们看不清楚下面。每飞过一段较长的距离,这些轻纱般的薄雾间或消散开,下面就呈现出凸凹不一的山峰的锯齿状轮廓,某条不知名的河流闪烁着隐隐波光。根据太阳的位置,能够粗略判断出飞机仍在向东飞行,时而略偏北;至于具体会飞向何处,还得根据飞行速度判断,这康维就没法准确推测了。可以推测的是,飞机恐怕已消耗了大量燃油;不过,这也得取决于具体情况,康维并不了解飞机的技术性能,但他坚信,不管这飞行员是谁,总之一定是个行家;能在乱石密布的山沟里安全着陆就足以证明这一点,之后的其他事情也可以证实。康维心里有一种无法抑制的情感,一种他与生俱来的,每当感受到自己拥有无可争议的才能时而产生的情感。他太习惯于别人向他求助了,以至于当他意识到某个人不想求助也不需要帮助时,都会平静下来,甚至在之后更令人窘困的场合中,也能保持头脑清醒和冷静。可是,康维并不打算和他的同伴们分享这种微妙的情感。他很清楚,比起他自己,这几位出于各自的理由,应该有更多的焦虑。比如,马林森已经同一个姑娘在英国订了婚;巴纳德也可能已经结婚了;布林克罗小姐则有工作、假期什么的。不知是否出于偶然,马林森恰恰又是最不镇定的一个,随着时间一小时一小时过去,他也变得越来越激动和敏感,并且开始对康维那一脸冷漠和平静的表情表示不满了,刚才他还在背地里对这种冷静大加称赞过一番呢。不一会儿,一场激烈的争论在飞机发动机的轰鸣声中爆发了。“看看,”马林森气冲冲地吼道,“难道我们就这样坐在这儿,听任这疯子为所欲为而无动于衷吗?怎么样能不砸掉隔板就把那家伙弄出来?”
“没有任何办法,”康维应道,“他有武器,而我们没有。另外,我们中间可没人会操纵飞机使它着陆。”
“这不难,我敢说你就能办到。”
“亲爱的马林森,为什么总是要我去创造这种奇迹呢?”
“唉,总之现在这种情况我已经烦透了;难道咱们就没办法让这家伙着陆吗?”
“你觉得该怎么做呢?”
马林森愈发焦躁。“嗨,他不就在那儿吗?差不多就离我们六英尺,而且是三个对付一个呀!难道就这样干瞪着他那该死的背影?至少可以逼他讲出一些真相啊。”
“好吧,那试试看。”康维说着,三步并作两步朝客舱与驾驶舱之间的隔板走去。驾驶舱位于飞机前端的上部,有一块六英寸见方的滑动玻璃隔板,飞行员头一转,就可以俯下身子透过它与乘客交流。康维拿手敲了几下玻璃隔板,如他所料,里面的反应滑稽可笑。玻璃滑到一边,一支左轮手枪伸出来冲他指了指,半句话没说,康维也没有与那家伙做什么争辩就退了回来,玻璃板又给关上了。
眼看是这样的结果,一直静观事态的马林森可不满意。“我不认为他真敢开枪,”他嘀咕道,“吓唬吓唬人罢了。”
“是的,”康维表示同意,“所以我觉得最好是你去证实一下。”
“我倒觉得咱们应该起来反抗,而不是任其摆布。”
康维表示赞同。从所有的英国军队和学校的历史教科书中,他了解这种已成惯例的传统认识:英国人永远英勇无畏,从不投降,且常胜不败。而他说的却是:“没有把握仓促上阵,这是很不明智的举动,我可不逞这种强。”
“说得好,先生,”巴纳德热情地插话进来,“当你被人任意摆布的时候,要心甘情愿,听之任之,逆来顺受呀,比如我,活一天就享受一天,来支雪茄吧!我希望你们别指望会有更多危险了。”
“我倒不介意,不过恐怕会影响到布林克罗小姐。”
巴纳德马上反应过来,赔礼道:“对不起,女士,我抽支烟,你不会介意吧?”
“啊,不不,”她通情达理地答道,“我自己虽不抽,但我喜欢雪茄的味道。”
康维认为所有的女人大概都会这么回答的,布林克罗小姐自然是最为典型的一个。无论如何,马林森的激动情绪稍稍平复了一些。为了示好,他给康维递上一支,自己却没抽。“我了解你的感受,”康维温和地说道,“前景很不妙,从某种程度上说可能会更糟,毕竟面对这种事我们没什么办法可想。”
“换个角度,也有可能朝好的方面发展呀。”他不禁又补了一句。他仍然感到疲惫不堪。他的性格中有某种一般人称作“懒散”的东西,虽然不是很明显。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没有人有本事去解决更棘手的问题,而且很少有人会更好地承担责任。实际上,他并不热衷于行动,也根本不想去承担什么责任。两点都体现于他的言行之中,而他把这两者结合得恰到好处。可他总盘算着让其他能够胜任或者能干得更出色的人来做这些事情。在某种程度上说,无疑正是这种小聪明使他在部队中获得了荣誉,也可以承担比预期更小的风险。现在,他没有足够的野心和勇气把责任硬推给别人,或者在真正无事可做的时候,为自己的无动于衷作一番振振有词的辩护。他的敏捷有时只能被简单地看做一种草率的举动,而他在危急时刻的冷静却令人钦佩,也经常让人觉得他过分谨慎。官方人士却更愿意认为康维是一个勇于承担责任的人,他表面上的冷淡,只不过是在掩藏他丰富而良好的情感和修养。一种暗暗的怀疑一直伴随着康维,有时这种怀疑会不断地涌上心头,难道他真的是表里如一地沉着冷静,无论发生什么事都一点不在乎?不过,正如“懒散”这词用在他身上并不合适,大多数外人对他的看法同样有失偏颇,其实他的这种个性,非常简单却令人迷惑——他只是喜欢清静、沉思,并且喜欢独处。
他已侧身坐了很长时间,眼下他也没什么能做的,于是干脆靠回座位睡起来。醒来时,他发觉几位同伴也放下先前的种种担忧和焦虑,照样屈服了。布林克罗小姐身体僵硬,闭目坐着,像一尊失去光泽的、废弃的塑料模特;马林森弓着身子,懒洋洋地坐着,一只手撑着下巴;而那个美国人正鼾声如雷。之前的争吵让他们感到很困倦。忽然,康维感到自己身上涌起一阵轻轻的眩晕,心跳也加快了,然后觉得有一种力量在猛烈地吞噬自己。他记得过去曾有过一次类似的反应,那是在瑞士的阿尔卑斯山上。
过了一会儿,他转头朝窗外望去。只见天空碧蓝如洗,午后的明媚阳光下,有一种梦幻般的景色向他飘来,仿佛一下子就把他余下的氧气从肺里吸了出来。远处,视野的尽头,隐隐呈现出绵延重叠的雪山峰峦,被冰雪装点得银光闪闪,雪峰仿佛飘浮在绵绵的云层之上。飞机整整盘旋了一周,然后向西飞去,渐渐同地平线叠合在一起。地面的色彩强烈而炫目,几乎有些花哨,仿佛是几个神志不清的印象派怪才笔下的画布。此时,在这巨大的舞台之上,飞机伴着嗡嗡声沉闷地盘旋在一个深不可测的峡谷上方,对面是一堵陡峭的白色悬崖,若没有阳光的照射,仿佛就是天空的一部分,就像从莫林看到的层层叠叠的少女峰闪耀着的灿灿银光。
普通的事物很难给康维留下印象,他也不太留心“风景”,尤其不屑于那些被“考虑周到”的市政当局装设了坐椅的著名景区。一次,有人带他到印度大吉岭附近的老虎岭,去看珠穆朗玛峰的日出,他却对这世界最高峰感到很失望。而此刻窗外的这一令人生畏的奇观则完全不同,它没有一点矫揉造作,在那傲然屹立的雪山冰峰中,蕴藏着某种自然原始而神奇的力量,一种壮丽雄奇之中交织着苍莽与粗粝的风格,令人感到难于接近。康维陷入了沉思,想着在地图上大概的位置,推算着距离、时间和航速。过了一会儿,他发现马林森也醒了过来,便拍了拍这小伙子的胳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