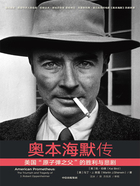
第4章
“这里的工作很不容易,所幸还算有趣”
我想你会喜欢哥廷根的……这里的科研比剑桥好得多,总的来说,恐怕找不到比这更好的地方了……这里的工作很不容易,所幸还算有趣。
——罗伯特·奥本海默写给弗朗西斯·弗格森的信,1926年11月14日
1926年夏末,跟一年前相比,奥本海默无论精神状态还是内心成熟度都可谓今非昔比。他坐火车经过下萨克森州,最终抵达哥廷根。哥廷根是一座中世纪的小镇,小镇引以为豪的是可以追溯到14世纪的一座市政厅和几座教堂。在赤脚街和犹太人街的拐角处,奥本海默可以坐在有400年历史的容克大厅里吃维也纳炸肉排,他头顶上有奥托·冯·俾斯麦的钢版画,这里的三层楼都装饰着彩色玻璃花窗。小镇狭窄蜿蜒的街道上随处可见古色古香的半木结构房屋。哥廷根坐落在莱讷河畔,其主要景点是哥廷根大学,18世纪30年代由德意志汉诺威公爵兼英国国王乔治二世创建。按照传统,该大学的毕业生都要蹚水走入一座喷泉,并亲吻喷泉中心的牧鹅女青铜像,这座喷泉就矗立在古老的市政厅前。
如果说剑桥大学是欧洲实验物理学的中心,那么哥廷根大学无疑就是理论物理学的中心。当时的德国物理学家对他们的美国物理学同行不以为然,以至于美国物理学会的月刊《物理评论》通常在出版1年多之后仍无人问津,最终被大学的图书管理员束之高阁。
奥本海默的幸运之处在于他赶上了一场理论物理学伟大革命的尾声,在这场革命中马克斯·普朗克提出了量子理论,爱因斯坦提出了伟大的狭义相对论,尼尔斯·玻尔提出了氢原子结构模型,还有维尔纳·海森伯的矩阵力学,以及埃尔温·薛定谔的波动力学。随着1926年玻恩发表了关于概率解释和因果关系的论文,这个真正意义上的创新时期也接近了尾声。1927年,海森伯的不确定性原理和玻尔的互补原理给这一时期画上了句点。奥本海默离开哥廷根时,后牛顿物理学时代的基础已经奠定。
作为物理系主任,马克斯·玻恩教授指导了海森伯、尤金·维格纳、沃尔夫冈·泡利和恩里科·费米的工作。1924年玻恩创造了“量子力学”这个名词,他指出量子世界中任何相互作用的结果都是由概率决定的。1954年,玻恩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作为和平主义者和犹太人,在学生眼中,玻恩是一位极富热情和耐心的老师。对像奥本海默这样敏感细腻的年轻学生来说,他是一位理想的导师。
1926年那一学年,奥本海默发现自己身边有一群了不起的科学家。詹姆斯·弗兰克也是奥本海默的老师,他是一位实验物理学家,一年前刚刚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奥本海默身边的科学家还包括:德国化学家奥托·哈恩,他将在短短几年内为核裂变的发现做出贡献;德国物理学家恩斯特·帕斯库尔·约尔当,他正与玻恩和海森伯创立量子理论的矩阵力学;奥本海默在剑桥遇到的年轻的英国物理学家保罗·狄拉克,当时他正在研究早期量子场论,1933年他将与埃尔温·薛定谔共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出生于匈牙利的数学家约翰·冯·诺依曼,他后来为奥本海默的曼哈顿计划工作过;出生于印度尼西亚的科学家、荷兰人乌伦贝克,他和古德斯密特一起在1925年年末发现了电子自旋。奥本海默很快引起了这些人的注意。前一年春天,在为期一周的莱顿大学访问期间,他已经见过乌伦贝克。“我们很投缘。”乌伦贝克回忆道。奥本海默对物理也相当痴迷,乌伦贝克甚至觉得“我们简直一见如故”。
奥本海默在一座私人别墅找到了栖身之所,这座别墅的主人是哥廷根的一位医生,他因医疗事故被吊销了行医执照。这位医生出身卡里奥家族,他们曾经非常富有,但是现在不名一文,只剩下这座位于哥廷根中心位置的别墅,这座花岗岩别墅非常宽敞,还带一个占地数英亩的有围墙的花园。一战后,德国的通胀蚕食了这个家族的财富,他们不得不招揽房客。奥本海默精通德语,他很快就感知到了魏玛共和国日益衰弱的政治影响力。后来他猜测卡里奥一家“怀有那种为纳粹运动提供土壤的怨恨之情”。那年秋天,奥本海默在给弟弟的信中写道,所有人都在关心“如何让德国成为一个现实中成功且理性的国家。他们对多愁善感憎恶之极。令他们厌恶的还有犹太人、普鲁士人和法国人”。
在大学校门之外,奥本海默看到大多数德国人都在艰难度日。“虽然这个大学里的人都非常富有,对我也和蔼友善,但是它所处的德国笼罩在悲惨的气氛之中。”他发现很多德国人都“心怀愤恨,阴沉郁闷……甚至怒火中烧,他们身上充满了导致后来那场大灾难的一切要素”。奥本海默有一位德国朋友来自富有的乌尔施泰因出版家族,他有一辆汽车,他和奥本海默过去常常一起长途驱车在乡间兜风。但是奥本海默惊讶地发现,他的朋友竟然“把车停在哥廷根城外的一座谷仓里,因为他担心被人看到开这辆车会有危险”。
对于美国侨民,特别是对奥本海默来说,生活完全是另一番景象。首先,他手头从不缺钱。22岁的他着装很随意,但是他身上那套皱巴巴的西装布料是英国最上等羊毛制成的人字呢。奥本海默的同学们还注意到他用的行李箱也与与众不同,那是昂贵的、泛着光泽的猪皮行李箱,而他们用的是布制行李箱。同学们有时会一起漫步到始于15世纪的黑熊酒吧喝鲜酿啤酒,有时还会去克龙科恩兰茨咖啡馆喝咖啡,但基本上是奥本海默买单。现在的他就像变了一个人,他十分自信、充满激情且目标明确。物质财富对他来说无足轻重,但来自他人的崇拜不可或缺。为达目的,奥本海默动用了他的机智风趣、博学多闻及那些不菲之物来吸引他看中的人,将他们俘获到自己身边,成为他的崇拜者。乌伦贝克说:“这么说吧,他就是所有年轻学生的中心……他真像是一位先知。他知识渊博。理解他并非易事,而且他才思敏捷。”在乌伦贝克看来,这样年纪轻轻就已经有“一群崇拜者”追随其后,实在是令人称奇。
与在剑桥大学时不同的是,奥本海默在哥廷根大学与同学们建立了令人愉悦的同窗情谊。“我是一个小圈子中的一员,这个圈子里的人有一些共同的兴趣和品味,在物理学领域,我们更是志趣相投。”在哈佛大学和剑桥大学,奥本海默获取知识的主要途径是书籍;在哥廷根大学,他第一次意识到自己可以从别人那里学习。他说:“我开始经历一些重要的变化,这些变化对我比对别人更有意义,也就是说,我开始与他人交流。我猜就是这些交流让我逐渐对物理学有了一些认识,慢慢地,我也有了物理学的眼光,如果我一直将自己锁在屋里,就永远不可能得到这些。”
和奥本海默一起寄宿在卡里奥家别墅的还有卡尔·泰勒·康普顿,39岁的康普顿是普林斯顿大学的物理学教授,后来他还担任过麻省理工学院的校长。在奥本海默面前,他会感到有些畏惧,因为奥本海默的多才多艺让人惊叹。如果谈论的话题是科学,他还可以和这位年轻人打个平手,一旦谈论文学、哲学甚至政治,他就不知所措了。奥本海默在给弟弟的一封信中曾提到那些在哥廷根的美国人,毫无疑问,他写信的时候一定想到了康普顿,他说那些美国侨民“都是普林斯顿、加州或其他什么地方的教授,均已成婚,生活体面。他们主要擅长物理学,但是完全未经文化熏陶。他们嫉妒德国人的才智和组织能力,还想把物理学也带到美国去”。
简而言之,奥本海默在哥廷根得以茁壮成长。那年秋天,他热情洋溢地给弗朗西斯·弗格森写信说:“我想你会喜欢哥廷根的。像剑桥一样,这里以自然科学为主,这里的哲学家主要感兴趣的是认识论的悖论问题和那些小把戏。这里的科研比剑桥好得多,总的来说,恐怕找不到比这更好的地方了。这里的人工作都非常努力,他们绝不轻易袒露自己的想法,但又有壁纸制造商一般志在必得的野心。结果就是,他们完成的工作简直像借魔鬼之手一般不可思议,又极其成功……这里的工作很不容易,所幸还算有趣。”
大多数时候,奥本海默都觉得自己情绪平稳,但是偶尔也有短暂的反复。有一天,保罗·狄拉克看见他晕倒在地上,就像前一年在卢瑟福实验室发生的那一幕。“我还没有彻底康复,”奥本海默几十年后回忆道,“那一年又发作了好几次,但是间隔越来越长,对我工作的干扰也越来越小。”那一年,另一位物理学专业的学生索尔芬·霍格内斯和他的妻子菲比也住在卡里奥家的别墅,他们发现奥本海默有时行为古怪。菲比经常看到他躺在床上无所事事,但蛰伏期过后,他又开始喋喋不休。菲比认为他“非常神经质”。偶尔还有人见过奥本海默有口吃的问题。
奥本海默变得越来越自信,与此同时,他发现自己已经名声在外。在离开剑桥大学前,他向剑桥哲学学会递交了两篇论文,一篇是《量子理论中的振动-转动谱带》,另一篇是《关于二体问题的量子理论》。前一篇关注的是分子能级问题,后一篇研究的是氢原子向连续态的转变。这两篇论文都在量子理论领域取得了微小但重要的进展,奥本海默到达哥廷根时欣然获悉剑桥哲学学会发表了这两篇论文。
论文的发表使奥本海默获得了更多的认可,其结果就是他狂热地参与各种学术讨论,他那些任性的举止经常惹恼他的同学们。“他天赋极高,”马克斯·玻恩教授后来写道,“他无法放下自己的优越感,这既令人尴尬又会惹来麻烦。”在玻恩的量子力学讲座上,奥本海默经常打断别人的发言,当然玻恩本人也不能幸免,奥本海默会手拿粉笔走到黑板前,用他带着美国口音的德语宣布:“用下面这种方法会好得多……”虽然其他同学对奥本海默的无礼抱怨不迭,他的老师也勉为其难地、礼貌地规劝过他,但是奥本海默本人对此无动于衷。但是有一天,玛丽亚·格佩特——一位未来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向玻恩递交了一份请愿书,这份请愿书写在厚厚的羊皮纸上,上面有包括她本人在内的大部分讲座参与者的签名。请愿书上写着,除非这位“神童”有所收敛,否则他的同学们将罢课。玻恩仍不愿意与奥本海默当面对质,他决定把请愿书放在奥本海默来找他讨论论文时肯定会看到的地方。玻恩后来写道:“为了保险起见,我还安排别人把我叫出去一会儿。这招真得奏效了。当我回到屋里时,我发现他脸色苍白,也不像平时那样滔滔不绝。”从那以后,奥本海默再也没有打断过别人的发言。
这并不意味着他被完全驯服了,奥本海默的直言不讳经常让他的教授也颇为震惊。虽然玻恩是一位杰出的理论物理学家,但是在那些冗长的计算过程中他有时会出些小差错,所以他经常请一位研究生重新检查他的数学运算。玻恩回忆说,有一次,他把对一组运算的检查工作交给了奥本海默。几天之后,他反馈说:“我找不到任何错误,所以这真是你一个人完成的吗?”玻恩所有的学生都知道他计算容易出错,但是正如玻恩后来写道的那样:“奥本海默是唯一一个能直截了当、毫不留情地说出这些话的人,他不是在开玩笑。我并没有觉得被冒犯,实际上这倒让我更加尊重他与众不同的个性。”
不久后,玻恩开始与奥本海默合作。在这一时期,奥本海默曾给他在哈佛大学的物理学教授埃德温·肯布尔写过一封信,这封信是一篇名副其实的工作总结:“几乎所有的理论物理学家都在研究量子力学。玻恩教授准备发表一篇关于绝热定理的论文;海森伯写的论文是关于波动的;也许最重要的是泡利的一个想法,他认为薛定谔方程中的波函数只是特例,而且只在特殊情况下(即原子光谱)才能给出我们想要的物理信息……我已经研究了一段时间量子理论中的准周期现象……我和玻恩教授研究的另一个问题是粒子的散射规律,比如α粒子经过原子核时发生的偏转。在这方面,我们还没有多大进展,但是我想很快就会有所突破。当然,这个理论一旦成形,它肯定不会像之前基于微粒动力学的旧理论那么简单。”肯布尔教授对这封信的内容印象深刻。在哥廷根待了还不到3个月,他教过的这位学生似乎已然沉浸在揭开量子力学奥秘的兴奋之中。
1927年2月,奥本海默认为自己已经掌握最新的量子力学知识,他对此颇有自信,于是他写信给他在哈佛大学的物理学导师珀西·布里奇曼,细致地阐释了量子力学:
在经典的量子理论中,如果两个低势能区被一个高势能区隔开,那么在任一低势能区的电子必须吸收足够的能量才能清除“障碍”——穿越高势能区,到达另一个低势能区。而根据新的理论,上述理论已经不再正确:电子有时在一个区域,有时在另一个区域……一方面新的量子力学理论提出了新的观点,然而在这一理论中看似“自由”的电子并不“自由”,因为它们携带的是均分的热能。为了解释维德曼-弗兰兹定律,可能需要采纳玻尔教授的观点:当一个电子从一个原子跃迁到另一个原子时,这两个原子会交换动量。顺祝一切安好。
您的J.R.奥本海默
奥本海默对新的量子理论信手拈来,作为他之前的老师,布里奇曼显然深受触动。但是奥本海默为人处世不懂分寸,这让其他人对他心存芥蒂。前一刻他还令人着迷、体贴周到,下一刻他就会粗鲁地打断别人。在宴席上,他一方面极为客套有礼,另一方面又无法忍受别人的陈词滥调。他的同学爱德华·U.康登抱怨道:“奥比的问题在于他反应太快,这让别人处于下风。而且,见鬼,他总是对的,或者至少言之成理。”
康登1926年刚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获得了博士学位,他现在仅有微薄的博士后津贴,还要用这笔收入养活自己的妻子和刚出生的孩子,日子过得捉襟见肘。让他懊恼的是,奥本海默在美食和质地精良的服装上花钱大手大脚,就好像对自己朋友的家事毫不知情。有一天,奥本海默邀请康登和他的妻子埃米莉·康登出门散步,但是埃米莉说自己必须留下来照顾孩子。奥本海默接下来说的话让夫妇二人倍感震惊,他回应说:“好吧,那你就留下来干这些乡下人的活计吧。”奥本海默确实偶尔说话尖酸刻薄,但他也会不时表现出自己富有幽默感的一面。有一次,他见到卡尔·泰勒·康普顿两岁大的女儿正在假装读一本小红书,那本书讲的是计划生育,奥本海默打量了一下又要临产的康普顿太太,揶揄道:“有点儿晚了。”
1927年冬季的那个学期,保罗·狄拉克到了哥廷根,他也在卡里奥家的别墅租了一个房间。对奥本海默来说,与狄拉克交往是人生乐事,他曾说:“狄拉克来了以后,给我看了他讨论辐射的量子理论的论文校样,这是我人生中最激动人心的时刻。”这位来自英国的年轻物理学家对奥本海默广泛的兴趣爱好感到费解。狄拉克对奥本海默说:“他们告诉我,除了研究物理,你还写诗。你如何能做到二者兼顾呢?在物理学领域,我们帮人们理解那些之前未知的东西,而诗歌恰恰相反。”奥本海默把这些话视为赞美,他只是付之一笑。奥本海默知道,对狄拉克来说,生活就是物理,没有别的;相比之下,他的兴趣则丰富多彩、无所不包。
奥本海默仍然热爱法国文学,在哥廷根的时候,他抽时间阅读了保罗·克洛岱尔的情节喜剧《少女维奥兰》,弗朗西斯·斯科特·菲茨杰拉德的短篇小说集《明智之举》和《冬天的梦》,安东·契诃夫的戏剧《伊凡诺夫》及约翰·荷尔德林和斯蒂芬·茨威格的作品。有一次,奥本海默发现有两位朋友经常读意大利语原文的但丁作品,随后他从哥廷根的咖啡馆消失了一个月,当他再次出现的时候,他已经可以用意大利语大声朗读但丁的作品。狄拉克不仅不以为然,还发牢骚说:“你为什么要在这些垃圾上浪费时间?我觉得你在音乐上还有你收藏的那些画上花了太多时间。”当他们在哥廷根漫步的时候,狄拉克不止一次劝他放弃这些过于感性的爱好,奥本海默对此只是一笑置之,他惬意地活在狄拉克无法理解的世界里。
哥廷根并非只有物理学和诗歌。奥本海默发现自己迷上了一位名叫夏洛特·里芬斯塔尔的德国女生,她是物理学专业的学生,也是校园里最漂亮的女生之一。他们相遇在一次去汉堡的学生旅行中,那次旅行在汉堡逗留了一个晚上。里芬斯塔尔在火车站的月台上候车时,她的目光被一只行李箱吸引,在一堆行李箱中只有这一只既不是便宜的纸板箱也不是破旧的棕皮箱。
“好漂亮啊,”她手指着那只发亮的棕黄色猪皮随身行李箱问弗兰克教授,“这是谁的?”
“除了奥比,还能有谁。”弗兰克耸了耸肩说道。
在回哥廷根的火车上,里芬斯塔尔叫人指给她看谁是奥本海默。然后她坐到了奥本海默的旁边,当时他正在读当代法国小说家安德烈·纪德的小说,纪德的作品多关注个体对世界的道德责任。让奥本海默惊讶的是这位漂亮的女生也读过纪德,而且能和他头头是道地讨论。火车抵达哥廷根时,里芬斯塔尔还漫不经心地提到她有多么喜欢他的行李箱。奥本海默感谢了她的夸赞,但让他不解的是怎么还会有人费心去欣赏他的行李箱。
里芬斯塔尔后来又把他们的对话讲给另一位同学听,这位同学预言奥本海默很快就会把行李箱送给她。奥本海默有很多怪癖,其中一个众人皆知的就是一旦有人喜欢上他的东西,他就觉得必须送给对方。奥本海默被里芬斯塔尔迷住了,尽管他无法摆脱自己那呆板又过于客气的举止,他依然在尽其所能地追求她。
里芬斯塔尔的追求者中还有一位奥本海默的同班同学——弗里德里希·格奥尔格·豪特曼斯,作为一位年轻的物理学家,他已经因一篇论述恒星能量生成的论文而为人所知。豪特曼斯的朋友们称他为“弗里茨”或“菲兹”,和奥本海默一样,他来哥廷根求学时也有家族信托基金的资助。豪特曼斯的父亲是一位荷兰银行家,母亲是有一半犹太人血统的德国人,他对此从不避讳。豪特曼斯蔑视权威,有一种无所顾忌的幽默感,他喜欢对那些非犹太朋友说:“当你们的祖先还在树上的时候,我的祖先已经在伪造支票了!”他在维也纳长大,高中时曾因在劳动节那天当众宣读《共产党宣言》而被开除。他和奥本海默算是同龄人,两人都在1927年获得了博士学位。他们都热爱文学,也都迷上了里芬斯塔尔。就像命中注定一般,奥本海默和豪特曼斯后来都将致力于研制原子弹,但豪特曼斯是在德国。
在近四分之一个世纪里,物理学家们一直在像即兴创作一般拼凑着量子理论,突然间,1925—1927年的一系列重大突破让量子力学得以成为一个革命性的、系统性的理论。那时各种新发现层出不穷,不断发表的文献也让人目不暇接。“在那段时期,伟大的构想层出不穷,”爱德华·U.康登回忆道,“以至于人们错误地认为理论物理学的发展速度就该如此。最令人气馁的是,那一年大多数时候你都在学术上处于消化不良的状态。”发表新发现的竞争异常激烈,来自哥廷根的量子力学论文数量超过了哥本哈根、卡文迪许或其他任何地方。奥本海默在哥廷根时发表了7篇论文,对一个23岁的研究生来说,可谓成绩斐然。沃尔夫冈·泡利开始把量子力学称为“男孩子们的物理学”[1],因为许多论文的作者都年纪轻轻。1926年,海森伯和狄拉克只有24岁,泡利26岁,约尔当23岁。
当然,这门新兴的物理学也饱受争议。马克斯·玻恩给爱因斯坦寄了一份海森伯1925年发表的论文,这篇论文的主题是矩阵力学,其中对量子现象进行了集中的数学表述,玻恩带着辩解的意味向这位伟人解释说,这篇论文“看上去有些不可思议,但它无疑是正确且意义深远的”。但是那年秋天爱因斯坦读完了这篇论文后,写信给保罗·埃伦费斯特说:“海森伯搞出了一个量子力学的大成果。哥廷根的那些人信以为真(我不信)。”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位相对论的提出者至死都认为,这门“男孩子们的物理学”即使没有根本性的错误,至少也是残缺不全的。1927年,海森伯发表的一篇论文使爱因斯坦的质疑有增无减,这篇论文指出了“不确定性”在量子世界的核心地位。海森伯的观点是,在任一给定时刻,不可能同时确定粒子的精确位置和动量,所以“原则上,我们无法知道当下的全部细节”。玻恩同意这一观点,他认为任何量子实验的结果都取决于概率。1927年,爱因斯坦在给玻恩的信中写道:“有个声音告诉我,这不是真正的实底。量子理论取得了很多成就,但是它并没让我们离上帝的奥秘更进一步。无论如何,我始终相信上帝不掷骰子。”
显然,量子物理学是一门年轻人的科学。反过来,年轻的物理学家们认为爱因斯坦对新物理学的负隅顽抗是一个信号,说明他的时代已经过去。几年后,奥本海默在普林斯顿拜会了爱因斯坦,但他显然不以为然,在给弟弟的信中他傲慢无礼地写道:“爱因斯坦是个十足的疯子。”但是在20世纪20年代末,来自哥廷根(和玻尔所在的哥本哈根)的男孩们仍然希望爱因斯坦能够加入他们的量子世界。
在哥廷根完成的首篇论文中,奥本海默阐明了有了量子理论才能测量分子带状光谱的频率和强度。他之所以痴迷于他所谓的量子力学“奇迹”,正是因为这个新理论以一种“和谐、一致和可理解的方式”解释了如此多能被观察到的现象。奥本海默用量子理论对连续光谱的过渡问题进行了研究。到1927年2月,玻恩对奥本海默在这方面的工作颇为满意,他甚至写信给麻省理工学院院长S.W.斯特拉顿说:“我们这里有不少美国人……其中有一位相当出色,他就是奥本海默先生。”因为才华出众,奥本海默的同龄人把他与狄拉克和约尔当相提并论。一位年轻的美国同学曾说:“这里有三位年轻的理论物理学天才,对我来说,他们一个比一个难以理解。”
奥本海默养成了通宵工作的习惯,他白天的大部分时间都在睡觉。哥廷根潮湿的天气和供暖不足的房间严重损害了他纤弱的身体。他总是一边走一边咳,他的朋友认为这可能由于他经常感冒或者抽烟太凶。但是就其他方面来说,哥廷根田园牧歌式的生活称得上舒心惬意。后来汉斯·贝特提到这一理论物理学的黄金时期时说:“在量子理论发展的中心——哥本哈根和哥廷根,尽管人们完成了大量的工作,但那里的生活依然是田园诗般的悠然自得。”
奥本海默总想结交那些声名鹊起的青年才俊,其他人则因此感到备受冷落。多年后,爱德华·U.康登颇有怨气地说:“奥比和玻恩成了非常亲密的朋友,他们经常见面,玻恩甚至因此都无暇理会理论物理学专业的其他学生,这些人可是专门为他而来的。”
那一年,海森伯经过哥廷根,奥本海默特意去见了这位德国最优秀的年轻物理学家。海森伯只比奥本海默大3岁,在与同行争论问题时,他口齿伶俐、富有魅力且不屈不挠。这两人都颇具创新精神,他们自己也很清楚这一点。海森伯的父亲是希腊语教授,海森伯曾在慕尼黑大学与沃尔夫冈·泡利同窗,后来又在玻尔和玻恩那里做博士后工作。和奥本海默一样,海森伯可以凭直觉抓住问题的本质。他是一个有着奇特魅力的年轻人,他的才华熠熠生辉、引人注目。据说奥本海默非常钦佩海森伯,对他的工作也推崇备至。他未曾料想到的是,在未来的岁月里他们将成为影子般的竞争对手。有朝一日,奥本海默将会揣度海森伯是否会忠于战时的德国,是否有能力帮助希特勒制造原子弹。但是在1927年,他基于海森伯的量子力学发现开创了进一步的研究。
那年春天,海森伯的一句话启发了奥本海默,他开始对如何用量子理论解释“分子何以成为分子”产生了兴趣。很快他就找到了一个解决该问题的简单方法。当他给玻恩教授看他的笔记时,比他年长许多的玻恩又惊又喜。随后他们决定合作一篇论文,奥本海默答应在巴黎过复活节假期时把自己的笔记整理为初稿。但是,当玻恩收到来自巴黎的论文时他“吓坏了”,这篇论文只有四五页,而且字数寥寥无几。奥本海默回忆道:“我觉得这些差不多就够了。在我看来,点到为止即可。”玻恩最终把这篇论文扩充到30页,在奥本海默看来,这是在用毫无必要的或显而易见的理论来拉长篇幅。“我不喜欢这么干,但是显然我也不可能跟一个高年资的作者对着干。”对奥本海默来说,他最在意的是论文核心的新想法,至于上下文的解释和学术上的粉饰都是画蛇添足,完全不符合他那极简的审美。
那年晚些时候,《关于分子的量子理论》发表了。这篇合著的论文中提出了“玻恩-奥本海默近似”,实际上更确切地说是“奥本海默近似”,至今它仍被视为利用量子力学认识分子行为的重大突破。奥本海默意识到分子中质量较轻的电子比原子核的移动速度快得多。将更高频率的电子运动单独综合计算之后,他和玻恩就可以近似地计算出核振动的波函数。这篇论文为此后70年高能物理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那年春末,奥本海默提交了他的博士论文,论文的核心内容之一是一种氢原子和X射线光电效应的复杂计算方法。玻恩建议将这篇论文评为“优秀论文”,他仅指出了这篇论文的一个缺点,那就是“晦涩难读”。即便如此,玻恩依然在评语中写道,奥本海默完成了“一篇复杂的论文,而且他写得很好”。多年后,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汉斯·贝特说:“1926年,奥本海默不得不靠自己推导出所有的计算方法,包括连续态波函数的归一化。当然,他的计算方法后来得到了改进,但是他正确地得出了K吸收边的吸收系数及其附近的频率依赖性。”贝特总结说:“即使在今天,这也是相当复杂的计算,超出了大多数量子力学教科书的内容。”一年后,奥本海默在一个相关领域发表了第一篇描述量子力学中“隧穿”的论文,这个效应指的是粒子实际上可以直接“穿过”位垒。这两篇论文都是了不起的成就。
1927年5月11日,奥本海默参加了论文答辩,几个小时之后,他以优异的成绩完成了答辩。物理学家詹姆斯·弗兰克也是考官之一,他后来对一位同事说:“我出来的可真是时候,他都开始向我提问了。”但是在最后关头,大学校方发现奥本海默没有正式注册学籍,所以他们威胁要扣留他的学位证书。玻恩替他出面求情,他向普鲁士教育部谎称“由于经济原因,夏季学期结束后,奥本海默先生将无法继续留在哥廷根”。奥本海默这才拿到了他的博士学位。
那年6月,埃德温·肯布尔正好在哥廷根访问,他很快就给一位同事写信说:“奥本海默比我们当初在哈佛时预想的还要出色,他总能迅速取得新成果,他可以和这里任何一位年轻的数学物理学家比肩。”奇怪的是,这位教授接着补充道:“很遗憾,玻恩告诉我他不善于将自己的想法付诸文字,就跟我们在哈佛看到的一样。”奥本海默的文字一直都极富表现力,但是他的物理论文经常简单扼要到敷衍了事。肯布尔认为奥本海默驾驭语言的能力确实令人惊叹,但是他在探讨物理学时与讨论其他日常话题相比简直“判若两人”。
看着奥本海默离去,玻恩颇为失落。他对奥本海默说:“对你来说离开不算什么,但对我不是,你给我留下了太多待完成的作业。”作为临别礼物,奥本海默送给他的导师一本珍版书——拉格朗日的经典著作《分析力学》。几十年后,也就是在玻恩被迫逃离德国很久之后,他在给奥本海默的信中写道:“这本书经历了革命、战争、移民和回国等种种动荡,我很欣慰它仍在我的藏书里,因为它充分地代表了你对科学的看法,即把它理解为人类历史进程中整体才智发展的一部分。”那时候奥本海默的名气已经远远超过玻恩,不过这倒不是因为他的科学成就,而是因为他被人搞得声名狼藉。
作为一个迈向成熟的年轻人,奥本海默在哥廷根取得了第一次真正的胜利。他后来说过,成为一名科学家“就像在隧道里爬山:你根本不知道自己能否爬出山谷或者干脆就是死路一条”。对身处量子力学革命前沿的年轻科学家来说尤其如此。虽然与其说奥本海默是这场剧变的参与者,不如说他是这场剧变的见证者,但他已经证明了自己拥有毕生从事物理学研究的天资和热情。在短短9个月里,他不仅取得了货真价实的学术成就,还获得了个人成长与自我价值感。这些重大成就和随之而来的自信已经战胜一年前还生死攸关的内心困扰。世界正在向他招手。
[1] 男孩子们的物理学是指量子力学初创时期(从1925年中至1927年初),约有80位作者发表了200篇论文,绝大多数论文的作者年纪不到30岁。他们约占所有论文作者的65%,9位主要贡献者中,有5位是年轻人。——校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