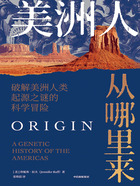
第一章
7月的一个下午,我正走在俄亥俄州格兰维尔镇(Granville Town)一条绿树成荫的街道上。每个院落都种满了精心修剪的树篱、蕨类植物和鲜花。这片郊区车辆稀少,因此,路边没有人行道,不至于破坏这些景观。花园里和通往大宅的石头小路边,不起眼地插着园林绿化公司和推销家庭安全系统的广告牌。邮箱上张扬地装饰着美国国旗和支持俄亥俄州立大学的横幅。
我听到一只红衣凤头鸟在歌唱,走到静谧的绿松树下时,看到它扑闪着红色翅膀飞走了。我能听到远处割草机传来的声音,还有微弱的高尔夫球杆击球所发出的独特的撞击声。我闻到微风送来的夏日气息:刚割除的青草,金银花的香气,有人在附近炭烤食物。我觉得自己正在美国中西部理想化的上流社区(主要居民是白人)中穿行。
向地平线望去,可以看到浣熊溪谷(Raccoon Creek Valley)另一边的悬崖顶部。街道略微向下倾斜,但仍位于溪流上方相当高的地方。我继续沿着街道前进,树木开始变得稀疏。在一座长满草的山前,道路一分为二。乍看上去,这里就像藏匿在精心规划的社区一角的公园,与其他社区一样,也是由业主委员会负责维护打理。这座山头是孩子们玩耍的好去处,也许有人会携家带口来此野餐,这里也能吸引人们偷偷溜出来,在此安静地读几小时书,晒晒太阳。如果是冬天,你可能会看到孩子们在下雪天坐着雪橇滑下来。山坡的角度刚刚好,很适合肆意滑降。山坡上长着几棵大树,但其他地方都是光秃秃的。站在山顶上一定能完美俯瞰浣熊溪谷的景色。
当我走近时,我注意到无处不在的狗粪袋发放箱,敦促人们清理宠物粪便。旁边则是我要找的东西:一处历史遗迹介绍牌。如果你和我一样,就会发现有些东西让人无法抗拒,尤其是格兰维尔这样的小镇(严格来说,应该称其为“村庄”),那里随处可见受到精心保护的历史建筑。
那块介绍牌上写道:“这座山上有俄亥俄州史前人类建造的两座大型动物象形丘之一。”这个土丘长约250英尺,宽76英尺,高4英尺,被称为“短吻鳄丘”(Alligator Mound)。
如果没有这块介绍牌,你可能根本认不出这是一座古老的土丘——原住民祖先的圣地。假如你站在山顶上,或者通过在线地图仔细观察这片区域,土丘的形状就会更加明显,但站在街道上,我看到的只有貌似自然隆起的土坡。
短吻鳄丘的历史比格兰维尔镇内所有的历史建筑都要久远。19世纪,伊弗雷姆·斯奎尔(Ephraim Squier)和爱德温·戴维斯(Edwin Davis)共同绘制了这座土丘的俯视图和侧视图,并在报告中描述说,土丘的形状像“某种动物,可能是短吻鳄”[1],尽管很明显不应该是短吻鳄(中西部地区也没有短吻鳄分布)。斯奎尔和戴维斯注意到,“祭坛”,即一个覆盖着石头、高出地面的环形空间,通过一道土堤从那动物的躯干上延伸出来,上面有燃烧的痕迹。(我首次看到这个土丘时,尚未读过任何关于它的描述,当时觉得祭坛和堤道是这只动物身上多出来的一条怪腿。)斯奎尔和戴维斯指出,短吻鳄丘是遍布县内的众多“工程”[2]之一。由于它位于断崖之上,所以整个地区都能看到。

短吻鳄丘,位于俄亥俄州利金县(Licking County)。摘自《密西西比河谷遗迹》(Ancient Monuments of the Mississippi Valley,1848),作者为伊弗雷姆·斯奎尔、爱德温·戴维斯,史密森尼学会出版。
短吻鳄丘和巨蛇丘
俄亥俄州历史联合会考古馆馆长兼考古学和自然史部门负责人、考古学家布拉德·莱佩尔(Brad Lepper)在一篇关于短吻鳄丘的论文中写道:“短吻鳄丘这个历史名称可能包含了某条线索,可识别其代表的生物形象。”[3]他与论文合著者托德·弗罗金(Tod Frolking)将这座土丘解读为象征着“水下黑豹”。它与雷鸟、长角水蛇是东部林地部落神庙中经常描绘的三种动物灵魂。
他们指出,如果欧洲殖民者询问美洲原住民,这个土丘描绘的是什么,那么这种长着大牙、拖着长尾巴的水下生物就很可能会让他们相信是危险的短吻鳄。
水下黑豹与河流、湖泊和地狱有关,大约从距今1040年前开始出现在北美东部地区的艺术作品中。该土丘大约建造于距今830年前。
短吻鳄丘是俄亥俄州两处动物象形丘之一。另一座距此地东南约80英里(1英里约合1.6千米),同样坐落在可俯瞰小溪的悬崖上。位于俄亥俄州皮布尔斯(Peebles)的巨蛇丘(Serpent Mound)是一项庞大的土方工程,从盘绕的尾部到张开的嘴巴,蜿蜒1300多英尺。这条蛇似乎正在吞噬一个椭圆形的土堆。在夏至日,蛇头完美地对准了夕阳。
19世纪80年代末,哈佛大学考古学家弗雷德里克·帕特南(Frederic Putnam)首先将巨蛇丘解读为一条嘴里含着蛋的蛇。帕特南试图将这一特征与欧洲文化联系起来。但莱佩尔及其同事在2018年发表研究成果,重构了土丘的原始尺寸,并摒弃以欧洲为中心的视角,重新做出解释。他们的发现推翻了早前的解读,表明巨蛇丘描绘的是代吉哈苏人(Dhegiha Siouan)创世故事中一个至关重要的时刻:世界上第一个女人和巨蛇结合。她就此获得了巨蛇的力量,创造了地球上的生命。[4]
在如今的高档社区中邂逅像短吻鳄丘这样一处古老而神圣的地方,就如同在街边排水沟的垃圾里找到一枚钻戒,令人感到很不和谐。每次我参观某个土丘,都会因看到神圣场所和世俗之物并列出现而感到不安。冬天,当在短吻鳄丘的斜坡上注意到雪橇留下的痕迹时,我便担心人们会不会正在用雪橇破坏土丘。建造这个土丘的古人会如何看待在山坡上玩耍的孩子呢?他们的后代对这种随意打扰祖先圣地的行为有何看法?解读土丘遗迹的工作包含了哪些人的声音?当我来到距圣路易斯市(St. Louis)不远处的卡霍基亚(Cahokia)遗址,站在100英尺高的僧侣丘(Monk’s Mound)上,听到刺耳的汽车轰鸣声从附近的55号和255号州际公路传来时,我不禁陷入了沉思。那些在此举行宗教仪式的部落领袖会作何感想?

巨蛇丘。
巨蛇丘和短吻鳄丘只是许多古代土丘建筑中的两座。它们用泥土建造,曾经遍布被考古学家称为“东部林地”的区域。这片土地位于密西西比河以东,及亚北极以南的北美地区。这些土方工程形式不同,建造方式多样。有些如巨蛇丘和短吻鳄丘,描绘的是某种动物或生物。有些则是高墙,将大片土地以极其精确的几何形状围起来,通常与冬至、夏至,或其他天文上的时间点相对应。有些工程呈高大的圆锥形,位于可俯瞰河谷的悬崖顶部或河漫滩上。有些工程则是金字塔形,顶部平整,用作祭祀活动或上层人士的居所。还有一些又长又低矮,类似于现代高尔夫球场上高低起伏的发球区和草地。
土丘通常聚集出现,大致反映出好几代人会选择相同的特殊位置筑丘,因为那里可能相当神圣,具有历史意义,或仅仅是方便而已。对于我们这些受过考古专业训练的人来说,只要看到土丘,就会想起曾经有成千上万的人在此生活、相爱、战斗、出生和死亡。
当初土丘建筑遍布整个“东部林地”,如今尚未因耕犁、开发或掠夺而破坏的土丘已所剩无几。在北美东部,很多土丘与购物中心、高速公路、房屋和公园挨得很近,然而许多人(非原住民)却几乎没有意识到它们的存在。[5]如果有某位非原住民能够察觉到它们,我希望他们对这些神奇的古老土丘产生和我一样的敬畏之情和好奇之心:它们是谁建造的?目的是什么?当初建造它们时,周围的环境是什么样子?
使用土丘的民族有何历史?[6]
﹡ ﹡ ﹡
当许多欧洲人最初意识到美洲原住民不是中国人或印度人,而是一个《圣经》中未曾提及的民族时,他们感到无比震惊。[7]欧洲人也很好奇,到底是谁建造了这些壮观的大地艺术品。当时它们主要集中在大陆东端,这证明那里的人口十分稠密。
尽管有一些关于美洲原住民工程技术和使用土丘的第一手书面说明材料,以及原住民自己的记录,证明是他们的祖先建造了这些工程,但人们依然普遍不相信。欧洲人费尽心机编造各种神话来解释土丘的成因。大多数故事围绕“一个消失的民族”,描述这个“先进”民族被当代美洲原住民灭绝。殖民者为了开垦土地而毫不顾及在土丘中发现的骨头和手工艺品,对他们来说,这显然是那个“消失的民族”的遗迹。[8]
对于神秘土丘建造者的确切身份,欧洲人也众说纷纭。由于注意到卡霍基亚的平台型大土丘类似于墨西哥的构筑物,因此许多人认为筑丘人是托尔特克人(Toltecs)。当然,他们本身就是原住民族。
此外,因在俄亥俄州发现的呈几何构图的土方工程与西欧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古墓存在些许相似之处,所以又有人推测它们与来自西欧地区的古代民族有关。也许筑丘人的年代还要更近一些。他们是威尔士王子马多克(Madoc)率领的水手,或是修道士圣布伦丹(St. Brendan)带领的爱尔兰水手后裔。[9]
还有一些人认为土丘出自腓尼基人或中国水手,以及罗马人或失落的亚特兰蒂斯大陆上的幸存者。19世纪成立的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The Church of Jesus Christ of Latter-Day Saints)相信,美洲原住民的祖先是拉曼人(Lamanites)后裔。《摩门经》记载,拉曼人消灭了虔诚的尼腓人(Nephites),于是受到诅咒,披上“一层黑皮肤”作为惩罚。[10]1901年,德国浸信会弟兄会(German Baptist Brethren Church)长老艾德蒙·兰登·韦斯特(Edmund Landon West)提出,俄亥俄,或者更准确地说,巨蛇丘是《圣经》中描述的伊甸园所在地。[11]
18世纪和19世纪的“筑丘人”理论强调,土丘建造者不是欧洲人遇到的美洲原住民的祖先。这套方便的说辞让殖民者相信,“印第安人”是美洲的后来者,因此并不合法地拥有那些欧洲人也想占据的土地。有些殖民者得寸进尺,通过循环论证,认为“消失的民族”就是欧洲人。
无论是谁先来到美洲,人们都一致认为,“印第安人”肯定不具备足够的智慧来创造那些欧洲人在摧毁土丘时所掠夺的非凡艺术品。通过宣扬筑丘人神话,他们将原住民与其祖先、成就和土地的联系割裂开来,强行制造一个缺口,以便于在美洲历史中插入新殖民者及其后代的故事。[12]
但并非所有欧洲人和欧裔美洲人都接受这套说法。何塞·德·阿科斯塔(José de Acosta)是一名耶稣会牧师,1572—1587年生活在南美和墨西哥多地。他在《印第安自然与道德史》一书中阐述了自己关于美洲原住民起源的理论。其基本假设是,美洲原住民是亚当和夏娃的后裔。至少在天主教教会内,关于美洲原住民是不是人类的问题已经得到了解决。教皇保罗三世在1537年《赞美上帝》的通谕中,已经对此确认。他告知天主教徒,印第安人和其他《圣经》中没有专门提及的“未知”民族是“真正的人类”,不应该受到奴役;关键是必须以任何必要的方式促使他们转变信仰。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受到了殖民者的人道对待。欧洲人对原住民施加了无数暴行,其中就包括奴役。
顺着上述思路,这些原住民既然是人类,那么就一定是亚当和夏娃的后代;他们一定是在大洪水中幸存下来的,或者更有可能是挪亚的后代,因为《圣经》写到挪亚一族遍布全球。阿科斯塔就此推断,他们必定是来自“旧世界”,而且由于《圣经》详细记载了地球年表,所以那肯定不是很久以前的事。他认为,他们,以及西半球的非凡动物是穿越亚洲和北美洲之间的某条陆地通道抵达美洲的,并非乘船横渡大洋。我们今天知道,这条陆地通道就是白令陆桥,存在于大约5万年至1.1万年前,是西伯利亚上扬斯克山脉(Verkhoyansk Range)和加拿大马更些河(Mackenzie River)之间的一片低地,在末次冰期没有结冰。
当然,16世纪的阿科斯塔从来没有到访过北极地区,也没有收集任何实地数据。相反,阿科斯塔的理论来自哲学思辨,引用《圣经》、天主教圣人和哲学家的著作,而不是实验数据。[13]尽管如此,他还是在当代考古学或遗传学研究方法发明前几个世纪就得出了关于美洲大陆人类(和非人类)起源的主流科学理论。他的思想远远领先于当时的其他欧洲学者,但在此后几个世纪里却几乎没有受到重视。有关筑丘人的无稽之谈反而大行其道。
﹡ ﹡ ﹡
另一套关于土丘成因的说法出现得稍晚,来自一位更知名的人物。托马斯·杰斐逊在他唯一出版的著作《弗吉尼亚州笔记》中,讲述了一段童年往事。他目睹了一群印第安人来到一座土丘,祭拜他们的祖先。杰斐逊在书中用了整整一章的篇幅,对盛行于欧洲知识分子中的一种科学理论予以毫不留情的驳斥。他认为这种理论对新成立的美国构成了生存威胁。当时著名的学者布丰伯爵(Compte de Buffon)曾断言,美洲动植物和原住民与旧世界的动植物和人相比发育迟缓,虚弱无力。这让自然主义统一论大行其道。他认为,新世界的植物和居民也许已经退化了,因为整个新大陆充满湿气,温度也更低,这使得鹿长得更小,植物生长不良,人变得更脆弱、更怯懦、更无能。
按照同样的逻辑,印第安人、美洲植物和动物的遭遇也会不可避免地发生在美洲殖民者身上。他们会退化、衰弱、萎缩,他们激进的自治实验永远不会开花结果。布丰在其皇皇巨著《自然史》中写道:“(美洲)生命体本质上就不那么活跃,也不强大。”
“退化理论”令许多美国开国元勋感到震惊和愤怒,认为这是对他们所珍视的国家的无情打击。[14]对杰斐逊来说,这就是莫大的侮辱,是对美国的嘲弄,完全是一派胡言。他的政治伙伴也以各种极具特色的方式予以反击。詹姆斯·麦迪逊从制定宪法的工作中抽出时间,专门整理布丰作品中的错误,还给杰斐逊寄去了一份关于美国鼬鼠的冗长而详细的描述报告,以便与欧洲鼬鼠进行比较。在巴黎,本杰明·富兰克林在“退化理论”的拥趸之一纪尧姆·托马斯·雷纳尔(Guillaume Thomas Raynal)的家中,举办了一次晚宴。富兰克林请法国和美国宾客都站起来比一比相对身高,以检测“哪一方面的自然属性退化了”。(美国宾客比法国宾客高得多,尽管富兰克林自嘲是个例外。)[15]
杰斐逊本人将这场斗争提升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层次。他送给布丰一只公驼鹿标本,以证明美洲动物同样体型巨大,还在《弗吉尼亚州笔记》中专列一章强有力地反驳《自然史》。《弗吉尼亚州笔记》虽然名字很不起眼,却用确凿可靠的数据巧妙而激昂地驳斥“退化理论”:对体型硕大的美洲动植物进行测量和详细描述,证明其各方面指标远超最接近它们的欧洲同类生物。(杰斐逊还将乳齿象——他称之为猛犸——作为现存物种并罗列数据,这未免有欺骗之嫌,不过他相信这种巨兽确实正生活在美洲某处。[16])
杰斐逊妙笔生花,描写美洲原住民的章节尤其富有激情。布丰曾把“新世界的野蛮人”描述为虚弱、冷酷、懦弱的人,杰斐逊则滔滔不绝地对每一点予以批驳。他指出,恰恰相反,“部落依赖勇气生存,原住民也勇敢非凡……他们对孩子们充满感情,小心照料,宅心仁厚……他们之间存在着牢固的友谊,彼此忠诚,绝无背叛”。他写下这段文字并非因为对美洲原住民有广泛了解,而是基于别人收集的语言和文化证据,以此反驳布丰。
杰斐逊为印第安人辩护不一定出于无私,也未必是摆脱了殖民主义窠臼。就像他对奴隶制的看法一样[17],杰斐逊对美洲原住民的看法也自相矛盾。
他是《独立宣言》的起草者之一。该文件将美洲原住民称为“残忍的印第安野蛮人”,但他又在其他作品中断言,他个人认为他们都是与欧洲人平等的人类,至少有这样的潜力;应该使其融入白人社会,而不是一除了之。(他没有考虑另一种可能性:白人应该离开,而原住民留在他们自己的土地上,按照自己的传统方式生活。)杰斐逊对美洲原住民的看法在启蒙时代相当普遍。让-雅克·卢梭就很好地阐述了“高贵的野蛮人”这一浪漫概念,并将原住民族描绘为原始、亲近自然、不受文明污染的族群。这种对印第安人的认知已经融入了美国的建国神话中。毕竟,正如考古学家戴维·赫斯特·托马斯(David Hurst Thomas)所指出的那样,那些在波士顿倾茶事件中扮作莫霍克人(Mohawks)的参与者已经把“印第安人视作无畏、坚强、充满个人勇气、勇于挑战绝望的象征”[18]。
杰斐逊终于凭借博物学证据驳倒了“退化理论”,成功地令其最终无人问津。杰斐逊推翻了由欧洲最重要的一位知识分子建立的主流科学理论,但他在揭示真相的过程中,还做了一件更了不起的事情。杰斐逊在一份早期手稿中补充了一些附录内容,描述了他在弗吉尼亚州自家庄园附近挖掘一座土丘的过程,此举本质上开创了美国科学考古的先河。
杰斐逊决定发掘这座土丘,是为了查明其建造原因和方式。当时人们普遍认为,土丘里埋葬着在战斗中牺牲的将士。杰斐逊,或者更有可能是他的奴隶,在土丘中心挖了一条沟槽,露出了层次分明的石层和土层,里面埋有骨骼及古代器物。杰斐逊检视了土丘的每一地层,确认了地质学家尼古拉斯·斯泰诺(Nicolaus Steno)在1669年阐明的“叠加原理”:底层是最古老的地层,其上每一层的年代逐次靠后。杰斐逊还检查了从每一地层中提取出来的人骨和人工制品。他指出,这些遗骸上没有暴力痕迹,而且它们在土丘内的位置也清楚地表明,大多数人并不是在死后不久被首次安葬的,而是在软组织腐烂后,有人将骨骼收集起来重新下葬。他估计,这座土丘埋葬了近1000人,涵盖各个年龄段。杰斐逊声称,综合以上事实分析,可知该土丘并不是战死士兵的坟墓,而是村落的公共墓地。据此推断,在美国东部发现的数千座土丘也应如此。[19]
谁建造了杰斐逊发掘的土丘?
杰斐逊发掘的土丘今天被称为“里瓦纳丘”(Rivanna),是已知的至少13座建在弗吉尼亚内陆的土丘之一。这些土丘大多建在河漫滩上,因各种自然侵蚀,以及人类耕作、修筑和劫掠而毁。里瓦纳丘已经不复存在,其确切位置也不清楚。但考古学家杰弗里·汉特曼(Jeffrey Hantman)和莫纳坎部落成员通过鉴定,确认埋葬在这些土丘内的古人正是莫纳坎人的祖先。
几千年来,莫纳坎人——一个讲苏族语言的部落联盟——一直生活在一片山麓地带,位于今日的弗吉尼亚州境内。莫纳坎的领土几乎涵盖了这个州的一半面积,地下蕴藏着丰富的铜矿。他们与居住在沿海地区的波瓦坦联盟(Powhatan)和西部的其他部落进行大规模贸易活动。他们在河流冲刷的河漫滩上建立村庄,在附近种植玉米、豆类、南瓜和向日葵。他们在村庄里轮流耕作,居住在狩猎营地中。他们举行繁复的仪式,将亲人安葬在巨大的土丘内。
莫纳坎人与欧洲人的第一次接触可能是间接的。与北美其他部落类似,他们也因殖民者带来的病毒和细菌罹患肺结核、天花、流感,进而大量死亡。这些传染病就像池塘里的涟漪一样在原住民中扩散开来。[20]即使是与欧洲人没有直接接触的内陆部落也受到了严重影响。
1607年,英国殖民者聚居詹姆斯敦(Jamestown)后不久,他们的贸易伙伴波瓦坦人就提醒说,内陆部落不欢迎外人,因此,波瓦坦人拒绝带领英国远征队进入内陆。
英国人对莫纳坎人仅有的几次造访鲜有记载。但从历史记录和考古研究中得到的总体印象是,莫纳坎人总是尽可能避免与英国人接触。一个名叫阿莫洛克(Amoroleck)的马纳霍克人(Manahoac)对约翰·史密斯(John Smith)[21]说,莫纳坎人认为英国人“来自地狱,要从他们手中抢走整个世界”。
莫纳坎人一语成谶。也许他们从波瓦坦联盟内的某个部落成员那里打探到了一些关于西班牙殖民者的情报。此人在历史上名为“唐·路易斯”(Don Luis)。他曾与西班牙殖民者和传教士一起前往墨西哥、古巴和西班牙,旅行了大约10年。唐·路易斯多次利用自己掌握的信息和特殊地位保护同胞。他在为一支西班牙远征军做向导时,故意带他们远离自己的家乡;只有在船上没有士兵,仅有耶稣会传教士的情况下,他才返回故土。唐·路易斯后来还帮助自己部落的战士杀死了那些传教士。此举引来西班牙人的报复性杀戮,但此后他们也放弃了在弗吉尼亚海岸地带探险殖民。唐·路易斯似乎还警告整个波瓦坦联盟,甚至更远的部落,告知他们殖民者的所作所为和企图。波瓦坦,可能还有莫纳坎和其他部落联盟,后来也多次通过和平或暴力方式与各类欧洲人,包括军队、宗教团体、探险考察队,以及企图建立殖民地如罗诺克(Roanoke)的队伍有过接触。
然而,这些策略也影响了英国殖民者对莫纳坎人的认知。英国人对内陆民族了解有限,导致了各种错误的假想。比如,约翰·史密斯将莫纳坎人描述为“主要以打猎和采集浆果为生的野蛮人”,当殖民者占领了莫纳坎人的领地时,他们把这里称为“无主之地”。而事实上,他们在地图上把许多土地标记为“印第安人田地”或“印第安人菜园”,这表明所谓“无主之地”只是为了满足他们的目的而编造的说辞。随着时间的推移,莫纳坎人逐渐淡出了欧美历史记载。杰斐逊的挖掘工作对任何一名考古学专业的学生来说,都耳熟能详,但很少有人知道埋葬在土丘里的人是谁。
随着殖民地数量的增加,不同部落做出了不同的应对。莫纳坎人选择了多种策略,但主要还是与殖民者保持距离。在欧裔美洲人逐步蚕食土地之际,莫纳坎人要么就地分散,躲到偏远的地方,要么迁移出去,加入其他部落。也许正是这种策略帮助莫纳坎人生存至今。在面对巨大的逆境时,他们表现出了非凡的韧性。今天,联邦政府承认莫纳坎族有超过2300名族人,并成立保护项目,允许他们在弗吉尼亚州阿默斯特县(Amherst County)贝尔山及周边祖祖辈辈传承的家园上复垦土地,传承文化。
莫纳坎部落已经与考古学家和生物人类学家建立合作,以更好地了解埋葬在弗吉尼亚土丘中的祖先的历史。
研究证实,杰斐逊的许多记录非常精确。与他所观察到的一致,莫纳坎人是逐渐加高土丘的,每举行一次葬礼活动,就会增加一层土石(从11世纪至15世纪)。一些土丘中安葬了大量遗骸,如拉皮丹溪(Rapidan Creek)遗址中估计有1000~2000人。[22]
虽然这不是他的主要关注点,但托马斯·杰斐逊在《弗吉尼亚州笔记》一书中将考古工作中的详细记录与人种学和语言学证据结合起来,论证建造这些土丘的古代民族就是欧洲人第一次到达北美东部时所遇到的族群。杰斐逊认为,数千种“印第安”语言一定花了非常长的时间才发展出来,而且大多数源自东北亚。他甚至提出了一条可能的起源路线。
后来从堪察加海岸航行到加利福尼亚海岸的库克船长也通过他的发现证明了这个猜想,就算亚洲和美洲两块大陆完全分开,中间也不过是一道很窄的海峡。因此,无论在哪一边,聚居者都可以穿行到另一边。美洲印第安人和东亚人之间的相似之处促使我们猜测,前者是后者的后裔,或反之,除了因纽特人。由于具有相似的生存环境和语言同一性,因纽特人一定来自格陵兰岛,而这些人又可能来自旧大陆的北部地区。[23]
尽管杰斐逊收集了相当可观的证据,但这一论点直到一个世纪后才被科学界接受。在18世纪,“筑丘人”假说已成为北美史前史的主流理论,也是根深蒂固的公众认知。[24]直到19世纪,学者和古器物研究者仍在争论筑丘人的身份,他们中的大多数同意筑丘人不是美洲原住民的祖先。杰斐逊出版他那本书仅仅40年后,安德鲁·杰克逊(Andrew Jackson)总统便明确将“筑丘人”假说作为签署1830年《印第安人迁移法》(Indian Removal Act)的部分依据。
我们从遍布西部广大地区的遗迹和堡垒中,看到了一个曾经强大的未知民族。这个民族惨遭灭绝或已经消失了,为现存的野蛮部落腾出了生存空间。[25]
就这样,天命论与种族划分的概念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当有人问我为什么对有线电视台所谓的“历史”节目宣传“失落的文明”和“筑丘人”概念如此愤怒时,我只能提醒他们:在杰克逊签署《印第安人迁移法》之后数年内,超过6万名美洲原住民被驱逐出他们的土地,并被强制迁移到密西西比河以西。数以千计的人,包括儿童和老人,死于美国政府之手。而这些谬误理论正是政府将其行为正当化的理由之一。
﹡ ﹡ ﹡
随着考古学在19世纪下半叶慢慢开始职业化,大多数考古学家摒弃了“筑丘人”假说。随后对土丘和村庄遗址的考古研究不断深入,海量证据证明这些土丘就是美洲原住民的祖先所建造的。借助原住民历史记录、考古学和生物人类学的综合证据,“筑丘人是谁”这个问题已经无可置疑地得到了解决。很多修筑土丘的族群现在已经能与某些特定的古老文化联系在一起。
杰斐逊采用挖掘和观察这样的直接方式,比现代考古学和体质人类学或好或坏的科学方法早了一个多世纪,因此,他也经常被誉为“美国考古学之父”。他适时创造了一种多学科交融的实证手段来研究历史。通过这种方法,我们从古人遗骸和他们留下来的人造器物中获悉大量信息,并随着时间推移而越积越多。但是杰斐逊也把原住民的遗体当作“标本”,视其为研究对象,而不是值得尊重的先人遗骸。正如考古学家戴维·赫斯特·托马斯所指出的那样,这也成为美国科学历史中丑陋的一幕。[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