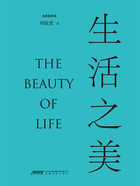
天时之美
我们就生活在“天之美”中。
庄子曾有句名言——“天地有大美”。天之美,实乃一种“大美”!
于是乎,我们就活在天之“大美”当中。对我们的日常生活而言,天气无所不在,也无时不在,甚至在我们出门的时候,天气之“气”就被吸入我们的体内。
所以,天气之美,才是与我们的生活最切近的“生活之美”。
那么,天气如何成就出“美”呢?我们每日每夜都在感受天气,但是如何审美化地体会到它的美感呢?
庄子赞美天地之美,那句原话便是:“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庄子·知北游》);孔子也说过:“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如此的大美,用来形容天气之美,似乎再合适不过了,但无论是孔子还是庄子皆关注天之“不言”。
大自然自身,从来不言说,无论人在或不在,它就在这里,的确有其大美,且自不言也!人才是那个真正的言说者,人能言说天之美何在,但是相形天的无言,默默地奉献大美,人的言说又何等渺小呀!
自从人类依凭进化的力量,在这个璀璨的蓝色星球上登场,人类就对自然进行着改造,这样的自然就成了所谓的“人化的自然”。
我们都知道,自从工业革命之后,随着工业废气释放量的增加,地球的大气结构被改变了。2015年夏天,我曾经在美国加州克莱蒙参加第十届“生态文明国际论坛”,遇到不少致力于生态保护的各国人士,他们其实对如今地球的生态系统忧心忡忡,认为海洋的酸化已经到了不可逆转的程度,就连播种的种子都已变得基本一致,从而违反了本就大小不一的“种子伦理”。
其实,早在工业革命开始之前,整个地球的大气就被人类深刻地改变了,这是人们所遗忘的人改变天气的历史。人类的“刀耕火种”曾首度大规模地破坏了森林,影响了气候,而其后又作用于人。
在新石器时代乃至更晚的时代,“刀耕火种”就成了能迅速满足人类生存并向自然索取资源的方式,也就是在初春使用石刀、石斧等砍倒山间树木,然后在春雨来临前放火烧尽所有山林,树木被燃尽后可以当作肥料,第二天趁土热下种,经过火烧的土地因变得松软而不用翻地。
这是一种一劳永逸的耕作方法,利用地表草木灰做肥料,这样播种后就不用再施肥,也不用再做任何田间管理了。这不像后来人类用手农耕的时间较长,当时的人类倒可以利用这些做农活的时间去狩猎小型动物或者圈养家畜。
然而,问题来了!问题就出现在刀耕火种所具有的“短期性”(时间上的)和“扩大性”(空间上的)。
一般规律就是两三年之后,被刀耕火种后的大地之土肥就已枯竭殆尽,基本就不能再种植了。人们通过积累经验,认识到了这一点,所以懂得土地轮休规律的本土汉人甚至采取一年一休的方式。如果时间上不再允许,那就只能在空间上加以拓展。所以新石器时代的人类就不得不开疆拓土,寻找新的林地继续进行耕作,而不是在原地种地。这就需要相当多的土地和山林来养活这批人。尽管我们无法精确估算多少亩地能养活一个人,但显然这绝不是一种经济化的耕作方式,原始生产力也只能如此。农业的进步就是建基在用越来越少的地来养越来越多的人,当今水稻种植技术的翻新就是顺应此道。
由此,人类对地球的第一次大污染也就出现了,在农业文明之前,耕作方式造就了这“第一次”。
今天人们常说的人为的“二氧化碳污染”,并非更多由自然山火导致的,而是可以追溯到那个时期的人类所为。因为,以林木的灰作为农作物的肥料的方式,乃是一种非常低效的方式,一片树林被燃尽后就只能再寻找下一片树林进行焚烧种植。随着这种技术的普及和扩大,也就能够以食物养活更多的人口。
但悖论又出现了:人口的增多,势必要烧更大面积的森林。一般而言,并不是每次烧了树林的土地都可以用于耕作,而是要烧尽比实际种植面积大五倍的森林,这就造成了巨大的环境污染,进而改变了地球的气候。
实际上,人盘剥地球并不是呈现出由低向高的直线发展。在精耕细作的农业技术发展之后,人类就不必大量烧山了,人类对大气的影响在新石器时代后应该说是变小了,不过今天“烧荒”的行为仍在大江南北存在着,也时常影响着秋季周边的小气候。150年前的工业革命,乃是这个曲线突然变直的时期,因为越来越大规模地使用化石燃料后,二氧化碳的增多,导致了新一轮的地球变暖,我们正处于这个历史阶段当中。
正是在人与自然的这种初步关联当中,人对自然产生了最初的审美意识,为什么这样说呢?
随着原始人类与自然抗争的深入,他们进一步掌握了自然规律如天气改变的规律,天气成为人们远离功利性的审美对象,而不只是令人恐怖的巨大存在。整体步入农业文明的人类发展阶段,天气之美就逐步地彰显出来。中国人所感受与创生出来的“天之美”,主要就是农业文明所塑造的结果。
在高度依赖天气与土地的农业文明生发之后,中国古人谈天论地,却并不是从大自然谈起,而往往从圣人说起:“圣人作则,必以天地为本,以阴阳为端,以四时为柄,以日星为纪,月以为量,鬼神以为徒,五行以为质,礼义以为器,人情以为田,四灵以为畜。……人情以为田,故人以为奥也。”(《礼记·礼运》)按照这种世界观,圣人制定法则,以天地为本源,以阴阳为发端,以春夏秋冬为握柄,以太阳星星为纲纪,以月亮为度量,以山川为徒属,以五行为实质,以礼义为器具,以人情为田基。

从战国时代的白玉双龙云纹佩可见传统审美“人天相合”的本土传统
其中,把“人情”当作田地,这个规定就非常有意味:圣人以情为本,由此就成了田地的奥主。既然这种人之“情”所走的是血气心知之路,所以就要以人情做田,从而来耕之、种之、耨之、聚之与安之。
中国人这种与天地自然之间的“深情款款”,便与人类的审美意识内在地相通了。中国人早就参悟天与人合体的智慧,明白人在天地之中所处的核心地位,毕竟感受天之变动的便是人,而人才是一种顶天立地的存在,这使中国人在各个文明当中对于人的彰显都显得那么突出。
实际上,中国古人早就“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了,在俯仰之间观天法地。
古希腊人亦较早地观天看地。第一批科学家兼哲学家就诞生在米利都,这批人被称为“米利都学派”。我曾经到米利都瞻仰过,当时内心的问题就是:为何这些古希腊人能在天地之间观出“哲学”呢?
后来这个迷惑很快就被解开了,去过米利都后来到另一座古城普里内,我突然发觉,自己与最早的哲人们有那么一点灵犀相通。直面碧绿的门德雷斯河三角洲,远方一线蔚蓝的爱琴海,还有浮在海面上的一层雾霭,我突然顿悟到:为何米利都学派哲人,将水、无限和气视为始基,这不正是来自他们在生活中所见的抽象吗?三角洲的土、海与河上的水,还有空中的气,不正是他们哲学智慧的自然之源吗?这种人类最早的哲思,就力求万物归一,中国人何尝不是如此呢?!
中国人的农书当中早就记载了此类的“实用理性”智慧,它一定是出于农耕的目的而滋生出来的。所谓“万物因时受气,因气发生,时至气至,生理因之”(《农书·天时之宜篇》),此处的“生理”乃指生长繁育之理。在“天—地—人”的架构当中,烟云乞于天,山川乞于地,性灵乞于人,无论中国人是如何地尊天亲地,最终还是重人本身的。
按照一种本土的气化宇宙观,人与天合,物乘气至。从这个宇宙化的一气到每个人的喜怒哀乐,中国人的确参透了其中的本然关联,“喜怒哀乐,一气流行,而四者实与时为禅代,如春过了夏,秋过了冬,冬又春,却时时保个中气,与时偕行”(《刘子全书·学言》)。好个喜怒哀乐!好个春夏秋冬!它们不仅是相通的,而且是与时俱进的,但中气随四季运转而不变,“自喜怒哀乐之存诸中而言,谓之中,不必其未发之前别有气象也”(《刘子全书·学言》),一气与中气都有着和谐共振的天人节奏。
同时,还有一种阴阳互动的思想,在儒家、道家乃至其他诸家当中都普遍存在,到了荀子那里,“天地合而万物生,阴阳接而变化起,性伪合而天下治”(《荀子·礼论》),从天与地、阴与阳到性与伪都是贯通起来的,且两方面乃是动态地互动与和谐地互补的。

秦朝云纹瓦当的卷云纹理中蕴藏着“阴阳和谐”之审美智慧
季节的变化,也被归之于天地阴阳互动的结果:“季春三月,丰隆乃出,以将其雨。至秋三月,地气不藏,乃收其杀,百虫蛰伏,静居闭户。青女乃出,以降霜雪。行十二时之气,以至于仲春二月之夕,乃收其藏而闭其寒。女夷鼓歌,以司天和,以长百谷禽鸟草木。孟夏之月,以熟谷禾,雄鸠长鸣,为帝候岁。是故天不发其阴,则万物不生;地不发其阳,则万物不成。天圆地方,道在中央。”(《淮南子·天文训》)
再据董仲舒的宇宙观,“天地之气,合而为一,分为阴阳,判为四时,列为五行”(《春秋繁露·五行相生》)。质而言之,无论是道家的自然一气论,还是儒家的道德一气论,皆形成了华夏气化宇宙观的底色,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气化和谐的深度美感意识。
既然按照自古至今的中国智慧,人与天气“通”,那么在此根基上,天气就可以成就出“美”来。
美国作家和思想家爱默生也深契这种天人智慧,他曾在《自然》这篇名文当中如此描述“天气之美”:“热爱自然的人是这样一种人:他的内在和外在感觉仍在真正地相互调节,他在成年以后依然童心未泯,他每天的粮食就是同天体和大地进行交流。在自然面前,他总感到有一股癫狂和快乐流经全身,尽管他可能正处在极大的痛苦之中。自然说:他是我创造的,无论他有什么悲痛,都是不适当的,都应该和我一起快乐。不仅只是太阳和盛夏,即使每个小时、每一季节也会产生它的快乐,因为每一小时,每一变化都对应和主宰不同的心境,从闷不透气的正午到最恐怖的午夜,概莫能外。自然这一背景既适应滑稽,又适应悲哀。在身体健康时,空气是一种难以置信的兴奋剂。暮色苍茫中,当我在乌云笼罩的雪地中翻滚不毛之地时,尽管没有想到什么特别的好运,我却还是在痛痛快快地呼吸。”[1]
所以我们才说,天气的变化,竟是如此微妙,从季节之变到时刻之变,从闷热的正午到恐怖的午夜,从乌云笼罩到大雪满地,无不与身处其中的人的“心境”相系。我们不仅在其中呼吸,而且就置身于现场的大气压强、湿度、温度之中,从而形成了“身心合一”之情,同时也成为“天人相合”之境。
中国古人以合天之心来感悟天气的美丽之所在——“当雪夜月天,心境便尔澄澈;遇春风和气,意界亦自冲融。造化人心,浑合无间”(洪应明《菜根谭》)——这便是人心与天心的合一。
从客观的角度看,随着天气的变化,气还要呈现为一定的“貌”,正如《说文》区分出气的黑白之色别,上升为雨呈白色,散而为风则呈黑色。这“在天为气”之气,必有各种样貌,中国古人究竟如何划分的呢?所谓“风、热、湿、燥、寒”(《素问·天元纪大论》),这是五分法;还有一种区分为六的:“天有六气……六气曰阴、阳、风、雨、晦、明也”(《左传·昭公元年》),这就形成了我们今天所说的“气象”。

中国古代纹样当中出现的各种云纹,恰是古人观天而总结出来的审美变化多端之结晶
为什么这样说“气象”呢?气象,因气成象,却与天气不同。我们对天气的感知,绝不是仅仅诉诸视觉的,想一想山雨欲来前的那种大气压强与湿度,你就会知道,对于天气,人是全身心投入其中的,而不是因视见象。况且,“气象”这个词,还用来形容人与社会,比如说古人所说的圣人气象,今人所谓的大家气象,还有社会气象的用法(如气俗、气尚、气脉),而“天气”这个词就仅指天而不指人,应该不会产生异议。
所以说,“天气美学”所指向的就是天之美,与人相通,这就要比“气象美学”更为合适。
天之美,对人而言,似乎呈现为无限的,乃是“最高”的美,因为天高地远嘛。前面提到的米利都哲人们,他们既抵御住了东方神秘主义诱惑,又没有受到俄耳浦斯教的影响,将古希腊神话当中的阿波罗所象征的光明与理性发扬光大。但是,与米利都相距甚近的萨摩斯岛深受神秘教化,其中的一位最著名的岛人就是毕达哥拉斯。
这位被视为西方数学鼻祖人物的毕达哥拉斯及其所形成的学派,认为宇宙在歌唱,不同星球沿着轨道以固定速度运行,从而产生各种和谐的音调和旋律。各行星与我们星球之间的距离,就像琴弦的弦长一样成比例,从而奏出美妙的天体音乐,为此,还生生造出一个“对地星”,以完成数字和谐的完整。这种宇宙美学更是无框的,这里所说的行星运作还只是太阳系,目前人类所探索的宇宙仍是无垠的,让人滋生一种“理性神秘”之感。天气之美还是有限的,因为它毕竟还属于地球上的美学形态,但我们每个人只是宇宙里的一粒尘埃,地球也是。
天气之美,与任何一种“人工之美”都不同,它具有自身的不可替代的特质。
第一,天气之美本身是“自然而然”存在的,它所构成的美自然,就在那里,与时协作,自然化生,从而不具有任何人工性质。
第二,对天气之美的感受,植根于人们的“自然生活”,乃是我们几乎日日、时时、处处能感受的自然美。
第三,对天气之美的投入,绝不仅仅依赖于耳目,而是要我们“全身心”地投入其中,也就是置“身心”于天气之中,而不能超乎其外。
第四,天气之美,正如自然本身不是风景画或山水画一样,它是没有框子的,也就是有“无框架性”,从而接通无限的宇宙。
第五,天气之美从来就不是静态的,没有“不动”的天气之美,它随时而变,千变万化,春夏秋冬,朝暮晴雨,与时俱进。
无论如何,最重要的规定,还在于人与天气之合。自然也不是那个外在的“它”,我们就置身其中。反过来说,天地对于人来说,概莫能外。那么,介入其间的审美,也是全身心投入的,因为你整个身体及感官都浸渍其中。从这个意义上说,不仅天之美乃是“至大之美”,而且人对天之美感的方式也是一种“全方位”的审美。
与此同时,我们所说的天气之美还是一种“天时之美”。

从梅清《黄山图轴》所描绘的黄山云海,可以体会『一气』充塞天地的样貌
谈到“天时”,其实就是把时间要素纳入天气之内。众所周知,天气就是在变化当中,所谓天时也就是出于自然运行的时序,从而指向了一种中国人所谓“天道”运行的规律。
天气之美,美在变化。中国人常说风云变幻,所谓“地载神气,神气风霆,风霆流形,庶物露生”(《礼记·孔子闲居》),风雨雷霆皆为流动变幻的,万物也在这流变当中得以显露与滋生。天气本身就具有这种易逝性与变动性,这就为中国人的“伤春悲秋”提供了最大的自然舞台。
春夏秋冬的“四季”或“四时”之美,油然而生。
“天地之道”者,“谓四时也,冬寒、夏暑、春生、秋杀之道。若气相交通,则物失其节。物失其节,则冬温、夏寒、秋生、春杀”。(《周易正义》)这冬寒、夏暑、春生、秋杀之铺陈与交替,就是绝妙的四时描述。
自古至今,四季变换,中国人都在发出两种时间感喟:一面是对春夏秋冬循环不已的感喟,另一面则是对时间一去不复返的感喟。这是由于,“古代中国一方面存在循环史观,另一方面存在天地间万物来去,光阴一去不复返这种直线性时间的概念。天地(自然)是永远的,一直存在于那里,时间无始无终。但是,万物(所有个物)出现然后消失,人生不会反复。就连某年桃花园的春夜(时间线上的一刻)一旦逝去,就不会再回来。一次,这一刻等于‘现在’,非常宝贵”。[2]
这里提到的“桃花园”,乃是李白的那首《春夜宴从弟桃花园序》里面的,其中那句“天地者万物之逆旅也,光阴者百代之过客也”,恰恰说明直线性时间观在中国的存在,但是不同于古希腊那种万劫不复的时间观。在中国时间观里,“古人秉烛夜游,良有以也”,则说明时间上的“这一刻”亦即现在,不会反复,这不同于中国历史时间的那种循环史观,但春夏秋冬又形成了一种日常时间的循环,只不过我们都要随着循环而老去罢了。
四季不仅是自然化的,在东亚已经被文化化了,这就形成了所谓的“四季文化”。这种四季之所以能成为文化,是因为四季被赋予了文化功能。这种功能分为几类,一类是符号化或象征化的,四季被视为与文化相关的符号,比如作为人格象征的梅、兰、竹、菊分别对应着冬、春、夏、秋。一类是仪式化的,比如日本兴盛的四季“花道”就是如此,插花被作为一种仪式化的文化行为过程。还有一类则是人际交往性的,不同季节也要送不同的花,不同的花也有不同的季节意蕴,从而形成一种优雅的人与人交流的方式。

顾禄《四时天运贴》题诗云“四时天运任推迁,女织男耕乐自然”,展现出一种农业文明之美
在华夏文明内部,这种四时审美积淀到了明代,明代生活美学家高濂在《遵生八笺》当中所说的四时幽赏,大概是集大成地总结了国人的四时审美。
以“冬时幽赏”十二条为例,就有“湖冻初晴远泛”“雪霁策蹇寻梅”“三茅山顶望江天雪霁”“西溪道中玩雪”“山头玩赏茗花”“登眺天目绝顶”“山居听人说书”“扫雪烹茶玩画”“雪夜煨芋谈禅”“山窗听雪敲竹”“除夕登吴山看松盆”“雪后镇海楼观晚炊”。其中,听雪一则最清雅:“飞雪有声,惟在竹间最雅。山窗寒夜时,听雪洒竹林,淅沥萧萧,连翩瑟瑟,声韵悠然,逸我清听。忽而回风交急,折竹一声,使我寒毡增冷。暗想金屋人欢,玉笙声醉,恐此非尔所欢。”
关于“冬雪”之美,再以张岱《夜航船》当中的论“雪”为例,其中搜集的许多条目,都充满了“生活美学”之情之感。说到“欲仙去”——“越人王冕,当天大雪,赤脚登炉峰,四顾大呼曰:‘天地皆白玉合成,使人心胆澄澈,便欲仙去!’”说到“嚼梅咽雪”——“铁脚道人,尝爱赤脚走雪中,兴发则朗诵《南华·秋水篇》,嚼梅花满口,和雪咽之,曰:‘吾欲寒香沁入心骨。’”说到“神仙中人”——“晋王恭尝披鹤氅涉雪而行,孟旭见之,曰:‘此真神仙中人也。’”说到“踏雪寻梅”——“孟浩然情怀旷达,常冒雪骑驴寻梅,曰:‘吾诗思在灞桥风雪中驴背上。’”还有“剡溪雪”中那个著名的乘兴而来、尽兴而归的故事——“王子猷居山阴,于雪夜棹小舟往剡溪访戴安道,未到门而返。仆问之,答曰:‘乘兴而来,兴尽而返,何必见戴?’”[3]


高濂《四时幽赏》由野间三竹配画的春景“西溪楼啖煨笋”与夏景“步山径野花幽鸟”


高濂《四时幽赏》由野间三竹配画的秋景“西泠桥畔醉红树”与冬景“西溪道中玩雪”
当今中国人在微博与微信当中“伤春悲秋”,其实也是继承了古人的“四时模式”。他们在微博和微信上进行“日常写作”,也好似传统文人进行书法日课一样,融入了许许多多“微公民”的日常生活程序。你会发现,圈内的女性微用户更能敏感地感受到冬去春来的季节变化,那一幅幅花开花落的图像与所配的心情文字,也好似传统水墨画里面的“书画合一”。写微博、晒心情如采取了文学的春秋笔法,实际上更接近古代文人撰写日常性的诗歌来抒怀。不是踏花伤春,就是夏日消暑;不是远足悲秋,就是冬日幽居,这亦是古诗中最常见的题材了,中国人的四时审美传统其实从未中断过。
农业文明中更标准的“天气之美”,非二十四节气莫属了。爱美恋情的中国人,早就把他们生活于其中的节气给审美化了。
我们就从二十四节气的开端立春谈起。其实立春并不是农历新年的开启,但是中国人更愿意把“正月”放到立春时节,似乎由此而发,一切都开始了。这仍然离不开对“气”的理解,由此《月令》中也说:“立春,正月节。立,建始也。五行之气,往者过,来者续。于此而春木之气始至,故谓之立也。”“春木之气始至”,才能使春得以“立”,似乎一年的真正起点就在此。所谓“风来传消息,枝头晾春衣。江河水乍暖,静心待花期”,立春之后,美丽的世界就即将来临了。
立春三候,吹来的风都不一样了,因为所“至”的乃是东风,作为春风的东风,最令人感到惬意了,“便觉眼前生意满,东风吹水绿参差”(张栻《立春偶成》)是也。中国人常讲“八面来风”,这还是从风的空间而言的,又根据立春、春分、立夏、夏至、立秋、秋分、立冬、冬至的时序性的“八节”,把风区分为“八风”:立春东风至,春分明庶风至,立夏清明风至,夏至景风至,立秋凉风至,秋分阊阖风至,立冬不周风至,冬至广莫风至,这恰恰是时空合一的结果,可以说这也是“风候”使然吧。
立春之美,古人早就感同身受。“春已归来,看美人头上,袅袅春幡。无端风雨,未肯收尽余寒。年时燕子,料今宵、梦到西园。”(辛弃疾《汉宫春·立春日》)这更趋于文人的个人感受,但立春的活动更是群体性的观感:“彩燕双簪翡翠翘,巧裁银胜试春韶。东风已到阑干北,看见娇黄上柳条。”(方岳《立春》)在大好春光当中,不仅女人们佩以美艳重饰,而且用绢与纸剪裁的迎春幡胜迎风飘摆。
春社也是如此,那既是祭祀的时令,也是狂欢的日子。在唐代以后的春社基本被定为立春后的第五个戌日,那可是看社戏的大好时节,那渺渺戏舞美化了乡间的生活,也是一年当中最值得怀念的美的岁月。远的不说,只要想一想鲁迅的《社戏》就会有场景跃然眼前:“最惹眼的是屹立在庄外临河的空地上的一座戏台,模糊在远处的月夜中,和空间几乎分不出界限,我疑心画上见过的仙境,就在这里出现了。这时船走得更快,不多时,在台上显出人物来,红红绿绿的动,近台的河里一望乌黑的是看戏的人家的船篷。”于是,一场社戏就鸣锣开场了……
到了明代的立春之日,宦官刘若愚所记的笔记《酌中志》就有这样的生动记载:“立春之前一日,顺天府于东直门外迎春,凡勋戚、内臣、达官、武士,赴春场跑马,以较优劣。至次日立春之时,无贵贱皆嚼萝卜,曰咬春。互相请宴,吃春饼和菜。以绵塞耳,取其聪也。自岁暮正旦,咸头戴闹蛾,乃乌金纸裁成,画颜色装就者;亦有用草虫蝴蝶者,或簪于首,以应节景。”
我们看到,这样的立春呈现了一种集成之美:无论是跑马的竞技、咬春的欢宴,还是戴闹蛾的各种应景装饰,各种节庆娱乐活动被整合在一起,跑出得意、吃出满意、闹出乐意,在这情趣当中美感油然而生。赛马是今人所说的体育娱乐,在比赛当中也给人以美的视觉享受,与那种头戴各种饰物的美化其实是异曲同工的。
更有趣的是,在立春日吃春盘、春饼、春卷、春盒,还有吃生菜和萝卜,被称为“咬春”。清人所作的《咬春诗》将这种春的滋味描述得绘声绘色:“暖律潜催腊底春,登筵生菜记芳辰。灵根属土含冰脆,细缕堆盘切玉匀。佐酒暗香生匕梜,加餐清响动牙唇。帝城节物乡园味,取次关心白发新。”
“咬春”,其实呢,不就是通过咀嚼应季的食物,来品尝当时的春意吗?!中国人的“春”,是可以“咬”的,也就是嚼出春的味道、春之美意,这不就是一种由口而生发的“生活美学”吗?!
春天来了,人们也不用“猫冬”了,他们纷纷出来“踏春”“邀春”“讨春”或“探春”。这几个对待“春”的方式,所说的乃是同一个活动,也就是春季的郊游。春游或踏青,就是一种人们对春天的邀约与探求,“踏青”的说法无疑更有色彩感了。清末震钧的《天咫偶闻》曾记载老北京每年三月三蟠桃宫庙会的盛况:“地近河堧,了无市语;春波泻绿,软土铺红;百戏竞陈,大堤入曲;衣香人影,摇扬春风,凡三里余。”这便是一种节庆“生活美学”的盛景!




《清院本十二月令》之『二月赏桃』『三月流觞』『五月竞舟』和『十月画像』的精华呈现
在这二十四节气的循环变换中,中国人就更有了自觉的宇宙生命意识,并把宇宙给音乐化了,这才是中国美学的大智慧。所谓“乐者,天地之和”,“大乐与天地同和”(《礼记·乐记》)。天地“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乐兴焉”,乐本自天,但乐也是启始:“乐著大始,而礼居成物。著不息者,天也。著不动者,地也。一动一静者,天地之间也。故圣人曰礼乐云。”(《礼记·乐记》)
这种天地生化的壮景被描述为“地气上齐,天气下降,阴阳相摩,天地相荡,鼓之以雷霆,奋之以风雨,动之以四时,暖之以日月,而百化兴焉。如此,则乐者天地之和也。化不时则不生,男女无辨则乱升,天地之情也”(《礼记·乐记》)。这就是天地宇宙本身之审美化节律,“天时之美”的华夏文化根源就在这里,这种生活美学智慧至今生生不息……
[1]【美】爱默生:《爱默生散文选》,姚暨荣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4页。
[2]【日】加藤周一:《日本文化中的时间与空间》,彭曦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7—8页。
[3]张岱:《夜航船》,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28—3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