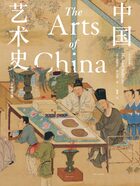
商代
陶瓷
陶瓷是早期中国艺术的支柱,不可或缺,无处不在,反映和满足了社会各阶层的实用需要和审美情趣。它们的形状和纹饰有时为金属工艺所模仿,偶尔也会借鉴金属工艺。商代最质朴的陶器是灰陶,这些灰陶上装饰着绳纹、刻画纹、用压印的方法形成的不断重复的方格或卷云纹、后世见于青铜器的简单兽面纹等纹样。卷云纹开创了后世雷纹的先河。在未干的陶胎上压印或刻画几何形纹饰的陶器在东南地区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就有所发现。在华南,这种技术一直延续到汉代,如果东南亚确实没有这种技术的本土渊源的话,当地的压印陶器技术有可能就是从华南传来的。华北地区的新石器时代陶器上很少用到这种技术,因此,在郑州和安阳陶器上出现这种纹饰应该表明,最晚在商代,南方民族的文化已经开始显著地影响到中原文化。
精美的商代白陶在中国陶瓷史上独一无二。由于太过精美,以至于有人误认为它是瓷器。实际上,它是由从西北沙漠吹到华北平原上的细腻的黄土通过陶轮加工,以1000℃高温烧制而成的一种非常脆弱的器物。很多学者已经注意到白陶纹饰与青铜纹饰的高度相似性。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一样,中国东南一带已经发明了在未干陶胎上压印纹饰的技术,并最终影响了铜器纹饰的设计。弗利尔美术馆(Freer Gallery)收藏的一件白陶罐(图2.13)在设计和装饰上与赫尔斯特伦收藏(Hellstörm Collection)中一件铜器极其类似。[8]因此,如果说青铜纹饰是用这些反向刻着纹饰的陶范铸成的,一点也不让人感到意外。郑州的发现表明,那些同时装饰在白陶和青铜器上的纹饰母题有可能源起于更早的压印纹饰灰陶;木刻技术和设计则是另外一种可能的渊源。河南和湖北的商代遗址中发现的某些灰陶和黄褐陶已经带釉,有些釉是木灰偶然落在陶窑中烧制的陶器上形成的,而在另外的例子中,这些灰釉则是特意施加的(图2.14)。江西和浙江北部的若干商时期遗址已经显露出瓷器元素,有的规模不可小觑。比如,江西鹰潭附近的角山就发现了多处“龙窑”,大量生产高温烧制的陶器,我们称其为炽器。内外施釉的器物在烧制之前施加了压印纹饰,窑炉废料中随处可见压印模块。广泛发现于华北、中原和华东一带的带釉陶器标志着一个传统的开始,这个传统在积累2000年之后,以浙江和江苏一带的越窑和青瓷为代表,达到巅峰状态。

图2.13 白陶罐,高33.2厘米,出自河南安阳,晚商,现藏于华盛顿史密森学会弗利尔美术馆

图2.14 黄褐釉印纹陶尊,高28.2厘米,出自河南郑州,中商
青铜礼器
传说中,夏禹“收九牧之金,铸九鼎,象九州”,九鼎中装盛各州的贡物,鼎上装饰了各地最具代表意义的物体形象。九鼎具有超自然力量:它们能趋利避害,可以不用火就蒸煮食物。随着王朝更迭,九鼎作为国家象征也不断迁移,到周代末年,九鼎遗失。秦始皇帝曾经试图在河床中探寻九鼎,但无功而返,汉代石刻以颇具嘲讽意义的笔调刻画了这个故事。无独有偶,汉代的一个皇帝希望通过祭祀实现同样目的,也未能如愿。九鼎传说影响如此深远,以至在唐代,武后也铸造九鼎,为她的登基正名。
早在发现商代的考古学证据以前,青铜礼器就见证了中国历史上这个遥远时代的权力和活力。青铜器为中国历代鉴赏家所珍视:伟大的收藏家和鉴赏家、宋代的徽宗皇帝(1100—1125年在位)就曾经派人专门在安阳一带搜寻青铜器以扩充其收藏。韩思复(Howard Hansford)精辟地指出,这些器物构成一种“沟通器具”,装盛供奉给祖先灵魂的食物和酒水,这正是王室和贵族施行的供奉礼仪的核心。[9]有的青铜器上带有短小精悍的铭文,一般是由两到三个字构成的族名。很多铭文外面有一个称为“亚形”的方框,“亚形”名称来自它和“亞(亚)”字的形似(图2.15)。关于它的意义已经形成多种理论。近期在安阳发现的青铜印章提示我们,这种形状很可能与族名有关。

图2.15 亚形,商代
化学分析显示,青铜包含着5%—30%的锡和2%—3%的铅,其余则是纯铜。随着时代的推移,青铜器上遍布漂亮的、深受鉴赏家喜爱的铜锈。取决于金属组成成分和器物埋藏的环境,铜锈颜色从孔雀绿、翠鸟蓝到黄色甚至红色,一应俱全。制伪者们不辞劳苦地模仿这种效果。有一个故事提到,一个造假家族每一代人都将伪造的铜器埋藏在经过特别处理的泥土中,等到下一代才挖掘出来出售。长期以来,商周青铜器被认为是由失蜡法制成的,因为人们相信,不用失蜡法,几乎无法实现青铜器上如此清晰的细节。然而,在商代,这种技术可能用来铸造小件器物,在安阳和郑州发现的内、外范和坩埚已经毫无疑问地证实,这些器物是用合范法制成的(图2.16),器物的腿和耳分别铸成后再焊接在一起。很多器物还带有不同的范块无法完美地拼合形成的范缝。

图2.16 青铜器的合范铸造法,据石璋如和张光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55年)第113、117页
青铜容器至少包括30种主要类型,其中24种如图2.17所示。它们的尺寸大大小小,有区区数厘米高的小件,也有高度超过1米、重达800千克的大鼎。这件铜鼎是一位商王为纪念母亲铸制的,1939年出土于安阳。它们可以根据在祭祀活动中的用途予以分类。在施祭中,那些食物的精华被祖先的灵魂摄取,而参与祭祀的人则在祖先灵魂离开之后才吃掉那些食物。主要的烹食器包括腿部中空的鬲、鬲盉(图2.18)和甗。所有这些器形都常见于新石器时代陶器,它们可能在原始的礼仪中就拥有某些非实用功能。鼎(图2.19)有三足或四足,常常带有大型的附耳,使其能从火上移开。盛食器包括带双耳的簋和盂。用来装盛液体(主要是酒)的器物包括壶、卣(类似,但如图2.20所示,有链或者提梁,有时还有流口)、觯(球腹敞口杯状体)、盉,用来倒酒的瘦长而带有喇叭口的觚(图2.21)及其比较矮胖的变体尊(图2.22,两者都出自陶器原型)、用于注酒和温酒的斝(图2.25)和用于调酒的觥(图2.24),觥的形状看起来像一个调味汁盘,常常配有盖和勺。其他的容器包括可能用于盥洗仪式的匜和盘。

图2.17 商周青铜器主要类型,据张光直,《美术、神话与祭祀》(三联,2013年)图38

图2.18 青铜鬲盉,高25.4厘米,中商,布伦戴奇收藏,现藏于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

图2.19 青铜方鼎,高42.5厘米,出自河南安阳妇好墓,晚商,现藏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图2.20 青铜卣,高36.5厘米,晚商,现藏于华盛顿史密森学会弗利尔美术馆

图2.21 青铜觚,高25.6厘米,出自河南安阳妇好墓,晚商

图2.22 青铜尊,高47厘米,出自安徽阜南,晚商,图片版权归属于巴黎小皇宫博物馆
公元前15世纪,青铜铸造是中国的主要艺术形式之一,艺术经历了一系列风格上的演化,进而反映出技术和装饰上的复杂化趋势,因此可以将器物年代卡定在一个世纪的偏差之内。前安阳时期的青铜器以郑州和盘龙城的发现为代表,一般器壁较薄,形态上也很拘谨。它们往往装饰了以一对大眼为特征的饕餮和龙的纹饰。所有这些纹饰要么是浅线纹浮雕(风格一),要么呈带状分布,看起来好像是铸造之前草草刻在陶模上(风格二)。紧接着的阶段(风格三)见于郑州和安阳,纹饰更加精美,更加完整。繁密、流畅的曲线设计常常覆盖了整个器物表面。在风格四中,饕餮纹、蝉纹、龙纹和其他纹饰单独脱模成形,与细密卷云纹构成的地纹分离开来。最终,在风格五中,主要的动物形纹饰形成突起的浮雕,而卷云状地纹则可能完全消失(图2.23)。

图2.23 礼器上的饕餮纹饰带,代表罗樾提出的商代铜器纹饰的五种风格。据李济,《中国考古报告集新编》第1本第71页和第5本第48、100页图版15
当罗樾(Max Loehr)教授于1953年首次提出五种风格时,[10]他认为这些风格按照整饬的顺序次第发生,但是晚近的发掘证明这个顺序有待完善。风格一和风格三出现在同一件青铜器上,而商代晚期商王武丁的妻子妇好的墓葬中出土的铜器上装饰了风格三、风格四和风格五的元素。在此之后,商代铜器风格的演化应该基本上是后三种风格的精细化。装饰商代青铜器并赋予它们无穷活力的动物形母题看起来不可计数,但从主要的组成部分和组合看,不过是少数元素——虎、水牛、象、兔、鹿、猫头鹰、鹦鹉、鱼和蚕等——的变形和组合。
所有这些动物都有可能被当作部族图腾来崇拜。[11]当器表仅有条带状装饰时,这些动物可能呈现为自然写实形态,但更常以高度概括的形式表现,以至于难以辨认;它们的身体被分解,它们的手足脱离身体,或者转化成其他动物。比如,夔可能以张开的下颚、喙、鼻子、翅膀或角为特点,但它也可能变成传说中最具视觉冲击力和神秘色彩的动物——饕餮的眉毛。
这种令人怔怖的面具常常出现在扉棱两侧,或者在器物腹部展开,是商代青铜器装饰的主导元素。宋代金石学家根据公元前三世纪文献《吕氏春秋》中的一段话,“周鼎著饕餮,有首无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以言报更也”,而将其命名为饕餮纹。至迟周代晚期,饕餮被视为怪物;后来,它被称为贪食者,用来警示人们切忌贪食过量。现代学者认为它代表虎或者牛;有时它显示出这种动物的特征,有时又显示出那种动物的特征。水野清一指出,在《春秋左氏传》中,饕餮是舜所驱逐的四凶之一,后来成为保护土地免受恶魔侵扰的神。[12]然而,商人如何称呼这种动物,以及它对商人意味着什么,都无从知晓了。
有两个例子可以说明不同的元素如何有效地组合并和器物本身的形状融为一体。如图2.24所示,觥盖一侧为虎首,而另一侧为鸮首;器物前部可以清楚地辨认出老虎的脚,后部则是鸮的翅膀。两者之间有一条蛇从底部一直盘旋到盖上,最后在背脊顶端以龙首结束。堪萨斯收藏的一件精致的铜斝(图2.25)上,一条水平低棱将主要纹饰饕餮一分为二,其中地纹为旋涡纹,中国金石学家因为它们和“雷”字象形,称之为“雷纹”。但是,正如仰韶陶器上无休无止的旋涡纹一样,它们的意义无从知晓。饕餮有粗大的“眉毛”或角,上部是一条由长尾鸟填充的纹饰带,在口沿之下是一条由高度抽象化的蝉纹构成的浮雕纹饰带。在中国艺术中,蝉是常见的重生象征。斝的上端是一只蹲踞的野兽,以及两个可被钳子夹住将整个器物从火上提开的巨大立耳,而足上则装饰了成对的夔龙纹饰。

图2.24 青铜觥,高24.2厘米,晚商,现藏于哈佛大学赛克勒美术馆,由温索普(Grenville L. Winthrop)捐赠

图2.25 青铜斝,高34.2厘米,晚商,现藏于堪萨斯城纳尔逊-阿特金斯美术馆
这些纹饰常常看起来离奇而夸张,结合起来也不令人愉悦,但是在最精致的器物上,器物表面上的主导装饰元素就像音乐中的主旋律一样,与由雷纹构成的地纹形成鲜明对比。事实上,我们可以进一步探索这种类比关系,这些纹饰可以被看成赋格曲(fugue)的主旋律部分,同时又与有力的旋律相配合。在流畅的仰韶彩陶装饰中,我们已经看到了这种独特的、以富有生命力的线条韵律表达形式能量的中国式手法。在铜器上,这种手法更强健,而多个世纪之后,它将在笔墨语言中得到无以复加的表现。
正如我们所知,青铜铸造工艺在公元前第二个千年纪晚期已经遍及中国各地,不同地区各具特色。三星堆青铜艺术代表了与安阳无甚关联的文化,1957年在安徽阜南出土的尊(图2.22)以一种较安阳晚期铜器更具有流动性和“可塑性”的风格装饰,代表了远在东南地区,生机勃勃的另一种本土传统。
商人使用的青铜兵器展示了这个多元文化的其他侧面。最纯粹的中国式兵器是铜戈(图2.26),铜戈援部前聚成锋,内部插入柄上穿孔,并绑缚起来,在较罕见的情况下,内部做成銎孔形状,套在柄上。铜戈可能源自新石器时代兵器,似乎具有某种礼制意义,因为制作最精良的商代铜戈往往配有玉刃,而内部常常镶嵌绿松石拼图。铜戚可能也源于石器,刃部较宽而形成弧线,类似中世纪行刑斧,而内部往往装饰饕餮或其他纹饰。图2.27所示是1976年在山东益都苏埠屯出土的一件精美的铜戚,在令人怔怖的面具两侧,分别出现了亚形徽标,中间有祭坛上用勺舀酒进行供奉的人的形象。不那么纯粹的中国式兵器包括铜匕和铜刀,有的见于郑州。在安阳,它们变得更具装饰意味,把手上常常带有一个铃铛,或者是马头、羊头、鹿头的形象(图2.28)。这些铜刀也见于鄂尔多斯沙漠、内蒙古和西伯利亚南部的“动物风格”文化中。

图2.26 青铜戈,长27.3厘米,出自河南安阳,晚商,现藏于西雅图美术馆,Paul Macapia摄影

图2.27 青铜戚,高28厘米,出自山东益都,商代

图2.28 羊首青铜刀,长27.5厘米,出自河南安阳,晚商
这些动物形象究竟源自中国还是中亚,长期以来一直争执不断。很大程度上,这取决于卡拉苏克等南西伯利亚遗址的年代,只有当这些年代被完全确定下来,先后顺序问题才能得到解决。看起来,公元前1500—前1000年,动物风格同时存在于西亚(卢里斯坦)、西伯利亚(卡拉苏克)和中国,中国工匠可能从西邻手中学会了这种风格,但进一步丰富了动物形式谱系。动物风格元素也出现在家具、兵器和车马器等青铜构件上。安阳的发掘实现了商代车马的复原,确认了当卢、銮铃、辕、辏、轭等部件的正确位置。
青铜器纹饰的渊源至今仍然是一个问题。其中最令人关注的部分是动物形纹饰在中国新石器时代艺术中几乎没有任何表现。商人和西伯利亚的草原、森林民族,甚至更为遥远的阿拉斯加、英属哥伦比亚和中美一带的族群拥有文化关联。某些商代设计和北美西海岸印第安人的艺术之间的类似应该绝非偶然。李济(1896—1979)曾经指出,装饰繁缛的四方形铜器可能是一种北方木刻艺术的金属变体。还有更多的证据证明,铜器上的装饰与北方游牧民族的装饰之间存在风格上的近似。在木器或陶土上刻画高度风格化的动物面具艺术至今仍然流行于东南亚和马来群岛。同样,在湿润的陶土上压印纹饰的技术也保存在现代东南亚人的生活中,而这种技术应该有助于中国青铜装饰中出现不断重复的圆圈和旋涡纹。但是,即使有的元素并不是中国本土的,它们组合在一起,就形成一种强有力的、极具中国特色的装饰语言。
不管这种语言的渊源是什么,我们不能认为它仅仅局限在青铜礼器上。如果时光倒流,我们有幸亲身参观一些富足的安阳贵族的豪宅的话,就会看到,房梁上绘制了饕餮、蝉纹、龙纹、虎纹,同样的纹饰也见于皮革或者蒲草墙幔上,甚至织入丝袍中。发掘出土的墓葬器物强调了这个观点:这些纹饰母题没有和任何特定青铜器的形式和功能捆绑在一起,而属于兼具装饰、象征和巫术意义的青铜时代早期艺术的整体。
玉器
早在一些新石器时代遗址中,我们就已经发现了玉器。因为坚硬、牢固和纯洁,玉被用来制作那些蕴含了实用之外目的的器物。商代,玉器刻镂技术进一步提高。有人认为安阳已经采用金属琢玉工具,有证据显示商代玉工使用了比现代金刚砂更坚硬的钻具。商代遗址中发现了一些圆雕小件,但是大部分是由厚度不过一厘米的玉片制成的兵器、礼器和装饰品。郑州所见玉器包括狭长而优美的戈、环、璧、龟以及用作服饰饰件和挂饰的鸟和其他动物牌饰。
安阳发现的玉器无论在美观、工艺还是器物类型上,都是在郑州发现的玉器无法比拟的。它们包括鸟形、鱼形、蚕形和虎形玉薄片,璧、琮、瑗和其他礼制性玉器,珠、刀和礼仪性玉斧(图2.29)。尤为罕见的是妇好墓出土的小型跽坐玉人(图2.30),对于安阳早期的服饰和发型资料具有独到价值。安阳发现的最大的玉器当数武官村大墓底部的石磬,尽管它们是大理石而非真玉(图2.31)。石磬从薄石板上切割下来,顶部穿孔以供悬挂,表面用细阳线浮雕虎纹,这类器物见证了音乐在商王室礼制中的重要地位。下一章中,我们将深入讨论玉器的象征意义和礼仪用途。

图2.29 玉斧,出自河南安阳,晚商

图2.30 玉人,高7厘米,出自河南安阳妇好墓,商代,现藏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图2.31 虎纹石磬,长84厘米,出自河南安阳武官村大墓,晚商
雕刻不仅局限在难以加工的玉器和大理石上。有些极尽妍美的商代纹饰也刻在骨器和象牙上。史前时期,大象出没于华北一带,到商代仍可在长江以南见到。我们知道,至少有一位商王曾经畜养过可能由南越进贡而来的大象。中国也可以从南部方国获取大量稳定的象牙资源。在区区几平方厘米,可能用作车马、家具或者奁盒装饰的象牙和骨板上,异常细腻而精美地雕刻了饕餮和其他纹饰(图2.32),有时还镶嵌绿松石。和铜器一样,这些骨器和牙器的刻镂艺术显示出和北美西海岸地区土著艺术的惊人相似。多年来,学者们都在探索这些相似蕴含的种种令人激动的可能性,但迄今为止还没有发现任何足以立论的考古学证据。

图2.32 雕刻骨器,长15厘米,出自河南安阳,商代,现藏于台北“中研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