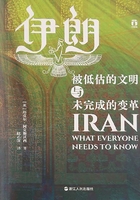
居鲁士大帝在公元前6世纪建立的阿契美尼德王朝有何独特之处?
公元前549年,一个名叫居鲁士(Cyrus)的波斯人发动叛乱,并成功占领了米底王国的首都埃克巴坦那。这一事件通常被看作波斯人建立阿契美尼德王朝的开端。(该王朝的名称根据居鲁士的祖先阿契美尼斯命名。阿契美尼斯在波斯语中被称为哈卡梅尼什。)在此之前,波斯人受米底王朝统治,而从公元前549年开始,情况彻底翻转。居鲁士大帝统治伊始,其施政与米底人截然不同,他更加强调米底人和波斯人之间的共同合作。(在统治之初,米底人可能占据绝大多数,居鲁士本人则拥有波斯和米底双重血统。)除了米底人和波斯人,与早期埃兰帝国有关的一些人,以官僚和书记员的身份在阿契美尼德王朝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阿契美尼德王朝的很多朝廷记录就是用埃兰文字书写而成的。

在随后的几个世纪中,特别是在色诺芬(Xenophon)的《居鲁士的教育》一书中,居鲁士被塑造成一个智慧、公正的国王形象。色诺芬的著作虽然有许多虚构成分,但却真实地揭示了居鲁士备受世人尊崇的事实(尽管希腊人一直习惯性鄙视波斯人)。犹太人对居鲁士可谓心怀感激,感激他在占领巴比伦后将犹太人释放,并同意他们回到耶路撒冷去重建圣殿。居鲁士的这一举措在伟大的“居鲁士圆柱”被发现后也得到印证。居鲁士圆柱刻制于公元前539年居鲁士占领巴比伦(巴比伦人在当年奋起反抗米底统治者)后,并于19世纪在巴比伦的废墟中重见天日,现存于大英博物馆。与亚述人、埃及人和其他帝国的创建者常常在铭文中记录囚犯、来袭的敌人和毁坏城市等以纪念胜利不同,居鲁士圆柱上刻载了居鲁士的仁慈、大度和宽容,以及对巴比伦人的主神马尔杜克(Marduk)的推崇:
当我以朋友身份进入巴比伦时,并以喜乐为准,在这天堂建立起政府时,伟大的神马尔杜克正在劝导宽宏大量的巴比伦人民去爱戴我,而我每天都不遗余力地崇敬他。我的大批军队在巴比伦境内行进,所到之处一片安宁祥和。我不允许任何人威胁苏美尔和阿卡德。我致力于捍卫巴比伦以及其他圣城的和平安宁。
居鲁士允许他的属民,不仅仅是巴比伦人和犹太人,去信奉各自的神明。在他统治时期和之后的一段时间里,各属国人民仍可以按照自己的习惯和法律进行自治,且管理者大多由本国产生。虽然并不是每一个居鲁士的后世君主都严格遵照他的模式进行统治,但总体来说,波斯人的统治明显带有松散和权力下放的特征。值得注意的是,居鲁士本人和他的继承者们无意将他们信仰的马兹达教强加给他人,但却将该教强调的道德品质和真理、正直、正义等融入全新、坚定且宽容的施政模式中。这些品质在阿契美尼德王朝后期的君主大流士一世时期的铭文中,比如贝希斯敦铭文和波斯波利斯圣殿(始建于大约公元前515年)的铭文中也有所体现。最近的学术研究对于大流士一世自称的正直与诚实提出了质疑,但是他所宣传的内容确实在不断强化“良政”的品质,虽然他本人的一些做法还未达到相关标准。波斯人不仅要把阿契美尼德王朝建成一个“刀剑的王朝”,更想把它塑造成一个“思想的王朝”。
在居鲁士统治末期,他的帝国已经成为当时有史以来最大的帝国,面积涵盖了从爱琴海到印度河流域的广袤地带。他的儿子冈比西斯二世继续扩张,并征服了埃及。大流士一世也没有停止扩张步伐,不仅征服了色雷斯和马其顿,还挑起了波斯人和希腊人之间一系列的战争。这些举动深深影响了后世欧洲人对于波斯的看法,乃至对于整个东方的态度。希腊人(特别是雅典人)更倾向于将波斯人的形象描绘成颓废堕落、专横残暴的人,这种广泛传播的论调从没有得到完全的印证,甚至从来没有被印证过,然而希腊人对于自身凶残的一面以及其他方面的过失却视而不见。正如世人所看到的那样,《圣经》中有关阿契美尼德人的记载对于以上观念起到了更正的作用。
希腊人对于阿契美尼德人的偏见也提醒着人们,世人(包括当代伊朗人)对于阿契美尼德历史的认知,无论是来自希腊古典文献还是19世纪转录的古代铭文,基本来自西方的记载和学术研究,而不是伊朗的历史传承。使用“Persia”(波斯)一词也反映了这一点。由于阿契美尼德人来自“波斯省”,所以希腊人称呼他们及其帝国的子民为“波斯人”。在此先例(以及其他惯例)的影响下,罗马人也称来自这一区域的人为波斯人。此后,欧洲人由于大量学习希腊和罗马的经典文献,直到19世纪仍一直称这些人为波斯人(欧洲人也同时吸收了希腊人和罗马人对于波斯人的各种偏见)。但是,在这漫长的岁月中,伊朗人一直称他们的国家为“伊朗”。最终在1935年,巴列维王朝的缔造者礼萨沙·巴列维(Reza Shah Pahlavi)正式要求各国驻伊朗使馆在正式的官方交往中称呼他的国家为“伊朗”(此举部分源自民族主义情结,同时也是为了将他本人缔造的巴列维王朝和被他推翻的恺加王朝加以区别,以确立自己的统治)。自此以后,“伊朗”一词成为大众普遍使用的名称。今日伊朗人仍然称他们的母语为法尔西语,即波斯语,因为在伊斯兰教进入伊朗之前,(古波斯)法尔斯省的方言就已经在文化上占据了主导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