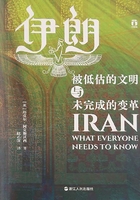
什叶派通过何种方式在19世纪的伊朗成为重要潜在力量?
直到1924年被凯末尔·阿塔图尔克(Kamel Atatürk)废除之前,哈里发制度一直是逊尼派伊斯兰国家最高宗教权威(一些人指出,近些年出现的类似于“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组织等神学无知团体是由废除哈里发制度所造成的真空状态引发的)。但是在16世纪萨法维王朝时期就将什叶派定为国教的伊朗却走上了另一条道路。直到1722年萨法维王朝倒台之际,什叶派一直与王室关系密切,但它们与王朝覆灭又存在千丝万缕的关系,其自身利益在随后的动荡中也受到冲击,首当其冲的就是纳迪尔沙没收了所有宗教财产。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不少教士纷纷移民印度、奥斯曼帝国伊拉克地区或是波斯湾南岸沿线地区。
此低潮时期一直持续到1979年。那一年出现了一位自称能够代表所有人的宗教人士,他夺取了国家的最高权力。为何会发生这样的事?它最早缘起于欧莱玛内部关于神职人员本质作用的争论,这种争论在18世纪末达到高潮(虽然争端的起源可以追溯至更早时期)。参与纷争的有两个派系——阿赫巴里派(Akhbari)和乌苏里派(Usuli)。阿赫巴里派认为每一个穆斯林都能够从《古兰经》和其他传统宗教典籍(《圣训》)中找到他所需要的指引,并且只能在有限的地方(如果能够知道的话),根据宗教法学对经典进行解读(创制,另作“伊智提哈德”(4))。此观点与伊斯兰教逊尼派的立场十分接近。乌苏里派的观点则恰恰与之相反,他们认为创制具有合法性,且有必要按照新情况、新理念,在每一代人中解释宗教律法。只有经过训练和学识渊博的欧莱玛才有资格进行释义。
19世纪早期,在伟大的宗教学者阿加·穆罕默德·巴克尔·贝赫贝哈尼(Agha Mohammad Baqer Behbehani,约1706—1790)的领导下,乌苏里派逐渐占据上风,而阿赫巴里派则逐渐被边缘化。同时,根据新的要求,穆斯林效忠于欧莱玛,并要将自己收入的一部分献给他们。在每一代宗教学者中都会有一到两名教士成为欧莱玛阶层和普通穆斯林的宗教事务最高领导。这名教士被称作导师(marja-e taqlid或marja,即他人效法或者见贤思齐的对象)。导师向下级教士发布教谕以回应下级传达给他的问题、意见或咨询。全国基层教士也都需要向导师进献财物。高级别的教士在回应问题和收取金钱的同时,名望和影响力自然而然地水涨船高。这就意味着在无需任何明确计划和蓝图的情况下,什叶派教会自然产生出宗教等级制度,这一点与天主教会十分类似,但却和逊尼派相对松散的制度大相径庭。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有满腔抱负的年轻人通过自身努力成为宗教学者,同时新的更高级别的身份标签也被不断创造出来以区别于普通教士,如霍贾特伊斯兰(hojjatoleslam)、阿亚图拉(ayatollah)。这套制度不仅帮助欧莱玛阶层不断加强自身在社会上的权威性,同时也帮助其实现财富的日益增长。在皇权相对衰微之际(即19世纪),欧莱玛成为独立于世俗统治的社会权威阶层。
沙里亚法,即宗教律法,用于规约穆斯林生活的方方面面。区别于基督教和其他很多宗教,宗教律法在伊斯兰教中存在着更加广泛的重要性,它赋予教士的角色和作用远远超越了在清真寺中组织信众进行祈祷活动。他们不仅是家庭矛盾、商务问题、司法纷争的仲裁人,还是刑事案件中的大法官、官方文件的公证人。在小城镇或乡村中,他们是唯一的权威人士,与当地长老或头人一道扮演事实上的长官角色。在较大的城镇和城市中,欧莱玛往往和集市中的商人及匠人关系紧密。商人与匠人在当地能够取得较高地位并非仅仅因为他们手中的财富,也是因为他们对于宗教的虔诚和敬重所带来的名望。他们往往通过捐钱的方式去表达这种虔诚和敬意,例如修补清真寺的房顶或为当地宗教学校捐款。商人家庭和欧莱玛经常通婚,二者共同组成的市镇统治阶层从19世纪末期以来就长期占据着政治生活的中心位置。通过宗教等级制度、长期宗教研修和家族关系建立起来的相互联系,欧莱玛在教士和普通穆斯林中编织起了一张遍布全国,甚至范围更广的巨大网络。
在伊朗社会中,当世俗权威无法发挥作用或者面临挑战时,普通民众就会转向欧莱玛寻求指引,这时教团就开始发挥作用。高级教士不断以政治异见人士的身份出现,例如1890—1892年,1905—1906年,1951—1953年(在非常有限的程度上),1963年,当然还包括1978—1979年。他们能与其他欧莱玛沟通联络并协调行动,时常利用新型科技进行宣传(1892年利用电报系统,1978年利用磁带和复印机)。与其他群众性运动的潜在领导者相比,欧莱玛固有的宗教权威赋予他们更多优势。宗教权威使他们在面对镇压时享有一定程度的豁免权。世俗统治者们甚至在制裁单个毛拉(5)时都会很难,有时还会起到反作用,甚至根本就不存在这种可能性,因为高级别的宗教导师们往往不在伊朗各级政府的管辖范围内,他们住在纳杰夫,或者伊拉克境内的其他“圣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