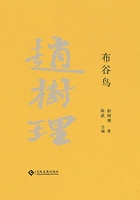
歌生[1]
朱弦响丁丁,
不留停,
把我的生平,
一声声唱向知人听。
我是一只游魂,
任便何人的躯壳,
我都能留存。
当我进了一个人的脑子,
就把他的灵魂一口吞噬;
这个人的躯体,
就能任我驱使。
及至我另换一个躯体,
这个躯体就要七孔流血而死。
当初我是一个叫花,
终日里只知道讨饭寻茶,
“道路”是我的朋友,
“野庙”便做了我的家;
但我是家本分汉,
从不曾设想过发达。
一日我连饭也没有找到一顿,
遇见了两个法警,
他们把铁索套向我的脖颈,
并且叱道:“老爷有话要问!”
法庭开审,
威风凛凛,
好个无礼老爷,
硬要说我和几个不相识者,
打伙劫人,
并且还要问我的同伙共有几人,
都叫作什么名姓?
他们向我施遍了酷刑,
痛杀人哟,
我可该说他们叫甚?
不好!
坏了!
他们给我上了镣铐,
拉到城外过炮。
我要死吗?
真正冤枉不明!
我向执枪者道了个:“饶命!”
他说道:“不行!”
刚刚道了个“不行”,
“砰!”
“……哼哼哼哼,
天师勒令!”
我听到这样个声音,
就应声而醒。
但我醒来时,
已入了一个小瓶。
方寸小瓶,
五花八门,
个中世界,
一言难尽:
小来时杯水难容,
大得来渺尔无垠。
万道霞光,
是宝石还是黄金?
上下八隅,
互相照映。
瓶外曰:
“吾乃逍遥真人,
告汝阴灵:
吾虽不能驾雾腾云,
也曾炼就了五百年道行。
我天师大发慈悲,
命我学救苦观音。
今见汝魂,
悲苦凄清。
汝蒙不白之冤,
吾心何忍?
吾今收汝于瓶,
能使汝得再生;
只要于瓶中住过四十九日,
任何人的躯壳汝皆可留存。
苦哉冤魂,
耐心耐心!”
七七四十九天,
功圆果满,
“逍遥真人呀,
请你放俺!”
“天圆地方,
律令九章……”
还有些听不分明的
“嗡嗡昂昂”。
我的眼睛一亮,
已附在一个人身上。
咦!
好一个生疏的人儿!
“你是谁?你是谁?”
——为什么又是他的口里说的?
我抬起我的手,
又为什么只抬了他的手?
我怀疑,
却只凝了他的眸;
我发愁,
却把他的眉头打成皱。
什么缘由?
真个是教人参不透。
对面一位老道,
向我微微笑:
“吾即真人号逍遥”,
慌得我忙跪倒。
——“莫闹,莫闹!
近前来听吾教:
汝虽附人身,
灵魂可出窍:
此身迁彼身,
彼魂汝吞掉,
彼身即属汝,
亦如再缔造。
先授汝咒几言——默念!
不可使人听见!
再授汝符千道——装好!
千万莫教丢了!
若遇大事难开交,
只需汝叩齿三通灵符三诵,
持一道灵符向空招,
那时间自有吾到。
尚有一事汝记牢:
每一移尸,
回首来需将灵符索讨,
切莫教遗在前尸腰。
得救哉汝魂,
汝可去了。”
行行行行,
我成了自由的灵魂。
真人的言语,
却不知灵也不灵?
待我试试行。
我是一个老人。
我厌老人脸上的皱纹,
将魂一纵,
我成了一个商人,
讨出符来行。
经商我是外行,
贩贷的事业我一件也不能。
将魂一纵,
我成了一个士兵,
讨出符来奔。
当兵的枪炮不离手,
况且又是人家的狗。
将魂一纵,
牺牲了一个小朋友,
讨出符来走。
行行行行,
我成了自由的灵魂。
真人的法语,
真是神而又神。
灵验啊真人!
这位小朋友为我牺牲,
我已成了个学生。
这双眼睛何其晶莹?
这双手臂何其灵敏?
小心儿清清,
小步儿轻轻:
可爱的孩子哟!
我情愿在此寄生。
这小朋友是那里人氏?
他叫作什么名字?
我今寄生于是,
我该向那儿去?
少下得带符念咒,
招问救我的那位道士。
真人的吩咐,
我一一照做:
小朋友的爹妈,
我认做母和父。
小学中学大学,
做了我十余年的去处。
从此寻得人生路,
识得些人情世故;
赏心事儿最堪数,
古今著读破万卷富。
爹妈要我做官。
恶贯满盈的做官啊,
我心如何得安?
逃逃逃!
这事真使人不堪。
穷得光净,
饿得要命,
一个子儿也不剩,
难禁,难禁!
真可谓“非凡养不住圣”。
常听说“士绅腰里多白金”。
我纵牺牲他一个,
也不为残忍;
可是这十余年的寄生恩身,
我怎忍一旦把他牺牲?
踟躇复踟躇,
因循复因循:
饥肠鸣不息,
一刻如一生。
十余年的恩身呀!
与其徐徐饿毙,
何如给你个快迅?
踟躇复踟躇,
因循复因循:
饥肠鸣不息,
一刻如一生。
十余年的恩身呀!
待街头那位士绅走近,
我决然要把你牺牲。
纵出恩身窍,
吞了士绅魂,
回头看恩身,
血泪辨不清。
对不起你啊,恩身!
讨出符来行。
捧符念咒问过了真人,
我将要往士绅的家庭,
“行不顾言”,我并非甘心,
为只为欲得多金。
咄!你蠢笨的顽躯,
胡为乎蠢劣如许?
油腻的脑筋已经不能思虑,
两腮的厚肉又大有碍于言语;
两腿既不适于行旅,
喉间又只留得喘吁。
你愚顽的东西呀!
我若得到了你的白金,
我决计要把你抛去。
行行行行!
已到了这士绅的家庭:
院里的竹石亭亭,
笼中的黄鸟嘤嘤,
卧室内堆花集锦,
客堂上缀玉点金;
忙煞双睛,
看不尽天台胜境。
竹荫动处,
蓦地里浮出天人:
古人云“倾国倾城”,
似这等美人儿,
便是天地[2]也难胜。
把世界上美丽的字样儿写尽,
又何曾道得着她半分。
只她那面人一掬溶人笑,
裙下八面醉魂风,
任你是心冷如水志如鹏,
见她时,
管教你一步也走不动。
我在阶前木一般地站,
她一步步走近我前面,
太鲜艳,
煌(晃)得我一颗心儿搏搏战,
大睁眼,
却不敢向她的面上看。
真人说这士绅有个女孩。
莫非就是她来?
站阶前我且默默地待,
且待她近前来朱唇怎么开。
银铃般的言语疑是燕儿骂,
先来了一声:“爸爸!”
“啊!”我几乎不敢回答。
“你几时回来,
为什么不先到家?”
她说着上前来扶我,
扶我到室内坐下。
这一来,更使我觉着身体笨而大。
走进来一个中年夫人——
她称作母亲,
真人也对我说过,
他一家只此三人!
咄!你这蠢货,
竟是行不能行,坐不能坐。
将魂一纵,
我竟把他的脑子冲破。
蠢大的顽躯七孔流血倒地,
他们母女放声号泣。
我这时惊慌失措,
一时不知该奔往谁的脑里。
我跃入女孩的脑子,
你玲珑小巧的灵魂儿哟,
我怎忍把它吞噬?
为只为两魂冲突我不敢迟迟,
残忍违心的我呀,
这也是没有法子。
凭着她的莺喉,
我假意儿号哭,
抱了顽躯叫爸爸,
暗暗地将灵符摸出。
妈妈说我丧了父,
着我身带一身素,
马萧萧,车辘辘,
送顽躯,归粪土[3]。
吊罢归来对镜晤,
疑是月里婵娟露:
休道何处最可人,
周身俱是可人处。
晤!
再休提什么人生路,
更不须什么古今著,
早知此间有仙人,
何须十年空白苦!
爱玉颜,常对镜;
怜娇音,每自语;
独自穿进花间去,
一步步低头顾。
明月窥人穿窗进,
倚枕自怜玉腕嫩;
抬头向月逞娇姿,
舌尖轻点桃唇润。
“我是何等的幸福啊?”
我是这样问。
有客有客市上过,
谣传不日有战祸;
报端所载亦如之,
太平景象形将破。
“女儿呀!
不日大战起,
我们何处避?”
“妈妈呀!
谣传自谣传,
何必有其事?”
警报连连街头挂,
三朝五日事戎马,
我军敌军将齐来。
前线已在城外划。
“女儿呀!
我说是真言,
你说是谎信。”
“妈妈呀!
谎信已成真,
何处可逃命?”
侦察飞机空中起,
城中男女蜂拥挤,
东西南北奔如潮,
都怕死在炸弹底。
急举符,忙念咒,
“求真人,速解救。”
“此是军家察山川,
大战还在三日后。
汝魂已自由,
何须来解救?
此身纵遭危,
灵魂还可择尸就。”
“真人呀!
弟子太无才,
尘缘未了透:
自得此美后,
身不终兮不愿走。”
“嗟乎吾弟子!
何必自寻苦恼受?
汝既甘如此,
焉得不汝救?
且待它轰天大炮吼如雷,
那时自有吾保佑。”
千军万马城外集,
军乐声声催人急,
两阵哔哔复澎澎,
爆竹声中加霹雳。
“女儿呀!
你说真人三日至,
今日误了性命事。”
“妈妈呀!
真人常是求必应,
想是暗中施法语。”
“赫赫阳阳,
日出东方;
昆仑作顶,
五岳为墙;
刀斧不入,
枪炮不伤;
天师勒令,
永保无殃。”
“妈妈呀,叩谢真人!”
“真人呀,圣德无疆!”
“弟子呀,不妨不妨!
保汝等身体安康。”
轰天大炮如雷吼,
人人闻之头如斗。
哭声伴着杀声嘶,
嘶向北南东西走。
啊!这一片哭声,
何等的刺耳惊心
恸杀人也!
我真不忍再听;
但这大苦难中的人们,
愈苦愈来得逼近。
举符念咒又复招问真人:
“逍遥真人我的师呀!
你曾云天师命你学救苦的观音,
这次啊,为何只佑我母女二人?
你听这满城中哭得何等的可怜,
你怎忍看着他们在轰击声中殒命?”
“弟子呀!
这是人们的大劫来临。
我纵有方怎敢违抗天运?
书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
吾弟子何必忧他人的温冷?”
“我的师呀!
你既不愿违抗天运,
弟子却生就几分叛性。
为只为实在不忍听这种哀音,
我的师呀,请你教我一件本领;
请把我的灵魂分作两分,
让一分儿守此美人,一分儿上阵。
待到把那些杀人的野杂种杀尽,
归来时好再向一处合并。”
“不能,不能,不能!
这是断断不能!
我只能使汝灵魂出窍,
不能教汝身外有身。”
“我的师呀,
你不必多心!
违抗天运我负完全责任,
永不教累及我师毫分。”
“吾弟子为何怀疑太甚?
吾实是无此本领!
‘少见多怪’的弟子呀!
吾将有远行,且待大劫过后,
吾度汝超凡入圣。”
山欲崩兮地欲裂,
掀天揭地连声接,
人人皆恨地无隙,
号兮杀兮嘶不歇。
促损娥眉恨难泄,
咬碎银牙怒更增:
“你无能的道人!
再莫使你的鬼八卦来愚人!
什么是‘大劫’?什么是‘天运’?
你莫非实塞了耳孔,
听不着半点声音?
满城中呼爷叫肉,
你却说‘超凡入圣’。
败兴,败兴!
真来无用!
似这等冷血动物我招你做甚?”
心头火起,我把灵符撕成粉碎。
大劫应是人人在,
怎能把我除外?
脱去了斗篷,
束紧了裙带,
誓向残贼弹雨中,
杀尽头颅方为快。
黑烟滚滚满城焦,
摧楼火焰各逞高,
市民无辜沿路倒,
伤尸和衣带血烧。
伤战同胞!
野贼们视如蓬蒿。
此仇一日不报,
此恨誓死难消!
但我既没有枪炮,
又没有利刀,
激破了肝肠啊,
如何谈得到征讨?
迎面跑来了骏马一骑,
马上既有壮健的身体,
又有鲜明的武器。
势已至此不容我迟疑,
将魂一纵我入了他的脑里。
假狐媚!
还容你误我到几时?
下回顾,
“揉碎桃花”一任他“红满地”。
你盖世无双的美人呀!
我生生害杀你矣。
跨出城来杀向敌线,
惊沙一片狂风劈面,
已不管他如雨的子弹,
更不怕他齐声呐喊。
俺这时一身都是胆,
横冲顺击疾如电,
纵马推开[4]鬣沙沙,
刀光飞处人头乱。
敌人见我马行疾,
个个瞄枪向我击。
血人血马血花飞,
马既仆兮人无力。
此身既遭毁,
魂向彼身匿。
借敌身,还杀敌,
使敌彼此殊难析。
杀到来日鸡声起,
我魂已是千百徙,
十人战,九人死,
百万军人,
中无完体。
惨淡晨光破晓初,
萧萧沙场集群鸟。
暴富野犬走西东,
败血如酱满地涂。
到头来我的腿上中了两弹,
战功上再没有好尸可换,
那时这位歌者走过我的前面,
可巧救了我这场急难。
我自得此身,
算来二十春,
口中门牙落,
鬓上白发生。
日日吟往事,
回回唱生平。
朱弦不绝手,
处处告知人。
[1] 本篇原载《民报》1932 年 3 月 12 日至 3 月 25 日第 4 版和山西教育学院《夜光》杂志(1932 年 3 月出版),署名均为“野小”。本篇据《民报》。
[2] “天地”,《夜光》杂志作“大地”。
[3] “粪土”,《夜光》杂志作“黄土”。
[4] “推开”,《夜光》杂志作“唯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