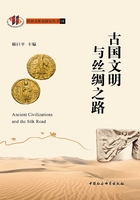
绪论
本书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丝路古国文明研究》(11JJD770024)的结项成果。当时拟定的研究重点是古代,也即公元7世纪以前丝路沿线国家的历史和文化。这些国家有的地处丝路的核心地区和交汇中心,有的地处丝路的终点,有的则处于丝路的支线地区。它们的兴衰与丝绸之路的走向与发展直接相关,丝路贸易、丝路文化交流是这些国家或地区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我们最初的计划是把丝路古国文明作为主要研究的对象,以丝绸之路上的巴克特里亚—印度—贵霜文明、帕提亚—萨珊波斯文明、塞琉古—罗马文明为个案进行分析。2013年,国家提出“一带一路”的倡议,我们在深受鼓舞的同时,也得到新的启示,对原来的研究重点做了调整。“一带一路”覆盖的现代国家大多都是在原来丝路古国的基础上发展而来,这些古代国家都曾是丝绸之路的推动者与得益者,它们都是通过丝绸之路与古代中国建立了直接或间接、这样或那样的联系。自司马迁以来,中国古代史籍对它们的记载延续不绝就是最好的证明。研究它们与丝绸之路的关系,并进而梳理它们与古代中国的关系,对于“一带一路”宏伟蓝图的实施可能会更有现实意义。为此,我们及时调整了研究思路,将这些古国或古代文明区域与丝绸之路的关系作为重中之重。我们确定了一些与早期丝路的开通和拓展有密切关系的国家、地区和民族作为个案研究的对象,统称为丝路古国,它们分别是张骞通西域时还存在于中亚、印度和东地中海地区的各希腊化王国,处于丝路西段当道的帕提亚帝国,公元后崛起于中亚、印度西北部的贵霜帝国,东扩至两河流域一线的罗马帝国,取代帕提亚帝国的萨珊波斯帝国,以及地处丝绸之路十字路口的粟特地区。在欧亚大陆的北方,横亘着一望无际的大草原(Steppe),它曾是无数游牧民族生存繁衍的地区,也是东西方文明的最早的交流孔道。早在绿洲丝路开通之前,中国的丝绸就已经通过游牧民族的接力传输到欧洲,后来它更是成为丝路北道的一个支线。所以,我们以公元前1000年纪中后期活跃于欧亚草原的斯基泰人为例,对他们在草原丝绸之路的开拓、开通以及在推动东西方经贸与文化往来方面所发挥的历史作用也做了梳理。
我们的研究证明,历史上凡是通过丝绸之路与中国中原王朝建立经贸和文化关系的国家、地区和民族,在为古代中西或东西方的文化交流做出贡献的同时,也促进了它们自身文明的发展。强大的汉唐帝国所输出的政治影响和散发的文明魅力曾经使数万里之外的远国都来归服,中国丝绸更是受到了远至罗马的丝路各国的欢迎和珍爱。与此同时,丝路各地的文明遗产也通过丝绸之路传到了中国境内,从而丰富了中华文明的内涵,有的经过改造吸收后,融入了中国文化传统的主流之中。最为典型的就是印度的佛教,竟然成为与儒、道并列的中国三教之一。这不能不说是中印两大文明交流史上的奇迹。既然这些早期国家和地区能够通过丝路与当时的中原王朝建立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联系与交流,中国能够以自己强大的帝国、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明对远至地中海的西域诸国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与这些丝路沿线国家、地区和民族建立友好的关系,为什么在今天的全球化时代,我们不能重建现代丝绸之路,与世界各国,尤其是古代丝绸之路(不论是陆上还是海上丝路)的沿线国家和地区建立起新的经济纽带和文化交流关系呢?本课题的研究或许可以对此提供一些历史的借鉴和启示。
关于丝绸之路的研究,最早始于19世纪后期。1877年,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其著作《中国:亲历与研究》一书中正式提出了“丝绸之路”这一名称[1],逐渐为学术界所接受。最早对我国境内丝路遗迹遗物产生狂热兴趣的是一批来自欧洲、日本的所谓探险家们。对于他们的政治背景和文化动机国内近百年来已有公论,但毋庸置疑的一点就是,这些所谓的学者、汉学家、探险家在我国西北的考察、发掘和窃取文物活动却拉开了丝绸之路研究的序幕。与此同时,西方的一些学者也从19世纪开始,对近东、中亚、印度等古老文明之地的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古代埃及、两河、伊朗、中亚、印度的历史都进入了他们的视野之中,古老的中国自然也不例外。在这一股对古老的东方文明研究的热潮推动下,丝绸之路自然成为重点关注的研究对象之一,丝路沿线国家、地区和民族的历史也就纳入了他们的近东史、中亚史和印度史当中。我国学者20世纪20—30年代组织参与的中瑞西北合作考古考察活动,40年代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的设立,都表明了当时国内各界认识到了丝路研究的重要性。向达先生的《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张星烺先生编译的《中西交通史料汇编》、冯承钧先生的《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第一编)都是当时享誉一时,且影响至今的代表作。冯先生的译作介绍了国外丝绸之路研究的最新成果,是值得特别重视的。
20世纪50年代以来,国内对丝路的研究一直没有中断,近年来尤其推出了一大批专门研究和译介之作。余太山先生多年以中国古代正史中有关西域的记载为基础,致力于古代西域诸民族、国家的历史研究,他的系列专著,如《两汉魏晋南北朝与西域关系史研究》、《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西域传研究》、《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西域传要注》以及《塞种史研究》、《嚈哒史研究》等,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普遍重视。[2]王治来先生的《中亚通史》,是国内学者出版的首部多卷本中亚通史。此书在20世纪80年代分别以《中亚史》、《中亚史纲》之名单册出版。[3]赵汝清先生的《丝绸之路西段历史研究》[4],将帕米尔高原以西到地中海方向的丝路划为西段,大致包括帕米尔高原、中亚、伊朗高原、两河流域、地中海东岸。该书认为:丝绸之路之前,东西方之间已有天青石贸易之路、雅利安人迁徙之路存在。即使是丝绸之路,也有草原路、绿洲路和海上路之分。该书的丝路西段就是绿洲之路。此书涉及对阿拉伯人到来之前的丝路沿线同时或先后出现的国家的历史,如塞琉古王国、帕提亚、贵霜、萨珊波斯、罗马、嚈哒等,重墨叙述中国与这些国家的关系以及它们之间的政治外交关系或文化传承关系,与本课题的研究范围比较吻合。这些年翻译过来的相关学术著作,不论就史料和观点上都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尽管其中相当一部分采用的都是20世纪初期或中期的版本。这些著作以宏观性的地域研究为主,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出面组织编写的六卷本《中亚文明史》(History of Civ-ilizations of Central Asia)可谓是代表之作。此书由国际中亚史的权威学者集体编写,而且他们大多是本土学者,就学术价值而言,自然属于最高水平,就史料价值而言,也是国内求之不得。其中第2卷《定居文明与游牧文明的发展:公元前700年至公元250年》[5]与本课题的研究最为有关。
从目前资料来看,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仍然是我们的主要参考依据。就丝路古国的研究基础而言,清末民初国外汉学家的第一手考察资料和著述尤其值得重视。主要有:英国学者斯坦因(M.A.Stein)的《古代和田》(1907年)、《西域考古记》(1921年)、《亚洲腹地考古记》(1928年)[6]、德国夏德(F.Hirth)的《中国与罗马的东方》(1885年)[7]、美国学者劳费尔(B.Laufer)的《中国伊朗编》(1919年)[8],日本白鸟库吉的《粟特国考》(1924年),《大宛国考》(1916年)、《月氏国的兴亡》(1904年)《罽宾国考》(1917年)、《塞民族考》(1917—1919年)、《大秦国及拂菻国考》(1904年)、《条支国考》(1926年)、《见于大秦传中的西域地理》(1931年)、《拂菻问题的新解释》(1931—1932年)等一系列关于西域各国的考证[9],藤田丰八(1869—1929年)的《西域研究》[10]、《西北古地研究》[11],桑原隲藏的《张骞的远征》(1916年)[12],羽田亨的《西域文明史概论》(1931)和《中央亚细亚的文化》[13]等。这些著作虽然时过百年或大半个世纪,但由于立足于实地考察和通晓多种古代语言的基础之上,所以仍是我们今天研究的起点。
丝绸之路的整体研究素来被国外研究者所重视。全球化浪潮的兴起,使古老的丝绸之路再次得到国际学界的关注。日本学者长泽和俊的《丝绸之路史研究》[14]、法国学者阿里·马扎海里的《丝绸之路:中国—波斯文化交流史》[15]以及近年新出的英文专著,如弗兰克和布朗斯通(I.M.Franck &D.M.Brownstone)的《丝绸之路史》[16]、余英时的《汉代中国的贸易和扩张:汉胡关系结构研究》[17]、贝克威斯(C.I.Beckwith)的《丝路帝国:青铜时代至今的中部欧亚大陆研究》[18]、刘欣如的《世界历史中的丝绸之路》[19]、韩森(V.Hansen)的《丝绸之路新史》[20]、弗兰克潘(P.Franko-pan)的《丝绸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21]都从不同的角度对丝绸之路的实质和内涵做了深入的分析。余英时和刘欣如是华人,熟悉中国方面的史料,对国外的研究成果又能及时地吸收,他们的著作相对而言有较高的参考价值。贝克威斯的《丝路帝国》主要关注的是欧亚大陆中部各主要游牧民族与大国之间的关系,对以前通行的观点做了重新审视与修正。作者认为,丝路的兴衰与沿线帝国的命运息息相关,所以要把二者联系起来进行研究。韩森是耶鲁大学的教授,精通汉语,她的《丝绸之路新史》选取了从中国长安到中亚撒马尔罕(Samarkand)之间的7个丝路重镇(其中6个在中国境内)作为个案,利用最新的考古材料说明:丝路只是各段的连接,丝绸只是丝路转输的商品之一,甚至也是丝路货币之一;出产于中国的纸也是丝路的主要商品;早期罗马帝国并没有和中国发生直接的丝绸贸易。该书重点在中国西域,但其研究方法值得借鉴。彼得·弗兰克潘的《丝绸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因其立意新颖、视野开阔,成为西方世界的畅销书。他将古代丝绸之路与现代历史现实结合起来,将丝绸之路演化为信仰之路、基督之路、变革之路、和睦之路、皮毛之路、奴隶之路、天堂之路、铁蹄之路、重生之路、黄金之路、白银之路、西欧之路、帝国之路、危机之路、战争之路、黑金之路、妥协之路、小麦之路、纳粹之路、冷战之路、美国之路、霸权之路、中东之路、伊战之路等24条不同的历史发展之路,似乎丝绸之路就是世界历史的源头,丝绸之路史就是一部世界史,而中亚——古老的丝绸之路的核心地段就是世界的心脏。这样的观点值得商榷,但就本课题的研究而言,该书在研究方法上的启示意义要大于它所提供的史料参考价值。
关于丝路古国的国别史研究,虽然近代学者大多未把它们与丝绸之路相联系,但对于本课题也很重要,因为它们提供了这些丝路古国的历史和文化概况。关于安息(帕提亚)、大夏(巴克特里亚)、萨珊波斯诸国,国外学者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就有专著问世,主要有乔治·罗林森的帕提亚—萨珊系列,如《古代史手册:从远古到萨珊波斯帝国的衰落》(1880)[22]、《东方第六大君主制国家或帕提亚的地理、历史和古物》(1873)[23]、《帕提亚》(1903)[24];休·乔治·罗林森的《巴克特里亚:从远古到巴克特里亚——希腊人的统治在旁遮普的消失》(1909)[25]和《巴克特里亚:一个被遗忘的帝国》(1912)[26]。近年来,巴克特里亚希腊人王国再度受到学者的重视,除了两大代表人物塔恩的《巴克特里亚和印度的希腊人》(1938年第一版,1951,第二版)[27]和纳拉因的《印度—希腊人》(1957)[28]分别于1984、2003年先后再版之外,关于巴克特里亚的新著有 H.西德基的《巴克特里亚王国:从亚历山大到欧克拉提德大帝》(2000)[29]和《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的兴衰》(2004)[30]。美国休斯敦大学的霍尔特教授是亚历山大和巴克特里亚希腊人王国研究的专家,近年来的一系列著作都是围绕巴克特里亚地区展开,与本课题有关的主要有:《亚历山大大帝与巴克特里亚:中亚希腊人边界的形成》(1988)[31],《发出雷电的宙斯:希腊化巴克特里亚的形成》(1999)。[32]巴克特里亚希腊人王国(大夏)虽然在张骞到来之前已经臣服于大月氏,但它为后来贵霜帝国的兴起以及从中亚到印度河口丝路的开通奠定了基础。
关于贵霜的研究近年也有几部专著出版,如B.N.慕克吉的《贵霜世系与编年研究》第一卷《贵霜世系》(1967)[33],S.J.科祖马和R.莫里斯合著的《贵霜雕塑》(1985)[34],B.R.摩尼的《贵霜文明:城市发展与物质文化研究》(1987,2013)[35],M.K.塔库尔的《迦腻色伽时代的印度》(1998)[36],P.L.笈多与S.库拉士勒士塔合著的《贵霜钱币与历史》(1994)[37]等。贵霜研究中的重大问题,如贵霜前期国王的王系编年,尤其是迦腻色伽的在位时间,贵霜王朝与犍陀罗艺术起源的关系等都是长期困扰学界的历史悬案。
一些大型系列丛书和中亚史著作也包含了丝路古国的历史,如第二版的《剑桥古代史》第7卷及其以下各卷(对希腊化世界、帕提亚、萨珊、罗马帝国与东方均有涉及)、《剑桥伊朗史》第2卷[38]、费耐生(Richard N.Frye,一译理查德·N.弗莱)的《古代伊朗史》[39],拉普森的《剑桥印度史》第1卷[40],麦高文的《中亚古国史》[41](1939年初版,中华书局2004年汉译重印),丹尼斯·西诺尔的《剑桥早期内亚史》[42]。这些丝路沿线国别史和地区史的研究成果对于分析它们的历史演变和文明因素构成极具参考价值。此外、丝路各国的钱币、艺术、宗教、音乐、民俗、社会经济诸方面也都有专门的资料汇编和论著问世。
以上只是对百年来丝路研究的简单回顾。面对浩如烟海、叹为观止的丝路研究资料和国内外各种语言文字的研究成果以及世界各地博物馆的收藏,凭我们的浅薄学力,根本无法全面构建丝路及沿线古国研究的学术史。但总的看来,现有的或我们所知的研究成果已经涉及到丝路的诸多方面,而且对丝路的历史作用认识也趋于一致,认为它不仅是东西方或中西之间的一条商贸之路,也是一条文化交流之路,甚至是一条共同发展之路。但目前国内的相关研究也有明显的不足:一是重点分散,以丝路遗物遗迹和文献考据为主,全线的系统研究不多;二是国内研究注重境内的考古发现,对国外丝路研究成果缺乏充分的吸收和利用,文献解读能力和研究基础还有待提高(如外语和必要的世界古代史知识与视野);三是丝路沿线文明古国对于丝路文明的形成和东西方文明互动的贡献和作用的研究还有待深入。丝路研究是个跨学科研究,需要历史学、考古学、钱币学、碑铭学、古文字学,甚至古人类学、古生物学、民族学、艺术史、宗教学等诸多学科的参与。我们的团队是从世界古代史、中外古代文化交流史的角度来研究这些丝路古国文明史的,因此,我们力求在吸收、综合、分析其他学科研究成果的同时,确定自己的研究方向,调整自己的研究思路。这些丝路国家、地区、民族到底在丝绸之路上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是我们研究的重点,也是贯穿于全书的主线。
如前所示,本课题的丝路古国是指公元前二世纪张骞西域凿空到公元七世纪阿拉伯帝国建立以前在丝绸之路沿线曾经存在过的国家、地区或文明。之所以以此为限,主要基于以下考虑:
根据现在学界的研究趋势,丝绸之路这一术语已经泛化,远远脱离了它最初的含义——中国通往地中海以丝绸为主要标志性转输品的陆路交通线。现在学术界公认的丝绸之路主干线有三条[43]:一条是绿洲丝绸之路(the Oasis Silk Road),就是张骞通西域之后连通中国中原地区与地中海世界这条东西方向的主干道。我们所说的丝路沿线国家、地区和民族主要就是围绕这条道路而言。一条是海上丝绸之路(theMaritime Silk Road),是将地中海的亚历山大里亚与中国南部城市联系起来的一条海上通道,途经红海、阿拉伯海、印度洋和南海。它在阿拉伯半岛、波斯湾、印度与陆上丝绸之路相连接。我们所说的丝路沿线国家多与海上丝绸之路有着这样或那样、直接或间接的关系。三是草原丝绸之路(the Steppe Silk Road)。由于草原游牧民族的流动性,这条道路时断时续,并没有成为丝绸之路的主要组成部分。更为重要的是,草原丝绸之路始于何时,学术界尚有不同说法。有的学者把丝绸之路看作是欧亚大陆民族迁徙之路,所以在中国新疆地区小河墓地欧罗巴人种特征的木乃伊出土之后,有学者就把丝绸之路的上限提到了公元前2000年代左右。[44]有的学者仍然坚持寻求丝路的基本证据——丝绸的遗迹,来确定草原丝绸之路的大致走向和西传的时间。在德国公元前6世纪一个克尔特人(Celts)首领古墓中发现的丝绸织物是现今所知最早传至欧洲的丝绸。[45]在约公元前5—前3世纪的阿尔泰(Altai)巴泽雷克(Pazyryk)古墓出土的丝绸刺绣、中国的山字纹铜镜证明草原丝绸之路先于绿洲丝绸之路的存在。[46]有人甚至设想,希腊古典时期人物雕塑所穿的细薄透明的衣服有可能来自中国的丝绸。[47]无论如何,中原的丝绸在张骞通西域之前通过游牧民族传输至中亚、欧洲是不争的事实。即使在绿洲丝绸之路全线开通之后,这些流动于欧亚草原上的游牧民族也同样参与了丝路贸易和文化交流的活动。其中有些在丝路沿线建国的民族本来就是从游牧的“行国”转化为定居的王国或帝国,如:建立帕提亚—安息帝国的阿帕尼亚人(Aparnians,Aparni)或帕尼人(Parni)、贵霜帝国的大月氏人、印度—斯基泰人(Indo-Scythians)王国的萨迦人(Sakas),甚至粟特人的祖先康居也是逐水草而居的“行国”。公元1世纪在阿富汗“黄金之丘”(Tillya Tepe)发现的具有草原游牧文化与希腊化艺术、中国汉文化相结合特征的艺术品,就是这些游牧民族参与丝绸之路活动的证明。《厄立特里亚航海记》(The PeriplusMaris Erythraei)中提到来自中国的毛皮,显然来自草原游牧民族。[48]中国西汉王朝初期给匈奴馈赠大批的丝绸(絮缯),也有可能被转手输送给西方。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以绿洲丝路为基础的丝路古国与海上丝路和草原丝路都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然而,这种丝路格局在阿拉伯帝国兴起后有所改变,丝路沿线的主要国家相对单一,即先是阿拉伯帝国,后是蒙古帝国及其汗国,丝路文明的统一性大于多元性。中原王朝则一度被辽、金、元所取代。而且元明之际,海上丝路成为东西方交往的主要通道,大有取代陆路交往之势。这两大帝国的历史及其对于丝路的贡献前人研究比较详备,但七世纪以前的这些丝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研究则相对薄弱。中西方史籍中常常提到的巴克特里亚(Bactria,大夏、后称Tukhara,吐火罗)、帕提亚(Parthia,安息)、萨珊波斯(Sassan Empire,波斯)、贵霜(Kushan,地跨印度、中亚)、粟特(Sogdiana,索格底亚那)、大秦(罗马帝国,Roman Empire,或罗马的东方,the Roman Orient)等这些古国与丝绸之路的关系,国内也鲜有系统的研究。而且,随着新的考古资料的出现,尤其是钱币、城市遗址、寺庙遗迹、墓葬、碑铭等实物的大量出土,都使进一步的研究成为必要和可能。利用这些实物资料,对这些文献记载比较模糊或阙如的国家和地区的文明进行重建和复原,特别是力求解决一些悬而未决的历史疑案,这对于弥补我国中亚、西亚古代文明研究之不足,改变重本土、疏域外的研究现状,建立以本土资源为基础的全线式、多方位丝路研究体系应该说还是有一定学术价值的。
此外,这些国家分布于中亚、印度、西亚到地中海一线,是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或终端,对丝绸之路的开通、延伸和延续以及丝路上东西方文明的接触、交流、融合或多或少、直接或间接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它们不仅是东西方文明的传播者,而且本身就是丝路文明的创造者。当然,由于所处历史时期、地理位置和自身文明发展程度的差异,这些国家和地区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这就需要在总体分析的基础上,对主要的国家和地区做深入的个案研究,尤其要关注它们和当时中国中原王朝的关系到底如何,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是否有实质性的交往。我们知道,汉唐之际正是中国和其他西域国家交往最为密切的时期。中外使者、商人、僧人不绝于道,传递的是友谊、文化和理解。中国输出的是丝绸、炼钢术、漆器、一些植物的栽种技术,但得到的却不仅仅是西域的奇珍异宝,或者葡萄、苜蓿,还包括佛教(Buddhism)、祆教(Zoroastrianism)、摩尼教(Manicheism),景教(Nestorianism)、伊斯兰教(Islam)以及这些宗教所携带的艺术,这些异域文化因素都不同程度地融入了中华文化的系统之中。所以,本课题将阿拉伯帝国建立之前不同时期的沿线国家和地区对丝路文明互动的贡献作为研究的重中之重。
本课题之所以选择各希腊化王国、帕提亚、贵霜、罗马、萨珊波斯、粟特人和斯基泰人(Scythians)作为研究的个案,是由它们在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历史地位决定的。
张骞大约自公元前128年起进入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等中亚腹地国家,事实上也就进入了希腊化世界,进入了远东希腊化文明圈[49]。当时,巴克特里亚希腊人王国虽然已经被大月氏人征服,但它的王朝仍然残存于巴克特里亚东部的山区和兴都库什山(Hindu Kush)以南的印度西北部。那些作为印度—希腊人的小王国正在蓬勃发展,像米南德(Menader,约公元前165/155—前130年在位)王国甚至一度有可能扩张到了恒河流域。张骞所亲历的这几个国家,原来都是亚历山大帝国、塞琉古王国(the Seleucid Kingdom)和巴克特里亚王国的辖地。大夏西边的安息即西方史籍中的帕提亚帝国。它也是从塞琉古王国独立而来,是个典型的亲希腊国家。[50]更西边的是以叙利亚为中心的塞琉古王国,它一直坚持到公元前64年被罗马征服。埃及的托勒密王国(Ptolemaic Kingdom)则直到公元前30年才灭亡于罗马之手。张骞抵达中亚之时,希腊化世界还存在于欧亚大陆,他所涉足的中亚地区也刚刚脱离希腊人的统治,希腊化文明的遗产随处可见可闻。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从印度、中亚到地中海,在波斯帝国时期就有比较完备的道路系统,亚历山大当年征服波斯帝国,利用的也是这套道路系统。希腊化时代初期,亚历山大帝国的亚洲遗产几乎都被塞琉古王国接受,这一道路继续保持畅通,即使在帕提亚人独立后,从地中海到中亚、印度的道路也没有出现完全中断的现象。阿育王(Asoka,Ashoka)派传教团到东地中海的希腊化国家,一位希腊人把德尔斐(Delphi)神庙的格言带到3000英里之外今日阿富汗的阿伊·哈努姆遗址(Ai Khanoum),都证明东西方道路的通达。所以,张骞一旦进入中亚,事实上就踏上了通往东地中海的道路。后来,其他的中国使者到达了更远的安息、身毒等国,事实上就等于与希腊化世界建立了联系。因此,此时仍然存在的希腊化王国:巴克特里亚—印度—希腊人王国、塞琉古王国、托勒密王国对丝绸之路的奠基作用也不应忽视。
帕提亚在中国史籍“前四史”关于西域的记载中,地位显著。张骞首次出使,只听到关于它的传闻。公元前119年,他二次出使西域,派副使前往,受到隆重欢迎。安息国王用两万骑兵把中国的使者从东界木鹿护送到都城番兜,然后又遣使回访中国,从而与汉王朝建立了正式的外交与商贸关系。这种和平友好关系一直维持到萨珊波斯时期。帕提亚地处丝路要道,商贸十分发达。它有大小数百城,有车、船水陆商路(“临妫水,有市,民商贾用车及船,行旁国或数千里。”),有通用货币——希腊式银币(“以银为钱,钱如其王面,王死辄更钱,效王面焉。”),素有经商传统(“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善市贾,争分铢。”)[51],与大秦、天竺“交市于海中,利有十倍”。[52]中国史书记载它阻隔大秦与中国的直接交往,大概也不是空穴来风。它的东部地区还是佛教在中亚的传播之地,所以会有东汉时期安息王子安世高放弃王位到中国翻译佛经的记载。
帕提亚的继任者萨珊波斯王朝与中国中原王朝的关系更为密切,不时遣使纳贡。波斯末代国王后人甚至到中国避难不归,[53]乾陵的胡人雕像中可能就有他们的身影。[54]拜火教(祆教)、摩尼教、景教就是在萨珊波斯时期或者通过萨珊波斯传入中原的。西安出土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揭示了景教入华的经过。它的祭所被称为“波斯寺”就充分证明了它和波斯的关系,尽管它是基督教的一个分支和异端,是在拜占庭帝国遭受迫害东传而来。
贵霜帝国与大月氏的关系本来很简单。根据《史记·大宛列传》与《汉书·西域传》的记载,大月氏本居敦煌、祁连间,也是个游牧民族(行国)。后来,由于受到匈奴的攻击,被迫走上了逃亡之路,经大宛,“西击大夏而臣之”。张骞抵达时,大月氏据有阿姆河(Amu Darya,即the Oxus)之北大夏之地,在此设立王庭,大夏仅保有阿姆河之南的巴克特里亚,成为大月氏的属国。大夏虽“无大君长”,但有自己的都城蓝市城,其余各城有小长,人口百余万。应该说还是一个大国。张骞历尽千辛万苦,不忘使命,辗转前来寻找大月氏,就是想向其国王传达汉武帝合击匈奴的愿望。但不料月氏王“既臣大夏而居,地肥饶,少寇,志安乐,又自以为远汉,殊无报胡之心”。张骞“从月氏到大夏,竟不能得月氏要领”,无奈之下,只好在“留岁余”后返回。这就是公元前128年前后的大月氏和大夏。公元前119年,张骞二次出使西域,还派副使访问过大月氏和大夏,可见此时,二地仍然保持原状。但一个多世纪之后,也就是在班固的《汉书·西域传》中,大月氏和大夏的记载发生了变化。此时的大月氏,已非行国,而是一个有明确的都城(监市城),有四十万人口和十万兵力的定居大国,“土地风气,物类所有,民俗钱货,与安息同”。此时的大夏分属五翖侯,各有治所。其中一个翖侯是贵霜,治所在护澡。大夏作为一个属国已不复存在。大月氏将其地全部占有,分为五个翖侯管辖。这至少应该是公元前后大月氏的基本情况,因为班固的《汉书》的下限就是此时。当然《汉书》的成书是在公元一世纪后期,班固是否会从担任西域都护的弟弟班超那里获得大月氏当时的信息,不得而知。五翖侯分治是否发生在张骞和司马迁之后不久,还是很久,也不得而知。但根据《后汉书·西域传》,月氏西迁大夏后,分其国为五翖侯。“后百余岁,贵霜翖侯丘就却攻灭四翖侯,自立为王。国号贵霜王。……月氏自此之后,最为富盛,诸国称之皆曰贵霜王,汉本其故号,言大月氏云。”这一段话讲得很清楚,五翖侯分治发生在大月氏西迁大夏后不久,贵霜是大月氏五翖侯之一。贵霜帝国是从大月氏发展而来。
由于资料的有限,贵霜帝国的历史一直比较模糊。我们现在仅仅可以肯定的是,在第一任国王丘就却和其子阎膏珍时期(约公元一世纪中后期)[55],贵霜先后征服高附、濮达、罽宾、天竺,其地盘从阿姆河流域扩展到了印度河地区,建立了一个中亚—印度大帝国。该帝国在第四任国王迦腻色伽(Kanishka)在位时期达到全盛,此后逐渐衰微,到三世纪之后消失。贵霜作为一个处于丝绸之路十字路口的帝国,南北连接草原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东西连接中国和西亚,它在丝绸之路上的枢纽作用不容低估。从现在的考古发掘来看,贵霜境内的城市在东西方文明交流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亚历山大、塞琉古王国、巴克特里亚—印度—希腊人在中亚、印度建立的城市几乎都在它的控制之下。现在的坎大哈(Kandahar)、贝格拉姆(Begram)、铁尔梅兹(Termez)、巴尔赫(Balkh)、塔克西拉(Taxila)、塔赫特·伊·桑金(Takht-i-Sangin),在贵霜时期都是著名的丝路城市。贵霜时期也是海上丝绸之路形成的时期,由于季风的发现,从埃及到印度的直航成为可能,北方草原的皮毛、印度的香料、中国的丝绸、漆器、地中海的葡萄酒、希腊—罗马式雕塑艺术品也都通过这条海路互通有无,希腊化的罗马艺术家也在此时通过海路来到印度贡献才艺。源于犍陀罗地区的佛教艺术就是在这一时期受到希腊—罗马艺术的第二波影响逐渐形成并发展起来的,佛教及其艺术也是在这一时期在中亚扎根并由此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中国的。贵霜帝国由于与中国东汉政府管辖的塔里木盆地接壤,曾经派兵深入中国西域,干涉其内部事务,但遭到班超的全力阻击,失败而归。但月氏还是想保持与汉朝的关系,多次遣使同通好。公元一世纪之后,西域都护撤离,贵霜的势力和影响乘虚而入。佉卢文(Kharosthi)木牍文书、希腊式人物雕像、汉佉二体钱(Sino-Kharosthi Coin)在此地的流行和使用,都证明了贵霜文化的影响及其与中原文化在这一地区的汇合。
大秦是丝绸之路西端的一个大国,现在一般将其比对为罗马帝国,或罗马的东方或埃及。大秦之名首次出现于东汉时期。据《后汉书·西域传》,“大秦国,一名犁鞬,以在海西,亦云海西国。……其人民皆长大平正,有类中国,故谓之大秦。”[56]关于大秦的记载《魏略·西戎传》更为详细。二书涉及内容大致相近,其中特别提到了它与天竺和安息“交市于海中”,事实上反映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存在。至于它是否和当时的东汉帝国有直接的丝绸贸易,学界仍有争议,但在公元前后罗马人接触到丝绸则是有据可证的。“前三头”之一的凯撒(Caesar,公元前100—前44年)曾经用来自中国的丝绸在罗马的广场上搭起天蓬遮阳,以取悦观众。[57]罗马作家普林尼(Pliny the elder,公元23—79年)曾经惊呼巨量的罗马金钱流入印度和赛里斯(Seres),[58]这些金钱确实流出了罗马,但主要流入了印度,部分也流入了安息,至于丝绸之路东端的中国,并没有见到这些罗马的钱币。到现在为止,在中国境内所发现的罗马金币都是公元四世纪以后的拜占庭(东罗马)帝国皇帝发行的。反之,贵霜帝国在丘就却(Kujula Kadphises)时期就发行了仿奥古斯都(Augustus)型钱币,到第三任国王威玛·卡德菲塞斯(Vima Kadphises)之时,金币大量出现,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迦腻色伽时期。贵霜金币的突然出现说明罗马金币的输入,在《厄立特里亚航海记》中,我们甚至可以看到,罗马金币不仅是支付的手段,更是交易的商品。[59]双方的贸易主要还是通过实物交换来进行。至于《后汉书·西域传》记载的东汉“桓帝延熹九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犀角、玳瑁”之事[60],显然是从印度而来的大秦商人冒充罗马安东尼王朝的使者,以抬高自己的身份,获取馈赠而已。但他们的到来标志着从埃及到中国的海上丝绸之路的全线贯通。这个事件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至于中国史书中对大秦的记载,显然是道听途说或杜撰的想象,是把一个遥远的国度理想化的结果,与真正的罗马帝国、罗马的东方、罗马的埃及都相去甚远。但其中还是透露了一些西方世界的信息,如关于它的海西位置(波斯湾还是地中海以西?),那些众多的城市、宫廷议事制度,那些琉璃、水晶、珊瑚、细布、香料等特产,那些关于与天竺、安息的海上贸易,那些关于金银之间1 ∶ 10的兑换比率,还是在一定程度上是有迹可寻的。大秦—罗马帝国的信息尽管很不准确,但它毕竟传到了中国。中国——罗马,欧亚大陆东西端的两个大帝国,终于通过丝绸之路联系起来了,这是古代中外文化交流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件大事。
至于中国与大秦的关系,向来是国际学界关注的话题。班超派遣甘英于公元97年出使大秦,“抵条支而历安息,临西海以望大秦”[61],已经到达安息西界,与大秦隔海相望,但却被安息西界船人所恐吓,中途而返。安息人为了垄断丝路贸易,不愿中国这个产丝大国与大秦这个丝绸消费大国接触,以海上航行之危险阻挠中国使者前往,似乎言之成理。但即使甘英出使大秦成功,中国的丝绸要想直接到达罗马,还是要经过帕提亚的所辖之地。它要中途作梗,还是易如反掌。但事实上,罗马此时已经开通了直达印度的海上航线,安息、天竺和大秦交市于海中,就是这种海上丝路开通的真实写照。
粟特在历史上是作为一个地区出现的,粟特人是作为一个民族出现的。历史上并没有出现过一个统一的“粟特”国家,但粟特地区曾经存在过许多诸如大宛这样的多城之国(“其属邑大小七十余城,众可数十万”[62]),大月氏、康居这样的行国,后来也存在过像“昭武九姓”这样的绿洲小国。粟特人地处中亚的河中(Transoxiana)地区,主要活动于以泽拉夫善河(Zerafshan River)流域为中心的地区,撒马尔罕(马拉坎大)、苦盏(Khujand,贵山城)、塔什干(Tashkent)、贰师城(故址在今吉尔吉斯斯坦西南部奥什市的马尔哈马特)、片治肯特(Panjikent)等应是粟特地区的中心城市。粟特(索格底亚那)曾是波斯帝国的一个行省,曾经派人参加过希腊波斯之间的战争。亚历山大征服中亚时,索格底亚那当地人曾经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以至于亚历山大用三年时间才平定局面。他在此地和巴克特里亚(Bactria)建立了至少8 座城市[63],其中最有名的是建于锡尔河(Jaxartes,the Syr Darya)畔的“最远的亚历山大里亚”(Alexan-dria Eschate)、马尔基亚纳(Margiana)的木鹿城和铁尔梅兹(Termez,都密),还有一个称为奥克苏斯河畔的亚历山大里亚(Alexandria on the Ox-us)[64],至今地址不详。撒马尔罕古城遗址(Afrasiab)就发现了希腊—马其顿驻军的城堡。亚历山大时期,此地归巴克特里亚总督管辖。他死后,巴克特里亚和索格底亚那各设有专门的将军。[65]塞琉古王国时期,两地重归于一位总督之下。巴克特里亚独立后,索格底亚那地区成为一个新的总督区,推翻狄奥多托斯(Diodotus)王朝(约公元前250—前230年)的欧泰德姆斯(Euthydemus,约公元前230—前200年)有可能就是此地的总督。大月氏人西迁经过的大宛,就是希腊人所说的索格底亚那的一部分。[66]张骞出使西域经过的大宛、康居、大月氏之地就属于索格底亚那地区或者广义上的巴克特里亚地区或河中地区。贵霜帝国时期,其统治范围是否包括希萨尔山(Hissar)以北的索格底亚那地区,没有明确证据,但此地显然是它在北面的统治极限,它的重心在阿姆河流域与印度河流域。我们对贵霜帝国时期的粟特地区了解甚少,但它无疑是汉代丝路北道的必经之地。四世纪以后,粟特之名开始出现于中国史籍(《魏书·西域传》)。粟特人的形象也逐渐清晰起来。他们善于经商,这在张骞时代即已知晓:“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国虽颇异言,然大同俗,相知言。其人皆深目、多须髯,善贾市,争分铢”[67]。粟特人利用自己处于丝路中心地区这一优越的地理条件,为丝路文明的发展和东西方文明的交往做出了独特的贡献。他们从事转手贸易,是丝路贸易的第一批中介民族,他们先后受到多个外来民族的统治,因此他们的钱币多元特征极为明显,希腊化王国的、帕提亚的、萨珊波斯的、贵霜的、甚至中国的因素在他们的钱币上都有反映。笔者在撒马尔罕的阿弗拉西亚卜(Afrasiab)的博物馆内,就看到了圆形方孔,有当地铭文的中国式钱币。粟特人信奉的是琐罗亚斯德教,并把它带到了中国,被称为拜火教或祆教。他们的商队就是一个小社会,商队首领萨保兼领世俗与教务管理之职。进入中国后,他们沿丝路定居,形成了一个个散布于丝路上的粟特人聚落。从北朝开始,中原王朝甚至设立萨保府,将这些粟特侨民纳入政府的管辖体系之中,近年来,在西安、太原等地出土了一些粟特人的墓葬,其中充满异域风情的石雕艺术大多反映的是祆教徒的生活和信仰。粟特地区作为一个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通道,印度的佛教、波斯的祆教、摩尼教,阿拉伯的伊斯兰教、拜占庭帝国的聂斯托利教(景教)都通过此地传入中原。粟特人不仅是陆地上的商业民族,也是多元文化传播的使者。
至于帕米尔以东、敦煌以西的中国西域地区,是秦汉以来与中原王朝接触的前沿地区。据《汉书·西域传》记载,西域“本三十六国,其后稍分至五十余,皆在匈奴之西,乌孙之南。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东西六千余里,南北千余里。东则接汉,厄以玉门、阳关,西则限以葱岭。”可见,班固的西域大致相当于今日甘肃的西端和新疆的南疆地区。张骞通西域时,此地是匈奴的势力范围,与中原并不相通。张骞之后,沿塔里木盆地的北、南边缘形成了两条重要的丝路——南道与北道。出南道通过瓦罕峡谷可以进入巴克特里亚,也可通过南道经罽宾线进入印度;出北道通过费尔干纳进入索格底亚那的泽拉夫善河流域。两道在木鹿汇合,沿伊朗高原的北缘大道西去,直抵米索不达米亚与地中海。因此,中国西域可以说是绿洲丝绸之路的咽喉地区,也是域外文化和中原文化首先相会的地区。这里的文明呈现出明显的中西融合特征是必然的。
这些西域绿洲小国地处丝路要道,不仅要应付外来的干扰,还要应对由于沙丘移动和水源枯竭带来的自然侵害。在千年历史长河中,有的绿洲国家消失了,但新的绿洲国家又出现了。在这些诸多绿洲国家中,有三个地区的文明很有代表性,这就是出土文物最为集中的和田地区、佛教石窟群为中心的龟兹地区,和以古城遗址、阿斯塔那墓地、吐鲁番文书著名的高昌地区。
丝路南道是斯坦因当年重点考察的地区,他在大漠之中的尼雅遗址、约特干遗址和米兰、楼兰古城,挖走了大量的钱币、木版画、木牍、泥塑、木制构件。这些文物现在大多收藏于大英博物馆。近年来我国考古工作者在和田及其周围地区的遗址上还有新的发现,如山普拉具有希腊化特征的毛织品、和田出土的“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织锦等。它们与斯坦因那一代人的发现证明,古代以和田为中心的丝路南道地区(包括鄯善—楼兰)是最先与中原和印度、中亚文化相接触的地区。佉卢文字和汉佉二体钱的流行,木牍封泥上的雅典娜(Athena)等希腊神形象,米兰佛教壁画中的有翼爱神(Eros)以及各种犍陀罗式图案、佛教泥塑人物头像,都说明希腊化世界的遗产最先传播到此地,这显然是丝路有关。
龟兹石窟是佛教传入中国西域后出现的第一座大型石窟群。笔者2000年曾到此地考察。当时曾为德国人勒柯克盗走许多壁画以致许多洞窟千疮百孔而深感痛心。2014年2月有机会到柏林亚洲艺术馆参观,看到了当年失落的部分壁画,看到中德考古学家已经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在研究和复原这些壁画,也有一丝欣慰。2014年1月,我在巴黎的吉美博物馆目睹了来自中国新疆图木舒克的佛教雕塑。这些雕塑的犍陀罗艺术特征非常明显,给人印象最深的是佛头上方相向而飞的天人形象,与希腊化钱币上跃跃欲飞的胜利女神像极为相似。此地位于喀什和库车(龟兹)之间,该泥塑与阿富汗哈达(Hadda)地区的泥塑风格没有什么区别,保持了原汁原味的犍陀罗艺术特征。但在龟兹石窟看到的则是大量的裸体佛教人物。有学者认为这是受到西方古典艺术裸体风格的影响。[68]龟兹对佛教东传的贡献还体现在一位名叫鸠摩罗什(Kumārajīva,公元344—413年)的僧人,他是龟兹人,曾到印度学佛,在西域名气很大,前秦将军吕光发兵龟兹,将他带到凉州。后来他进入长安,翻译佛经多达94部425卷,推动了佛教在中原的传播。
高昌即今日的吐鲁番地区,此地在北新道开通之后,成为进入丝路北道的门户。笔者2000、2013年先后到此地考察,主要参观了高昌古城、阿斯塔纳墓地和当地的博物馆。高昌对丝路文化的贡献主要在于它是多元文明汇聚之地,佛教、祆教、摩尼教、景教都在此地流行,拜占庭金币、萨珊波斯的银币也都流入此地。粟特人同时由此把中原的钱币带到中亚,被当地人仿造。
这些中国西域的绿洲小国虽然并非本课题的研究重点,但它们是连接中原和帕米尔之外丝路国家的桥梁,实际上担当了中介、信使、向导和后勤提供者等多种角色。他们的历史作用同样不应忽视。此处特别提及,也是对正文没有专门为它们设立专章的一种补充。
在这些丝路文明区域的北面是绵延于多瑙河口到中国的蒙古高原之间的欧亚大草原。在这个游牧世界中,生活着各种各样的游牧部落。他们很少有自己的文字,关于他们的名称、部落分布、民族特性、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繁衍流动、兴衰存亡大都是借助于农耕世界的记载而零散保存了下来。以希腊人熟知的斯基泰人为例,波斯铭文中出现的萨卡人,或者中国史籍中出现的塞人可能是对同一种族的不同称谓或者是指同一种族的不同部落或分支。汉代与中原王朝打过交道的匈奴人、大月氏人、乌孙人等都可能与斯基泰人有过接触或联系。他们就是草原丝绸之路的开拓者,来自中国的丝绸就是通过他们接力传递到欧洲的。如果把欧亚大陆之间印欧民族的迁徙和流散作为草原丝绸之路(就草原民族迁徙的路线而言)的开始,那“小河公主”[69]这一批印欧人就应是最早的丝路开拓者了。但真正沟通欧亚大陆的游牧民族应该是公元前一千年代活跃于欧亚大草原的斯基泰人。尽管他们有部落、地域、语言、文化之别,但总体上看,属于那种逐水草而居的行国,是以畜牧为生的民族。他们的游牧特征决定了他们与农耕世界的相辅相成关系。表面上看,这些游牧民族是定居民族的天敌,他们需要掠夺粮食和其他生活资料,常常是定居民族严厉防范的对象,但另一方面,二者也有相互利用的一面,游牧民族需要用自己马匹、毛皮换取定居文明的粮食、衣帛、手工制品、艺术品、甚至金银钱币,反之亦然。丝绸作为最为轻便、又最为珍贵的物品自然受到游牧民族的青睐,成为他们之间交往的媒介之一,真正意义上的草原丝绸之路从而形成。但由于游牧民族的流动性,各个部落之间、区域之间的交往只能时断时续,因此,草原丝绸之路的兴衰存亡主要取决于这些游牧民族与定居文明世界的关系,而且这些草原丝绸之路事实上就是绿洲丝绸之路的支线和延续,并通过后者和海上丝路相联系。这一点在贵霜帝国时期尤为明显。本书增加这一章,就是要说明,尽管历史上没有留下多少明确的这一时期草原帝国或王国的记载,这不等于它们的不存在(著名的如匈奴帝国),他们至少是有类似于部落联盟的国家形态和文明形态,因此,探讨他们对丝路文明交流的贡献也是非常必要的。
万里丝路,千年沧桑,丝路国家的沉浮,丝路文明的兴衰,对于我们而言,神秘的面纱远未揭开。特别需要说明的是,我们课题组成员都是世界古代史的学习者或研究者,我们是从世界史的角度,以古代文明的对话与交流作为主线,对古国文明与丝绸之路的关系进行考察,我们所依据的材料,除了文献资料之外,主要是其他学科领域专家,尤其是考古学家的研究成果。因此,本书中错讹之处在所难免,还望方家不吝赐教。
杨巨平
2021年5月改定于南开
[3]王治来:《中亚史》(第一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中亚史纲》,湖南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中亚通史》(第二版),新疆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4]赵汝清主编:《丝绸之路西段历史研究——兼论沿途民族迁徙及国家关系》,甘肃文化出版社1999年版。
[10][日]藤田丰八:《西域研究》,杨鍊译,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
[11][日]藤田丰八等:《西北古地研究》,杨鍊译,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
[12]此书有杨鍊译本:《张骞西征考》,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
[14][日]长泽和俊:《丝绸之路史研究》,钟美珠译,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15][法]阿里·玛扎海里:《丝绸之路中国—波斯文化交流史》,耿昇译,中华书局1993年版。2006年新疆人民出版社再版。
[16]I.M.Franck & D.M.Brownstone,The Silk Road: A History,New York: Factson File,1986.
[19]Xinru Liu,The Silk Road in World History,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0.
[24]George Rawlinson,Parthia,New York: G.P.Putnam's Sons,1903.
[26]Hugh George Rawlinson,Bactria: the History of a Forgotten Empire,London: Probsthain &Co.,1912.
[30]H.Sidky,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aeco-Bactrian Kingdom,Jaipur: ABD Publishers,2004.
[39]Richard N.Frye,The History of Ancient Iran,Munchen: Beck,1984.
[40]E.J.Rapson,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India.Vol.1:Ancient India,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22.
[42]Denis Sinor,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Early Inner Asia,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
[43]学界也有四条丝路之说,即将以成都平原(蜀地)为出发点,经我国西南地区连通东南亚、南亚和中亚的交通路线视为南方丝绸之路。
[45]Jorg Biel,“Treasure from a Celtic Tomb”,National Geographic,Vol.157,No.3,1980,pp.429-438.
[46][苏联]С.И.鲁金科:《论中国与阿尔泰部落的关系》,《考古学报》1957年第2期。
[49]关于远东希腊化文明圈,参见杨巨平《远东希腊化文明的文化遗产及其历史定位》,《历史研究》2016年第5期。
[50]关于帕提亚与希腊化文化的密切关系,参见杨巨平《帕提亚王朝的“爱希腊”情结》,《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11期。
[51](西汉)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二十三《大宛列传》,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162、3174页。
[52](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八十八《西域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919页。
[53]参见(北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西域下》,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6258—6259页。
[56](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八十八《西域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919页。
[60](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八十八《西域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920页。
[61](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八十八《西域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931页。
[62](西汉)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二十三《大宛列传》,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160页。
[67](西汉)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二十三《大宛列传》,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17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