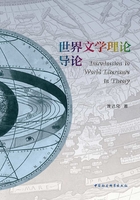
三 作为思想观念的世界文学
概要而言,歌德的“世界文学”就是指跨国界、跨语言文化的文学交流。这是指在全球化的语境当中,一系列文化的、文学的对话、交流,乃至于重组和创新。难能可贵的一点是,歌德的概念中所指涉的双方或多方的对话和交流是平等的。唯有在这种大前提之下,双方(或各方)的个性(或民族性)才不至于被抹杀,也才有可能发现了不同文化的共性(也即普遍性)。我们也可以将“世界文学”看作一个交流的平台、一个互动的空间,提供来自不同文化、不同身份的读者、作家、艺术家,通过翻译、评论、辩论等种种合理而有效的方式,相互研究学习,最终目的在于促进世界文化的多元共生。这或许是一种天真的期待,但是我们不应忽略歌德的心路历程。在后拿破仑战争时代,民族主义盛嚣尘上的德国,歌德希望借助文学的交流,来促进世界各地区各民族的相互认识,从而更加和谐地相处,避免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等偏见带来的世界性灾难,企求全球文明对话、共融和重生。
让我们对歌德“世界文学”事件的讨论来作一总结如下。
第一,“世界文学”,是一种世界主义理想,一种乌托邦式的、天启式的愿景、一种未来完成式的瞻望。
这里包含了几个层面。第一个层面“世界主义的理想”,是指人们应当抛却民族主义的偏见,拥抱更为广阔多元的世界。需要注意的是,歌德的“世界主义”观念的产生,有明显的拿破仑战争后欧洲格局的时代特征,当然这种观点也应归功于赫尔德的影响。第二个层面是歌德的世界文学愿景是一种乌托邦,多少有点受基督教的千禧年主义(Millennialism)的影响,也可说是一种天启式的愿景,因而这是一种未来完成式瞻望。在歌德看来,“世界文学”是一种合乎世界主义的理想,一种能够推动各民族文学逐渐打破孤立、割裂状态的力量,一种相互影响融合而形成的一个有机的统一体。歌德的世界文学观念,指向是一种不断朝向未来的可能,也是一种充满活力的号召。然而,歌德个人的言论前后有矛盾之处,显示出其时代的局限。比如,他的普遍主义和乌托邦有时也彰显出相反的特征,而当他论及东西文明优劣时,他又有着明显的他所处时代的人所具有的帝国主义腔调和东方主义想象。
第二,一种全球化时代的文学跨国流通现象。
歌德的“世界文学”,并非是指一系列的欧洲的乃至人类的经典文学(作为质的世界文学),也不是美国大学中出现的新一代修正过的世界经典,当然也不是所有语言写就的文学作品的总集(作为量的世界文学)。歌德所提及的法译或英译中国文学,其实在中国文学传统之中都不算是经典。换言之,歌德的“世界文学”是描述一种文学的跨国流通现象——这在全球化的今天已经成为一种常见的事实。歌德强调翻译的重要作用,尤其是通过翻译更好地理解原作。在歌德的时代或者更早的时代,这种跨国的文学交流已初现端倪。比如,意大利耶稣会教士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来华后,用意大利语写有一部《中国札记》,后来被他的后辈传教士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1577—1629)翻译为拉丁语,并作了一些增补,很快便在欧洲流通开,不久便又有了法语、德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转译本,到了19世纪又被东印度公司的译者转译成英语。[64]这便是当时世界文学流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案例。
第三,世界文学是彰显民族文学独特价值的场所,在这里世界性(普遍性)与本土性(民族性)并存共在。
民族文学在世界文学中的角色是怎么样的呢?“民族的”与“世界的”,这两个词汇似乎是对立的意思,但其实并非如此。歌德所处的德语文学世界,还没有一个非常悠久的传统,在他之前还没有举世闻名的作家和作品。当歌德提到“世界文学”这个概念时,他非常敏感地看到法语文学在欧洲近乎独尊的地位。他渴望德语也能够享受这样的尊崇。他渴望德语文学在世界文学形成的过程中,扮演“光荣的”“美好的”角色。这一点正如瓦尔策尔指出的,“歌德习惯从世界史进程的承载者——伟大人物的立场出发来把握世界史的过程”[65]。歌德的世界文学观念中,民族性与世界性两者是相互成全、相互补足对方的,而不是相互排斥的。世界文学中的“文学”,“既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而且往往“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
哈佛大学达姆罗什教授曾对世界文学和歌德的案例有独到的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关于“世界文学”的三层定义。
(1)世界文学是民族文学间的椭圆形折射。
(2)世界文学是从翻译中获益的文学。
(3)世界文学不是指一套经典文本,而是指一种阅读模式——一种以超然的态度进入与我们自身时空不同的世界的形式。[66]
第二三层我们上文已经提及,其创见在于第一层定义。第一层定义,很明显是受萨义德(Edward Said,1935—2003)的“旅行的理论”观念的影响。也可以说,在达姆罗什的概念里指的正是文学文本或思想观念旅行。达姆罗什借用了光学上的“椭圆形折射”(elliptical reflection)概念来形容世界文学,即在一个椭圆形的空间里,一个焦点上的光源通过反射作用重新聚焦到第二个焦点之上从而形成了双焦点。“源文化和主体文化提供了两个焦点,生成了这个椭圆空间,其中,任何一部作为世界文学而存在的文学作品,都与两种不同的文化紧密联系,而不是由任何一方单独决定。”[67]萨义德的文本旅行理论,解释了文本从原语境(original context)到流通过程,遭遇到新语境,被有条件地接受或抵抗,并最终在新语境中本土化的过程。这种过程,涉及了源点和原语境,也涉及翻译或流通的过程(如何移植、传递、流通和交换)的复杂情况,以及文本到了新语境的种种复杂反应,最终的接受和重生。这种描述,也如同本雅明(Walter Benjamin,1892—1940)在《译作者的任务》中对译本的定位一样,译作是原作的继起的生命,是其来世,应当被看作一个新的生命。[68]与以上观念相似,达姆罗什看到了评价世界文学的双重标准,即既是而非的“双焦点”,这一方面看到了文本承载的民族内涵,另一方面也更看到了文本旅行的过程和到新语境中的变形或再生。
关于“椭圆形的折射”,达姆罗什还有这样的解释:“文学作品通过被他国的文化空间所接受而成为世界文学的一部分,对该空间的界定有多种方式,既包括接受一方文化的民族传统,也包括它自己的作家们的当下需要。即使是世界文学中的一部单一作品,都是两种不同文化进行协商交流的核心……世界文学总是既与主体文化的价值取向和需求相关,又与作品的源文化相关,因而是一个双重折射的过程。”[69]
最后,“世界文学”这个概念给我们建设和发展“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什么样的启示呢?1886年爱尔兰学者波斯奈特(Hutcheson M.Posnett,1855—1927)出版了《比较文学》(Comparative Literature)一书,“比较文学”作为一门专门学科才正式确立。[70]这是第一部以“比较文学”(Comparative Literature)命名的专著,是这一领域的第一部理论著作。波斯奈特有其独特的文学史观念,具体表现在他如何描绘人类文学发展的过程——从“氏族文学”(Clan Literature)、“城邦文学”(The City Commonwealth Literature)、“世界文学”(World-Literature)到“民族文学”(National Literature)的发展过程。在这里,“世界文学”比“民族文学”更早发生。波氏使用了全书五分之一的篇幅来讨论“世界文学”。波氏认为世界文学产生的基础是“政治上的世界大同主义”(political cosmopolitanism。这里“大同主义”也可译为“普遍主义”或“世界主义”)。他指出,部落共同体大举扩张之后,共同体成员有了共同的信念(比如希伯来的宗教)。同样,“雅典和罗马等城市共同体的类似扩张,促生了一种政治的世界主义,也因而在共同文化圈内出现了人类联合的理想——这需要中央势力保障整个疆域的和平,也呈现出了高度个性化的特征。”[71]在波氏这里,世界文学的产生至少有如下三种关键的原因:一是部落共同体的大幅度扩张,形成了一个更大的、更有势力的政治共同体(比如罗马帝国);二是随后产生了一种人类联合的理想——这是他一再强调的一种高度社会性的观念;三是呈现出了高度个性化的文化特征。在波氏看来,西方文学传统中的罗马帝国时代的拉丁语文学,便是世界文学,其立论的基础是罗马帝国是一个世界性帝国,而拉丁语文学是有世界性影响的高雅文学。波氏看到了文学的世界性或普遍性的一面。受十九世纪的进化论所影响,波氏认为随着人类聚合的不断扩大——从氏族部落到城邦共同体,再到更大的世界(比如罗马帝国),文学也越来越普遍化,最终产生了具有普遍主义的世界文学。波氏似乎完全忽略了歌德的世界文学概念,也没有回应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48)里所讲及的在世界市场中存在的一种同质性的“世界文学”。[72]
歌德和马克思等人的“世界文学”观念,与后来发展起来的欧洲比较文学稍为不同之处便在于,前两者有更大的抱负,包含了更大的范畴,有更宏阔的前瞻远景。19世纪下半叶比较文学学科的发展史,尤其是“法国学派”的研究,反而看起来像是放弃了宏伟的目标,而聚焦在欧洲各国族文学的“借贷关系史”。也即是说,由世界文学向比较文学影响研究的窄化。到了20世纪上半叶,走向比较文学(比较诗学)则变成民族国家时代的文学研究者的一种普遍呼声。伴随着对于比较文学学科和性质的界定和重新界定,对其种种危机和消亡的深入讨论,比较文学一直是人文学科中最具争议的一个领域。无可争议的是“比较文学”一直是人文学科这组交响乐的第一把小提琴(苏源熙语),引领着人文学科向前探索。到了20世纪末,甚至有学者宣告了这个学科的死亡[如斯皮瓦克(Gayatri C.Spivak,1942—)所著的《一门学科的死亡》],或者呼吁重建一种新的比较文学(如爱普特的《翻译地带:一种新的比较文学》),这些论调却有意无意地促进了学科的向前迈进。[73]20世纪最后二十年,比较文学经历了文化研究的挑战和翻译研究的转向,其后又在2000年有了新的变化,即走向了“世界文学”。这一方面,以莫莱蒂的《世界文学猜想》(及其续编)为代表论著,打开了世界文学(及其理论反思)的新局面。在此之前,“世界文学”是一个众多学者提及,但一直是语焉不详或讨论未定的范畴。在此之后,更是争议蜂起,可以说当今比较文学学界所讨论的“世界文学”,虽是源于歌德的概念,但是经过了两百年的发展,已经是一个全新的领域,发展出许多新的子方向。
[1] 与民族国家密切相关的种种思想观念,来自于民族国家体系。1618年至1648年,欧洲爆发了大规模的国际战争。1648年战争结束,各国签订了一系列的和约,即为《威斯特伐利亚和约》(The Treaty of Westphalia)——现代民族国家体系源起于此。
[2] 曹顺庆:《比较文学论》,四川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47页。
[3] 张隆溪:《比较文学研究入门》,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页。
[4] 2015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外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下设“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二级学科。
[5] 张隆溪:《钱锺书谈比较文学与“文学比较”》,《读书》1981年第10期,第137页。
[6] 卢康华、孙景尧:《比较文学导论》,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76页。
[7] [美]达姆罗什:《后经典、超经典时代的世界文学》,载[美]达姆罗什、刘洪涛、尹星主编《世界文学理论读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59—170页,尤其是第162页。David Damrosch的姓氏,也译为“丹穆若什”,本书正文采用“达姆罗什”这一译名,引文则据所引书的版权页。
[8] 泰戈尔(Rabindranath Tagore,1861—1941),孟加拉族人(Bangal),是一位印度诗人、哲学家和反现代民族主义者。在西方国家,泰戈尔一般被看作诗人,而很少被看作哲学家,但在印度这两者往往是相同的。他的诗中含有深刻的宗教和哲学的见解。对泰戈尔来说,他的诗是他奉献给神的礼物——如“吉檀迦利”的意思即为“献给神的诗”。他的诗在印度享有史诗的地位。他本人被许多印度教徒尊崇为圣人。有两点需要强调的是:首先,他的父亲是一位本地的印度教宗教领袖,接触过基督教神学和传教士(这一点在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词和当时的评论中有特别的强调)。其次,他的诗歌主要是以孟加拉语写成(2000多首诗),而非英语。但是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主要是因为如下两点,即其思想受到基督教的影响(这是西方评论者的东方主义误读)和其英文诗作乃是英语文学的一部分(然而,孟加拉语的原作或许更佳)。
[9] 方维规主编:《思想与方法:地方性与普世性之间的世界文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Weigui Fang,Tensions in World Literature,Between the Local and the Universal,Singapore:Palgrave Macmillan,2018.
[10] 方维规:《何谓世界文学》,《文艺研究》2017年第1期,第15页。
[11] [德]爱克曼辑录:《歌德谈话录》,朱光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113页。
[12] [德]赫尔曼·格林:《歌德——在柏林大学所做的讲座(第一次讲座)》(1874年),载叶隽编选《歌德研究文集》,译林出版社2014年版,第52页。
[13] [德]赫尔曼·格林:《歌德——在柏林大学所做的讲座(第一次讲座)》(1874年),载叶隽编选《歌德研究文集》,译林出版社2014年版,第52页。
[14] 拿破仑战争(法语:Guerres Napoléoniennes),是发生于1803—1815年欧洲的一系列战事。历史学家认为,拿破仑战争由1789年法国大革命引发,此后拿破仑上台,法国迅速崛起,称雄于欧洲,但在1812年侵俄失败之后又迅速败落。1815年6月,拿破仑率领的法军在滑铁卢战败,随后欧洲各参战国签订了巴黎和平条约。1815年11月20日拿破仑战争结束。
[15] 狂飙突进运动(德语:Sturm und Drang)是指18世纪60年代晚期到80年代早期在德国文学和音乐创作领域的变革,是文艺形式从古典主义向浪漫主义过渡时的阶段。其名称来源于剧作家克林格(Friedrich Maximilian Klinger,1752—1831)的同名剧作《狂飙与突进》(Sturm und Drang),其中心代表人物是歌德和席勒。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是其典型代表作品。该书表达的是人类内心感情的冲突和奋进精神。余匡复:《德国文学史》上册,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第107—110页。
[16] 德国作家维兰德在其翻译的贺拉斯《书札》(1790年修订版)的手记中使用了“weltliteratur”(世界文学)一词。维兰德提及,“世界知识和世界文学以及成熟的性格培养和良好品行的高雅趣味”。贺骥指出,“维兰德在此所说的 ‘世界文学’指的是奥古斯都时期的一流作家(贺拉斯、维吉尔和普罗佩提乌斯等人)博览了古今各民族的文学杰作,掌握了世界文化文献,他们具有广博的学识、丰富的阅历和高度的文学艺术修养,他们所创造的文学乃是一种世界主义的高雅文学。”详细讨论请见:Weitz,Hans-Joachim,“‘Weltliteratur’ zuerst bei Wieland,”in Arcadia 22,Berlin:De Gruyter,1987,s.207.贺骥:《“世界文学”概念:维兰德首创》,《社会科学》2014年第7期。
[17] 法语作为西方世界的一种“通用语言”,最早可追溯至17世纪,在此后两百多年间,被广泛地使用于政治、外交和文化等领域。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英语取代法语,成为新的国际通用语言。在歌德的时代,法语是欧洲的通用语言,法语文学在欧洲的所有语言文学中影响最大。
[18] Hans Kohn,“Romanticism and the Rise of German Nationalism,”The Review of Politics,Volume 12,Issue 4,October 1950,p.460.
[19] [德]爱克曼辑录:《歌德谈话录》,朱光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114页。
[20] [德]顾彬:《从语言角度看中国当代文学》,《南京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第74页。朱安博、[德]顾彬:《中国文学的“世界化”愿景——德国汉学家顾彬访谈录》,《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3期,第120页。
[21] 王岩等编:《西方史学之路》,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01页。[德]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齐世荣等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
[22] [美]雷纳·韦勒克:《歌德》,载叶隽编选《歌德研究文集》,译林出版社2014年版,第367页。[美]韦勒克:《近代文学批评史》第1卷,杨自伍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版,第265—298页。莪相(Ossian),又译奥伊辛,是凯尔特神话中的古爱尔兰著名的英雄人物、优秀的史诗诗人。荷马,古希腊盲诗人,伟大的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是其根据民间流传的诗歌编写而成。荷马史诗在很长时间里直接塑造了西方的宗教、文化和伦理等方面的观念。
[23] [德]爱克曼辑录:《歌德谈话录》,朱光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113页。
[24] 歌德在提及这一句时,他借助的是他刚读到的叙事诗体英译本《花笺记》,所以既是表面的“诗”的实指,同时也指向更大的范畴、更多的内容。关于《花笺记》英译等情况,请参第六章和第八章的讨论。
[25] Eric A.Blackall,Goethe and the Novel,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76,p.137.
[26] 弗里德里希·席勒(Friedrich von Schiller,1759—1805),德国18世纪著名诗人、哲学家、历史学家和剧作家,德国启蒙文学的代表人物之一。
[27] Eric A.Blackall,Goethe and the Novel,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76,p.137.
[28] [美]雷纳·韦勒克:《歌德》,载叶隽编选《歌德研究文集》,译林出版社2014年版,第372页。
[29] [美]雷纳·韦勒克:《歌德》,载叶隽编选《歌德研究文集》,译林出版社2014年版,第377页。
[30] 笔者认为这首诗便是汤姆斯英译《花笺记》,请参第八章讨论。汤姆斯(Peter Perring Thoms,1790—1855),英国人,印刷工出身,后来自学成长,成为汉学家。汤姆斯1814年来华,主要是在广州和澳门活动,任职于英国东印度公司,在该公司的澳门印刷所里负责中文铅活字的研制和应用。汤姆斯曾帮助排版早期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1834)的《华英字典》(A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Macao,China:Printed at the Honorable East India Company's Press,1812—1822)。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汤姆斯受命于英国官方全权代表义律(Charles Elliot,1801—1875),出任翻译官。汤姆斯著译有:(1)Peter Perring Thoms,The Emperor of China vs.the Queen of England.London:Warwick-Square,1853.(2)Peter Perring Thoms,A Dissertation on the Ancient Chinese Vases of the Shang Dynasty,from B.C.1743 to 1496,London,1851.此书内容是关于中国的“博古图”。(3)译著《花笺记》:Peter Perring Thoms,Chinese Courtship,London:Published by Parbury,Allen and Kingsbury,1824.关于《花笺记》的整理本、外译和汤姆斯英译的相关研究请见:(1)梁培炽辑校、标点:《花笺记 会校会评本》,暨南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2)王燕:《〈花笺记〉:第一部中国“史诗”的西行之旅》,《文学评论》2014年第5期。(3)美国学者夏颂(Patricia Sieber)运用达姆罗什的世界文学的概念来理解《花笺记》的外译,并指出,“毕竟《花笺记》不仅传至欧洲,在越南和东南亚也有流行,这使得汤姆斯的译文成为某些中国纯文学作品的‘世界文学’性质的一部分”。[美]夏颂《汤姆斯、粤语地域主义与中国文化外译的肇始》,陈胤全译,载王宏志主编《翻译史研究 2016》,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270—294、293页。
[31] 具体可参第六章的案例分析。
[32] 这种神圣化、崇高化,还经由该书的翻译(重译)和出版等环节来完成。请参[美]丹穆若什:《什么是世界文学?》,查明建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9—40页。此外,这一小节的写作受启于达姆罗什(丹穆若什)的精彩分析,对其论述有概括总结和细节补充。
[33] J.P.Eckermann,Conversations with Goethe,John Oxenford trans.,London:J.M.Dent & Son Ltd,1935,p.xxiv.第三卷前序有,“My relation to him was peculiar,and very intimate:it was that of the scholar to the master;of the son to the father;of the poor in culture to the rich in culture.He drew me into his own circle,and let me participate in the mental and bodily enjoyments of a higher state of existence.”
[34] [美]丹穆若什:《什么是世界文学?》,查明建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4页。
[35] J.P.Eckermann,Conversations with Goethe,John Oxenford trans.,London:J.M.Dent & Son Ltd,1935,pp.ix-x.“I read of nothing and thought of nothing but only of him,wherever I went,wherever I remained:in my walks and in my daily affairs,he was in my thoughts,even at night he entered into my dreams.”
[36] 爱克曼对未婚妻Houben有点若即若离,关系并不是一直都好。爱克曼还爱上了他作为家庭老师指导的学生。他的未婚妻Houben甚至调侃他说:但丁(Dante)找到了他的碧翠丝。但丁作品《神曲》中,碧翠丝为引导但丁进入天堂的完美女性。
[37] J.P.Eckermann,Conversations with Goethe,John Oxenford trans.,London:J.M.Dent & Son Ltd,1935,Introduction,p.x.
[38] [德]爱克曼辑录:《歌德谈话录》,朱光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266—267页。
[39] [德]歌德:《歌德谈话录》,杨武能译,河北教育出版社2015年版,第500页。奥克森福德(John Oxenford)英译本在这一段中,用了一系列词汇来描述歌德的崇高伟岸和爱克曼对歌德的忠诚和爱戴。“Stretched upon his back,he reposed as if asleep;profound peace and security reigned in the features of his sublimely noble countenance.The mighty brow seemed yet to harbour thoughts.I wished for a lock of his hair,but reverence prevented me from cutting it off...I was astonished at the divine magnificence of the limbs.The breast was powerful,broad,and arched;the arms and thighs were full,and softly muscular;the feet were elegant,and of the most perfect shape;nowhere,on the whole body,was there a trace either of fat or of leanness and decay.A perfect man lay in great beauty before me;and the rapture which the sight caused made me forget for a moment that the immortal spirit had left such an abode.I laid my hand on his heart—there was a deep silence—and I turned away to give free vent to my suppressed tears.”J.P.Eckermann,Conversations of Goethe with Eckermann and Soret,vol.II,John Oxenford trans.,London:Smith,Elder & Co.,1850,pp.429-430.
[40] “整部《谈话录》里,爱克曼在歌德英雄般的威权面前,扮演着满心崇拜却害羞的少女角色。……爱克曼少女般的含蓄使他在歌德富有表情的巨大威力面前保持沉默,这种表情的威力甚至印入他的肌理之中。一年后,爱克曼仍在使用恋爱中的少女的语气,记述他的爱情。”[美]丹穆若什:《什么是世界文学?》,查明建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4页。
[41] 奥克森福德,是英国的剧作家、批评家和翻译家。他自学成才,除英语外,还精通法语、德语、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等语言。著有68部剧本,译作也颇丰。1846年,将歌德的《诗与真:歌德自传》(The Autobiography of Goethe:Truth and Poetry from My Own Life)译成英文出版。1850年,他将爱克曼德文原著的《歌德谈话录》译成英文出版。1853年,他将加勒尔(J.M.Callery,1810—1862)等用法语编著的有关太平天国的历史著作《中国叛乱史》(History of the Insurrection in China)译成英文出版。1853年后,德国哲学家叔本华(Arthur Schopenhauer,1788—1860)因为奥克森福德在杂志上撰文大力推荐,方得到英国和国际哲学界的认可,并最终奠定了其哲学家的声誉。
[42] [美]丹穆若什:《什么是世界文学?》,查明建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9页。
[43] [美]丹穆若什:《什么是世界文学?》,查明建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9—41页。这几页中,达姆罗什(丹穆若什)对爱克曼的态度和《歌德谈话录》的经典化过程有精彩的分析。
[44] 转引自J.P.Eckermann,Conversations with Goethe,Gisela C.O'Brien trans.,New York:Frederick Ungar Publishing Co.,1964,Introduction,p.v.尼采的话,请参英译文:Friedrich Nietzsche,Human,All too Human,R.J.Hollingdale tran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6,p.336。
[45] J.P.Eckermann,Conversations of Goethe with Eckermann and Soret,John Oxenford trans.,London:Smith,Elder & Co.,1850.该译本并未在封面标明爱克曼为辑录者(参图1-1)。
[46] 这一个案例,有一大部分的内容来自于达姆罗什的精彩分析,参见[美]丹穆若什《什么是世界文学?》,查明建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41页。
[47] J.P.Eckermann,Conversation with Goethe,in the Last Years of his Life,S.M.Fuller trans.,Boston:Hilliard,Gray,and Co.,1839.1852年在波士顿有重印本(Boston and Cambridge:James Munroe and Company,1852)。
[48] J.P.Eckermann,Conversation with Goethe,in the Last Years of his Life,S.M.Fuller trans.,Boston:Hilliard,Gray,and Co.,1839,p.viii.“He is merely the sounding-board to various notes played by the master's hand;and what we find here is,to all intents and purposes,not conversation,but monologue.”
[49] 这一点人人文库版《歌德谈话录》的编者前言已经提及,而丹穆若什(达姆罗什)在其《什么是世界文学?》的第一章也有详论如是:“《谈话录》因翻译而获益,但爱克曼本人却损失不小。这本原名《歌德谈话录》的书,后来却变成了《与爱克曼的对话》。奥克森福德把歌德而不是爱克曼,定为该书的真实作者。”[美]丹穆若什:《什么是世界文学?》,查明建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8页。
[50] J.P.Eckermann,Conversations with Goethe,John Oxenford trans.,London:J.M.Dent & Son Ltd,1935,Introduction,p.xviii.
[51] 重印本见J.P.Eckermann,Conversations with Goethe,Gisela C.O'Brien trans.,New York:Frederick Ungar Publishing Co.,1964,Introduction,p.xv。
[52] J.P.Eckermann,Conversations with Goethe,John Oxenford trans.,London:J.M.Dent & Son Ltd,1935,p.xvii.
[53] J.P.Eckermann,Conversations with Goethe,Gisela C.O'Brien trans.,New York:Frederick Ungar Publishing Co.,1964,Introduction,p.xiv.
[54] 哈菲兹(原名Shams al-Dīn Muhammad Shīrāzī,简称Hāfiz,约1320—1389),14世纪波斯伟大的抒情诗人。哈菲兹幼年就能写诗和背诵《古兰经》,他名字的含义是“熟背古兰经的人”。哈菲兹一生共留下五百多首诗,被称为“诗人的诗人”。
[55] 卫礼贤(Richard Wilhelm,1873—1930),德国来华传教士,博学的、杰出的汉学家。1899年,他受魏玛差会所派,来中国青岛传教。后在中国传教达20年之久,同时投身于办教育、办医院,翻译和研究中国传统典籍,可谓是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上“中学西传”的一位大功臣。他曾将《大学》《论语》《孟子》《老子》《庄子》《易经》等经典作品译为德文并附注出版。
[56] [德]卫礼贤:《歌德与中国文化》,载叶隽编选《歌德研究文集》,译林出版社2014年版,第170—183页。
[57] Thomas Percy trans.& ed.,Hao Kiou Choaan or The Pleasing History,4 vols,London:Dodsley,1761.更详细讨论请参第八章。
[58] 威廉·格林(Wilhelm Grimm,1786—1859),德国人类学家、作家。格林兄弟中的弟弟。格林兄弟编译有《格林童话》。
[59] John Francis Davis trans.,Laou-seng-urh,or “An Heir in His Old Age”,London:John Murray,Albemarle-Street,1817.
[60] Peter Perring Thoms,Chinese Courtship,London:Parbury,Allen,and Kingsbury,1824.
[61] Jean Pierre Abel Rémusat,Iu-Kiao-Li,ou Les Deux Cousines,Paris:Libraireie Moutardier,1826.
[62] [德]爱克曼辑录:《歌德谈话录》,朱光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7页。
[63] [德]卫礼贤:《歌德与中国文化》,载叶隽编选《歌德研究文集》,译林出版社2014年版,第182页。
[64] [意]利玛窦:《耶稣会与天主教进入中国史》,文铮译,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前言”。
[65] [德]瓦尔策尔:《歌德与当代艺术》,载叶隽编选《歌德研究文集》,译林出版社2014年版,第166页。
[66] [美]丹穆若什:《什么是世界文学?》,查明建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09页。
[67] [美]丹穆若什:《什么是世界文学?》,查明建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11页。
[68] 《译作者任务》一文见[德]阿伦特编《启迪:本雅明文选》,张旭东、王斑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具体讨论请参本书第三章。本雅明是20世纪非常重要的一位思想家、学者、译者,德国犹太人。著有《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启迪》《单向街》《摄影小史 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等作品。本雅明的部分著作请参哈佛大学出版社Belknap分社出版的《本雅明作品选辑》(Walter Benjamin:Selected Writings)全四卷。Walter Benjamin,Walter Benjamin:Selected Writings,Volume 1-4,H.Eiland,M.W.Jennings eds.,Cambridge:Mass:the Belknap Press,2006.其生平请参其传记,Howard Eiland,Michael W.Jennings,Walter Benjamin:A Critical Life,Cambridge,Mass:Belknap Press,2014.其作品中译可参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自2014年始出版“本雅明作品系列”丛书,包括《评歌德的〈亲合力〉》《德意志人》《莫斯科日记》《无法扼杀的愉悦》《德国浪漫派的艺术批评概念》《德意志悲苦剧的起源》等作品。另,部分文章可参[德]瓦尔特·本雅明:《本雅明文选》,陈永国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69] [美]丹穆若什:《什么是世界文学?》,查明建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11页。
[70] Hutcheson Macaulay Posnett,Comparative Literature,London:Kegan Paul,Trench & Co.,1886.汉译本请参[爱尔兰]波斯奈特《比较文学》,姚建彬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
[71] Hutcheson Macaulay Posnett,Comparative Literature,London:Kegan Paul,Trench & Co.,1886,pp.235-236. 汉译本请参[爱尔兰]波斯奈特《比较文学》,姚建彬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35—236页。
[7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5页。英文版见,Karl Marx and Friedrich Engels,The Communist Manifesto,With an Introduction and Notes by Gareth Stedman Jones,London:Penguin Books,2002,pp.223-224.“In place of the old local and national seclusion and self-sufficiency,we have intercourse in every direction,universal inter-dependence of nations.And as in material,so also in intellectual production.The intellectual creations of individual nations become common property.National one-sidedness and narrow-mindedness become more and more impossible,and from the numerous national and local literatures,there arises a world literature.”
[73] Gayatri C.Spivak,The Death of A Discipline,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5.汉译见[美]斯皮瓦克:《一门学科之死》,张旭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Emily Apter,The Translation Zone:A New Comparative Literature,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