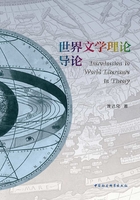
一 翻译转向与学科的重心
阿拉姆语(Aramaic)所表示的“翻译”一词,传达的是“将包袱扔过河去”的面画,而且事实是:在翻译的过程中,这个包袱从来就不会准确地到达河的另一边,像翻译开始之前它在河的这边所处的位置那样。[2]
最早的一部以“比较文学”为题的专著是1886年波斯奈特所著的《比较文学》,上引文便出自该书,此处是波斯奈特论及比较文学中翻译研究的重要性时举了这样的一个“扔包袱之喻”。翻译的“扔包袱之喻”极为形象地解释了翻译的性质:两种语言的河岸中间隔着或宽或窄的河面,我们或许可以想象中间的水流是文化的、历史的元素或诗意的表达方式。这种翻译行为在实施时——即便是成功地将包袱抛掷至对岸,对岸相对应的位置也与此岸的位置绝不可能等同。也就是说,原作与译本之间始终隔着语言或文化的河面,即便是平行的对应,也绝不可能完全地等同。正因为如此,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要面临的翻译问题,通常较为复杂,因为涉及翻译背后文化的、历史的、政治的内涵。大多数的翻译个案中,其问题很有可能有其独特的呈现方式,也会引出令人意想不到的解答。波斯奈特在《比较文学》中还曾追问:“翻译的准确性,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可能的?”[3]这个简单的问题引发的是一系列相关的复杂问题:翻译(或者说理解)是否可能?译文与原文的对等关系是如何被假设成立,并被接受为合法的?译者是否忠于原文,还是翻译行为可以允许有一定程度上的“创造性叛逆”?忠于原文,是最为重要的衡量标准吗?严复所论的信、达、雅,三者是否能够兼具?……可以肯定地说,与翻译相关的问题,是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领域的学者无法绕开的问题。
1931年,法国比较文学学者梵·第根(Paul van Tieghem,1871—1948)在其著作《比较文学论》中也讨论了译本和译者的种种相关问题,并提醒研究者要关注译本中的增删问题,以及比较研究译作与原作的具体细则。[4]此后,许多学者也一再地论及比较文学与翻译研究的主题。那么,在比较文学的新时代——世界文学的时代呢?所谓比较文学的新时代,或者说,新的比较文学时代,是阿普特(Emily Apter)在其名著《翻译地带:一种新的比较文学》一书中所提出的说法。[5]她认为,比较文学研究不应以国别为中心,即研究的重点不应是跨国别的比较,而应是跨语言的比较,不应以民族国家为单位,而应以翻译为中心,即“一种基于翻译的新的比较文学”[6]。翻译研究变成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的中心,与20世纪的理论热、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文化研究热颇有关系。
20世纪八九十年代翻译研究经历了一种文化转向,反过来说也成立——文化研究经历了一次翻译研究的转向。这两个领域出现了许多相互交叠的地方。在翻译研究领域则是出现了所谓的文化学派,以勒弗菲尔(André Lefevere,1945—1996)、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1945—)和韦努蒂(Lawrence Venuti,1953—)等学者作为代表人物。勒弗菲尔在其名著《翻译、重写和文学声名的操控》中指出,任何翻译都是一种重写(rewriting),其背后受到诗学形态和意识形态的操控(manipulation),从而影响到译文的书写和作者的声名。[7]这种操控涉及了诸如赞助者、编辑(editing)、编辑文选(anthologising)等方面。传统的翻译研究,大多仅仅停留在两种语言功能对等这种表层,即原文与译文在语义方面的对等,但是忽略了与译文或译者相关的文化的、历史的、意识形态的、诗学的种种因素,更忽略了改写或接受等层面及其背后在起决定性作用的种种权力关系。翻译过程中的每一个步骤——从一部外国文本的选择到翻译策略的实现,到编辑、评论和译本的阅读——都由目标语(target language,或译“目的语”“译入语”)中通行的不同文化价值观调和产生,而这些价值观总是处于某种等级秩序当中。
翻译绝非对原文的复制,也非原文的衍生物,故而翻译并非简单的文化交流,而是一种文化的改写。勒弗菲尔指出:“当然,翻译是对原文文本的改写,改写即操纵,所有改写者不管出于什么目的,都反映了某种意识形态和诗学。通过操纵文学,‘改写’在特定的社会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发挥作用。从积极的方面来看,改写有助于某种文学和社会的进化,即可以引进新的概念、新的风格、新的手法。翻译的历史,就是文学革新的历史,是一种文化对另一文化施加影响的历史。”[8]正因为翻译多数时候是有意识的操控,而且有各种权力因素的参与,所以韦努蒂反对译文通顺的策略,主张以一种差异性的翻译策略来对抗异质文化的霸权,以彰显文化差异性和混杂性,在翻译中保留甚至突出边缘文化。文化学派的翻译理论,对处于全球化和后殖民时代的现当代文学及其翻译有许多警示作用,也有助于我们思考翻译与世界文学的种种关系。
关于翻译与世界文学的讨论,另一位重要学者巴斯奈特认为:翻译是最为有效的改写方式。从世界文学的视角看,译者作为一个中介在参与文学的流通和再生产的过程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在世界文学作品流通和接受的过程中,翻译起了极为关键的作用。在全球化的时代,翻译被看作是两种或多种文化系统之间的协商,翻译和译本流通的过程也是跨越文化的过程。20世纪末,翻译研究在经历了文化研究之后,几乎有取代比较文学研究的趋势,但是到了21世纪又转变成世界文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方向。[9]简言之,翻译研究在21世纪的今天已经居于世界文学研究领域的核心。2003年,达姆罗什在其后来产生巨大影响的专著《什么是世界文学?》一书里,便重新界定了世界文学的概念,其中有一项关于世界文学的解释是“从翻译中获益的文学”。这一层概念特别强调了世界文学文本的翻译和跨界流通,将世界文学看作一种现象而非一个序列的经典,同时将翻译研究当作阅读、教学、研究世界文学的一种行之有效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