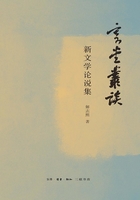
三
顺便也谈谈《平凡的世界》的艺术问题。因为这样一部深受广大读者喜爱的作品,却由于它的艺术不够时髦而长期得不到当代中国文学评论界和研究界的重视和好评,尤其在所谓学术中心的高层学术圈子里,《平凡的世界》其实是备受冷遇的。比如,前几年由北京大学资深教授严家炎先生领衔主编、十多家著名高校学者参与编写的“国家级教材”《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在叙述到新时期文学的时候,也只在一处顺便提了一下路遥的名字,就一笔略过了。说来惭愧,我也是该书的编写者之一,但这部分不由我写,所以我也无可奈何。
这看似奇怪的冷遇其实并不奇怪,甚至可以说是必然的遭遇。要问主流批评家们为什么不待见《平凡的世界》?那是因为他们觉得这部作品“不入流”——不符合文学发展的新潮流。然则什么才是新时期中国文学——比如小说写作——的新潮呢?他们认为那就是80年代中期以来接连出现的“寻根小说”“先锋小说”“新写实小说”以及“后先锋小说”等新潮,他们觉得这些新潮作品或有神话、原型、象征,或有形而上的玄思加形而下的下半截展露,或有精神分析、意识流以至于魔幻感,在艺术上能够花样翻新而且技艺复杂,读来颇给人深沉得神神道道或深刻得玄玄乎乎或时髦得奇奇怪怪之感,正因为如此,这些作品才堪与国际文学潮流接轨,被视为“入流”以至“领潮”之作了。相比之下,他们觉得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可真是平凡无奇之至、老土得人人都看得懂,那还有什么好说的呢?!
这让我又想起批评家马尔科姆·考利的一段话——很抱歉,我已在别处两次引过他的话,此处就再引一次吧。考利说有一次他指导一个大学写作讲习班的短篇小说习作,一个学生不等他开口就说:“我明白问题所在,某某教授已告诉我,我没有好好利用门的象征作用,盘子的象征作用……”考利认为这是胡闹,他大声疾呼必须提出三个口号以挽救现代批评——
如果不真实,就不可能是象征;
如果不成故事,就更不成神话;
如果一个人活不起来,它不可能成为现代生活的原型。(4)
我觉得同样需要挽救的乃是当代中国的文学批评,而非路遥的《平凡的世界》。路遥继承了柳青的《创业史》所开创的革命现实主义的农村叙事范式,而又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做了适度的调整和改造,使之成为一种“改革开放的现实主义”——改掉了过重的政治意识形态色彩和对集体主义的过度眷顾,而更加开放也更有同情地看待社会与个人的关系,力求忠实地写出中国改革开放的社会进程,写出跻身于这个不凡进程中的平凡人物之典型,以及相应的社会风俗之变迁。这样一种“改革开放的现实主义”,对他所要描写的“平凡的世界”和“平凡的人物”无疑是恰当其用而且尽够用了,别的更摩登更时髦的文学风尚反而与之格格不入。正因为如此,路遥绝不跟风,而是踏踏实实地用了将近六年的心力,苦辛耕作他自己的文学园地,奉献给读者的是一部朴素而大气的文学巨著《平凡的世界》。
作为一部巨幅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的艺术成就其实是并不平凡的。这里只举其荦荦大者。其一,路遥在这部巨著中不仅出色地描写了一场非常复杂的社会改造进程,而且有条不紊、有声有色地讲述了一大套生动感人的故事,大故事中穿插着小故事,叙事结构井然有序,具有很强的可读性。这是一个不小的成就,因为小说毕竟是一种叙事文类,万变不离其宗,讲好故事乃是起码的艺术要求。与路遥同时或比他稍后的不少作家,虽然能写出相当繁复的作品,却往往因为不善于讲故事、不会结构作品而功败垂成。其二,《平凡的世界》更重要的艺术成就,乃是它成功塑造了众多鲜活的人物形象。不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小说都是伴随着个人意识的觉醒而崛起的写实文类,而写出有血有肉的个性化人物,对小说来说乃是比讲好故事更高的甚至是最高的艺术要求。鲁迅的小说之所以令人印象深刻、钦佩不置,首要的就是塑造人物的成就很高,哪怕是短短两千字的《孔乙己》,也把孔乙己写得活灵活现。新时期的小说在这方面其实是日渐逊色的,而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却让读者们念念不忘,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它写出了众多栩栩如生的人物,其中不少人物都堪称典型,即使一些次要人物,如孙玉亭、王满银等小角色,也都写得性格鲜明、很接地气,令人读来如在目前、过目难忘。其三,《平凡的世界》的心理描写和细节描写也颇为出色。这部小说中的人物大都是接地气的平凡人物,路遥是很“贴心”地描写这些来自乡土的父老兄弟姐妹们的,所以作品中的主要人物的心理活动,都有细腻的展示和渐趋深入的层次感。路遥特别体贴乡村妇女和来自乡村的女知青的爱情心理,他曾经在作品中感慨地为她们抱屈说——
有文化的城里人,往往不能想象农村姑娘的爱情生活。在他们看来,也许没有文化就等于没有头脑;没有头脑就不懂得多少感情。可是实际也许和这种偏见恰恰相反。真的,正由于她们知识不多,精神不会太分散,对于两性之间的感情非常专注,所以这种感情实际上更丰富,更强烈。(《平凡的世界》第一部,第230页)
这确是深谙人性人心底细的话。此所以《平凡的世界》对乡村女性和出自乡村的女知青,如贺秀莲、田润叶和郝红梅等年轻女性的爱情心理之刻画,无不体贴而周至、细腻而动人。至于细节对于一部巨型长篇小说的重要性,其实不亚于大的情节,因为有没有丰富可味的细节,决定着一部长篇小说是否真正地肌质丰满,而不仅仅是骨骼突出。《平凡的世界》的大故事固然讲得有声有色,小细节也写得丰富有味——那些细节描写常常出现在有关风俗人情的场景和人物之接人待物的场合,这只要打开书页,可谓触目皆是,而无须多言了。
当然,《平凡的世界》在艺术上也的确存在一些不足之处而有待于完善。即如它的语言就热情畅达有余而有时不免直露,夹叙夹议的语调和本色的生活语言相杂糅,则显现出路遥从政治抒情的语言向生活化的语言过渡的痕迹。这不难理解——路遥在“文革”后期就开始创作,不可能不受那时语言环境的影响,而路遥所敬爱的柳青对他的影响也不全是有益的,比如那种夹带着政治激情的夹叙夹议的语调,就是柳青的影响之遗留。路遥其实已经意识到这些问题,因而在新时期的创作中非常努力地去改进,积极地尝试运用一种更为本色的生活化语言来写作。但令人遗憾的是,年轻的路遥没有来得及完成这种转换,四十刚出头就去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