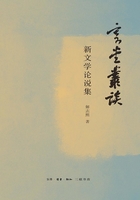
“毛戴”的影射问题
——《章秋柳:都市与革命的双重变奏》之疑义
前天收到刚出版的《上海文化》杂志2007年第5期,翻开目录,有一篇题作《章秋柳:都市与革命的双重变奏》,作者是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院的陈建华先生,一位很有水平的学者,文章的题目又很吸引人,所以我就先翻到陈先生的这篇大作,读了下去。
文章很长,但很精彩。通过对茅盾《蚀》三部曲的最后一部《追求》的女主人公章秋柳的分析,陈先生至少提出了两个令人耳目一新的创见。一是认为茅盾当年的“内在紧张在《追求》中的章秋柳身上得到激情的迸发而达到世纪末式的辉煌,而他的现代主义的美学探索亦臻至极致”。我觉得这个创见完全成立。长期以来,我们比较熟悉的是自然主义的、革命写实主义的茅盾,虽然也知道早年的他曾经对“新浪漫主义”颇感兴趣,却很少想到后来的茅盾会在其革命叙事中激情迸发“而达到世纪末式的辉煌,而他的现代主义的美学探索亦臻至极致”,如今陈先生敏锐地发现了这一点,并有相当精细深入的分析,如对《追求》中的革命与颓废的复杂纠结之剖析,就相当精彩而令人信服。
文章的另一创见,是认为茅盾“尽管行将就范,臣服于‘历史必然’的铁律”,却仍然意犹未尽,在《追求》中借章秋柳的形象曲折地表达了不“跟着魔鬼跑”即对左倾政治“盲动主义”的质疑,而被质疑的左倾“盲动主义”代表人物,则“不仅是指瞿秋白,恐怕也包括毛泽东”,作者并进而推断说茅盾写《追求》乃将他对“大革命”失败的反思“转化为意蕴丰富的文学形象及某种文化姿态”,那姿态“毋宁是像章秋柳拒绝(跟)曹志方去当‘土匪’一样,乃是一种人性的姿态,即不主张激进流血”云云。这一创见,即推定茅盾写《追求》乃曲折地将政治反思的矛头不仅指向瞿秋白,而且指向毛泽东,真可谓石破天惊之论。不过,让我惊叹的并不是陈先生这个创见的政治意味,让我更为憧憬的乃是这个创见的美学意义——如果能够从《追求》中找到茅盾质疑毛泽东左倾政治盲动主义的痕迹,从而把这位大作家从令人厌憎的革命暴力恐怖和极左政治黑幕中释放和洗刷出来,那岂非美事一桩?所以,我并不反对陈先生的第二个创见,甚至乐观其成。
然而读完全文,我遗憾地发现,陈先生的第二个创见虽然充满了丰富多彩的想象与推论,而至关重要的文本根据却相当薄弱,甚至不无误读、曲解之嫌。
按,被陈先生指称为形象地表达了茅盾不仅对瞿秋白,更可能对毛泽东的左倾“盲动主义”之质疑的,乃是《追求》中描写章秋柳的噩梦般心理的一段文字。为免读者翻检之劳,这里谨依陈建华先生文章所引,复录原文如下——
她无可奈何的阖了眼,一些红色的飘动的圆圈便从眼角里浮出来,接着又是王诗陶的惨苦的面容,端端正正的坐在每一个红圈上。然而这又变了,在霍霍地闪动以后,就出奇的像放大似的渐渐成了一个狞相。呀!这就是东方明的咬紧牙齿的狞相!红圈依旧托在下面,宛然像是颈间的一道血线。章女士惊悸地睁开眼来……
她恨恨的想,用力咬她的嘴唇,皱紧了眉头。现在的情绪,矛盾纷乱到极端,连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虽然她痛切地自责太怯弱,但是血淋淋的红圈子始终挂在她眼前,她的光滑的皮肤始终近于所谓“毛戴”,她赤着脚乱走了几步,又机械的躺在床里,对天花板瞪眼。她努力企图转换思想的方向,搜索出许多不相干的事来排遣,但是思绪的连环终于又崛(倔)强地走回到老路上,她几乎疑惑自己的神经是起了变态,在对她的自由意志造反。……因为这是高热度的同情,所以不能挥去血淋淋的红圈子,所以那样惊悸,所以流入于怯弱么?
在援引了上述文字之后,陈先生便抓住其中的一个意象和一个词语大做文章。那个意象即是章秋柳挥之不去的“血淋淋的红圈子”。陈先生指出这“显然是一个具政治含义的象征指符,自然会使人联想到革命志士的鲜血或国民党的血腥屠刀”。这也是人们惯常的理解。“然而”,陈先生觉得这不够,他以为“对‘红圈子’这一意象的丰富内蕴稍做推敲,也何尝不是指使茅盾痛心疾首的‘左’倾‘盲动主义’?章秋柳所表现的恐惧折射出茅盾在写作《追求》当中的鲜活感受,也即对于1928年继续发展的‘盲动主义’的反应,这不仅是指瞿秋白,恐怕也包括毛泽东”。如此把茅盾质疑的矛头指向毛泽东,这或者不失为一说,但根据何在呢?陈先生紧接着提出了他的别出心裁的推论——
在三部曲里,《追求》最富于政治性,而对章秋柳的艺术表现也直接牵连到50年代的政治实际。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刻画章秋柳的大段引文在1954年的修订本中被完全删去了。这“红圈子”的噩梦段落为三部曲与“革命”的直接联系提供了重要见证,即不光是对“过去”的反思,也是对“当下”的批评。而且对于理解章秋柳这一人物身上所体现的都市与革命的双重主题的剧烈冲突,也极其重要。
这一段被删掉,或许也与那个带引号的“毛戴”有关,指的是什么,令人费解。在茅盾《回忆录》中并不讳言1927年对于“工农运动过火”的反应:“当时农运‘过火’之说早已传布,我们也知道党中央有两种意见,一种是陈独秀的,一种是瞿秋白支持的毛泽东的,而且还听说这两种意见反映了当时在武汉的国际代表之间的不同态度。”茅盾的反应是一面“感到由衷的欣喜”,一面也“存有疑虑,譬如把农民家中供的祖宗牌位砸了,强迫妇女剪发,游斗处决北伐军军官的家属等。尤其对后者,我们议论较多,认为我们现在手中还没有军队,万一这些军官反到蒋介石那边去了,局势就很困难”。所谓“‘过火’之说早已传播”,指的是毛泽东在1926年主持湖南农民运动,便声言“有土皆豪,无绅不劣”。至1927年3月发表《湖南农民运动调查报告》,力主“矫枉必须过正”,驳斥“过火”论。结果“疑惑”变成现实,发生何健、夏斗寅、许克祥等叛变,遂演成“反共清党”之局。这就是《动摇》所描写的,尽管茅盾对反动派口诛笔伐,但以情色的讽喻描绘了农民运动的“过火”行动,如上文言及的癞头农民瓜分地主小寡妇,即为一例。
茅盾也许真有政治上的先见之明,但此处且不管它,现在我所关心的问题只是:上述茅盾的文学文字是否真在以情色的描绘来讽喻毛泽东的左倾“盲动主义”,如他指导下的农民运动的“过火”行动呢?陈先生的分析多为推测之论,依他的推论,上述《追求》那段文字中唯一能够与毛泽东挂上钩的乃是“那个带引号的‘毛戴’”,尽管他说这个词语“指的是什么,令人费解”,却又在未提任何有力证据的情况下,理所当然地将“毛戴”视为对毛泽东的影射——陈先生虽然没有直接用“影射”二字,但他的下文显然无疑地将“毛戴”和“毛泽东”关联了起来,力图引导读者相信茅盾确在借此讽喻毛泽东。这就不仅是望文生义、穿凿附会,而且实在有点成见在胸、急不择言了——即使“毛”真是指毛泽东,那么“戴”指何人,也总该有个解释吧?可他却那么不管不顾地把“毛戴”一股脑儿戴到毛泽东头上。这在学理和学德上是有缺憾的。
事实上,“毛戴”指的是什么,并不像陈先生夸张的那么“费解”。从《追求》的具体语境中就不难判断出茅盾写“她的光滑的皮肤始终近于所谓‘毛戴’”,其实是说章秋柳的皮肤光滑漂亮如模特,也即是说“毛戴”乃model(模特)的一种音译而已。当然,model的这种音译,在今天已经难见,所以对一般读者来说确乎有些“费解”或难解。可是,陈建华先生出于国际著名学者之门,外语尤其是英语很好,治学又擅长考辨外来语汇概念在现代中国之演变,如在他的这篇大作中说到《追求》中被戏称为“迭克推多”的曹志方时,就特意在“迭克推多”后加按语说:“英语dictator,即‘专制君主’。”所以,“毛戴”也者,对学养深厚、外语很好且擅长解词的陈先生来说,不是问题正在情理之中,而竟然成了问题、生了误解,反倒让人难以理解了——坦率地说,令我纳闷的并不是陈建华先生对“毛戴”的离奇解释,而是如此离奇的解释怎么会出现在他的笔下?是智者千虑的偶然一失,抑或还有别的原因呢?我不能妄加推测,也不想吹毛求疵。我只想就事论事地辨正一点:《追求》中的“所谓‘毛戴’”肯定是指模特而非影射毛泽东,所以陈先生要完成他的论证,还得从文本中别寻证据。
2007年10月9日于清华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