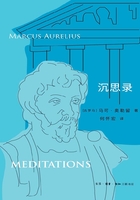
导读 “每时每刻都要坚定地思考”
何怀宏
一
马可·奥勒留生平
斯多亚派著名哲学家、古罗马帝国皇帝马可·奥勒留·安东尼(121—180),原名马可·阿尼厄斯·维勒斯,生于罗马,其父亲一族曾是西班牙人,但早已定居罗马多年,并从维斯佩申皇帝(69—79年在位)那里获得了贵族身份。马可·奥勒留幼年丧父,是由他的母亲和祖父抚养成人的,并且在希腊文学和拉丁文学、修辞、哲学、法律甚至绘画方面受到了在当时来说最好的教育,他从他的老师那里熟悉和亲近了斯多亚派的哲学(例如爱比克泰德的著作),并在其生活中身体力行。
还在孩提时期,马可·奥勒留就以其性格的坦率真诚得到了哈德良皇帝(117—138年在位)的好感。当时,罗马的帝位常常并不是按血统,而是由选定的过继者来接替的。在原先的继嗣柳希厄斯死后,哈德良皇帝选定马可·奥勒留的姑父安东尼·派厄斯为自己的继嗣,条件是派厄斯亦要收养马可·奥勒留和原先继嗣的儿子科莫德斯(后名维勒斯)为继嗣。当哈德良皇帝于138年去世后,马可·奥勒留获得了“恺撒”的称号——这一称号一般是给予皇帝助手和继承者的,并帮助他的姑父治理国家,而在其姑父(也是养父)于161年去世后,旋即成为古罗马帝国的皇帝。遵照哈德良的意愿,他和维勒斯共享皇权,但后者实际上不起重要作用。
马可·奥勒留在位近二十年,这是一个战乱不断、灾难频繁的时期,洪水、地震、瘟疫,加上与东方的安息人的战争、来自北方的马可曼尼人在多瑙河流域的进逼以及内部的叛乱,使得罗马人口锐减,贫困加深,经济日益衰落,即使马可·奥勒留凭借其坚定精神和智慧,夙兴夜寐地工作,也不能阻挡古罗马帝国的颓势。在他统治的大部分时间里,尤其是后十年,他很少待在罗马,而是在帝国的边疆或行省的军营里度过。《沉思录》这部写给自己的书,这本自己与自己的十二卷对话,大部分就是在这种鞍马劳顿中写成的。
马可·奥勒留与安东尼·派厄斯的女儿福斯蒂娜结婚并生有十多个孩子。据说,他在一个著名的将军、驻叙利亚的副将卡希厄斯发动叛乱时表现得宽宏大量。但他对基督徒的态度比较严厉,曾颁布过一道反对基督徒的诏书。
公元180年3月17日,马可·奥勒留病逝于文多博纳(今维也纳)。
斯多亚派哲学
斯多亚派哲学主要是一种伦理学,其目的在于为伦理学建立一种唯理的基础,它把宇宙论和伦理学融为一体,认为宇宙是一个美好的、有秩序的、完善的整体,由原始的神圣的火演变而来,并趋向于一个目的。人则是宇宙体系的一部分,是神圣的火的一个小火花,他自己也可以说是一个小宇宙,他的本性是与万有的本性同一的,所以,他应该同宇宙的目的相协调而行动,力图在神圣的目的中实现自己的目的,以求达到最大限度的完善。为此,他必须让自己的灵魂清醒,让理性统率自己,正如他统率世界一样。
所以,斯多亚派对人们的要求是:遵从自然而生活,或者说按照本性生活(nature有“自然”“本性”两层意义),而所谓自然、本性,实际上也就是指一种普遍的理性,或者说逻各斯(在某些方面类似于中国的“道”),或者说一种普遍的法(自然法的概念就是由此而来)。自然—本性—理性—法,不说它们有一种完全等价的意义,它们也至少是相通的,并常常是可以互用的。而作为一种理性存在物的人的自然本性,就是一种分享这一普遍理性的理性,一种能认识这一普遍理性的理性。安东尼在《沉思录》中常常讲到一个人身外和身内的神,讲到身外的神(或者说宙斯)把自身的一部分分给了人的理性灵魂(身内的神),人凭内心的神,或者说凭自己支配的部分,就能认识身外的神,就能领悟神意。他说的其实也是这个意思。我们还需要注意的一点是:这里所说的理性主要不是对自然事物的认识,而是道德德行的践履,所以,理性和德行又联系起来了。
总之,在斯多亚派哲学家的眼里,宇宙是一个井然有序的宇宙,世界是一个浑然和谐的世界。正如《沉思录》中所说:“所有的事物都是相互联结的,这一纽带是神圣的,几乎没有一个事物与任一别的事物没有联系。因为事物都是合作的,它们结合起来形成同一宇宙(秩序)。因为有一个由所有事物组成的宇宙,有一个遍及所有事物的神,有一个实体,一种法,一个对所有有理智的动物都是共同的理性,一个真理;如果也确实有一种所有动物的完善的话,那么它是同一根源,分享着同一理性。”在这个世界上,低等的东西是为了高等的东西而存在的,无生命的存在是为了有生命的存在而存在的,有生命的存在又是为了有理性的存在而存在的。那么,有理性的存在,或者说理性的动物(人)是为何与怎样存在的呢?理性动物是彼此为了对方而存在的,所以,在人的结构中首要的原则就是友爱的原则,每个人都要对自己的同类友好,意识到他们是来自同一根源,趋向同一目标,都要做出有益社会的行为。
这样,就把我们引到人除理性外的另一根本性质—社会性。人是一种理性动物,也是一种政治动物(这里沿用了亚里士多德的说法)、一种社会动物。《沉思录》的作者认为,在人和别的事物之间有三种联系:一种是与环绕着他的物体的联系;一种是与所有事物所有产生的神圣原因的联系;一种是与那些和他生活在一起的人的联系。相应地,人也就有三重责任、三重义务,就要处理好对自己的身体和外物、对神或者说普遍的理性、对自己的邻人这三种关系。人对普遍理性的态度前面已经说过了,就是要尊重、顺从和虔诚。对自己的身体和外物,斯多亚派一直评价颇低,基本上认为它们作为元素的结合和分解,并没有什么恒久的价值。身体只是我们需要暂时忍受的一副皮囊罢了,要紧的是不要让它妨碍灵魂,不要让它的欲望或痛苦使灵魂纷扰不安。对于我们和邻人的关系,人们的社会生活和交往,斯多亚派则给予了集中的注意,事实上,人的德行就主要体现在这一层面。
一般来说,斯多亚派哲学家都是重视整体、重视义务的。他们认为,人不能脱离社会、脱离整体而存在。使自己脱离他人,或做出反社会的事情来,就好比使自己变成脱离身体的一只手或一只脚。如果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就要致力于使自己与整体重新统一起来。人作为宇宙的一部分,个人作为社会的一部分,对于来自整体的一切事物都要欣然接受,都要满意而勿抱怨,因为,凡是为了整体的利益而必须存在的,对于个体也就不会有害。对于蜂群无害的东西,也不会对蜜蜂有害;不损害国家的事情,也不会损害到公民。《沉思录》的作者说,我们每天都要准备碰到各种各样不好的人,但由于他们是我的同类,我仍然要善待他们。不要以恶报恶,而是要忍耐和宽容,人天生就要忍受一切,这就是人的义务。要恶人不作恶,就像让无花果树不结果一样是不可能的。我们只要能完成自己的义务就够了,对于其他的事情完全不要操心,我们要表现得高贵、仁爱和真诚。
看来,斯多亚派哲学家对个人的德行、个人的解脱看得比社会的道德改造更为重要,这也许是因为他们觉得自己生活在一个个人无能为力的时代,生活在一个混乱的世界中。所以,他们特别注意区分两种事情:一种是在我们力量范围之内的事情;一种是不在我们力量范围之内的事情。许多事情,例如,个人的失意、痛苦、疾病、死亡,社会上的丑恶现象,等等,这些往往并不在我的力量范围之内,但是,由于所有对我发生的事情都是符合宇宙理性的,我必须欣然接纳它们。我也可以做在我力量范围之内的事情,这就是按照本性生活,做一个正直、高尚、有道德的人,这是什么力量也不能阻止我的,谁也不能强迫我做坏事。在斯多亚派哲人对德行的强调中确实有许多感人的东西。例如,奥勒留谈道:德行是不要求报酬的,是不希望别人知道的,不仅要使行为高贵,而且要使动机纯正,要摒弃一切无用和琐屑的思想。要使自己专注于这样的思想:当你在思考时,别人问你想什么,你任何时候都能立即坦率地说出来。而且,不仅要思考善、思考光明磊落的事情,还要付诸行动,行动就是你存在的目的,全然不要再谈论一个高尚的人应当具有的品质,而是成为这样的人。
总之,斯多亚派哲人所追求的生活是一种摆脱了激情和欲望、冷静和达观的生活,他们把对他们发生的事情都不看成是恶,认为痛苦和不安仅仅是来自内心的意见,而这是可以由心灵加以消除的。他们恬淡、自足,一方面坚持自己的劳作,把这些工作看作自己的应分;另一方面又退隐心灵,保持自己精神世界的宁静一隅。斯多亚派哲学的力量可以从它贡献的两个著名代表看出:一个是奴隶出身的爱比克泰德,另一个就是《沉思录》的作者、哲学家皇帝马可·奥勒留·安东尼。他们的社会地位悬殊,精神和生活方式却又相当一致。但是,另一方面,奥勒留作为柏拉图所梦想的“哲学家王”,他的政绩、他所治理的国家状况却和理想状态存在差距。所以,我们一方面看到斯多亚派哲学精神的巨大力量,看到它如何泯灭社会环境的差别而造成同一种纯净有德的个人生活;另一方面又看到这种精神的相当无力,它对外界的作用、对社会的影响比起对个人的作用相对微弱,因为它本质中确实含有某种清静无为的因素。但是,一种清静无为,一种谨慎地不以巨大权力来改造社会和人性的精神也有助于防止巨大的灾难。
此外,我们也看到,斯多亚派的道德原则并不是很明确的。把本性解释为理性,把理性又解释为德行;道德在于按照本性生活,而按照本性的东西就是道德。这里面虽有某种强调理性、普遍和共相的优点,但也可能有形式化的循环论证的弱点。在斯多亚派哲学中有令人感动的对道德的高扬,但也有令人泄气的对奋斗的放弃。它也许永远不失为一条退路,但对于朝气蓬勃、锐意进取的人,尤其是生命力洋溢的年轻人来说,走这条路还是一件太早的事情。它还不像基督教,它没有过多的对于彼岸的许诺,而是强调在此岸的德行中自足,但在情感和意绪方面也为基督教的盛行做了某种铺垫和准备。我们大概可以说,斯多亚派哲学能够为一个处于混乱世界、面对道德低潮又感到个人无能为力的人,为一个在个人生活方面遭受挫折和失望(这是永远也免不了的),但又不至于让上帝援手的人,提供最好的安慰。最后,我们也注意到,斯多亚派哲学虽然不可能像有些理论(例如社会契约论)那样对社会制度的变革和改善发生直接的影响,但是,它其中所蕴含的那种胸襟博大的世界主义,那种有关自然法和天赋人权、众生平等的学说,却越过了漫长的时代,对近现代的社会政治理论及实践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沉思录》的特点
《一生的读书计划》的作者、美国教授费迪曼认为《沉思录》有一种不可思议的魅力,它甜美、忧郁而又高贵。我们可以同意他的话,并且说,它的高贵,也许是来自作者对身羁宫廷的自己和自己所处的混乱世界的感受;而它的甜美,则只能是由于作者心灵的安宁和静谧了。这几个特点往往是结合在一起的,比如说,当我们读到《沉思录》的最后一段,即说从人生的舞台上退场的一段,我们一方面感到忧郁,因为这就是人的命运,人难逃此劫,即使你觉得你的戏还没有演完,新的演员已经代替你成为主角了,这里的忧郁就像卓别林所演的《舞台生涯》中那些老演员的心情:苦涩而又不无欣慰,黯然而又稍觉轻松;另一方面,我们又感到高贵,因为我们可以体面、庄严地退场,因为我们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并给新来者腾出了地方。
我们也要记得,《沉思录》是写给自己的,而不是供出版的,而且,这里是自己在同自己对话,字里行间常常出现的不是“我……”,而是“你……”,并常常用破折号隔出不同的意见。既然是自己与自己的对话,自己说服自己,自然也就不需要过分讲究辞藻、注意效果和安排结构,而是注意一种思想的深入和行进。有时话没说完又想到别处,并经常出现“但是”这样的转折。我们在阅读中不要忘了这些,不然,也许会因为它不是一个精美的体系而感到失望。只要我们让我们的心灵沉静下来,就能够从这些朴实无华的句子中读出许多东西。这不是一本时髦的书,而是一本经久的书,买来不一定马上读,但一定会有需要读它的时候。近两千年前,一个人写下了它;再过两千年,也一定还会有人去读它。
二
要像峙立于不断拍打的巨浪之前的礁石,
它岿然不动,驯服着它周围海浪的狂暴。
——《沉思录》卷4-49
正如前述,古罗马帝国皇帝马可·奥勒留·安东尼在位的近二十年间,国家不断遭遇到台风、地震、瘟疫等自然灾害,帝国的边境也不安宁,发生了一些部落的侵袭或反抗,而内部也有总督叛乱。所以,马可·奥勒留执政的大部分时间并没有待在罗马,而是在戎马倥偬中度过。对于这些灾难,奥勒留表现出一种斯多亚派哲学家的冷静和镇定精神,他以静制动,坚如磐石,克服了种种磨难,使罗马帝国在他统治的岁月依然被英国著名罗马史家吉本称为“人类过着最为幸福繁荣的生活”的时期,他自己也被列为“古罗马五贤帝”的最后一位。
但即便有如此的政绩,如果不是在这功业的作者那里还具有一种比这功业远为深沉的精神,以及这精神又被赋予文字的载体并幸运地流传下来,大概也还是不会有多少人记得这位近两千年前的皇帝。奥勒留的《沉思录》使其成为人类历史上罕见的一位真正的哲学家皇帝。下面我们就来具体介绍一下他的《沉思录》大致是怎样的一本书:其中包含一些什么样的思想,尤其是人生哲学和伦理的思想,它的精神信仰、思想特质和由此反映出来的作者品格特征,以及我们如何阅读它,等等。
《沉思录》主要在思考什么
一般认为,《沉思录》所表达的是一种斯多亚派哲学,奥勒留是斯多亚派哲学的最后一位主要代表。为方便起见,我们可将斯多亚派哲学的发展主要分为两个时期:一是公元前古希腊的理论体系构建时期;二是公元后古罗马的伦理思考与实践时期。斯多亚派哲学的创始人是芝诺(前336—前246),早期斯多亚派哲人就已经相当重视伦理学了,他们认为哲学分为三个部分:以动物为喻,则逻辑学是骨腱,自然哲学是肌肉,而伦理学是灵魂;以鸡蛋为喻,则逻辑学是蛋壳,自然哲学是蛋白,伦理学则是蛋黄;以田园为喻,则逻辑学是篱笆,自然哲学是土地,伦理学则是果实。
到斯多亚派哲学发展的晚期——罗马帝国的斯多亚派哲人这里,其世界观、本体论、认识论就更是围绕着伦理学展开了,甚至考虑的中心问题都是伦理学的问题,而且主要是自我的心灵如何安顿、个人的行为如何展开的问题。罗马共和国时期的西塞罗(前106—前43)还有不少篇幅考虑制度和政治问题,而后来帝国时期的重臣塞涅卡(前4—公元65)、被释奴隶爱比克泰德(约55—约130)就都是主要思考个人伦理学的问题,尤其爱比克泰德对马可·奥勒留的影响最大。而且,他们都很重视言行合一,重视道德的自我实践与训练。
所以,我们在《沉思录》中看到,它主要也是一种伦理学或者说道德哲学的思考。而由于在古代社会,伦理学和人生哲学、精神信仰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乃至是以后者为主导的,所以,它也可以说是一种人生哲学、实践哲学和精神哲学。但《沉思录》并不是一种精心构制的哲学体系,甚至不是连贯的论著,而是一种始终联系于自己生命和道德实践的片段思考,所以,我们下面尝试从社会伦理、个人伦理与精神信仰三个方面来概述其思想。
有关社会伦理
奥勒留在社会伦理方面的思考可能是最少的,却可能是最好的,或者说是在古典心灵中与现代社会最为契合的。所以,在这方面我们尽量做一些引证,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明。
的确,我们首先会注意到,奥勒留并不想在社会政治的层面普遍地实现自己的哲学理想,在他那里,实际上是政治的归政治,哲学的归哲学。尽管是罗马帝国的最高统治者,但奥勒留从未考虑过使用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权力来推行他的哲学,因为,他深深知道,精神的力量必须自我唤醒、自我培育和自我训练。而且,一种至高的精神追求也不是所有人都能够,甚至愿意达到的。
在心灵的深处,奥勒留永远为自己保留了哲学的亲密一角,而作为罗马帝国的皇帝,他深知自己必须承担起自己的职责。他知道他握有不仅是当时帝国,而且也许还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权力,但他同时又认为,就权利而言,自己又是一个公民团体中的普通一员,就像他的前任老安东尼皇帝一样,“把自己视为与任何别的公民一样平等的公民”(卷1-16),告诫自己不要欲求“一切需要墙和幕的东西”,不要去关心“灵魂究竟在身体中寄寓多久”,而是要“在全部的生命中只关心这一点:他的思想不要离开那属于一个理智的人、属于一个公民团体的人的一切”(卷3-7)。
而且,奥勒留不仅把自己视为一个罗马公民,同时也是一个世界公民。他说:“我的本性是理性的和社会的,就我是安东尼来说,我的城市与国家是罗马;但就我是一个人来说,我的国家就是这个世界。”(卷6-44)奥勒留甚至说:“如果一个人生活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像生活在一个国家(政治团体)中一样,那么住这儿或者住那儿对他并没有什么关系。”这当然主要是就德行的磨炼而言,对一个有德行的人来说,他的确可以四海为家。奥勒留有一种世界主义的情怀,他超越了国家主义的狭隘眼界,不仅从一个特定政治社会的角度考虑自己的义务,也从一个普遍的人类大家庭的一员考虑自己的义务,从人既是理性的存在又是社会的存在这一人的本性的角度考虑自己的义务。他认为自己也是一个伟大国家(人类世界)里的一个公民。他说:“人是至高之城的一个公民,所有其他的城都像是至高之城的下属。”(卷3-11)
的确,奥勒留看重人,甚至尊崇人,但尊崇的是人的理性和责任。他甚至表现出对大自然的一种歉疚之情,他谈到自己及先辈不断从大地得到营养,“当我践踏它,为许多的目的滥用它时,它默默地承受着我”(卷5-4)。他认为,一个人在辞别人世的时候,应该感谢哺育了他的树林(社会)和大地(自然)。他认为人比动物是更高的存在,但是,“对于那没有理性的动物与一般的事物和对象,由于你有理性而它们没有,你要以一种大方和慷慨的精神对待它们”(卷6-23)。“我们在缺乏理性的动物中发现蜂群、畜群、对雏鸟的抚养、某种意义上的爱;因为甚至在动物中亦有灵魂”(卷9-9)。而人作为更优越的存在自然更应当自觉地按照理智和社会的本性生活和行动。
当然,奥勒留也为自己是一个罗马人而感到骄傲。他希望自己“每时每刻都要坚定地思考,就像一个罗马人”(卷2-5)。他希望自己能够总是追忆“古代罗马和希腊人的行为”(卷3-14)以为榜样,他希望自己像雅典人那样尊严地向神灵祈祷。奥勒留还写道:“那不损害到国家的事情,也绝不会损害到真正的公民;那不损害到法(秩序)的事情,也绝不会损害到国家;而被称为不幸事件的这些事物中并无一个损害到法,这样,不损害到法的东西也就绝不会损害到国家或公民。”(卷10-33,卷5-22)从这段话看来,他更强调整体而非部分,更强调国家而非公民个人。但他也同样强调国家受法的支配,“法统治着一切”(卷7-31)。这种法也就是自然法,它贯穿于自然、社会与个人,体现的是一种普遍的理性或本性。这种自然法也是一种道德法,它规定了国家与公民的各自权利和义务。它高于任何特殊国家的实存法,所以,它不会损害到个人的国家已经先定地具有一种道德的规定性,“理性动物的目的就是要遵循理性和最古老的城邦和政府的法律”(卷2-16)。
奥勒留还写道:“我接受了一种以同样的法对待所有人、实施权利平等和言论自由的政体的思想,以及一种最大范围地尊重被治者的所有自由的王者之治的观念。”(卷1-14)这是一种令人吃惊的、具有现代意义的有关制度伦理的思想。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人们享有言论自由和权利平等,最大范围地尊重被治者的所有自由,这是一种真正具有自由精神的王者之道。
有关个人伦理
不过,奥勒留的伦理思考主要还是一种个人伦理学,是一种自我伦理学,或如中国的儒家学者常常称谓自己的学问那样,是一种“为己之学”。由于奥勒留的思考主要是集中在这一方面,在书中有大量的内容,我们不再多引证,而是想在奥勒留的思想与中国的传统思想之间进行一点比较,以便较清晰地显示他的思想特征。这里也顺便说说,奥勒留大概是第一个与中国发生直接联系的罗马皇帝。《后汉书》曾经记载,在桓帝延熹九年(166),大秦王安敦(马可·奥勒留·安东尼皇帝)派遣使者经日南送来象牙、犀角,并与中国建立通商关系。
从奥勒留的思想与中国主要思想的比较角度来看,我们或可在某种意义上说它包含着道家精神与儒家伦理的某种结合。一方面,我们注意到,老子也谈到了一种贯穿于世界万事万物的“道”,而且强调“道法自然”,所以,人也应当按照自然的道来生活,接受自然的安排。庄子也认为,“万物与我为一”,追求“天放”的理想,主张齐生死、齐寿夭,摆脱功名利禄,乃至不以自己的身体为意,而重视自己精神上的自由。
奥勒留在对世界及人在其中的处境和命运的看法上,和道家颇有相合之处。但是,他并不像道家思想的突出代表——比如庄子以及后来受其影响的许多文学家那样,希望摆脱社会和政治义务的牵累或者与社会拉开距离,而做一个精神上逍遥的真人。相反,奥勒留极其重视对社会义务的承担,甚至把这种承担强调到了一种绝对义务论的程度,这就使他又颇接近于儒家的伦理。就像孔子强调遵循社会之“礼”、孟子努力阐明普遍之“义”一样,奥勒留也强调,黎明即起,就要毫不懈怠地去努力做好自己作为一个人、一个公民和一个皇帝所必须做的事情(参见卷5-1)。而在待人方面,奥勒留也像儒家一样强调不能逃离自己的同胞,要与人为善,乃至善待品行不良的人,这是他一日之始就告诫自己的另一条座右铭(参见卷2-1)。他还为如何宽容地对待冒犯自己的人确立了十条原则(参见卷11-18),其中的内容和孔子提倡的“忠恕之道”颇有相通之处。
除了道家的天地精神和儒家的普遍义务感,在奥勒留的思想中,甚至还表现出某种墨家的节俭刻苦和法家的严峻刚硬。当然,他有自己的完全不同于这些流派的特点,有自己的在西方思想中的传承。他可能更注意痛苦的消除,而非快乐的希求——哪怕是纯精神的快乐。他更强调德行的自我坚持,既不像儒家相当执着地追求社会政治方面的理想,又不像道家追求一种具有审美意义的自由或超越。
我们还可以从如何认识与对待死亡的问题来观察一下奥勒留哲学与中国有关思想的不同。比如说,我们在《古诗十九首》中读到:“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飙尘。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之四)“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奄忽随物化,荣名以为宝。”(之十一)“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万岁更相迭,贤圣莫能度。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之十三)“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为乐当及时,何能待来兹?”(之十五)。这里从生命短暂引出的结论是对权力、荣名和快乐的追求。
奥勒留在其《沉思录》中也同样多次地谈到了人的生命的脆弱和短暂。他谈到,死亡对所有人都是平等的,无论伟人还是仆人、最有权力者还是最有智慧者、被哀悼者还是哀悼者、一些个人还是家族、抱怨社会者还是不抱怨社会者、害怕死亡者还是不害怕死亡者……最后都无一例外地走向死亡,迅速地被人们忘记。即便那些名人的名声,也不久就会飘散(分别参见卷3-3,4-32,4-33,4-48,4-50,6-24,6-47,8-25,8-31,8-37,10-27,10-31,12-27)。他和《古诗十九首》的作者对死亡的认识应该说是大致一样的,但引出的人生态度却截然不同,后者主张及时行乐。在这方面,我们还可以引《列子》的观点为证,其《杨朱篇》说:“万物所异者生也,所同者死也。……然而万物齐生齐死,齐贤齐愚,齐贵齐贱。十年亦死,百年亦死。仁圣亦死,凶愚亦死。生则尧舜,死则腐骨;生则桀纣,死则腐骨。腐骨一矣,孰知其异?且趣当生,奚遑死后?”既然人生如此短暂,死后的名声也不可靠,杨朱的结论是,人不妨纵情于生前的声色犬马之乐。
但是,在奥勒留那里,这种对死亡的清醒认识,除了可以用来帮助我们摆脱对死亡的恐惧和无穷无尽的烦恼之外,也可以有助于我们看淡对世间功名利禄的追求。他认为一个人过一种有德的一生,而非纵欲的一生,才是真正体现了一个人与自然本性相合的本性。所以,奥勒留的结论是“及时行德”而非“及时行乐”,甚至有一种“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当然,这里的比较并不是要显示中西之异,只是应用一个现成的例证来说明奥勒留思想的特点,并说明同样承认一种事实却可以引出不同的价值观点。
有关精神信仰
由死亡的问题也引向了信仰的问题。在人的身体死后,人的灵魂是否继续存在?灵魂是否不朽?有没有一种“永恒的记忆”?乃至于有没有超越的、唯一的人格神?奥勒留虽然也谈到神灵,但谈的不多,并没有一个统摄一切、至高无上、全知、全能、全善的人格上帝的概念。他基本上还是使自己留在哲学的而非宗教信仰的领域。这一哲学甚至可以说是那些对世界与人生有一种超越的思考,却还是不能或不愿信仰一个唯一的人格神并达到一种确定的宗教信仰的人所能达到的最佳思想,或最高精神境界。在“神”的这一意义上,它或者可以说是一种不信“神”的精神,或者说,是一种非入“神”的近神而居。
但这种人生哲学或道德哲学是否是自足的?是否它还只能是过渡的?或者恰恰因此它才是永久的?19世纪的法国学者雷朗表达了他的一种看法,他认为,奥勒留的《沉思录》是那些不相信超自然力量的人们的福音书。他说:“作为一种真正永久的福音书,《沉思录》绝不会变老。因为它不肯定任何教义。现在的福音书的某些部分会变得陈旧,因为科学不再允许构成其基础的对超自然的天真观念。而在《沉思录》中,超自然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斑点,不影响背景的令人惊叹的美。科学会摧毁上帝与灵魂,但《沉思录》将因其携带的生命与真理而保持年轻。马可·奥勒留的宗教是绝对的宗教,就像耶稣的宗教过去常常是的那样,它产生于一颗高贵的、面对宇宙的道德良心这一事实。这一高贵的道德良心,是任何种族、任何国家、任何革命、任何进步、任何发现都不可能改变的。”
我们是否同意雷朗的看法?人是否完全能够在自身的德行中自足?信徒和非信徒、渴求信仰者与崇尚理智科学者大概会产生不同的看法。我想,对这样一些问题的最终回答,最好还是留给读者自己。
这种思考表现出怎样的精神和品格特质
接下来我想指出奥勒留思想所表现出来的这样四个精神及品格的特质:
第一就是一种理智的诚实。斯多亚派是理性主义者,但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一种试图通过理性来解释和解决一切问题的理性主义者。到了罗马的斯多亚派哲人这里,这种理智的诚实更表现于理智探索范围的缩小,他们不愿过多地去探究不能确凿把握或知悉的东西。他们甚至缺乏这样一种对未知世界的强烈好奇心,也没有激情和想象来加强他们的求知动机和扩大他们的欲知范围。他们努力在人能确切知道的东西和不能确切知道的东西之间划上一条明确的界线,而他们主要是关注他们能够确切把握的东西,这就是自身的德行及其训练。这种理智的诚实还特别表现于对死后灵魂和神灵的探究上。他们坚定的理性主义限制了信仰的渴望。所以,我们看到,在《沉思录》中,在没有把握的情况下,作者不多谈死后,不打探来世,不讨论灵魂不朽,当然更没有死后的赏善罚恶、天堂地狱或者来世的因果报应。奥勒留经常谈到神意、神性,但对神灵的存在及如何存在其实谈的很少,他只是按自己的理解大略地肯定神灵的存在,并在星空尚未被自然科学“脱魅”的情况下,认为神灵是以某种星辰的形式存在。他并不去仔细地分辨神灵是一还是多、是人格的还是非人格的,也不去过多地探讨神与人的关系究竟是怎样的。他只是大致地满足于他们感觉到的自然界的神意和人身上的神性,而这种神性其实也是一种普遍的理性。但是,他也绝不否定神的存在,以及某种天意与人的德行的必然联系。
第二个特点是平衡的中道。从中道的角度观察,思想史上可以看到两种发展或演变形态,一种是由中道到极端,从中和到分化。如孔子是相当中和、中道的,后来则有内圣和外王两派的不同发展。相当具有综合性的苏格拉底之后也有大苏格拉底派和小苏格拉底派两个方面,而在小苏格拉底派中也有向快乐主义与犬儒派两个极端的发展。还有一种发展则是由极端到中道,比如说从犬儒派发展到斯多亚派。犬儒派的思想行为更趋极端,甚至其中有一种有意如此以引人注目的因素,而斯多亚派却渐趋中和。比如说,它不再刻意强调睡木桶、穿破衣等自找苦吃的行为,而是比较顺其自然,但心底其实是更为淡漠地对待外物。这一点我们在奥勒留《沉思录》卷一中提到的几位斯多亚派哲人及他自身的行为方式中可以看得很清楚。在对待物欲方面,他们绝不纵欲,但也不禁欲,而只是自然而然地节欲。这是从心底里更看轻这些外物,也是要更专注于自己的精神。他们平时的生活和行为一如常人,并不炫人耳目,然而,不管外界发生什么变故,他们将始终坚定如常。
这就把我们引到奥勒留精神和品格的第三个特点:温和的坚定。他不仅用理性和意志节制自己的欲望,也用理性和意志控制自己的激情。他始终是温和的,甚至常常可能会让人觉得是冷淡的。斯多亚派哲人对自己的一个基本要求就是不动心。他试图调动自己心灵的最大力量来使心灵不为任何外物和事件所动。他使自己坚如磐石,但这并不是像磐石一样来自本身的自然属性,而主要是一种意志磨炼的结果。他是温和的、宽容的、与人为善的,但也是坚定的、决不改变自己道德原则的。
第四种精神特质则是一种此世的超越精神,即立足于此世,不幻想和渴望彼岸;但又超越于世俗的权名,淡泊于人间的功利。其中“超越权名”尤其是对已掌握或欲追求权名者而言,“淡泊功利”则可对所有人而言。奥勒留在自己的思考中不仅反复指出权力和名声根本性质上的虚幻,也指出财富和功利同样是不值得人们那样热烈地去追求的。
这里有一个有趣的问题:为什么相当多的政治家,包括伟大的政治家,比如腓特烈大帝,或者许多处在权力巅峰的人会对奥勒留的《沉思录》心有所感,乃至深深契合?为什么那么多要忙着处理重大政治问题和经济事务的人,那么多正处在权力或影响力巅峰的人会腾出身来,如此耐心而且常常是倾心地聆听这样一位教导权力和名声并无价值的斯多亚派哲人的声音?一个外在的原因或者可以说是奥勒留也同样处在这样一种权力的顶峰,他有自己亲身的体验,他们想听听这位皇帝说了些什么。但更重要的原因,则无疑是一种既能够恰当地运用和把握权力,又不以不顾一切地攫取和牢固地占有权力为意图的超越精神。这种超越精神能够使人恰如其分地看待自己以及自己所掌握的权力,使他知道,无论这种权力以及由它带来的名声有多大,本质上都仍然是过眼烟云。有了这种超越精神和对权名恰如其分的认识,他就不容易自我膨胀,不容易滥用权力。而一个附带的有益结果可能是,不管他在政坛成就如何,甚至事业失败或者个人失意——这种失败和失意其实比成功更为常见,那么他还可以由这种超越精神得到一种安慰和解脱,使自己的心灵得到一种宁静。
至于淡泊于功利,则可以说对所有时代的所有人都有意义,而对现代人可能尤其有意义。和古代世界不同,现代世界是一个最为崇尚经济成就的世界,也是一个更为追求物质利益的世界。我们甚至不难在有些时期和有些地方看到物欲横流、功利滔滔的状况。而奥勒留的书可以使我们转过来也关心一下自己的精神,可以使我们知道,对人的评价并不应当主要看财富的多寡或者物质的成就,而应当主要看他的德行、品格和精神。物质财富上的成功,也不是所有人都能达到的,甚至不是多数人能达到的,而心灵德行上的成就,则是任何身份、任何处境里的人都能通过自己的努力达到的。
总之,一种理智上诚实但又随时准备聆听一种来自上方的感召的精神,一种在各种极端中保持平衡和恪守中道的精神,一种温和待人和坚定地应对万事万物的精神,一种超越和淡泊于权名功利的精神,以及一种履行自己职责、磨炼自身德行的精神,一种按照本性自然而然地生活的精神,在现代世界里绝没有失去意义,甚至仍然是现代人最需要珍视的价值所在。
当然,我们也在奥勒留的思想中发现某些困难或者说困惑,其中一个是有关抗恶的问题,一个是有关幸福的问题。奥勒留是不主张以恶抗恶的,那么怎样对待恶?他认为我们应当劝告作恶者,并且自己决不受作恶者的影响,仍然循德行而行。而别人的恶行,对按照本性生活且具有自由意志的我来说并不构成恶,不仅不会影响,甚至有助于磨砺我的德行。但是,这些恶肯定还是恶。从社会的观点来看,是不是还可以比这更积极地对抗恶,减少恶,不仅不让恶在我这里蔓延,也不让恶在社会蔓延?而在这方面,斯多亚派的哲学是较少思考的,它主要还是一种自我磨炼的伦理学,而如果立足于社会,肯定还是可以采取一种更积极的态度,可以考虑从制度上如何约束恶,以及在某些危急关头动员和联合好人们奋起抗击恶。我们的确看到近代以来有些理论对改造社会的期望过高,但是否奥勒留对改造社会的期望过低呢?这些都是可以讨论的。
另一个问题是有关幸福的问题,这包括人们的自由、自尊及符合“人之为人”的物质生活条件,而即便是自由和自尊,也常常是需要某种物质手段来支撑的。斯多亚派的哲人所谈到的自由经常只是一种否定的自由、是说“不”的自由,但更具实质意义的自由肯定还是应当包括选择的多种可能性的。幸福的条件也需要包括某些外在的因素:比如他人的评价、社会的尊重,以及一定的物质生活资料、好人有好报,等等。
以上两个问题可以说是有联系的,它们都涉及纯粹自我德行以外的东西。而完全在自身德行中自足的观点,从实践的角度看,还是相当精英化的,适合作为社会道德的榜样而非大多数人常行的准则。
如何阅读本书
最后再简略谈一下《沉思录》这本书的风格和读法。《沉思录》与其说是一本著作,不如说更像是灵魂的低语。你必须使自己安静下来,才能清晰地听见它的声音。当然,它本身又有一种使心灵宁静的力量。它是朴实的,作者从来没有想到它会发表乃至传世,他只是要说出自己心里的话,只是要帮助自己进行一种精神和德行的训练。但它也表现出一种美,一种从纯净心灵中汩汩流出的美。
所以,读这本书,是可以随时拿起,随时放下的,一次能读多少就读多少。不必一次读完,也不一定都按顺序读。而一种相对散漫的阅读方式也是符合作者的思考和写作方式的。奥勒留是在极繁忙的事务中随手记下自己的思考的。他不求系统甚至没有想过发表。而对读者来说,重要的是我们能够深入其思想,脱离日常的喧嚣而进入沉思。
所以,这本书不妨片段地读,但值得反复地读。它不是一次写完,也不必一次读完。而不知不觉中,你可能就读了许多遍了。它成了你的枕边书或者案头书。当然你也可以很久不去读它,在尘封了许多日子之后,你偶尔拿起它,又会像遇到一位老朋友。而如果有比较集中的时间的话,我也主张连贯地读一两遍全书,这样可以把握其总体思想,也不致对某些概念或表述感到突兀和不能理解。《沉思录》在自己的流传史上,也曾是长期尘封。在经历了一千多年近乎湮没无闻的岁月之后,它又突然在现代世界广泛地流传开来。这是否说明:现代人的心灵比起中世纪人的心灵来,更容易,或者毋宁说更需要感受其心灵的低语?一些人可能由“神”退向它,而还有一些人则可能由它走向“神”。
三
与《道德箴言录》的比较
20世纪80年代,我翻译了两部篇幅不大的西方人生哲学和伦理学的经典:一部是古罗马帝国皇帝马可·奥勒留的《沉思录》:另一部是法国贵族拉罗什福科的《道德箴言录》。现在对这两本书做一点简单的比较,或可进一步加深我们对《沉思录》的理解。
这两本书所涉及的内容都是人很内在的心灵部分或很隐秘的心理部分。但如果说《沉思录》是在思索人的心灵应当追求什么,它告诉我们,甚至在外在的生活环境与自己的本性很不契合的时候,心灵也还是可以做一种独立高远的追求;那么,《道德箴言录》则是在说人们内心事实上在追求什么,它告诉我们,甚至当人们在行善的时候,他们的心里也很可能掺杂了一些其他的利己动机。前者展示了人的心灵可以飞翔得多么高,后者则告诉我们人事实上还匍匐得有多么低。
所以,在某种意义上,合观两书,或许恰好可以达到帕斯卡尔对人的一种认识:人既伟大而又悲惨。人在知、情、意方面所能达到的目标和状态都是有限的,甚至常常是处境悲惨的,但人能够意识到自己的限度。人有这样一种有关限度的思想,并仍然抱有一种对于无限的渴望,他就是伟大的,就在精神上无比地高于其他动物。人的伟大就在于能够认识自己的有限但仍然渴望无限。
这样,我们就不妨在我们的心灵里包含两端:一方面要具有现实感,对人性、对人所能达到的道德完善状态或人生幸福状态不抱太过分的期望;另一方面,又不要因此失望,失去善良或追求善良的动力,相反,我们因此更需要一种超越的精神力量,更应当努力向上和向善,努力地拔出自己,而不是停留在一种泥泞、黏稠乃至污秽的状态中。
当然,当我们说《沉思录》一书展示了人的心灵——其实是奥勒留自己的心灵——在努力向上、努力向无限追求的时候,我们并不是说奥勒留不知道人的限度,尤其是社会的限度。他作为一个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一个帝国的真正的哲学家皇帝,并没有将自己的哲学思想强加于社会,他个人的最高精神追求甚至不为这个社会所知,他对社会上的人们只是尽力履行自己作为最高统治者的职责——但并不包括安排和规定他们的精神价值追求的“职责”。然而,由于他的著作的流传,他的思想和精神追求无论如何还是深深地影响了后人。
同样,当我们说《道德箴言录》深刻地揭露出人们阴森复杂的心理动机的时候,我们也不是说拉罗什福科就放弃了对于人精神追求的希望,否定了人达到比较善良、社会达到比较健全状态的可能性。他说他的揭露性描述“仅仅考虑了那些处在本性被罪孽腐蚀的可悲状态中的人们”,而与“上帝以一种特别的恩惠所眷顾的人们无关”。他对作为人们行为主要动机的“利益”的理解也是宽泛的,不仅指物质财产的利益,也包括了对荣誉和名誉的追求。
所以,在奥勒留和拉罗什福科那里,他们的内心其实也都同时包含了对无限的深沉渴望和对有限性的清醒认识的两端,只是各自都有一端比较彰显而另一端隐而不显。他们隐晦或沉默的一部分或可由对方彰显的部分而形成某种平衡和互补。
还有一些另外的对照,比如他们所处的时代,生活在公元2世纪的奥勒留是处在古典社会——古希腊罗马社会—的晚期,也是一个强调更彻底和超越的基督教精神信仰时代的前夕;而生活在公元17世纪的拉罗什福科则处在这个信仰时代向一个重新世俗化的时代(近现代)回归的早期,这个时代比之古典时代不仅更重视此世,而且更重视实利。所以,他们的思想都可以说有某种预示或预感的意义。又比如虽然他们都同样主张要接受命运,但奥勒留更强调其间的必然性,而拉罗什福科更强调其间的偶然性;还有像奥勒留更推崇理性,而拉罗什福科更重视激情;等等,不一而足。但在思想的层级上,他们都是处在高端而非低端;在文字上,他们也各自把一种短小精深、最具个性的思想形式——随感和箴言——发展到一个相当完美的地步。
《沉思录》是自己写给自己的隐秘手书,《道德箴言录》开始也只是在沙龙里口耳相传,直到出现了多有错误的盗印本,作者才不得不自己将其整理付梓。这两部书都不是为出版而作,不意却成为经典之作,甚至有一本还成为今天中国的热门畅销书。虽然说它不仅留传而且也流行总归是一件好事——和时下坊间许多畅销书相比,“与其你流行,还不如我流行”呢,但是,它的流行的确和作者,也许我还可以说和译者没有多少关系。它们的确不是那种好读而又实用的畅销书,读它们是颇要费些力气的,而且还可能令人感到不安——为什么我不能有另一种生活,不能让我的生活有更具精神性的一面?甚至还可能让人感到不快——难道我的内心真的还有这样多不洁的东西?但是,好书终究还是好书。对最好的一类书,我们要努力去配得上它,而不是让它来迁就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