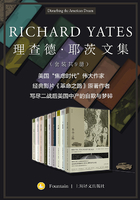
第12章 革命之路(10)
自一九三六年霍华德·吉文斯和太太从城里搬出来之后,他们再也没有搬回去,并且每隔两到三年就会换一次住所。他们总是解释说,这是因为吉文斯太太在买卖房子方面很有手段。她可以看上一处条件不太好的房子,搬进去,然后精心照料提高它的价值,最后以高价出售,挣到的利润会投资到下一栋房子里。他们最先到韦斯切斯特,然后慢慢向北移居到普南郡,后来再到康涅狄格州,前后共买卖了六栋房子。但是他们对现在居住的第七栋房子的感觉却很不一样。在这里住了差不多六年之后,他们不确定以后还会不会搬走。就像吉文斯太太常常说的,她已经爱上了这个地方。
在革命山庄,这是为数不多在新开发区之前就建好的、仍具有传统地方风格的房子之一。房子依傍着两棵大榆树,这一带的树已经不多了,吉文斯太太喜欢把它想象成一个最后的阵地来对抗四周的粗俗。在工作日里,她不得不深入“敌营”,笑吟吟地站在那些难看的小农庄或错层房子的厨房门口,跟那些极端粗鲁的人打交道,还要慎防他们的孩子骑着三轮小车撞向她的小腿,或者把果汁洒到她的裙子上。她可能不得不忍受路上的废气,以及十二号公路冷清的超市、比萨店及冷饮店所带来的荒凉感。不过正因为这些东西,她更能感受到回家的喜悦。她最喜欢路程最后几百码的荫蔽小道,因为这意味着她马上就要到家了。她喜欢轮胎摩擦碎石子的脆响,喜欢在整洁的车库里熄灭引擎,然后疲惫而勇敢地经过香味浓郁的花床,走向那扇带着浓厚殖民地气息的大门。进门首先可以闻到雪松木地板和地蜡的干净味道,古老却迷人的伞架上方悬挂着的柯里尔和艾夫斯版画,马上就能让她心里充斥着一种柔软的浪漫化的情怀——“家”的感觉。
刚刚过去的这一天尤其难熬。本来对房地产行业来说,星期六就是最忙碌的一天。这一天下午,比繁杂的工作更麻烦的是,她还得自己驾车到格林纳克斯——当然不是去看望她的儿子,只有丈夫陪着的时候她才会这样做——而是跟他的主治医生会面。这件事总让她感到肮脏。心理医生不该是那种理智、声音沉稳、看上去很可靠的人吗?但如果你见到的这个人只能让你感到肮脏,你会怎么想呢?他是一个眼睛通红的、喜欢咬指甲的小个子男人,戴着用透明胶粘合起来的眼镜,胸前别了一个连锁超市买来的领夹,以便让领带服帖地固定在白底白花的衬衣上。他用大拇指沾了口水,在一叠厚厚的黄褐色文件夹中翻找了好久,才弄清楚她所说的病人是谁,“哦,对了,我知道了。那么,你有什么问题吗?”
现在,无论出于哪个圣人对疲惫行者的护佑,她终于回家了。“亲爱的!”刚进玄关她就跟丈夫打招呼,因为非常肯定他就在客厅里看报纸。她没有停下来聊天,而是直接走进了厨房。清洁女工已经把茶具都摆好了。那只冒着热气的茶壶看起来多么舒服,多么让人高兴啊!厨房有着高高的窗子,既宽敞又整洁。这里让她感到非常平和,只有当她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在父亲位于费城的美丽厨房里跟女仆们闲聊,她才有过这样的感觉。奇妙的是,她常常在想,以前她拥有的厨房无论多精致,从来不曾给她这种安全感。
哦,当然,人是会改变的。有时候她告诉自己:对这栋房子的留恋只是因为我老了,疲倦了。但在她内心却偷偷地滋长另一个想法:她相信,有能力去爱这栋房子,是这些年来她本性中少数几个深刻的、积极的变化之一。这些正面的变化让她用一个全新的角度来看待过去。
“因为我喜爱。”许多年前丈夫气急败坏地问她为什么不肯放弃城里的工作时,她这么说。
“这份工作肯定不怎么有意思,”他会说,“而且我们也不缺钱,所以那到底是为什么呢?”她的回答永远只有一个:我喜爱。
“你喜爱霍斯特·鲍尔轴承公司?你喜爱当速记员?怎么会有人喜爱这样的东西?”
“碰巧我就是这么一个人。而且你很清楚如果还想雇用一位全职用人的话,我们需要更多的钱。你也知道,我并不是什么速记员,”事实上她是一名行政助理。“霍华德,说真的,我们讨论这个没有意义。”
她无法解释,甚至无法理解的是,她喜爱的不是这份工作——对她来说什么工作都一样——也不是这份工作能带来的独立自主。(虽然这对于一个在离婚的悬崖边上摇摆不定的女人很重要。)她内心深处所喜爱并需要的,其实是工作本身。“努力工作,”她的父亲常常说,“是治疗伤痛最好的药物,对男人或女人来说都是如此。”她对此一直深信不疑。她喜爱办公室里的拥挤、紧迫、喧嚣和目光注视,推车送过来的简便午餐,处理文件和办公电话的清脆利落,加班工作时的精疲力竭,以及晚上回到家把鞋子甩到地板上的轻松感。这个时候她已经被榨干得只剩下一点力气服下两片阿司匹林,泡个热水澡,吃一点晚餐然后上床睡觉,多么纯粹。这就是她爱的实质;就是这些东西帮助她对抗着婚姻和为人父母的压力。正如她自己时常说的,如果没有这些,她肯定早就精神失常了。
后来她真的放弃了这份工作,搬到郊区并且做起了房地产经纪人。这是一个艰难的过渡。房地产行业的工作量太少,那个时代根本没几个人买卖房子,而且,用于学习分期付款法规和建筑规章制度的时间也很有限。她一整天无所事事,只好不断地整理玫瑰木桌上的文件,一面等着电话响起来。在空闲中焦虑不断积压,以至于她差点要大声尖叫,直到她发现心里的骚动是可以宣泄出来的:通过着手改造周围的东西。她用自己的双手扒开墙纸和刮下石灰,让里面的橡木板重新露了出来。她给楼梯安上新的扶手,卸下普通的窗框代之以精美的殖民地风情小格窗框。她画出楼台和车库的设计蓝图,然后监督整个建造过程。她整理并栽培出上百平方英尺的新草坪。三年的时间内,她拾掇后的房子市值已经增加了五千美元,她说服丈夫把它卖出去买下另外一栋,然后继续她维修改造的工程。第三栋,第四栋,一栋栋房子做下来,她的房地产生意也同时蒸蒸日上,在其中最忙碌的一年,她甚至每天工作十八个小时:十个小时做生意,八个小时维修房子。“因为我喜爱,”她一再强调,夜深了她依然不知疲倦地切削、捶打、抛光和修理,“我就爱干这样的活,难道你不喜欢吗?”
这样会很傻吗?当她摆弄着托盘上的茶具,心底一片平静安详时,这个念头忽然冒了出来。她妥协似的叹了口气,发现这些年来自己做的一切多么傻,多么错误、愚蠢。哦,现在她是变了,这一点毋庸置疑。人是会改变的,只是有的改变会像花儿绽放一样灿烂,有的则会像花儿凋谢一样凄凉。对她来说,现在的这种改变就像是花的最后一次绽放,一种延迟了好多年的女性特质的复苏。
她对这栋房子依恋的增长以及对工作热情的减退,只是这种变化里最小最浅薄的两个症状。里面还有一些更深刻的东西,生理上的东西,既困惑而又带来一种奇异的愉悦感。有时候厨房收音机播出贝多芬交响曲,她就会感到既疼痛又喜悦,这曲子会把她触动得掉眼泪;有时候她跟丈夫聊天时,她会感到一种痒痒的念头——好吧,就说是一种痒痒的欲念。她想要用双臂搂着他,把他那亲爱的衰老的脑袋紧紧贴在自己的胸口。
“我想我们今天喝点茶就好了,”她一边说话一边端着盘子走进客厅。“我希望你不要介意。关键是如果我们现在吃饱了,晚餐可能就吃不下去了。今天我们会很早就吃晚饭,因为你知道我八点要赶到惠勒家去。恐怕这个时间安排确实有点尴尬。”她把茶盘轻轻放在一张古董咖啡桌上。从桌面上胶水粘过的裂痕,就可以想象在警察上门的那个可怕夜晚,他们的儿子约翰怎样把这张桌子扔向房间的另一端。
“能像这样坐下来休息真是太好了,”吉文斯太太说,“忙碌了一天之后,还有什么事能比这样坐着更舒服呢。”
一直到她按照丈夫喜欢的方式,在茶里添上三块方塘,并递到他面前时,她才抬头确认丈夫是不是坐在那里。而霍华德·吉文斯也是突然闻到了茶的味道,抬头看到了她,才发现她已经回到家了。整个下午他的助听器都没打开。妻子骤然出现在眼前,使他的脸看上去像个受惊的婴儿。他放下手里的《先驱论坛报》,一只微颤的手摸索着助听器的按钮,另外一只接过茶杯和托盘。手的抖动让杯子一阵摇晃。她没有注意到丈夫的脸色,自顾自地讲了下去。
霍华德·吉文斯看上去比六十七岁的真实年龄更苍老。他的整个成年期都消耗在世界第七大保险公司里,当个不起眼的小职员。退休以后,沉闷单调的办公室生涯在他身上留下了清晰的印迹,就像风和太阳会在一个老水手身上留下的一样。他柔软,苍白。面孔并没有因为衰老而褶皱密布或脸颊下垂,而是相反地膨胀了起来,像小孩一样光滑,头发也像小孩般轻柔如丝。他从来都不是个健壮的男人,现在肚子上硕大的赘肉更凸显了他的柔弱,他肚腩大得让他在坐着时双膝都合不起来了。他穿了一件很整洁的红格子衬衣、一条灰色的法兰绒长裤配灰色的袜子,以及一双高帮矫正黑皮鞋,鞋面已经老旧得到处都是褶皱,跟他光滑的脸孔形成对比。
“没有蛋糕了吗?”他清了清嗓子问。“我以为我们还有一点椰子蛋糕呢。”
“嗯,是的。不过亲爱的,我想我们今天就喝点茶好了,因为我们会早点吃晚饭……”她把刚才已经说过的要去见惠勒夫妇的事情重述了一遍,心里模模糊糊地想起好像已经说过同样的话。而他则点了点头,心里模模糊糊地理解着她在说些什么。她说话的时候心不在焉地看着最后一束绯红的阳光从丈夫的耳垂下穿透出来,让他的头皮屑看来像火的碎片;而她的思绪早就飞奔到晚上的约会中去了。
这是一次不寻常的会面。事实上,她经过深思熟虑才踏出这一步。几个星期前的一个黄昏,当她的焦虑又升腾起来时,她只好在后院的草坪上踱步来平静心绪,这时她脑海里出现一幅家庭欢聚的画面:这里面有爱波·惠勒,她坐在一张白铁椅子上,美丽的脸孔看向身边的霍华德·吉文斯,并且因为他睿智慈爱的话而动情地微笑。霍华德旁边是一张白铁桌子,上面放着冰块和鸡尾酒,而对面是弗兰克·惠勒和约翰。弗兰克站在那里,身体微微前倾,拿着一个酒杯跟约翰展开一场诚恳的交谈。已经进入良好康复阶段的约翰放松地坐在白铁躺椅上,微笑着,神态平静而礼貌地跟弗兰克谈些政治、书籍、棒球或任何年轻男人喜爱的话题,并在无关痛痒的枝节上提出一点不同的见解。最后约翰还会抬头跟她说:“妈妈,您不想参加我们的讨论吗?”
这幅画面一再重现在她脑海里,直到跟杂志插画一样真实。她还不断地对画面加以改进,她甚至把惠勒夫妇的孩子都放了进来。他们可以乖乖地在玫瑰花丛的阴影下面玩耍,穿着白色短裤和网球鞋,还会把抓到的萤火虫放进玻璃罐里。这幅画面越具体生动,她就越觉得这不是个虚幻的想象。能跟年纪相仿而且敏感、意气相投的人相处,对约翰肯定有莫大的好处。而对惠勒夫妇来说,也不存在牺牲的问题。他们不是曾经多次告诉过她,他们非常渴望交到志趣相投的朋友吗?而革命山庄上那对令人厌倦的夫妇(克兰达还是坎贝尔?)显然不能满足他们所期待的那种交流。而约翰,无论他成不成才,毕竟是个知识分子。
所以这对所有人都是件好事。她知道这一点,她确信这一点。不过她明白这一切不能操之过急。这件事从一开始就要慢慢去实行,一步接一步。
最近几次跟丈夫一起去探望约翰时,院方同意他们把约翰带出医院兜风,一小时后再送回来,作为试验。“我觉得现在带他回家的时机还不成熟。”一个月前他的主治医生一边说,一边在桌面的吸墨纸上一根接一根地按响自己的指节,指节沾着墨水,声音非常讨厌。“最好还是把他留在医院,考虑到家庭气氛对他的刺激和其他的因素,现在最好让他局限在短距离的外出。以后再看看情况怎样。下一步你们可以尝试带他去见一些相熟的朋友,尽量把他放在比较温和的环境,这样会比较合理。你们可以自己判断该采取哪个步骤。”
她已经跟霍华德商量过了,甚至开车带约翰出去的时候,还好几次委婉地跟他提起自己的计划。上周她考虑了各种因素并且分析了约翰的状态之后,最终判断采取下一步行动的时机已经成熟。她安排了今天跟医生的会面,其实就是要宣布自己的决定,同时向他征求一点小小的建议。她想知道,她应该向惠勒夫妇透露多少关于约翰的病情呢?不过她事先就应该料想到,这位医生给不了她任何帮助。他还是那么一句话:你们自己判断吧。现在吉文斯太太只能感谢他没有反对自己的决定。到目前为止进展顺利,就看惠勒夫妇的反应了。她本来希望把这次会面安排在自己家里,就在这张被烛光照亮的桌边,这样她会觉得更舒服更得体。不过现在已经无法实现了。
“我希望你们不会觉得我强人所难,”她一边清洗茶具一边小声演练着,“不过我还是想请你们帮我这个忙,这件事情跟我儿子约翰有关……”噢,她不用去考虑怎样措辞,到时候一开口她自然会想到合适的字眼。而她很有把握惠勒夫妇会理解她的。上帝保佑这两个年轻人,他们肯定会理解的。
之后她就忙着准备晚餐、伺候丈夫吃完晚餐、收拾餐具,再也没空想下去。而当她在厅里停留一会儿,补补口红,并跟丈夫说“亲爱的,晚上回来再见”时,她兴奋得像是个小女孩。
只是一走进惠勒夫妇的客厅,兴奋感就变成了恐慌。虽然他们走着笑着聊着,她却感觉自己像是一个入侵者。
她以为惠勒夫妇会像以前每次迎接客人那样,既紧张又混乱。两人会同时开口说话,在她周围团团转忙着收拾东西,同时抢着把一个尖锐的玩具从椅子上拿开以免吉文斯太太一屁股坐下去。但是今天大不一样,他们平静地接待了她。爱波不需要一再强调屋子没收拾好,因为屋子一点也不乱。弗兰克也不需要跟她说“我去给您弄点喝的”之后急急忙忙跑进厨房,把冰箱什么的磕碰得砰砰作响,因为饮料已经摆好在咖啡桌上。显然早在她到访之前,惠勒夫妇已经安静地在这里喝酒聊天了。对于她的到来他们表现出合乎礼仪的欢喜,但如果她没来的话,他们肯定会在自己的小天地里怡然自得的。
“哦,我只要一点点就可以了,谢谢,这就很好。”吉文斯太太听到自己说“哦,能这么坐下来真是太好了”,“天哪,你们家今天看上去很漂亮”和一些类似的寒暄。随后她说:“我希望你们不会觉得我强人所难,不过我还是想请你们帮我一个大忙,这件事情跟我儿子约翰有关。”
惠勒夫妇脸上的肌肉非常轻微地跳动了一下,轻微得连最精密的照相机也不可能捕捉到,但吉文斯太太感到被掴了一巴掌。他们知道了!她把这个计划方方面面的变故都细想到了,除了这个。是谁告诉他们的?他们到底知道多少?他们知道约翰把房子搅得天翻地覆,剪断了电话线,甚至招来了警察吗?
但话一出口,她已经不能回头了。她的声音在跟他们说,约翰的情况不太好。由于工作太操劳及其他一些原因,他的精神崩溃了。她一直为孩子在离家那么远的地方生病而心烦意乱,好在有一天他回来了。但是他回来后病情没好转,让他们夫妇俩很操心。他的医生认为他最好能找个地方好好养病,所以现在他暂时……
“呃,事实上,现在他暂时住在格林纳克斯疗养院。”除了声音是活的,吉文斯太太身体的其他部分全部麻痹了。
她的声音向他们保证,格林纳克斯疗养院比他们想象的还要好得多。从设施和人员配备来看,它比这个地区其他的私人疗养院都更优越。
她的声音继续说下去,越来越弱,直到最后说出了重点:某一个即将到来的周日——当然不是那么紧急,她是说未来的某个周日——惠勒夫妇愿不愿意……
“我们当然愿意,海伦,”爱波说,“我们很乐意跟他见面。你能想到我们,我们觉得很荣幸。”弗兰克一边给她续杯一边附和地说,他觉得约翰是个很有意思的人。
“那么下一个周日怎么样?”爱波说,“如果你们方便的话。”
“下周日?”吉文斯太太假装在盘算着。“嗯,让我想想看。我不是非常肯定——哦,好的,就这样定了吧。”她知道自己应该感到高兴,她已经达到她最想要的结果。但现在她只想离开这里,尽快回到自己的家。“不急的,如果下个周日你们不方便的话,我们可以再商量一个别的……”
“不用了,海伦。下周日没问题。”
“嗯,”她说,“那好吧,就这样说定了。哦,天哪,看看现在都几点了。我恐怕得——哦,你们有事情想问我,对吧?这次又是我一个人在说了,跟往常一样。”她喝了一口酒,感觉嘴巴干涩,像是肿了起来。
“嗯,其实,海伦……”弗兰克开始说,“我们有个非常重要的消息……”
半个小时以后,吉文斯太太已经在开车回家的路上。在整个路途当中她的眉毛高高扬起,久久都不能从震惊里平复下来。她已经等不及要告诉丈夫这个消息了。
她发现丈夫还是坐在扶手椅上,旁边是一座在战前拍卖会上她买来的无价古董钟。他仍在黄色灯光下阅读,只是《先驱论坛报》已经换成了《世界电讯与太阳报》。
“霍华德,”她说,“你知道那两个孩子告诉我什么了吗?”
“什么孩子啊,亲爱的?”
“惠勒夫妇。你知道吗,就是我去见的那两个人?住在革命路一座小房子里的年轻夫妇,我觉得约翰可能会喜欢的那两个人?”
“哦,我不认识。他们说了什么?”
“首先我知道他们经济能力并不稳定,连房子的首付都是借来的,而且这还只是两年之前的事情。此外……”
霍华德·吉文斯试图去听妻子说话,但他的眼睛还是忍不住瞟向放在腿上的报纸:印第安纳州南本德有一个十二岁的小男孩向银行贷款二十五美元给他那条名叫“小玻”的狗买药,银行经理竟然亲自签批了申请文件。
“……于是我问他们:为什么要卖掉呢,等你们回来的时候肯定会想要这个房子的。然后你知道他怎么说吗?他用非常警惕的眼神看着我说:‘呃,说到重点了。我们不打算再回来了。’于是我问:‘你们已经在那边找好工作了吗?’‘没有,’他就这样回答了我。然后我又问他们是不是打算跟亲戚住在一起,或者是朋友之类的。‘没有。’”说到这里吉文斯太太装出一副她所能想象到的最不负责任的神色,“‘没有,一个认识的人都没有。我们就是想去,仅此而已。’真的,霍华德,你不知道那时气氛有多尴尬。你能够想象吗?这太让人无法接受了。我是说这整个事情。”
霍华德摸了摸自己的助听器,然后回答:“无法接受?这怎么说呢,亲爱的?”他猜自己已经乱套了,没有跟上她说的话。一开始妻子说的好像是关于什么人去欧洲,现在显然已经是别的什么事情了。
“难道不是吗?”她问,“两个一文不名的人,还带着刚刚上学的孩子。我觉得人们一般不会这样的,难道不是吗?除非他们是要逃避什么东西。我很不愿意去想有什么事情会……算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去想,这才是关键。他们看来像是踏实安定的人。这不是很怪异吗?而且最尴尬的是,在他们爆出这个消息之前,我已经把他们搅和进约翰的事情里,现在只好完成它了,虽然已经没什么意义。”
“完成什么,亲爱的?我不太明白——”
“带约翰去他们家一趟,霍华德,你到底有没有在听?”
“噢,是的。当然在听。我的意思是,为什么这就没有什么意义了呢?”
“因为,”她不耐烦地说,“他们秋天就要一去不回头了,把他们介绍给约翰又有什么价值呢。”
“价值?”
“嗯,我的意思是说,他需要的是可以长期交往的人。当然,让他们见见面,在他们离开之前把约翰带过去一两趟,也没什么坏处。只是我考虑的是那种长期的关系。哦,亲爱的,这实在是太让人意外了。为什么这些人就不能……”说到这里她已经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或者想要说些什么。她惊异地发现,她竟然一边说话一边把手绢紧紧拧成一条绳子,手上的汗都把手绢弄潮了。“我认为啊,人心难测。”她总结道。然后起身离开,快步走到楼上,打算找出一套舒服的衣服换上。
经过楼梯平台时,她在镜子里看到自己。她自豪地想,她的形象看起来——至少眼角匆匆一瞥时看起来,仍然是一个娇养在漂亮房子里灵巧袅娜的女孩。当她站在卧室的大地毯上快速地把外套和裙子脱下来时,就好像回到了从前,她正在少女时代的闺房里飞快地换着衣服准备参加下午的舞会。那时候她的血液跟最后一些急需打理的细节一般奔驰着:应该用哪一种香水呢?快啊!哪一种?等收拾妥当,她就会奔到楼梯围栏边上喊道:“等等!我就来了,我马上就下来!”
挂在衣柜里的旧法兰绒衬衫和松垮的裤子把吉文斯太太拉回现实。她不由得开始责骂自己:真是太愚蠢了,我怎么越来越喜欢胡思乱想。接着她坐在床上,脱下丝袜,真正的震惊才向她袭来。她以为自己会看到一双纤细洁白、掌骨柔和的脚,上面会布满淡蓝色的静脉血管。然而她真正看到的是两只像癞蛤蟆一样的怪物趴在地毯上,粗糙不堪,脚趾因为拇囊炎而指节突起。这双脚正努力地把变形的脚指甲蜷缩隐藏起来,她连忙把脚掌塞进浅色的挪威拖鞋里(穿着这种鞋在屋子里闲荡是再舒服不过了),然后很快翻出一套简单舒适的家居服。可是已经太晚了。接下来的五分钟她只好双手稳稳抓住床柱紧紧地闭着嘴巴,因为她在哭泣。
她哭是因为今晚她对惠勒夫妇寄予厚望,而现在她却非常、非常、非常失望。她哭是因为发现自己五十六岁了,双脚已经变得肿胀丑陋,不堪入目。她哭是因为从前上学时女孩不喜欢她,长大之后男孩也不喜欢她。她哭是因为霍华德·吉文斯是唯一一个向她求婚的男人,而她接受了他,她哭,是因为他们唯一的儿子是个疯子。
但这情绪很快过去了。她意识到她唯一该做的就是走进浴室,擤掉鼻涕,洗脸梳头。重新振作起来之后,她穿着那双拖鞋轻快地、悄悄地走到楼下,熄掉所有多余的灯只剩下扶手椅边的那盏,然后在丈夫对面的摇椅上坐了下来。
“我现在感觉舒服多了。真的,霍华德。刚才跟惠勒夫妇谈完了之后,心里一团乱麻似的。你想象不到他们多让我失望。我一直以为他们是踏实可靠的年轻人。我以为现在所有结了婚的年轻夫妇的生活理应更加稳定。你不这样认为吗,尤其是在我们这样的社区中。这真是太不可思议了,以前我听到的都是年轻夫妇千方百计要在这里安顿下来,抚养他们的孩子……”
她说啊说,在房间里走啊走。霍华德及时地点头、微笑和咕哝几句。他做得如此明智审慎以至于她完全没有意识到,他早已经把助听器关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