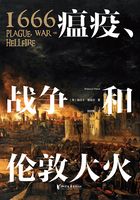
3 逆转的潮流
他的堂弟蒙塔古
(因宫廷动乱而沦为御马官)……
然后,泰迪意识到丹麦人不会采取行动,
将六名船长送去英勇赴死。
——安德鲁·马维尔《给画家的第二个建议》[119]
北海
这是一个奇怪的约定。他们的船离英国越来越远了,十几岁的罗切斯特伯爵催促他的朋友们,温德姆(Windham)先生和爱德华·蒙塔古(Edward Montagu),要求他们与他达成一项协议。如果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在任务期间死亡,他要以魂灵的形式回来,向他们证明还有一种“未来状态”。蒙塔古充满了不祥的预感,确信自己不会活着回来,便拒绝了这个提议,而与罗切斯特年龄相仿的温德姆却同意了。
那是1665年7月,伦敦正与鼠疫进行斗争。这三名同行者来自一群所谓的“绅士志愿军”,他们自愿加入桑威奇伯爵的舰队,由此逃离了瘟疫,他们认为这次任务风险低、收益高。[120]桑威奇和一些人一样,没有党派倾向,他因此可以毫无障碍地从一个忠诚的克伦威尔主义者过渡到一个值得信任的保皇派人士。同时,他也是一名强悍的军事领袖。洛斯托夫特海战中,约克公爵险些丧命,之后,桑威奇被授予了舰队的实际指挥权。几个月来,英国外交人员和间谍组成网络,一直在海牙收集情报,并在哥本哈根密谋外交协议,试图给荷兰人致命一击。乔治·唐宁(George Downing)从海牙发来消息称,一支荷兰东印度船队即将返航,运载的货物价值连城。不仅如此,由荷兰海军上将米希尔·德·鲁伊特(Mich-iel de Ruyter)率领的一支来自几内亚的舰队也将很快抵达。桑威奇此行的任务是追踪、封锁并突袭返航的荷兰商船。如果成功,英国的收益将摧毁荷兰,也许使之再无反击之力,并为整个战争筹得资金。
丹麦国王弗雷德里克三世(Frederick III)的协助对计划的成败至关重要,他同时统治着丹麦和挪威。自战争爆发以来,返航的荷兰船只都避开了英吉利海峡,改为绕道苏格兰,向南航行返回荷兰,途中经常在中立的北欧港口泊锚。英国人正是想在其中一个中立港口附近对敌人进行伏击。早在1664年,哥本哈根的英国特使吉尔伯特·塔尔博特爵士(Sir Gilbert Talbot)就一直在与丹麦国王进行秘密谈判,试图说服他背弃与荷兰的贸易协定,协助英国的袭击。对荷兰负债累累的丹麦人将获得一部分预期的战利品;而且,一旦荷兰报复的话,英国承诺给予海军援助。如果丹麦人同意,新联盟就有可能切断荷兰与波罗的海的联系——有效阻止他们进入。对于囊中羞涩的查理二世来说,这个机会令人陶醉。
经过几个月的摇摆不定,英国在洛斯托夫特的意外胜利改变了丹麦人的想法。事实上,这次胜利让许多外国观察家大为惊讶。英国士气高涨,弗雷德里克三世随即与英国达成了协议。桑威奇起航时,整个行动的策划者塔尔博特还在与丹麦国王商谈条款,因此,丹麦人具体如何参与其中的关键细节尚未敲定。尽管存在种种不确定性,英国海军还是起程了。
即使按照17世纪的标准,船员的条件也非常艰苦。几个月后,桑威奇对佩皮斯说:“从来没有舰队会在给养条件如此糟糕的情况下出海。”[121]他有充分的理由感到懊恼。这一时期英国海军的一大弱点是,除了布里德灵顿一个小港口外,在哈威奇港和索勒湾以北,可供停泊和补给的地点有限。实际上,围绕不列颠群岛的海战几乎完全集中在英吉利海峡沿岸,或北海的下半部。向北航行如此远的距离——如桑威奇现在的做法——意味着将船队逼至其后勤输送能力的极限。[122]更严重的是,许多已认定的供粮船来自感染瘟疫的地区,不得不加以禁运。伦敦大批的箍桶匠失踪,用来装水和啤酒的木桶陷入短缺。人们担心衣物会带有“瘴气”,所以合格的衣服也供应不足。在这样的境况下,众多海员将难以熬过北海的狂风和恶劣的天气。[123]除此之外,自一个多月前的洛斯托夫特海战以来,大多数船员都没有获准上岸休假。对瘟疫的恐惧使他们实际上处于隔离状态。
健康的年轻新兵永远受欢迎。洛斯托夫特战役过去一个月后,罗切斯特在斯卡伯勒以南的弗兰伯勒岬附近加入了舰队,同行的还有“奥布赖恩中尉和一名法国绅士”。此前,罗切斯特一直跟随托马斯·阿林爵士(Sir Thomas Allin)的小型船队航行,据说他“非常迫切地想加入舰队”。于是在7月12日,阿林派了一艘双桅纵帆船和“成功号”战舰护送他前去。[124]7月15日,桑威奇在日记中写道:“罗切斯特大人来了……在我的船上参加这次航行。”[125]应查理国王的要求,罗切斯特由海军上将亲自关照,并在“皇家王子号”旗舰上安排独立舱房,这艘雄伟的旗舰已有五十年历史,配有90门大炮,是英国海军中最强大的战舰之一。它在詹姆斯一世时建成,几十年来历经改建和修葺,在奥利弗·克伦威尔的指挥下参加了第一次英荷战争,最近又参与了洛斯托夫特战役。桑威奇十五岁的儿子西德尼也在船上。桑威奇说自己已“竭尽所能”为罗切斯特安排了最好的住宿。一天后,爱德华·蒙塔古也加入了舰队,他乘坐装配60门火炮的三级护卫舰“迅捷号”从索勒湾过来。[126]7月17日,桑威奇列出所有加入舰队的舰只的清单,它们将一同驶往“挪威海角”。[127]值得注意的是,罗伯特·霍姆斯舰长不在其中,在洛斯托夫特战役期间的舰队司令提拔中,他被忽略了,他一气之下辞去了海军中的职务。
北海水域航行艰难。那里的水流呈逆时针流动,同时有危险的浅滩,天气变幻莫测,大风常常变为飓风或暴风雨。在17世纪,哪怕是最有经验的水手,稍一分心就会偏航几英里,或撞上北边的岩石。这是帆船航海的时代——利用风向并找到“上风位置”至关重要(这种状态较为有利,风在帆后推着船前进;在战斗中,这也意味着与敌舰交战时有更好的位置),对战役的胜负起决定性作用。然而,新的研究表明,1665年正在发生一场深刻的转变,舰队里的任何人都始料未及。自1560年以来,世界一直处于小冰河期;1629年后,小冰河期由于温和的气候和西风而中断。然而,1662年,天气再次开始变化,东风逐渐增强,急流进一步向南推进。[128]粗略地说,这意味着在克伦威尔领导的第一次英荷战争期间,天气条件经常有助于英方来“设定战役的走向”,但1665年持续的寒冷天气以及东风往往会给荷兰人带来优势。[129]
在海上恶劣的条件下,很容易缔结友谊。罗切斯特可能早就认识温德姆了,因为他之前和温德姆的兄弟托马斯一起在牛津念书。至于他是否在航行前就与蒙塔古相识还不太确定,但可以确定的是,这两人有太多相同之处。这名年轻的伯爵曾试图绑架伊丽莎白·马莱特,惹恼了国王,而蒙塔古做的事更糟糕。作为桑威奇伯爵的堂弟,蒙塔古出身权贵,享有受人尊敬的名号,以及由此带来的机会。蒙塔古至少比他的堂兄小十岁,但他曾鼓励桑威奇支持保皇派,最终促成了复辟——对此,他记忆犹新——1662年,他和桑威奇一起去里斯本接查理二世未来的新娘——布拉干萨的凯瑟琳(Catherine of Braganza)。
尽管已经二十三岁了,凯瑟琳一直过着受庇护的生活。返航途中,蒙塔古赢得了凯瑟琳的信任,回到英国后不久,他被任命为王后的御马官。蒙塔古不太受同辈人的待见,他得罪了许多朝臣,债台高筑(在当时当地并不罕见),而且似乎觊觎新王后的家室。1664年5月,他越界了。凯瑟琳是一个虔诚的女人,她很快发现自己周围全是查理那些反复无常、美貌风趣的情妇,眼见着王室私生子接二连三诞生。很明显,她还是爱查理的。1663年病重时,她还哭着向他道歉,觉得自己不是一个好妻子。即便查理并不爱她,他也对她抱有深深的敬意,对她很呵护。
1664年初,佩皮斯注意到,蒙塔古“比其他人更受(王后的)喜爱,会和她单独交谈两三个小时”。他开玩笑地补充说,“国王周围的大臣”会告诉查理,“他必须照看好自己的妻子……因为有人在对她献殷勤”。[130]有一天,蒙塔古和凯瑟琳单独在一起,他摸了摸她的手。这是一场危险的权力游戏,也是公开的亲密行为,有很大的风险。尽管这不是亨利八世的宫廷,但对于王后忠贞度的怀疑仍有可能损害斯图亚特王朝的合法性。没人知晓蒙塔古脑子里到底在想什么。后来,凯瑟琳天真地问丈夫,男人抚摸女人的手是什么意思,并向他交代了事情的经过。这个“快活王”并不觉得好笑。蒙塔古被逐出了宫廷。
毫无疑问,此次航行将为罗切斯特和蒙塔古提供一个重获国王青睐的机会,但他们无疑也渴望财富。私掠商船活动在英国深入人心,在整个17世纪都是合法的。事实上,来自伦敦、多佛和布里斯托尔等港口城市的商人财团都投资了私掠计划,许多在与荷兰的战争中丧夫的遗孀也参与了——甚至连佩皮斯也投资了一项计划,派遣私掠船“飞行猎犬号”。[131]对于海上的船员来说,只有上层人士才有可能获益。除了军官和像蒙塔古和罗切斯特这样的绅士志愿军,普通船员从俘获的船只中收获甚微。从罗切斯特的信件中可以看出,他和同伴们“满怀希望和期待”,计划着如何瓜分战利品。罗切斯特想要“衣物和黄金”,其他人则选择了香料、丝绸和钻石。[132]
舰队继续向北。过往船只传来一些关于德·鲁伊特和荷兰东印度船队行踪的消息,[133]但都没有得到证实。7月22日之前,舰员们已经开始在寒冷的海水中捕捞新鲜的鳕鱼。库存消耗殆尽。最糟糕的是,啤酒没几天就要定量供应了。7月23日,桑威奇收到了令人失望的消息:德·鲁伊特的舰队已经返回荷兰共和国。另外,挪威的卑尔根港泊有大量的荷兰舰只。7月30日,桑威奇在“皇家王子号”上召开战时会议,制订了一项计划。卑尔根是一个难以停泊的地方,不适合大型战舰。因此,桑威奇决定派遣一支由二十二人组成的小型舰队,配备四级和五级护卫舰以及三艘火攻船。这支队伍由海军少将托马斯·泰德曼爵士(Sir Thomas Teddeman)指挥,政治家托马斯·克利福德爵士也在舰上,前去与卑尔根的长官谈判条件。克利福德出身于德文郡的一个普通地主家庭,是托特内斯的国会议员,他今年三十四岁,有两个年幼的儿子,至少五个女儿。他是国务大臣阿灵顿勋爵的门生,才智敏锐卓绝。与许多年轻的政治家一样,这次与荷兰的战争对他而言是一次绝无仅有的机会,可以在国务上大显身手。
泰德曼和克利福德将乘坐“复仇号”,这艘战舰是这些小型舰只中最大的一艘,有十一年的历史,配有60门火炮。之前的会议已达成一致意见,食物供给短缺(剩下的粮食估计只能维持三个星期)意味着他们要么即刻行动,要么“一事无成”。[134]分割舰队是一个大胆且有风险的举措,据说,威廉·佩恩爵士最初表示反对;然而,后来的情报改变了他的想法:据报告,十艘满载货物的荷兰东印度船只也正在向港口靠近。
在海上航行了几个星期后,罗切斯特不想错过任何一次行动。他直接找到桑威奇,请求加入泰德曼所在的“复仇号”,声称,“于我而言,错失任何一次为国王效忠的机会都是不合适的”。他的请求得到了批准。最终,他和桑威奇的小儿子西德尼、温德姆先生和爱德华·蒙塔古一同加入了泰德曼的旗舰。当晚六点,这支队伍起航了,舰队里剩下的人由桑威奇领导,留在环绕大陆的零星岛屿外等待。在北海汹涌的波涛中,一阵疾风推着泰德曼的舰队破浪前行。他们在克拉奇福特住了一夜,次日中午前往卑尔根。一名老练的水手告诉罗切斯特:“那些岩石危险极了……他们根本没见识过。”[135]他们继续一路向北。
英国
他闭上眼睛,凝视黑暗,任“视觉幻想”恣意延展。首先,出现了一个蓝色的斑点,越来越亮,最后成了“白色的亮点”。接着,红、黄、绿、蓝、紫颜色的五个圆圈围绕着它,这些圆圈上都罩着一层深绿色或红色。然后图像变成蓝色和红色。最后,他睁开眼睛,感觉像是始终在直视太阳。亮的物体呈红色,暗的物体看起来是蓝色。[136]
他把自己的观察简略地记录在一本翻旧了的笔记本上,这个本子被他称为《某些哲学问题》(Quaestiones Quaedam Philosophicae),里面记满了他对光、声、自然世界和人类情感的思考。扉页上潦草地写着一句格言:“柏拉图,吾友也;亚里士多德,吾友也;唯真理为吾挚友。”[137]这个年轻人在剑桥大学读书,他在大学导师眼中并不很出众。导师们都热衷于古典课程,以盖伦、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为根基,但他一直默默地以其他方式来扩展自己的思路,一丝不苟。他私下里如饥似渴地阅读笛卡儿、霍布斯、伽利略、开普勒和波义耳的著作,并进行梳理,以形成自己的理论,提出新的问题。艾萨克·牛顿(Isaac Newton)那年二十三岁,已在剑桥大学圣三一学院度过了四年这样的双重生活——一方面是独立的思想家,一方面是顺从的学者。
在一个世纪里,圣三一学院造就了一批英国自然哲学和数学领域顶尖的思想家。仅一代人之前,它就培养了自然学家约翰·雷(John Ray)和弗朗西斯·维卢格比(Francis Wil-lughby)。再往前推几十年,文艺复兴时期伟大的思想家弗朗西斯·培根爵士(Sir Francis Bacon)在学院与世隔绝的高墙内彻底改变了科学理论。牛顿的导师艾萨克·巴罗(Isaac Barrow)也是数学和微积分领域的领军人物。圣三一学院由亨利八世于1546年创建,是剑桥最大的学院之一。学院建筑群包括一个壮观的大庭院(被视为欧洲最大的封闭庭院)、一座新建的大厅,以及一系列住宅建筑。正是在这里,牛顿与他在1663年结识的约翰·威金斯(John Wickins)同住一室。
17世纪60年代中期,圣三一学院由五十二岁的保皇党人、学者兼传教士约翰·皮尔逊(John Pearson)主持。导师和院士们如艾萨克·巴罗和詹姆斯·杜波特(James Duport)等都支持他。那时牛顿已获得了学士学位,正准备进一步深造,瘟疫的危险却进一步升级。剑桥这座城市具有一定规模,也占有重要地位,城市居民自然感到恐慌。这里最近的一次大规模暴发是在1630年,大学里有些资历的教员们仍对此记忆犹新。在初夏的某个时候,牛顿离开剑桥,回到林肯郡的伍尔斯索普庄园自己的家中。他也跻身为在英国四处搬迁、躲避瘟疫的大批男女老少中的一员。这次避难过程将是他一生中学术成果最丰富的时期。
就像吸墨纸上的一滴墨水,伦敦一旦染上瘟疫,疫病就一定会进一步蔓延开来。随着恐慌的伦敦人大批离去,疫情也随之散播,沿着公路,蜿蜒进入邻近的城镇和村庄。骇人听闻的故事比比皆是:许多人还没找到避难所就死在了荒野或农田里,而当地人害怕感染,就把暴露在外的腐烂尸体留给狗和乌鸦捕食。[138]在多塞特郡的多切斯特市外,一名染病的男子在农场的一间“破陋的小屋”里了此残生。多切斯特的人不愿处理他的尸体,就用木板封住茅舍,连人带屋扔进了深坑。[139]南安普敦城外2英里处,一个男人、一个女人和一个孩子曝尸荒野。女人大概是最后一个死的,她用手挖了一个很浅的坟墓,将丈夫埋了一半。[140]托马斯·克拉克写道:
(乡野间,)有些人被绑在柱子上,
脖子上勒着绳子,被拖进洞里;
而有些尸体则曝露在荒野,
等待着过往禽兽的处置。
这场景确有出现,如同二次死亡,
引得幸存者痛心哭泣,
因为他们害怕自己
被抓住的话,也是同样的下场。[141]
整个17世纪,公共集市日益流行,其特色是一些公共娱乐活动,诸如木偶戏、音乐和市集。伦敦方圆50英里以内的所有公共集市都被禁止,包括巴塞洛缪集市和斯陶尔布里奇集市(一年前,牛顿还在那里买过几本书)。在多佛、坎特伯雷以及重要的粮食储备镇伊普斯威奇,人们都紧闭房门。[142]哈德利镇上,一些荷兰囚犯死了,引起恐慌,但验查尸体时发现,他们并非死于瘟疫。[143]瘟疫传到了伍尔维奇造船厂,造船师克里斯托弗·佩特(Christopher Pett)表示,“担心会死不少人”。[144]在普尔市,染病的人都被转移到一家隔离病院。[145]那里没有护士照顾病人,于是一个已经被判死刑的年轻女人被劝去照看病患,她被承诺可以免于死罪。但她并未能逃脱死亡的命运。
大多数城镇都对外来人员关上了大门。伊普斯威奇只准许有健康证明的人进入。在巴斯,从疫区过来的人就算持有健康证明,也必须证明他们至少已经离开疫区二十天,所有车辆和货物都必须在城外接受一段时间的检疫。埃普索姆镇紧邻皇家学会成员逃往的地方,已紧闭城门,禁止收留投宿者。然而,尽管严防死守,瘟疫还是来了。在利奇菲尔德,一名染病的男子进入一家啤酒馆,几天后店主就死了。守卫驻扎在雅茅斯,以防止居民离开城镇,屠夫、面包师和其他食品供应者都禁止进入。这样一来,人们开始挨饿,于是枢密院命令地方官员想出办法,既不削弱防护措施,又能为居民提供食物。然而没人知道该怎么做。通过北大道等主要公路与伦敦相连的城镇尤其危险,泰晤士河沿岸的村庄也是如此。瘟疫蔓延到了柴郡,治安官关闭旅店以防止疾病传播。病毒还通过从泰晤士河来的运煤船到达了东北部的泰恩河。[146]
在这一时期,疫情最严重的地区是德比郡的一个小村庄埃亚姆。相传当地的裁缝从外地亲戚那里得到了一些图案模子和布料。一打开材料盒,他就闻到一股奇怪的潮味,于是把布料挂在火旁烘干。这个裁缝乔治·维卡斯(George Vic-ars)不久后死于瘟疫。随后,疫情席卷了整个村庄。威廉·蒙佩森(William Mompesson)等教会领袖眼看邻近的村庄也将陷入险境,于是将埃亚姆这个拥有350户居民的村庄自行封锁隔离。瘟疫在村中肆虐了足足几个月的时间,疫情解除时仅有83人幸存。
英格兰的邻居迅速采取了行动。苏格兰议会发布公告,禁止与伦敦和其他受感染的英格兰城镇进行贸易,所有从英国过来停靠在苏格兰港口的船只都必须进行检疫。商人和旅客在苏格兰边境被拦截,并进行强制隔离。任何前往苏格兰的人都必须持有健康证明。对于苏格兰人来说,瘟疫离他们并不遥远;就在1645年,爱丁堡和利斯港曾暴发瘟疫,数万人死亡。在英吉利海峡的另一边,法国拒绝任何英国的船只入境,违者处死。瘟疫却让荷兰人乐不可支,据《乌得勒支时报》(Utrecht Couranter)报道,“现在,瘟疫把英国搞得一败涂地,(我们)只要动动手指就能把他们打得落花流水”。[147]
瘟疫甚至袭击了王室宫廷,有几个边缘人物遭了殃。人们非常担心病毒追随国王和王后来到他们在索尔兹伯里的度假居所。索尔兹伯里小镇的一条街道上,西班牙大使的一名仆人死于疫病。一个女人在邻近的费舍尔顿村染病身亡,她的丈夫是王后侍从队伍里的马夫哈索尔先生;甚至连国王的蹄铁匠也因疑似患病被关了起来。查理下令向镇上的居民征税,以建立一个隔离病院。在宫廷扩建集镇期间,任何人不得进入,除非持有市长颁发的健康证书。当然,国王不用遵守这些严苛的规定。他来去自由,利用不在首都的这段时间多次乘船前往港口,监督和协调海军的准备工作,以期证明《乌得勒支时报》的评论是错误的。
同样,约克公爵也在“不停地行动”,他与妻子安妮一起北行,会见忠实的支持者,消除本土“狂热分子”、反叛者(包括清教徒)和贵格会教徒的威胁:人们担心,如果发起陆上攻击,这些公认的荷兰同情者会帮助敌人。[148]他向北方贵族发送信件,让他们务必在自己的辖区管住“危险人物”。国王给各郡治安长官写信,对瘟疫没能阻止叛乱行为表示失望,并请求他们的帮助,镇压任何潜在的叛乱。在多佛,三四百名反叛者在集会时遭到伏击,全国各地数十名“狂热分子”被捕。在迎接公爵并承诺效忠的贵族中,有古怪的泰恩河畔纽卡斯尔公爵和公爵夫人,以及威廉·卡文迪什(William Cavendish)和玛格丽特·卡文迪什(Margaret Cavendish),他们的维尔贝克庄园位于诺丁汉郡。
玛格丽特几乎完全不符合17世纪贵妇的既定形象。她自学成才,知识广博,对科学、自然哲学和传奇故事都很感兴趣,最重要的是对她自己本人兴趣浓厚。她在1656年出版的自传《我的出生、血统和人生的真实关系》(A True Relation of My Breeding,and Life)被广泛传阅,其中有这样一句引人入胜的话:“我一生的渴望唯有声名。”她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保皇派,在政权交替期间曾是查理二世的母亲亨利埃塔·玛丽亚(Henrietta Maria)的侍女。她随王室前往巴黎、鹿特丹和安特卫普,其间与内战时的保皇党将军威廉·卡文迪什相爱,并嫁给了他。威廉是剧作家约翰·德莱顿和托马斯·沙德韦尔(Thomas Shadwell)的赞助人。不同寻常的是,他鼓励妻子做学问,与顶尖的思想家会面。玛格丽特·卡文迪什早期出版的一本书的卷首插图中,甚至绘有她领导小组讨论的画面。这对夫妇确实不容小觑。
到1665年,玛格丽特已经出版了几部作品,最近的一部收集了一系列写给一个匿名“夫人”的信件,其中陈述了她对当时各种哲学话题的看法。她的一个主要论点是,人类获取的一切都是物质的。至于心灵,她指出,它并非“由破布和碎片组成,而是自然界中最纯净、最质朴、最微妙的物质”。她的作品也触及了上帝和信仰的非物质本质,她认为:
在我看来,证明灵魂的不朽与劝说无神论者皈依一样奇怪,因为世上几乎不可能存在无神论者:谁会愚钝到去否认上帝呢?因此,无论是证明上帝,还是证明灵魂不灭,都会让人对两者同时产生怀疑。[149]
然而,一条最重要的线索贯穿她写作的始终——她明确地渴望可以在学识上被平等接受。
她的这个愿望并未实现。她文章中提到的思想家都没有和她公开接触过。约翰·伊夫林与她相识多年,待她很热情,却在日记中称她“可能是个冒牌货,无论在学问、诗歌还是哲学上”。[150]她思想前卫,认为男女智力平等,区别只在于学习。[151]她还因与众不同、“非常特立独行”的风格,[152]以及抵制时尚潮流而闻名。她四处游历时,用天鹅绒装扮她的男仆,出人意表。甚至连对她有所了解的伊夫林再次见到她时仍感到震惊,认为她“行为怪异,奇装异服,言谈惊人”。[153]世人对她放肆而自信的举止既着迷又反感。几年后,她和丈夫访问伦敦时,佩皮斯描绘了她的光彩形象:
关于这名女士的一切都是传奇,她的所作所为也非常罗曼蒂克。她的男仆穿着天鹅绒衣服,而她自己穿着复古衣裙,就像人们说的那样……人们会跑来看她,仿佛她是希巴女王。[154]
与约克公爵会面时,她正在准备出版一本新书,是一部很有想法的乌托邦式的科幻小说,名为《描绘新大陆:燃烧的世界》(The Description of a New World,Called The Blazing World)。这是一个冒险故事,讲的是一个女人去北极旅行,进入了一个全新而神奇的地方,那里住着猪人、狐人和各色奇异的生物。
卡文迪什夫妇与约克公爵及其随从同行了15英里,在拉福德招待公爵一行,然后返回自己的庄园。他们约定,等公爵这行人再次到来时定会“盛情款待”。[155]
大约在同一时间,拉福德以南100多英里的地方,一个名叫托马斯·埃尔伍德的贵格会教徒正在准备一次较为低调的重聚。他接到一项任务,他之前的老师很快就要离开伦敦,他需要为老师及家人安排一个合适的住所。埃尔伍德很快在查尔方特圣吉尔找到一座乡村别墅,如一个“漂亮的盒子”,离他自己在白金汉郡的家不远。他本打算等着迎接他们到来,但不幸的是,他被捕了,被送进艾尔斯伯里监狱,大概是因为他的宗教信仰(这已不是头一回了)。尽管如此,他五十六岁的老师在年轻的红发妻子的陪伴下,于7月安全抵达查尔方特。这个老师就是约翰·弥尔顿,他的随身物品中有一部十卷的手稿,过去几年里,他一直秘密进行着这部书的写作。自1652年起,弥尔顿已失明,所以这个作品并非由弥尔顿执笔;他对不同的助手和近亲口述,每次三四十行,孜孜不倦。弥尔顿的智力没有因失明而下降;同样,他惊人的自负也丝毫未减。
弥尔顿“总是让人为他读书”,通常是熟人或熟人的儿子。[156]他早期的一个助手是诗人安德鲁·马维尔(另一名剑桥大学圣三一学院的毕业生)。1662年,埃尔伍德被共同的朋友推荐给了弥尔顿。埃尔伍德说,他每天下午都会去老师家为他读拉丁文的书——当时弥尔顿住在伦敦的杰温街。弥尔顿鼓励他的学生要“多与外国人交谈,无论在国外还是在国内”,以此来提高拉丁语水平,学习正确的发音。[157]他仅凭埃尔伍德的声调就能判断出他的学生是否明白他所读的内容,如果不明白,弥尔顿会让他停下来,解释这些话的意思。有段时间埃尔伍德病了,他们在一起的时光戛然而止,但两人关系一直很好;所以伦敦遭受疫情影响时,弥尔顿求助于埃尔伍德也就不足为奇了。
弥尔顿不但活了下来,还享有自由,这不啻为那个时代最大的奇迹之一。查理二世在处理悔过的议员时表现得相当克制。根据《豁免法》,许多克伦威尔的支持者得到了宽大处理,只有五十人受到十分严厉的处置。对那些签署了他父亲死刑执行令的人,他给予了最残酷的惩治。然而弥尔顿却是个例外,他本该在那五十人之中。尽管他不是签署者之一,他曾被克伦威尔政权聘为外文事务大臣,写了一系列慷慨激昂、广为传诵的清教徒小册子,坚定地主张处决查理一世。克伦威尔去世后,弥尔顿就失势了,他的那些小册子被公开烧毁。直到复辟的那一刻,乔治·蒙克精心策划着国王的回归,弥尔顿还在反对查理二世的复位,呼吁建立一个“自由联邦”。在他1660年春出版的小册子中,他论证道:
如果我们回归王权,不久就会后悔(我们肯定会后悔,我们开始意识到,旧时的体制正一点点侵蚀我们的良知,其根源必然是王权和神权因共同利益结为一体),我们也许会不得不为我们曾奋斗的目标重新战斗,再一次付出代价。[158]
复辟之后,弥尔顿被囚禁在伦敦塔,时间不长,多亏他之前的门生安德鲁·马维尔凭着专业的谈判技术让他获释。之后,弥尔顿就沉默了,没有发表任何东西,东躲西藏。也许正是这种沉默,加上国王的实用主义理念,救了弥尔顿一命。
埃尔伍德在艾尔斯伯里监狱短暂服刑,一经释放,就南行前去小屋看望他的老师。寒暄之后,弥尔顿让人拿出从伦敦带来的手稿。他把手稿交给埃尔伍德,让他在闲暇时读一读,读完后,可过来告诉他有什么想法。埃尔伍德拿走的文本是一部剧本的纲要,剧名为《被驱逐的亚当》(Adam Un-paradized),但后来按《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风格改编成一部史诗,名为《失乐园》(Paradise Lost)。
埃尔伍德第一次读这部作品时,就觉得它是“最优秀的诗歌”。将手稿归还时,他向弥尔顿表示,自己能被征询意见是莫大的荣幸。两人在小屋里讨论这部作品,埃尔伍德对弥尔顿说:“关于‘失乐园’您谈了很多,那您对‘得乐园’有什么见解呢?”弥尔顿没有回答,“而是沉思了一会儿”,随后便中止了他们的谈话。[159]
北海
卑尔根是挪威最重要的西风港口,城中的木质建筑环绕着狭窄的港口,形成一个封闭的马蹄形。两侧有卑尔根胡斯城堡和斯维雷斯堡的石头堡垒庇护,城外的农田与石头山相接。要到达港口,舰只必须通过星罗棋布的礁石,穿过其中一连串狭窄的自然通道。负责这次任务的是海军少将托马斯·泰德曼,他在前往卑尔根的途中已损失了几艘舰,这些舰被大风卷走了。舰队向北漂得太远了,就连他自己的战舰“复仇号”也搁浅了,费了点工夫才脱离困境。
他残缺的舰队终于抵达了港口,显然,他们得到的关于荷兰商船现身此地的消息很可靠。这些船就在眼前,已经泊锚了。强风意味着泰德曼的小舰队需要立即“向港口和城堡下的荷兰船只靠近”,以便停泊。当时,这只是一个组织进攻的问题,很可能泰德曼希望得到卑尔根的协助。他很快收到了长官克劳斯·冯·阿勒费尔特(Claus von Ahlefeldt)的讯息,“语气谦恭,表示乐于提供帮助”,却又告诉泰德曼说,不能“带乘有超过五名舰员的(战舰)入港”。[160]泰德曼解释说,他“必须确保舰只都安全进港”。消息来来往往,泰德曼安排了八艘舰排成一列,将“装有大炮的舷侧对准港口”。[161]蒙塔古充当信使,向阿勒费尔特阐明了他们此行的目的——夺取荷兰的船只。阿勒费尔特的答复让他们大吃一惊。他声称并没有接到弗雷德里克三世要与英国人合作的命令,并说他“不会侵犯港口,这有违《和平条款》”。[162]他要求英国人暂缓行动,等他接到国王的命令再说。
几天前,在数百英里之外的哥本哈根,英国特使吉尔伯特·塔尔博特爵士得知了桑威奇决定追踪驶往卑尔根的荷兰船只,他给桑威奇发了一封重要信件,解释目前的外交局势。但这封信没能及时送到桑威奇手上,更别说泰德曼的小舰队了。他在信中警告说:
如果他(卑尔根长官)看起来对你的行动非常不满,并对你大发牢骚,不必感到奇怪,这仅仅是为了取悦荷兰人做的秀,并向外界为自己开脱罢了。[163]
与此同时,丹麦国王弗雷德里克三世向卑尔根长官发送了一封类似的信件,说已和英国达成协议。他让长官允许英国人袭击,但未提及会提供积极支持。对弗雷德里克三世来说,保持表面上的中立更划算,英国取胜的话可分得一半的利益,而不用冒险与荷兰开战。但这封信也未能及时送达。
泰德曼的小舰队陷入了困境。补给严重不足,行动延误会严重影响士兵的健康状况和士气。还有人怀疑他们被愚弄了。克利福德和蒙塔古继续与阿勒费尔特谈判,据说蒙塔古甚至向他许诺了丰厚的报酬,[164]包括嘉德勋章,但阿勒费尔特不为所动。蒙塔古改变了策略,转而对他进行威胁,警告他“最好小心保全自己为妙”。[165]
几个小时过去了,信息来来回回地传递,但什么都没有发生。英国人抵达卑尔根时,荷兰人正在舰长皮特·德·比特尔(Pieter de Bitter)的带领下享受着上岸假期,显然在卑尔根过得很惬意。丹麦人食言了吗?夜幕降临在这座挪威的海港,荷兰人似乎趁着夜色,在城镇周围建造临时堡垒,并将大炮运送到城堡中去,包括罗切斯特在内的不少人都目睹了这一幕。最明显的是,他们还将吨位最重的舰只排成一列,横跨港口,配有大炮的舷侧一律对外。泰德曼感到其中有诈。8月2日太阳升起时,他让小舰队排成半月形,大炮一致瞄准荷兰船只和城镇,其中有“审慎玛丽号”“布莱达号”“远见号”“本迪什号”“快乐回归号”“蓝宝石号”和“彭布罗克号”。包括“复仇号”在内的其余舰只则对着海岸的炮台。
年轻的水手们悄悄从英国舰队下层甲板的储藏室里把火药安全地运了出来,为战斗做好准备。清晨五点,英方的战鼓敲响,战士们做了祈祷,泰德曼下令舰队“发射战斗炮火”。士兵把新火药装入炮管,用布或旧绳将之固定。将沉重的炮架推向舷墙,确保炮管能够伸出舰侧的炮口。大炮即刻向敌舰展开轰击。
荷兰舰船以密集的炮击回应。事后泰德曼解释说,堡垒和要塞那处的人对他开火后,他才对卑尔根镇开的火。丹麦人也借口说,英国的炮弹先击中了堡垒,造成四人死亡,他们才开始反击。在激烈的战斗中,也许双方都认为自己的说法才是正确的。不管怎么说,卑尔根还是把矛头指向了英国。
荷兰大炮连续猛击英方舰只,使其上层甲板严重受创。每一次炮弹落在舰上,都掀起一阵尘土和碎片,如风暴穿透人体,让靠近的人窒息。“审慎玛丽号”的舰长托马斯·哈沃德(Thomas Haward)、“布莱达号”的舰长托马斯·西尔(Thomas Seale)、“根西号”的舰长约翰·乌特伯(John Ut-ber),以及其他三名舰长全部阵亡。英方处于逆风向,所以战斗中的硝烟向他们滚滚袭来。在这样的条件下,使用火攻舰如同自掘坟墓。罗切斯特后来慷慨激昂地指出:“不然,我们会完美地完成任务。”英方护卫舰的第一层和第二层甲板上,士兵们迅速把火药和炮弹塞进大炮,向敌人发起猛攻。在敌方的炮火中,这项本就困难的任务变得更为艰辛。虽然他们距离荷兰舰只仅有一百米,却一直没能击中目标。战斗就这样持续了三个小时。
“复仇号”上,罗切斯特和战友们遭到了来自挪威要塞和荷兰军舰的猛烈炮击。尽管他们很卖力,但“城堡没有被(击)垮”,得益于坚固石墙的防护,它几乎毫发无伤。罗切斯特的朋友温德姆开始颤抖。他抖得越来越厉害,蒙塔古冲过去帮他,搂住这个仅十几岁的少年,让他站直。炮火在他们周遭接连不断。罗切斯特听到一声爆炸,一颗炮弹击中了这两个人,温德姆当场死亡,蒙塔古的腹部被撕裂。英国人割断锚索,任战舰随海浪漂流。仅三个小时,英方就死了五百人,六名舰长阵亡。蒙塔古过了六个小时才死去,过程缓慢而痛苦。据说,他全程精神状态良好。那天,大部分阵亡的人都沉入水中,将尸身祭献于无止无尽的北海,但蒙塔古和温德姆除外。他们血迹斑斑的尸体被存放在空的炮管里,准备被带回英国埋葬。泰德曼的小舰队土崩瓦解,随后便撤退了。罗切斯特在第二天写给母亲的信中说:“我们把整个镇子打得稀巴烂,没有损失一艘舰。”
在海上航行数周后,这次损失极其惨重。糟糕的计划,不可靠的情报,舰员忍饥挨饿、报酬微薄,许多人丧命。罗切斯特尽其余生,也没等到温德姆和蒙塔古的灵魂回来告诉他,是否还有另一个世界。
英国
卑尔根战役的余波对桑威奇伯爵来说是毁灭性的,但其影响并非立竿见影。英国人以为会赢得这场战争。在他们看来,他们有更好的战舰、更好的指挥官以及最近一次在海上击败荷兰的战绩,所以克利福德带回的战败消息使人们产生了巨大的心理阴影。事实上,他们处于巨大的劣势。首先,英国没有用于战争的长期资金——他们以为军事费用可由击败荷兰的战利品来抵扣——而且,与敌人不同的是,英国人在打造新军舰上投资很少。卑尔根战役的失败严重挫伤了士气,约克公爵的秘书威廉·考文垂在给阿灵顿的一封信中写道,对他来说,这次不幸的任务最严重的“后果”是,“剩余舰队的信心被击垮了,特别是他们大多数都未参战”。[166]在荷兰共和国,人们铸造硬币以庆祝胜利。这次行动也将丹麦人和荷兰人绑在了一起。
精明的桑威奇很快意识到,自己的地位岌岌可危,于是他利用夏天剩余的时间来挽救这场灾难。8月下旬,他招募了两百五十名新兵,并充实了舰队的补给。[167]9月初,他捕获了两艘在风暴中脱离船队的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船只。几天后,他又俘获了八艘荷兰商船和四艘军舰。这是一个巨大的转机。依然留在舰队的罗切斯特——表现得“勇敢”而“勤勉”[168]——被派去向国王汇报成果。在战役开始时,英方希望用缴获的荷兰商船来“支付十二个月战争的火药和子弹费用”[169],预计收益将达到20万英镑,有助于缓解财政压力。[170]佩皮斯在日记中写道:
舰队屈辱地返程,并要求一大笔钱(这钱是拿不到的)来遣散许多染上瘟疫的人,或填补舰上更大的开销。就他们目前的所作所为来看,议会肯定不会给钱,国家也拿不出钱来。如果给了钱,在瘟疫时期,状况如此糟糕,整个国家一定会毁灭……[171]
事实上,对于普通海员来说,海军干瘪的钱包已经使他们陷入绝境。上岸后,海员们用本就可怜的工资来抵债,他们身无分文,健康状况堪忧。在海滨城市朴次茅斯,许多领不到工资的海员“被房东扫地出门”,“像狗一样地”死去。海军收容了许多人,但也没钱发给他们。托马斯·米德尔顿(Thomas Middleton)在朴次茅斯给塞缪尔·佩皮斯写了一封慷慨激昂的信,信中写道:“只要付这些可怜的人伙食费,两百人就可以干原先三百人的活。”[172]至于那些以票代薪的人,他们可以选择在酒馆或放债人那里以极低的价格兑换。[173]桑威奇自己的部队成员从卑尔根返回时就已经营养不良了。[174]除此之外,英国还需要为数千名受伤的海员提供食宿,并给数百名荷兰俘虏腾出地方,“其中一些病得很重”。9月中旬,伊夫林告诉乔治·蒙克,“除非我们立即拿到1万英镑”,否则那些他管辖的战俘“都会饿死”。[175]同年又过了些时候,佩皮斯记录了一起可怕的事件,有人袭击了格林尼治的海军委员会:“一百名海员在那里待了一下午,在下面骂骂咧咧……他们打碎玻璃窗,发誓说下周二要拆了这所房子。”[176]
由于瘟疫影响到全国许多地区,临时岗位变得稀少,贸易也无法正常进行。正如彼得伯勒伯爵(the Earl of Peterborough)所说,“瘟疫无限期干扰了整个国家的贸易”。国家急需用钱。
在给桑威奇的信中,考文垂和蒙克都敦促他保管好赢得的珍贵货物,以免遭到抢劫和盗用。蒙克已经与东印度公司达成协议,答应借给海军财政部5000英镑,作为预期战利品的一部分。然而,蒙克和考文垂很快就发现,在那些货物被依法定为战利品之前,桑威奇手下的许多军官已经拿走了一部分。桑威奇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主要是为了笼络他的海军将领们。战利品一被公开,这些人可能就分不到多少了,许多人认为那是他们应得的奖赏。并且,只有拉拢他们,桑威奇才更有可能获得1666年军事行动的指挥权。然而这是一个灾难性的判断失误,而且,作为最资深(约克公爵除外)、最可靠的海军成员,桑威奇完全有罪。他收到了查理国王签署有较早日期的委任书,但这不足以堵住政治火山的爆发。许多与他一起参与此次行动的军官都拒绝分取战利品,而约克公爵的秘书威廉·考文垂嗅到了血腥味,便精心策划让桑威奇垮台。
他认为,在那些货物正式成为战利品之前就私自拿走,应被定为重罪,并且,他极力主张对桑威奇进行弹劾。这种敌意还包含了另外一个层面:桑威奇是国王的人,考文垂对他的不满中还夹杂着他的主人约克公爵的怨恨,在洛斯托夫特战役后,约克公爵被解除了海军现役职责。有迹象表明,热爱大海的查理国王曾嫉妒他的弟弟积极领导国家防务的能力。对许多人来说,公爵被解除现役的原因并不使人信服。国王最信任的顾问、大法官克拉伦登伯爵认为,很明显,朝臣们千方百计地让詹姆斯确信,自己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
这对王室兄弟有许多共同的经历,但他们的性格却截然不同。查理思维敏捷,情商高,是个彻头彻尾的实用主义者。他有一种不可思议的识人能力,知道如何取悦他人,把握恰当的时机,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但这种令人愉悦的魅力掩盖了他天生狡猾的性格;而詹姆斯并不像他的兄长那样智力超群、世故老练,他的心思和原则全都写在脸上,常常意气用事。他遗传了他父亲的固执,而这一特点会在他今后的生活中造成毁灭性的后果。抛开这些差异,他们对于继续对荷兰的战争有着同样坚定的决心,即使这样会削弱国家的财政。
国王的钱袋空空如也,召集议会就成了头等大事。9月初,宫廷从索尔兹伯里迁到了牛津。牛津是保皇派聚集的城市,在17世纪40年代的内战中充当了保皇党的大本营,城内的建筑奢侈浮华,足以供王室居住。9月底和10月初,国会议员和贵族们从全国各地来到牛津。詹姆斯把妻子留在了约克,陪伴她的是御马官亨利·西德尼爵士(Sir Henry Sidney)——“他那个时代最英俊的年轻人”[177]——詹姆斯命令他务必好好照看她,就像自己在的时候一样(西德尼和公爵夫人有点过于认真地遵循了公爵的指示)。
公爵到达牛津后,王室兄弟之间的竞争加剧了,但这与国家事务没有多大关系。弗朗西丝·斯图尔特(Frances Stew-art)于1662年来宫廷,担任布拉干萨的凯瑟琳的侍女,查理立刻就迷上了她。弗朗西丝美丽、天真而轻佻。查理的妹妹说她是“世上最漂亮的女孩,最适合装点宫廷的门面”。塞缪尔·佩皮斯认为她是“我一生中见过的最美的女人”。[178]但她却在这复辟王朝中保有最稀奇的东西:贞洁。1663年王后病重,人们在悄声谈论国王的下一任妻子时,都把目光投向了这个天真无邪的少女。或许她觉得步卡斯梅恩夫人的后尘没什么好处,或许她对王后太忠诚了,又或许她只是不喜欢国王。不管是什么原因,弗朗西丝不愿成为国王的情妇。查理感受到了单恋的痛苦(也可能只是未能满足的情欲)。他写了一首关于她的诗,开头是:
我在一片荫翳的古老树林中度过所有的时光,
但见不到我的爱人,我每日如行尸走肉,
我望向每一条路径,我的菲利斯已远逝,
想起我们独处的日子,我叹息:
哦,那时,只在那时,我想地狱
就犹如爱情,爱得过深便入地狱。[179]
相思成疾的国王每天在吃早餐前都会去她的房间——也会去怀孕的情妇卡斯梅恩夫人那里。公爵自然也注意到了弗朗西丝的美貌,他也成了这名年轻女子的爱慕者。威廉·考文垂向塞缪尔·佩皮斯透露了一个“惊天秘密”,说:“国王和公爵之间的矛盾很深,宫廷上下对他们的滥情一片哗然。约克公爵深深地爱着斯图尔特夫人。”[180]至于弗朗西丝,她似乎对公爵更不感兴趣。
王室的风流韵事逐渐发酵之时,议会于10月9日在牛津的基督教堂学院大厅举行。会议由查理主持,克拉伦登负责传达细节。其间国王请求议会给予战争更多的资金,承认这场战争“确实比我预想的更费钱”,并向他的臣民保证,“他们(荷兰人)根本没有优势,除了瘟疫的持续蔓延”。他还警告说,“希望这援助不仅可以继续这场战争,并且能让你我可以与更强大的邻国(法国)抗衡,如果法国更乐意与荷兰结交的话”。[181]
为了煽动反荷兰情绪,克拉伦登对议会说,荷兰人的“方言太粗鲁了,只有他们的语言里才会有,只有荷兰人才会说,是时候去改造他们了”,接着又说,“我国那些声名狼藉的变节者”已加入了荷兰人的行列,“放肆地踏上敌人的舰船”。[182]自战争爆发以来,确实有一些英国臣民投靠了荷兰。少数人是出于意识形态的原因,多数人则为金钱所驱使。简而言之就是,荷兰人付了钱。议会投票决定,再拨出125万英镑用于战争。议会议长宣称:“正如河流自然会注入大海,我们希望国家的金银财富都汇入这片海洋,以维护国王陛下在四海之内的正当主权。”
此时桑威奇伯爵已从海上归来,到了牛津。那个月初,他离开了船队前往牛津,试图平息宫中对他日益增长的厌恶感。然而对他而言,不凑巧的是,荷兰共和国的政治领袖大议长约翰·德·威特(Johan de Witt)决定让他的舰队准备进攻,舰只停靠在东南海岸。荷兰人发现英国舰队的状态如此糟糕,便撤回了。不过,趁桑威奇不在,乔治·蒙克正好抓住这次机会大肆调动舰队,以彰显自己的权威。如此,蒙克领导1666年战役的概率就变大了。
动荡持续着。与此同时,蒙塔古的遗体被运回了北安普敦郡的家,埋葬在当地的教堂。他的死讯在惨败发生几周后传到了宫廷,并在《情报者》上公布。讣告中写道:“在死难者中,爱德华·蒙塔古先生是一位勇敢可敬的绅士,他和温德姆先生一同为君主和国家光荣牺牲。”[183]然而,他很少被人哀悼。的确如此,彼得伯勒伯爵回忆说:“在我的一生中,我从没见过死亡对谁如此有用。”[184]
在英吉利海峡的另一边,法国的威胁日益增长。这一年里,英法关系急剧恶化。严格说来,1662年的一项条约规定,如果英荷之间爆发战争,法国有义务援助荷兰共和国,但国王路易十四一直都不愿遵守该条款,直到1665年秋天。虽然对法国人的仇恨在英国人心中根深蒂固,但路易的宫廷中有许多人(尤其是他弟弟的妻子亨利埃塔)基于原则,反对与英国开战。英国由一个看似优柔寡断的君主统治,而荷兰共和国却是——如名所示——一个共和国。另外,法国海军其实尚处于初建阶段,尽管正飞速扩充和壮大,但仍然不是英国的对手。
西班牙国王菲利普四世于9月去世,奇怪的是,这倒把法国拉了进来。菲利普四世的继承人只有四岁,身体虚弱、畸形,是近亲婚配所生。因此,谁来继承西班牙王位对路易十四来说至关重要。路易希望荷兰默许他扩张到西属尼德兰的计划,而他清楚,只要履行条约就可以达成。随着西班牙势力的削弱,英国的中立就不再必要。此外,越来越明显的是,英国对欧洲的现状构成了威胁。如果查理成功推翻荷兰议会,那么奥兰治家族——有年轻有为的威廉王子在——将掌握权力的平衡,有效地将荷兰共和国变成英国的受保护国。这样就讨好了德国王子们;瑞典被诱以金钱;丹麦则面临压力。
英国人已经俘获了几艘载有荷兰货物的法国商船,并坚持要求外国船只沿英吉利海峡航行时向其致敬。对此,路易命令在地中海航行的所有船舶向法国船只致礼,承认法国对这片海域的掌控权。这导致了英法之间的一系列冲突。路易的海军上将波弗特公爵(the Duke of Beaufort)俘获了两艘英国船只,把它们带到土伦。到12月,法国即将对英宣战这件事已尽人皆知。
迫在眉睫的战争的威胁并没有阻止宫廷的奢靡生活。罗伯特·哈利爵士(Sir Robert Harley)的法国仆人丹尼斯·德·雷帕斯(Denis de Repas)当时随王室去了牛津,他描述宫廷整日欢宴纵乐、奢侈无度时写道:“这里没有瘟疫,只有欢爱的肆虐;不谈别的,只论芭蕾、舞蹈和华丽服饰;竞争也只是关于谁的外貌更胜一筹……人们只为‘我是你的’而斗嘴……”他甚至听到一个传言,说要发布一个公告,谁不高兴就要受罚,戴上木枷示众。[185]对于久居牛津的居民来说,宫廷里的人“无礼、粗鄙、荒淫”。[186]错综复杂的钩心斗角、风流韵事、暗箭伤人、酗酒豪饮、政治勾当,凡此种种让牛津居民能给予这些上层人士的一点点尊重也消耗殆尽了。据吉尔伯特·伯内特(Gilbert Burnet)说,罗切斯特伯爵从海上归来后,“(陷)入了那帮荒淫无度的人群中”,释放了他性格中“放纵”的一面。这“群”人里可能也有像白金汉公爵和巴克赫斯特勋爵这样天性活泼又有点滑稽的人。当时的学者安东尼·伍德(Anthony Wood)对牛津宫廷的种种行为和陋习提出了一个有趣的见解:
职位高的朝臣高高在上,傲慢无礼,视学者如书呆子或教书匠……他们衣冠楚楚,但实际上非常恶毒、残忍,临走前,把自己的排泄物弄得到处都是,烟囱里,书房里,煤房里,地窖里。[187]
凯瑟琳王后和宫廷侍女们一直待在大学城里,侍女中有国王的情妇卡斯梅恩夫人。当时城里散发着大量言辞恶毒的传单,她成了焦点人物。这些传单似乎是大学学者们搞的,最让人热衷的是一张用英文和拉丁文书写的字条,这张字条就钉在卡斯梅恩夫人的房门上,上面写着:“她之所以没被浸水里/是因为上她的人是恺撒。”[188](这不是卡斯梅恩夫人第一次被比作妓女,当然也不是最后一次。)
即使在远离宫廷的地方,达官贵人也一直丑闻缠身。这对王室兄弟似乎很擅长把年轻英俊的男子送到自己的妻子面前。爱德华·蒙塔古死后,凯瑟琳王后让他的弟弟拉尔夫(Ralph)继任御马官,他是个“自尊自爱”的人。显然,这位虔诚的王后是不会背叛婚姻的,但有报道却确凿无疑,“(约克)公爵夫人自己……爱上了她的新任御马官,一个叫哈里·西德尼(Harry Sidney)的人”。西德尼同时也是约克公爵的内廷侍臣,传说他“非常爱她”,所以“公爵好几天都没有和公爵夫人说话”。直到1月中旬,西德尼被逐出宫廷,两人之间的嫌隙才得以消除。[189]
当然,这些都不太为人所知。当宫廷迁至牛津时,官方新闻通过新的喉舌《牛津公报》发布。公报由亨利·麦迪曼(Henry Muddiman)创办,取代了《情报者》成为英国官方报纸(尽管直到1670年才真正使用“报纸”一词)。那时,新闻期刊是社会上相对较新的东西,在17世纪初起源于斯特拉斯堡,随后的几十年中逐渐在欧洲流行,阿姆斯特丹、巴塞尔、巴黎和安特卫普均有此类出版物。英国最早的定期刊行的报纸始于1621年,是一份荷兰报纸的翻译版。这份早期的报纸为读者提供关于国外事件的信息,但里面没有英国国内的新闻。
英国新闻消费在内战期间实现了突破,当时对信息的需求有了新的迫切性。政府的垮台催生了出版自由,反对派创办出版物以集结力量,并迅速传递消息。在克伦威尔统治期间,管制又严格起来,但人们对国内新闻的胃口已经被吊了起来,不会消失。《牛津公报》每周一和周四印发,里面的信息来源于麦迪曼和他的线人网络收集的情报,最著名的线人是国务大臣办公室的约瑟夫·威廉姆森。人们既可以订阅,也可以当日购买。它看上去就是一张纸,双面印刷,报纸样式的排版,里面有来自不列颠群岛不同地区的事件,以及驻外大使和记者的报道。第一版发行于1665年11月7日,佩皮斯认为它“非常漂亮,新闻充实,没有愚蠢的花边新闻”。[190]
随着1666年日益临近,其他地区出现了变化的迹象。皇家学会自成立以来,就一直利用整个欧洲大陆的知识网络,并由学会秘书亨利·奥尔登堡整理和传播。瘟疫肆虐期间,学会一直很忙碌:做实验来改进船只,并与科学家和思想家们定期通信。1665年12月8日,奥尔登堡给在阿姆斯特丹的犹太哲学家斯宾诺莎写了一封信,好奇地询问在英国熟人中流传的一则传言:
这里的每个人都在谈论一则报道,说犹太人在离散了两千多年之后,即将返回他们的国家。虽然很少有人相信,但许多人希望这是真的。请告诉我你听到的消息,以及对此的看法。于我而言,除非这消息被君士坦丁堡可靠的来源证实,因为那是直接相关的地方,否则我是不会相信的。我很想知道阿姆斯特丹的犹太人对此的说法,以及这种重要消息对他们产生的影响。如果消息是真的,这无疑会预示着世界末日的来临。
相信我是你最热忱的,亨利·奥尔登堡[191]
【注释】
[1] Edward Chamberlayne,The second part of the present state of England together with divers reflections upon the antient state thereof(London,1671),p.206.
[2] John Milton,Paradise Lost,Book ix,lines 446.
[3] Thomas Ellwood,The history of the life of Thomas Ellwood: or an account of his birth,education,&c.with divers Observations on his Life and Manners when a Youth: and how he came to be convinced of the Truth; with his many Sufferings and Services for the same.- Also several other remarkable Passages and Occurrences.Written by his own hand.To which is added A supplement,by J.W.(London,1791),p.147.
[4] John Gay,Trivia(London,1716),p.13.
[5] John Evelyn,Fumifugium(London,1661),Preface.
[6] Samuel Pepys,The Diary of Samuel Pepys,Vols i-ix,ed.Robert Latham and William Matthews(HarperCollins,1995),henceforth cited as Pepys's Diary,1 February 1666.
[7] John Graunt,Natural and Political Observations Mentioned in a following Index,and made upon the Bills of Mortality(London,1676),p.55.
[8] John Evelyn,The Diary of John Evelyn,Vol.ii,ed.William Bray(M.Walter Dunne,1901),henceforth cited as Evelyn's Diary,9 Feb-ruary1665; 1 July 1664.
[9] Pepys's Diary,20 February 1665.
[10] Ibid.,11 August 1665.
[11] 贵格会,又名教友派、公谊会,兴起于17世纪中期的英国及其美洲殖民地。
[12] ‘Charles II-volume 114: March 1-15,1665’,in Mary Anne Everett Green(ed.),Calendar of State Papers Domestic: Charles II,1664-5(London,1864),p.244; Abbot Emerson Smith‘The Transportation of Convicts to the American Colonies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39.2(1934): 232-49.
[13] Intelligencer Published for the Satisfaction and Information of the People(London),Monday,13 March 1665,Issue 20.
[14] Ibid.
[15] John Aubrey,Letters Written by Several Eminent Persons in the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ies,Vol.2,Part 2(1813),p.623.
[16] Robert Hubert,A catalogue of many natural rarities with great in-dustry,cost,and thirty years travel in foraign countries / collected by Robert Hubert,alias Forges(London,1665); Intelligencer,Monday,13 March 1665,Issue 20.
[17] Intelligencer,Monday,13 March 1665,Issue 20.
[18] 这个数据基于复辟时期的统计学家约翰·格朗特(John Graunt)的估算。
[19] William Taswell,‘Autobiography and Anecdotes by William Taswell,D.D.,sometime Rector of Newington,Surrey,Rector of Bermondsey and previously Student of Christ Church,Oxford.A.D.1651-1682’,Camden Old Series,55(1853),pp.9-10.
[20] Graunt,Natural and Political Observations,p.60.
[21] Pepys's Diary,13 May 1666.
[22] 塞缪尔·佩皮斯在1664年1月9日的日记中写道,伊丽莎白·豪利告诉他,“米切尔太太在婚前有一个女儿,现在快三十岁了,我简直不敢相信”。
[23] Kate Loveman,Samuel Pepys and His Books: Reading,Newsgath-ering,and Sociability,1660-1703(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5),p.170.
[24] Intelligencer,Monday,13 March 1665,Issue 20.
[25] Ibid.,Monday,6 March 1665,Issue 19.
[26] 匿名,The English and Dutch affairs Displayed to the Life both in matters of warr,state,and merchandize,how far the English engaged in their defence against the most potent monarchy of Spain,and how ill the Dutch have since requited the English for their extraordinary favours,not onely in the time of Queen Elizabeth their protector and defendress,but also in the time of King James,by their bloody mas-sacree of them at Amboyna,their ingratitude to King Charles the First of glorious memory,and the true state of affairs as they now stand in the reign of our royal soveraign King Charles the Second / by a true lover and asserter of his countries honour(London: Printed by Thomas Mabb for Edward Thomas,1664).
[27] Poor Robins character of a Dutch-man(London,1672),转自Steve Pincus‘,From butterboxes to wooden shoes: the shift in English popular sentiment from anti-Dutch to anti-French in the 1670s’,Historical Journal,38(1995),p.337.
[28] 匿名,The Dutch Boare Dissected,or a Description of Hogg-Land.A Dutch man is a Lusty,Fat,two Legged Cheese-Worm: A Creature,that is so addicted to Eating Butter,Drinking fat Drink,and sliding,that all the World knows him for a slippery Fellow,an Hollander is not an High-lander,but a Low-lander; for he loves to be down in the dirt,and boar-like,to wallow therein(London,1665).
[29] 更多信息见Helmer J.Helmers,The Royalist Republic(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5),p.203.
[30] Nederlandtsche nyp-tang(1652),转自ibid.,p.204.
[31] Steve Pincus‘,Popery,Trade and Universal Monarchy: The Ideo-logical Context of the Outbreak of the Second Anglo-Dutch War’,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Vol.107,No.422(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2),pp.5-9.
[32] 更多关于霍姆斯使用弹簧式摆钟的细节,参见:5 March,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1665,Vol.1,Nos 1-22,pp.13-5.关于霍姆斯个性的引文参见Pepys's Diary,1 September 1661.
[33] March 1665,‘Venice: March 1665’,in Allen B.Hinds(ed.),Calendar of State Papers Relating to English Affairs in the Archives of Venice,Vol.34,1664-1666(London,1933),pp.81-93.
[34] 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Vol.1,pp.190-1.
[35] ‘Charles II - volume 113: February 19-28,1665’,in Everett Green(ed.),Calendar of State Papers,1664-5,p.216.
[36] 这项法案由理查德·霍奇金森印制。1664年,他住在泰晤士大街贝纳德城堡对面。
[37] 查尔斯·特罗洛普基于该地点的考古证据形成这一理论。从海里共找到五门大炮,其中三门装满弹药筒,一门装了一半,另一门是没装。特罗洛普认为是在装填第四门大炮弹药筒时发生了爆炸。舰的残骸在装有火药的货舱上方裂开。
[38] State Papers 29/114 f.147.
[39] Pepys's Diary,8 March 1665.
[40] State Papers 29/114 f.132.
[41] State Papers 29/114 f.147.
[42] Pepys's Diary,8 March 1665.
[43] Ibid.
[44] Evelyn's Diary,9 March 1665.
[45] State Papers 29/114 f.155.
[46] Pepys's Diary,11 March 1665.
[47] Evelyn's Diary,16 May 1665.
[48] Thomas Greene,A Lamentation Taken up for London(London,1665),p.2.
[49] Roy Booth(ed.),The Collected Poems of John Donne(Wordsworth Poetry Library,2002),p.27.
[50] 对近代早期的瘟疫的生物性质还没形成一致的共识。DNA证据证实,17世纪中期新教堂墓地“墓葬坑”中埋葬的骸骨上存在鼠疫杆菌。这些骸骨是在2015—2016年横贯铁路公司在 利物浦街站的挖掘过程中找到的,在此期间首次将该杆菌以科 学的方式放置在伦敦,为整个欧洲的DNA证据增添了一笔。尽管如此,一些人认为,17世纪鼠疫的症状与现代淋巴腺鼠疫并不相符。有一些其他理论,认为是埃博拉(Susan Scott和Christopher Duncan,2001)、炭疽(Graham Twigg,1984;John Findlay D.Shrewsbury,1970)、斑疹伤寒或另一种未知且已灭 绝 的疾 病( Samuel K.Cohn,2002)。 研究还在进行中,但作者赞同主流观点,即1665年的大瘟疫 是一种有毒菌株的淋巴腺鼠疫,以寄宿鼠类身上的跳蚤为主要载体。作者认为,现代鼠疫和近代早期鼠疫的症状有很强的相似性。感染模式表明,存在人与人之间的传播。这是否是通过肺炎性鼠疫(证据表明,这也是存在的),还是另有载体,有待最终证明。最近的研究表明,人体虱子可以有效地传播疾病,并可能与人体跳蚤一起在近代早期的流行病中发 挥了 作用 。参见:S.Haensch,R.Bianucci,M.Signoli et al.,‘Distinct Clones of Yersinia pestis Caused the Black Death’,PLOS Pathogens,7 October 2010; S.Ayyadurai,F.Sebbane,D.Raoult,M.Drancourt,‘Body Lice,Yersinia pestis Orientalis,and Black Death’,Emerging Infectious Diseases,2010;16(5): 892-3; and Lars Wall-e,‘Medieval and Modern Bubonic Plague: Some Clinical Continuities’,Medical History,Supplement 27(2008): 59-73.For a lively overview see John Kelly,The Great Mortality: An Intimate History of the Black Death,the Most Devastating Plague of All Time(HarperCollins,2 0 0 6).
[51] 生物学的详情参见:B.Joseph Hinnebusch,Amy E.Rudolph,Peter Cherepanov et al.,‘Role of Yersinia Murine Toxin in Survival of Yersinia Pestis in the Midgut of the Flea Vector’,in Science(26 April 2002),Vol.296,Issue 5568,pp.733-5.
[52] Nathaniel Hodges,Loimologia or,an Historical Account of the Plague in London in 1665: With precautionary Directions against the like Contagion(London,1721),p.3.
[53] 参见J.A.I.Champion(ed.),‘London's Dreaded Visitation: The Social Geography of the Great Plague in 1665’,Historical Geography Research Series(1995).
[54] Hodges,Loimologia,p.3.
[55] 1623年,据记载这个地区有897座房屋,到17世纪末,房屋数量增加到2000座。
[56] Hodges,Loimologia,p.3.
[57] Pepys's Diary,8 May 1663.
[58] George W.Stone,William Van Lennep,Emmett L.Avery,Arthur H.Scouten,Charles B.Hogan(eds),The London Stage,Part I: 1660-1700(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1965),p.87.
[59] February 1667,‘Charles II - volume 191: February 6-14,1667’,in Mary Anne Everett Green(ed.),Calendar of State Papers Domestic: Charles II,1666-7(London,1864),p.502.
[60] 这名受害者叫“玛格丽特,是约翰·庞特医生的女儿”;引自: A.Lloyd Moote and Dorothy C Moote,The Great Plague: The Story of London's Most Deadly Year(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2004),p.52.
[61] Intelligencer,Monday,17 April 1665,Issue 29.
[62] Case discussed at court at Whitehall in the presence of Charles II,28 April 1665,1665 Jan.2-1666 Apr.27,Vol.5,Privy Council Register 2/58.
[63] Ibid.
[64] Pepys's Diary,28 April 1665.
[65] Ibid.,30 April 1665.
[66] April 1665.‘Charles II - volume 117: April 1-11,1665’,in Everett Green(ed.),Calendar of State Papers 1664-5,pp.102-3.
[67] 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Vol.1,p.94.
[68] Robert Hooke,Micrographia: or Some Physiological Descriptions of Minute Bodies Made by Magnifying Glasses with Observations and Inquiries Thereupon(London,1665),Schem.34.
[69] ‘An Account of Micrographia,or the Philosophical Descriptions of Minute Bodies,Made by Magnifying Glasses’,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Vol.1,pp.27-32.
[70] Pepys's Diary,21 January 1665.
[71] Graunt,Natural and Political Observations,Preface.
[72] Pepys's Diary,15 May 1665.
[73] Ibid.,3 June 1665.
[74] John Dryden,An Essay of Dramatick Poesie(London,1668),p.1.
[75] Evelyn's Diary,3 June 1665.
[76] George DeForest Lord(ed.),Anthology of Poems of State Affairs: Augustan Satirical Verse 1660-1714(Yale University Press,1975),p.38.
[77] Evelyn's Diary,8 June 1665.
[78] Pepys's Diary,3 June 1665.
[79] Intelligencer,Monday,12 June 1665,Issue 45.
[80] Taswell,‘Autobiography’,pp.9-10.
[81] Pepys's Diary,22 January 1666.
[82] Thomas Vincent,God's Terrible Voice in the City(London,1667),p.35.
[83] J.R.Wardale,Clare College Letters and Documents(Macmillan and Bowes,1903),p.51.
[84] 关于新教堂墓地的描述参见Vanessa Harding‘,Burial of the Plague Dead in Early Modern London’,in J.A.I.Champion(ed.),Epidemic Disease in London,Centre for Metropolitan History Working Papers Series,No.1,1993,pp.53-64.参见Champion,‘London's Dreaded Visitation’,pp.56-7.
[85] 拉姆齐一家比较有意思,因为传统认为玛丽是该地区第一个感染鼠疫的病患。尽管记录中并未写明她姐姐的死因,但在这段时期死于其他原因而非鼠疫,这种偶然性较小。
[86] London Metropolitan Archives,Bridewell Chapel,Bishops-tran-scripts of baptisms,marriages and burials,1665-1666,DL/A/E/192/ MS10952A.
[87] 玛丽·戈弗雷的父亲有可能是托马斯·戈弗雷,根据炉膛税的记录,他住在“波特斯巷”,离新教堂墓地很近。科里普门外的圣吉尔教区记录两次提到“玛丽·戈弗雷”的葬礼:第一次在1665年8月31日;第二次在1885年9月2日。这可能是在记录死亡人员时的疏漏,也可能是不同寻常的巧合。两次都提到父亲为托马斯·戈弗雷,前一条记录中显示他为农夫。Parish registers: London Metropolitan Archives,St Giles Cripplegate,Composite register,1663-1667,P69/GIS/A/002/MS06419,Item 006 and Hearth Tax records:‘Hearth Tax: City of London 1666,St Giles(without) Cripplegate,Golding Lane West’,in London Hearth Tax: City of London and Middlesex,1666(Centre for Metropolitan History,2011).
[88] 葬礼登记参见London Metropolitan Archives,St Olave Hart Street,Bishops-transcripts of baptisms,marriages and burials,1665-1666,P69/OLA1/A/002/MS28869,p.30;炉膛税文献参见:‘Hearth Tax:City of London 1666,St Olave Hart Street’,in London Hearth Tax.
[89] Cynthia Wall(ed.),Daniel Defoe: A Journal of a Plague Year,(Penguin,2003),p.58.
[90] Neil Cummins,Morgan Kelly and CormacóGr-da,‘Living standards and plague in London,1560-1665’,CAGE Online Working Paper Series(Department of Economics,University of Warwick,2013),pp.9-10.
[91] Graunt,Natural and Political Observations,p.13.
[92] John Bell,London's remembrancer,or,A true accompt of every par-ticular weeks christnings and mortality in all the years of pestilence within the cognizance of the bills of mortality,being xviii years(London,1665),pp.2-3.
[93] August 1665,‘Charles II - volume 129: August 11-22,1665’,in Everett Green(ed.),Calendar of State Papers 1664-5,pp.516-7.
[94] ‘Venice: August 1665’,in Hinds(ed.),Calendar of State Papers...Venice,pp.172-86.
[95] Pepys's Diary,12 August 1665.
[96] Joseph Frank Payne(ed.),Loimographia an Account of the Great Plague of London in the Year 1665 by William Boghurst an Apoth-ecary(London,1894),p.29.
[97] Frances Parthenope Verney and Margaret M.Verney(eds),Memoirs of the Verney Family from the Restoration to the Revolution 1660 to 1696: Compiled from the Letters and Illustrated by the Portraits at Claydon House,Vol.iv,(London,1899),p.118.
[98] Hodges,Loimologia,p.22.
[99] John Bell,London's remembrancer,p.17.
[100] Hodges,Loimologia,pp.8-9.
[101] Anonymous,Famous and effectual medicine to cure the plague(London,1670).
[102] Hodges,Loimologia,p.48.
[103] Ibid.,p.128.
[104] Ibid.,p.13.
[105] Ibid.,p.181.
[106] Vincent,God's Terrible Voice,p.38.
[107] William Munk,The Roll of the Royal College of Physicians in London,Vol.1,1518-1700(London,1878),p.334.
[108] Hodges,Loimologia,p.15.
[109] Pepys's Diary,12 February 1666.
[110] Ibid.,16 February 1666.
[111] Ibid.,3 September 1666.
[112] Taswell,‘Autobiography’,pp.9-10.
[113] Thomas Clarke,Meditations in my confinement,when my house was visited with the sickness in April,May and June,1666,in which time I buried two children,and had three more of my family sick(London,1666),p.9.
[114] Ibid.,p.10.
[115] Payne(ed.),Loimographia,p.57.
[116] Hodges,Loimologia,p.11.
[117] Vincent,God's Terrible Voice,pp.44-8.
[118] Pepys's Diary,14 September 1665.
[119] Lord(ed.),Anthology of Poems of State Affairs,p.41.
[120] The practice of giving naval opportunity to well-bred young men developed significantly during the Dutch Wars.See J.D.Davies,Gentlemen and Tarpaulins: The Officers and Men of the Restoration Navy(Clarendon Press,1991).
[121] Pepys's Diary,18 September 1665.
[122] J.R.Jones,The Anglo-Dutch Wars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Longman,1996),p.23.
[123] Ibid.,p.161.
[124] R.C.Anderson,(ed.),The Journals of Sir Thomas Allin,1660-1678,Vol.1(Navy Records Society,1929),p.240.
[125] R.C.Anderson(ed.),The Journal of Edward Montagu,First Earl of Sandwich,Admiral and General at Sea,1659-1665(Navy Records Society,1929),p.243.
[126] Ibid.,p.244.
[127] Ibid.,p.247.
[128] Jones,The Anglo-Dutch Wars,p.17.
[129] Dagomar Degroot,‘“Never such weather known in these seas”: Climatic Fluctuations and the Anglo-Dutch Wars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1652-1674’,Environment and History,Vol.20,No.2,May 2014,pp.239-73.
[130] Pepys's Diary,20 May 1664.
[131] J.D.Davies,Pepys's Navy: Ship,Men and Warfare,1649-1689(Seaforth Publishing,2008),p.35.
[132] Treglown(ed.),The Letters of John Wilmot,pp.46-9.
[133] Ibid.,p.43.
[134] Anderson(ed.),Journal of Edward Montagu,p.252.
[135] Treglown(ed.),The Letters of John Wilmot,p.43.
[136] 1661年到1665年,艾萨克·牛顿在剑桥大学的本科学习期间,在笔记本中记录了许多观察结果,这只是其中一例。资料可查询剑桥大学图书馆的Portsmouth Collection,Certain Philosophical Questions,MS Add.3996,folio 109r.
[137] Certain Philosophical Questions,MS Add.3996,folio 3r.
[138] Payne(ed.),Loimographia,p.54.
[139] Walter George Bell,The Great Plague in London(Folio Society,2001),p.86.
[140] Ibid.
[141] Clarke,Meditations,p.6.
[142] August 1665,‘Charles II - volume 129: August 11-22,1665’,in Everett Green(ed.),Calendar of State Papers 1664-5,p.502.
[143] August 1665,ibid.,p.506.
[144] August 1665,ibid.,pp.517-9.
[145] Walter George Bell,The Great Plague,p.86.
[146] Ibid.,pp.87-8.
[147] Ibid.,p.88.
[148] M.Bell,‘“Her usual practices”: The later career of Elizabeth Calvert,1664-75’,Publishing History(1994),35,5.
[149] Margaret Cavendish,Philosophical Letters: or,Modest Reflections Upon Some Opinions in Natural Philosophy Maintained by Several Famous and Learned Authors of this Age,Expressed by Noble Letters(London,1664).
[150] Evelyn's Diary,30 May 1667.
[151] Harleian MS 6828,fols.510-23,British Library.
[152] Evelyn's Diary,27 April 1667.
[153] Ibid.,18 April 1667.
[154] Pepys's Diary,11 April 1667(注:这里也可能是“瑞典女王”,不管哪种情况,意思是一样的).
[155] State Papers 29/132 f.97.
[156] Ellwood,The history of the life of Thomas Ellwood,p.143.
[157] Ibid.,p.146.
[158] John Milton,The readie and easie vvay to establish a free common-wealth and the excellence therof compar-d with the inconveniences and dangers of readmitting kingship in this nation(London,1660),p.23.
[159] Ellwood,The history of the life of Thomas Ellwood,pp.143-8.
[160] Treglown(ed.),The Letters of John Wilmot,pp.46-9; Anderson(ed.),Journal of Edward Montagu,p.262.
[161] Anderson(ed.),Journal of Edward Montagu,p.262.
[162] T.H.Lister,Life and administration of Edward first Earl of Clar-endon; with Original Correspondence and Authentic Papers Never Before Published,Vol.iii(London,1837),pp.393-5.
[163] Treglown(ed.),The Letters of John Wilmot,pp.43-5.
[164] Lister,Life and administration,pp.394-5.
[165] Ibid.
[166] State Papers 29/129 f.58.
[167] August 1665,Everett Green(ed.),Calendar of State Papers 1664- 5,p.532.
[168] State Papers 29/132 f.127.
[169] August 1665,Everett Green(ed.),Calendar of State Papers 1664-5,pp.514-5.
[170] September 1665,Ibid.,pp.557-8.
[171] Pepys's Diary,9 September 1665.
[172] August 1665,Everett Green(ed.),Calendar of State Papers 1664-5,pp.520-2.
[173] Jones,The Anglo-Dutch Wars,p.57.
[174] Ibid.,p.23.
[175] Evelyn's Diary,25 September 1665.
[176] Pepys's Diary,22 November 1665.
[177] J.J.Cartwright(ed.),Memoirs and Travels of Sir John Reresby(London,1904) p.145.
[178] Pepys's Diary,13 July 1663.
[179] Antonia Fraser,Charles II(Weidenfeld & Nicolson,1979),p.311.
[180] Pepys's Diary,17 November 1665.
[181] ‘The second parliament of Charles II: Sixth session(Oxford) - begins 9/10/1665’,in The History and Proceedings of the House of Com-mons,Vol.1,1660-1680(London,1742),pp.85-92.
[182] Ibid.
[183] Newes Published for Satisfaction and Information of the People(London,England),Thursday,24 August 1665,Issue 65.
[184] State Papers 29/129 f.81.
[185] Richard Ward(ed.),The Manuscripts of his Grace the Duke of Portland preserved at Welbeck Abbey,Vol.iii(London,1894),p.293.
[186] Andrew Clark(ed.),The Life and Times of Anthony Wood,antiquary,of Oxford,1632-1695,described by Himself(Oxford,1891),p.68.
[187] Ibid.
[188] Ward(ed.),The Manuscripts of his Grace the Duke of Portland,p.296.妓女经常遭受“浸水刑凳”的惩罚,她们坐在上面,被一根铁棍固定捆住,然后“浸入”或沉入水池中。这种装置主要用来羞辱当事人。
[189] For description of Ralph Montagu see State Papers 29/131 f.73.For remarks about the Duchess of York and Henry Sidney see Pepys's Diary,9 January 1666.
[190] Pepys's Diary,22 November 1665.
[191] Benedict de Spinoza(trans.R.H.M.Elwes),On the Improvement of the Understanding / The Ethics / Correspondence(Dover Publications,1955),p.2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