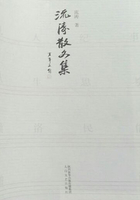
第3章 票年代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一个月黑风高的冬夜,敬爱的老爸突然把我和哥从热呼呼的被窝拎出来,派我弟兄俩去执行一项非常重要的采购任务—买肉。拿着二斤肉票和皱巴巴的人民币,临走爸千叮咛万嘱咐我哥俩不要丢了肉票和钱。我和哥顶着寒风,匆匆奔赴到县食品公司卖肉的窗口前准备去排队,非常渴望迎接一个有肉吃肥腻腻的春节,我虽然冻得直哆嗦鼻涕长流,但看在即将有肉吃的份上我没有一句怨言,而且还兴致勃勃,屁颠屁颠地跟在哥后面跑。可是,还没到食品公司门口,就看见从食品公司延伸出来的队伍已蜿蜒成了一条长龙。我哥俩以为起来早却遇到了还没有睡觉的,立即融入到队伍里哈手跺脚,耐心等待黎明的到来。那漫长的冬夜啊!二斤肉票就紧紧地被我攥在手心里,捏出了汗,也从此凝固了我关于二斤肉票的记忆。要知道有多少人因为没有肉票而吃不上肉啊?我也因此深深地知道了票证的重要。
那个年代,除了买肉要凭肉票排队外,买米面排队的场面也异常火爆,一点不比我们今天春运排队买火车票逊色。先要辗转托熟人搞到米面票,然后才有资格加入到队伍里去挤。有挤破鞋子的也有挤破脑袋的,常有因加塞打架骂仗的,男女老少混杂在一起挤,撕破脸皮,也完全忘却了性别界限,纠结在一起近似于肉搏。有模仿能力强的学生娃把这种挤法移植到了学校,冬季聚拢在一块拥挤取暖,后逐渐流传蔓延到社会的各个角落,创造了一种游戏,叫“挤油油”,估计是把身上的油都能挤出来的意思。只要买东西就要做好“挤油油”的准备,如果中规中矩老老实实排队,有可能没排到你时,东西就卖完了。因此,“挤油油”这种游戏因物资匮乏要抢购而迅速普及成为当时一种独特的社会现象。
那时候,几乎每个人的脸上都写着计划经济所形成的眼巴巴渴望等待救济物资时的表情。票证满天飞,啥都凭票供应,进食堂吃饭要粮票、扯布要布票、做棉衣要布票加棉花票,吃糖要糖票、点煤油灯要油票,没有票据你就会寸步难行。因为限购,一件衣服,黄的确凉或者蓝涤卡,老大穿不上了老二穿,老二穿不上了老三穿,只要破得不彻底,就补丁摞补丁,实在穿不成了才缝成被褥或者下放做抹布,让使用价值充分彰显,发挥到极致。一直到后来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人员猛增的势头才有所减弱,这种普遍传承衣服的做法才逐渐减少。买吃食,一个馒头或一碗面条也需要粮票,家家基本上吃的都是体积大、质量小的糊涂面和包谷糊汤,肚里盛得再多,出去溜达一圈,就迅速干瘪。所以,那时人们一般轻易不会运动,更谈上去锻炼,做无用功消耗体力,尽量让食物在肚中保留久些,也未见久坐囤积脂肪变成胖子,大家清一色标准的瘦肉型。若偶尔遇到一身材臃肿的,八成是生病浮肿假冒伪劣的胖子。
拥有票证的除了掌握物资分配权的个别领导外大多都是布衣出身的劳动模范或各行各业的先进分子。只有他们能从供销社光明正大地领到各种各样的票证,根本不用走后门看人脸,因为他们都是通过奖励获得的。谁拥有的票证越多,就能充分证明谁的面子越大荣耀越高。那时自行车可是稀罕物,要凭票供应,如果是飞鸽牌或凤凰牌那更是神仙放屁——非同凡响,相当于今天拥有了奥迪或宝马,在路上骑行,回头率甚高,车主的荣誉感和骄傲情绪会油然而生。
最难忘的是每年暑假暑期教师培训会结束后,会上都要炖几大锅萝卜肉,教师们要凭饭票用餐。我妈是光荣的人民教师,总舍不得吃,就把饭票郑重地交给我们弟兄,让我们享用。拿到饭票的那一刻我那激动的心情,简直就和我接到大学录取通知书时的心情相似乃尔,到如今那萝卜肉味还唇齿留香,让我无限思念。我还清晰地记得那些吃完萝卜肉的老师们走路雄纠纠、气昂昂、硬郎朗的样子。
最有趣的是抽烟也需要烟票,有地位的人抽中华、熊猫或者云烟、贵烟之类,一般工薪阶层抽春城、画苑、喜梅、红梅、牡丹等,而底层出苦力的农民们则抽一毛钱的羊群、两毛钱的宝成、三毛钱的大雁塔。市井流传:“男人有品位,抽的是云贵。活得不如人,咂的是羊群。”根据抽烟的牌子可把人辨出三六九等,那时,社会的阶层意识虽然已初现端倪,但社会各群体间的差别还未明显扩大,人际关系尚纯真简朴。
无论身处那个时代,人如果被划分成等级、贴上标签都是一件很悲哀的事,而成长则是一件极其烦恼的事。我的青春小鸟是从贫穷但快乐的时光飞过来的,已步入中年的我常想逃避现在沉湎于过去,不愿意面对自己内心的困惑。只喜欢把过去那些陈芝麻烂谷子抖落出来,捡拾些往事,来抚慰我这颗浮躁的心。可是,怀旧除了能证明我年龄大了变得多愁善感还意味着什么呢?
2011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