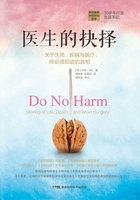
最后一条熏鳗鱼
一年后,我几乎忘记离开基辅时心中的期盼,而且万万没想到,我竟然收到了伊戈尔寄来的圣诞贺卡,他还附上了一封拉马丹诺夫院士的信。拉马丹诺夫院士请求我把伊戈尔带到伦敦,让他学习现代神经外科手术。
在我看来,这不过是一次临时出行,但却造成了严重的后果。伊戈尔遭到了乌克兰医疗机构的排挤。在伦敦与我学习3个月之后,伊戈尔回到了乌克兰,那时,他的资助人拉马丹诺夫院士已经去世。他并未寻求新资助人的支持(乌克兰社会很重要的一项要求,被戏称为“头上的保护伞”),反而在公开场合继续宣称乌克兰的神经外科手术极其原始、落后,急需变革。当时,恰逢有一个笃信东正教的人正想方设法继任拉马丹诺夫的职位,这令本就糟糕的情况变本加厉。院士的职位会带来诸多便利,例如会住进大公寓、配备专车司机等。伊戈尔的顶头上司一直觊觎该职位,但是他的愿望由于伊戈尔的不服管教而大打折扣。
接下来的几年对于伊戈尔来说的确很艰难,他努力重组科室并进行现代化改造,希望与西方国家同步发展。伊戈尔还忍受着一连串的官方检举、调查和恐吓电话。有段时间,伊戈尔每天晚上睡觉都要换一个地方。我简直无法想象,他是怎样熬过来的。
我知道,帮助他的想法过于天真,并未解决任何实际问题,反而造成了更多麻烦。然而,此时我还不能置伊戈尔于不顾,每当他口中声声念叨的“诋毁者”想要把他“干掉”、撤掉他的科室或者遣散他手下的员工时,我都会竭尽全力帮他。我也必须承认,这种帮助都是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暗中进行的。每次我出差到基辅,无论与高级官员的见面多么令人不快,我知道自己都会平安返回。在伊戈尔的帮助下,我向乌克兰的报纸投稿、举行新闻发布会,开车把二手医疗设备运到基辅,再把他手下的年轻医生带回伦敦跟随我学习。我曾实施过一些神经外科手术,这些手术以前在乌克兰从未有人做过。回想起来,考虑到糟糕的手术条件以及与医疗机构无法调和的敌对关系,那些年我的所作所为看起来绝对疯狂愚蠢。这无疑需要高度的自信与独立,但后来这些品质我都失去了。
尽管手术伊始出现了不祥的征兆以及令人蒙羞的恐慌,这位女患者的三叉神经痛手术仍然大获成功。第二天,她出现在国家电视台的新闻中,在电视里她声称终于彻底摆脱了这么多年来的病痛。我飞回波兰取回放在朋友家里的车,再驱车把手术用的显微镜运到波兰西部的朋友家中,然后伊戈尔从乌克兰弄来了一辆旧面包车来接我和手术设备。
去机场的路上,我们绕道去了基辅市中心的比萨拉比亚市场。在基辅,这座市场就相当于法国巴黎的中央市场和英国的考文特花园市场。比萨拉比亚市场是一座19世纪建成的环形建筑,有螺纹铸铁的玻璃屋顶,屋顶下就是市场,水果蔬菜和各种腌菜都被摆放成锥塔形,体格强壮但态度和蔼的妇女戴着颜色亮丽的头巾,站在高高堆起的货物后面。市场设有鲜花专售区,在任何社交场合乌克兰人都会彼此赠送鲜花。在肉类区,随处可见整个猪头和成堆的鲜肉,猪的后鞧像裤子一样挂在钩子上。这里能够深刻反映乌克兰的特色,你能体会到一种简洁明快、天然原始和粗犷豪放的美感,但是随着大型超市的出现,这种地方正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伊戈尔告诉我这座市场仍在运作,并且已经成为旅游景点。他指着一个鱼摊,突然间兴奋起来。
“很少见!”他指着玻璃柜中3条长长的熏鳗鱼说。他买了一条送给我作为礼物。礼物的味道很难闻。
“非常少见!”他自豪地说,“它们被列入红皮书了。”
“什么是红皮书?”我问道。
“记录即将灭绝动物的册子。熏鳗鱼已经绝迹了,你很幸运,能够拥有一条。”他兴奋地说。
“伊戈尔,这可能是乌克兰最后的鳗鱼了!”我看着这条原本美丽修长的生灵,它曾经通体闪亮,畅游于乌克兰偏远的江河中,但现在却被制成了熏鱼,装在“乔治·阿玛尼”的塑料袋中。我从伊戈尔手里毕恭毕敬地接过来,放在行李箱中。
回到伦敦后,没过几天我就把熏鳗鱼扔到了后花园,我不忍心把它吃掉,但想到了一只经常光顾的狐狸可能会喜欢,每天清晨都会看见它从这里悄悄地经过。第二天,我发现鳗鱼不见了,但随后在几码(1码约合0.914米)外的灌木丛中发现了它,我更加难过。连狐狸都不喜欢这条熏鳗鱼,于是我挖了一个坑把它埋了。这条乌克兰最后的鳗鱼就安葬在花园一端茂密的花圃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