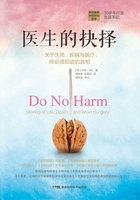
每位医生心中都有一块墓地
第二天一大早,我躺在床上,脑海中回想着上周刚刚接受手术的那名少妇。这位患者颈椎的第六和第七关节间的脊髓长了一颗肿瘤。不知为何,手术前我一直认为事情会进展得非常顺利,结果术后醒来,她发现右侧身体完全瘫痪。很有可能我切除了过多的肿瘤组织——我一定太过自信了。那次手术并未令我产生足够的警惕与担心。现在,我仍然对即将到来的这次手术充满了渴望。这次手术的部位是松果体,如果手术顺利、结果完美,大家从此就会过上快乐幸福的日子,而我的内心自然也会恢复平静。
我知道,无论我多么遗憾、内心如何凄楚,无论这次松果体瘤手术如何成功,都无法挽回我对那位少妇造成的伤害。我的不幸与她和她的家人相比,不值一提。这次松果体瘤手术没有理由不顺利,因为我特别希望手术能够成功,抑或是上一例手术太令人失望。无论肿瘤是良性还是恶性,可以切除还是长在大脑上无法切除而演变为绝症,所有的一切都可能出现可怕的偏差,进而令这次松果体手术的结果超出我的掌控。我清楚,随着时间的流逝,我对那位少妇的愧疚难过之情会逐渐褪去。现在,她躺在病床上,瘫痪的肢体成为我心中一道抹不去的疤痕,而非偶尔的心痛。法国医生莱利彻曾经说过,每一名医生心中都有一块墓地。我的患者罹难表中将会增加那位少妇的名字,而且我的墓地中也将为她增立一块新的墓碑。
一旦手术开始,那些病态的恐惧感将瞬间消失。我从一个金属盘上拿起手术刀(依照《健康安全协议》,医生禁止从消毒护士手中获取手术刀),带着医生的自信,精准地划开患者的头皮,鲜血从刀口涌出后,紧张刺激的忙碌随即开始。一切都在我的掌控之中,至少平常是这样。此时此刻,上周的手术灾难令我进入手术室时,就带着明显的怯场情绪。我没有像往常那样与消毒护士和迈克闲聊。迈克是协助我的外科实习生,这些实习生叫作专科注册医生。现在,我擦净了患者的皮肤,默默地铺上了手术单。
迈克已经与我共事几个月之久,彼此之间非常熟悉。在30年的职业生涯中,我培训了许多注册医生,自认为与他们之中的大部分人关系还不错。我在医院对他们进行培训,为他们的行为负责;而他们会协助我、支持我,必要时还会鼓励我。我很清楚,这些注册医生只会对我讲他们自认为我想听到的话,不过这也是一种非常亲密的关系,就像战场上士兵间的战友情一样。也许,这将是我退休后最怀念的人际关系。
“怎么了,头儿?”迈克问。我戴着口罩咕哝道:“有人说神经外科手术是平静、理性地应用科技技术,这纯粹是胡说八道。”我继续说:“反正我是这么认为的,上周那例血淋淋的手术让我紧张得就像30年前一样,根本不像一名马上要退休的医生。”
“我等不及了。”迈克回应道。迈克是我手下注册医生中的冒失鬼,由于我马上就要退休了,他经常会开这样标准的玩笑。现在的实习生比顾问医生的岗位要多得多,我的实习生都在为前途闷闷不乐。“无论怎样,她可能会有所好转的,”他补充了一句,“毕竟手术刚做完。”
“我看很难。”
“但你也很难断言……”
“我看她的下半生也就那副样子了。”
说这些话时,我们就站在患者的身后。麻醉后失去意识的患者被支撑起来,身体直立坐在手术床上,迈克早已把他脑后的一窄条头发剃掉了。
“刀。”我对消毒护士艾格尼丝说道,她很快递来一个托盘,我从里面拿出一把刀,迅速在患者脑后一划,切开头皮,然后迈克用一块吸盘把血擦干净,我随即分开患者颈部的皮肉,这样我们就能钻开他的颅骨。
“酷毙了。”迈克说。
患者的头皮被切开,肌肉缩向刀口两侧,颅骨被打开,硬脑膜向外翻转着——骨切开术开始。外科手术也有特殊且古老的描述性语言。我让助手拿来手术显微镜,然后坐在手术椅上。松果体瘤切除手术不同于其他脑肿瘤手术,无需切开大脑就可发现肿瘤。只要打开硬脑膜(头骨下包裹着大脑和脊髓的一层薄膜),就能看到一条狭窄的缝隙,这条缝隙将大脑上部的脑半球和大脑下方的脑干和小脑分开。在这个过程中,你仿佛在一条狭长的隧道中爬行,向下3英寸(1英寸约合2.539厘米)就能发现那颗肿瘤。在显微镜中,这3英寸的视觉长度增加了上百倍。
我一直盯着大脑中部这块幽深玄妙之处,人类维系生命与意识的重要功能器官都聚集在这里。这个部位的上方像一座教堂的巨大穹拱,那是大脑深处的静脉(即大脑内静脉),再往上是罗森塔尔基底静脉,中间是大脑大静脉(即盖伦静脉)。在显微镜中,这些静脉呈深蓝色,熠熠发光。这就是令神经外科医生肃然起敬的解剖学。这些静脉将大量的静脉血从大脑带走,一旦静脉受损就会导致死亡。现在,展现在我们眼前的就是颗粒状的红色肿瘤,肿瘤下方是脑干的顶盖,脑干受损将导致患者永久昏迷。大脑后动脉位于脑干两侧,大脑视觉中枢的一部分由其供血。再向前越过肿瘤就是第三脑室。一旦肿瘤被切除,就像直接打开了一扇门,穿过一条长长的白壁走廊,直达第三脑室。
上面这些华丽、富有诗意的外科术语,连同现代化的自动平衡显微镜带来的完美视角,共同造就了这例最完美的神经外科手术。如果一切顺利,那么手术就很完美。如果在手术刀接近肿瘤时,有些血管挡住了去路,则必须剪掉,而作为神经外科医生,你必须知道要牺牲哪些,留住哪些。那时,我的学识和经验好像突然间不见了踪影,每分离一根血管,我的心里就会一颤。作为神经外科医生,我在从业早期就学会了如何应对紧张与焦虑的情绪,这是每天工作的常态,无论如何都要坚持下去。
手术进行了一个半小时,终于看到了这颗肿瘤,我切下一小片让助手送到病理实验室做分析,随即身子向后一靠,坐在手术操作椅上。
“现在我们得等一会儿了。”我长舒了一口气,对迈克说。手术中间能停下来休息是很不容易的事,我全身肌肉紧张,瘫坐在椅子上。事实上,我渴望继续手术,希望病理科的同事报告称这个肿瘤是良性的,完全可以手术治疗;我还希望这名患者能活下来,那样就可以告诉他太太手术之后一切都会好起来。
45分钟过去了,我再也等不及,从手术台前推开椅子,跳起来直奔最近的电话而去,此时我的身上还穿着无菌手术服,手上戴着消毒手套。我接通了病理实验室,要求病理师立刻接电话。过了一会儿,他接过了电话。
“冷冻切片!”我大喊道,“怎么样了?”
“哦,”病理师的语气听上去倒是很沉着,“不好意思耽误了这么长时间。我刚才在医院的其他地方。”
“结果到底怎么样?”
“好,我正在看呢。啊!是一颗简单的良性松果体瘤。”
“太棒了!多谢了!”
听到这个结果,我立刻就原谅了他的延误,回到了手术台前。大家都在等着我。
“继续手术!”
重新消毒后,我爬上了手术操作椅,胳膊肘倚在操作椅的扶手上,继续处理肿瘤。每个大脑肿瘤都迥然不同,有些硬如顽石,有些软似果冻,有些血液供应很少,有些血液供应丰富。在手术过程中,患者会有极大的概率因失血过多而死亡。有些肿瘤就像从豆荚中脱落的豆粒,有些则与大脑和脑血管长在一起,如果遇到这种情况,医生也束手无策。仅凭脑扫描图,医生无法完全掌握肿瘤形成的基本原理,只有在即将切除时,才可洞悉一切。用外科医生的话说,这颗肿瘤还算合作,具备比较优秀的手术条件,也就是说,没有和大脑长在一起。我慢慢剔掉肿瘤的内核后,其余部分自然内缩,遂与周围的大脑组织分离。3个小时后,大部分肿瘤都被切除了。
由于松果体瘤极其罕见,一个同事专门从他的手术室来到我这里,希望观察手术怎样进行。他可能有点嫉妒我。
他就站在我身后静静地看着。
“还不错嘛。”
“目前还行。”我答道。
“只有不抱什么希望的时候,情况才会变得糟糕。”他说完转身回自己的手术室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