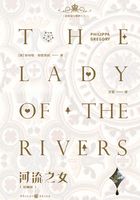
1435年9月
法国 鲁昂
整个漫漫夏季,公爵大人都在传唤他的律师和曾效忠于他的议员们,这些人曾助他在法国艰难摄政十三载。每一天使节们都从他们在阿拉斯召开的和平会议上来了又去,每一天我的大人都让他们来告知最新进展。他为英国的年轻国王寻得一位法国公主的联姻以平息法国王位之争,并提议将整个法国南部都交给阿尔马尼亚克人统治;他不能继续让步了。可对方要求的是让英国人交出所有法国领土,还否认了我们坐上王座的权力——就好像我们不曾花上几近一个世纪为王座而战一样!每一天我的大人都在提议新的让步,抑或是协约的新草案,而每一天信使踏上通向阿拉斯的大路之时,他都在鲁昂城堡的窗边眺望斜阳西沉。某天晚上,我看见信使从马场出来,向加莱疾驰而去。我的大人写信召唤理查德·伍德维尔了,然后他叫我过去。
律师把大人的遗嘱带来给他,他命令要改一些地方。他的财产都属于男性继承人,也就是他的侄子,英格兰的小国王。他难过地一笑。“我绝不怀疑他有多渴望继承我的财产,国库里连一毛钱也不剩了;我也绝不怀疑他会把钱财都挥霍一空。他会连想都不想就把钱财都送出去的,他是个慷慨大度的孩子。可是这些都是理应属于他的,他的议会也会给出忠告。上帝会帮助他在我弟弟和叔叔的建议之间做出抉择。”而我也将得到他名下三分之一的财产。
“大人……”我不知如何开口。
“这些是你的,你是我的妻子,尽了好妻子的义务,应得这么多。只要你还冠着我的名字,一切都是你的。”
“我并不想……”
“是的,我自己也不想。我没想过这么快就要立下遗嘱。不过这是你的权利,也是我的愿望,你应该得到你那一份。但是还不够,我还要把我的书通通留给你,雅格塔,我那些美丽的书卷。它们现在都归你所有了。”
这些书毋庸置疑都是宝物。我跪在他的床边,将脸颊贴在他冰冷的手上:“谢谢你。你知道我会好好研读、好好保管它们的。”
他颔首:“那些书,雅格塔,那些书中有一本含藏着所有人都在寻找的答案——如何永生,如何制造纯粹的水,如何从煤灰和暗物质中提炼出真金。也许某天你会在阅读时找到它的,那时我已经死去很久了。”
泪水在我的眼中打转:“别说这种话啊,大人。”
“出去吧,孩子,我得在上面签名,然后就要睡觉了。”
我屈膝行礼,悄悄离开房间,把他和律师们留在那里。

他一直不让我去见他,直到第二天下午,我们才又见面。就算才隔了这么短的时间,我也眼睁睁看着他又失去了一些生气。他黑色的眼睛更加呆滞了,鹰钩鼻在消瘦的脸上显得更宽更大;我可以看得出他正在片片崩塌。
他坐在高大如王座的椅子中,面朝窗户好看到通往阿拉斯的路,路上的人们仍为和平协议争论不休。窗外照进的余晖让一切都闪闪发光。我想这可能是他的最后一夜了,他也许将随着太阳一起消逝。
“这城堡正是我第一次见你的地方,还记得吗?”他望着太阳沉入金色的云层,苍白的月影升上天空,“当时我们就在这座城堡,就在这座城堡的入口大厅,为了圣女贞德的审判。”
“我记得。”我记得太清楚了,可是我从没为贞德之死谴责过他,即使我经常自责没能为她出言辩护。
“真是奇怪,我是来这儿烧死一位圣女的,却又发现了另一位。”他说,“我把她当做女巫烧死,却又因为你的能力而想要你。真是奇怪啊,这事儿。看见你的瞬间我就想要你了。不是当做妻子,因为我那时有安妮。我想要把你当做一件宝物。我坚信你有预知能力,我知道你继承了梅露西娜的能力。我本以为你能带我找到贤者之石。”
“对不起。”我说,“我很抱歉我的能力不足……”
“哦……”他做了个手势表示不关心,“没这回事。也许如果我们有更多时间……可是你的确看见过一顶王冠,对不对?还有一场战争?还有一位王后,在钉马后蹄上的马蹄铁,你还看见了我的家族的胜利,还有我侄儿和他的血脉将永远君临天下,对吗?”
“是的。”我这样说是为了安慰他,即使这些景象没有一样是我真正看清过的,“我看见你的侄儿坐在王座之上,我确信他会守住法国。加莱不会在他手上丢失。”
“你确信吗?”
至少这一点我能向他保证:“我保证加莱不会输在他手上。”
他点点头,沉默地坐了片刻。然后他极轻极低地说:“雅格塔,你能脱掉你的裙子吗?”
我吃惊到不由得退了几步:“我的裙子?”
“是的,还有内衣,所有衣服。”
我感到自己尴尬地脸红了:“你想看我赤身裸体?”
他点头。
“现在吗?”
“没错。”
“我是说,在光天化日之下?”
“在这夕阳西下之时,没错。”
我别无选择。“如果这是您的命令,大人。”我从椅子上起身,解开长裙的系带,任它垂到脚边。我从中跨了出来,羞赧地将它放到一边。我摘下华丽繁复的头饰,把辫子统统散开。头发落在我脸上,就好像一层遮掩我的面纱,接着我脱下亚麻衬裙,还有精致的丝质内衣,我站在他面前,不着一缕。
“抬起你的手。”他命令道。他的声音很平静,望向我的目光不带任何欲望,而是某种沉思般的愉悦。我意识到我曾见过他这样,当他看那些图画,那些织锦画,那些雕像时正是这样的眼神。此时此刻,一直以来,我在他眼里都是这样:一件美丽的物品。他从没把我当做一个女人来爱。
我顺从地把手举过头顶,像一个准备潜入深水的泳者。我眼中的泪水已流过脸颊,因为我知道了,我是他的妻子、他的床伴、他的伴侣和他的伯爵夫人,而即使到了现在,即使他已濒临死亡,他还是不爱我。他从未爱过我,也永远不会爱我。他指示我稍微侧身,让最后的金色余晖洒在我赤裸的皮肤之上,将我的身体两侧、小腹和乳房都染成同样的金色。
“火之少女。”他轻声道,“黄金圣女。真高兴能在死前看见这样一幕。”
我顺从地一动不动,即使感到自己纤细的身体在啜泣中轻轻颤抖。在他临死之时,也把我视作一件幻变成黄金的物体;他看到的不是我本人,他不爱我,甚至不是因为我本人而需要我。他的眼睛扫过我全身上下每一寸,如痴如醉;却没有察觉我在流泪。我重新穿好衣服后,将泪水悄然拭去。
“我现在要休息了。”他说,“真高兴能看见这样的景象。告诉他们来扶我上床,我要睡觉了。”
他的仆人们走进来,将他舒服地置于床上,接着我亲吻他的前额,让他沉入梦乡。就这样,那一晚他在睡梦中去世了,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也是他最后一次见到我:不是作为挚爱的妻子,而是一尊被落日镀成金色的雕像。
早上七点左右,我被叫醒,来到他的房间看见了他。他几乎和我离开时一样,看上去正睡得安详,只有丧钟独自在鲁昂教堂的钟楼里缓慢低沉地长鸣,告诉整个家族和全城,伟大的约翰公爵已经溘然长辞。后来女人们清洗了他的身体,为殡仪做好准备。管家着手准备在教堂举行入棺仪式,木匠订制木材,开始制作他的棺木,只有理查德·伍德维尔想到把我带到一旁,与我一样在周围的嘈杂和劳作声中不知所措,沉默不语。他带我回了我的房间。
他为我叫来早餐,把我交给侍女,交代她们看着我吃,看着我休息。缝纫女工和裁缝们马上就会来为我们量体裁衣制作丧服,鞋匠也会来为我制造一双黑鞋。手套师傅会为我制作一双双黑手套,好分发给家族成员。他们会用黑布铺点前往教堂的路,还要给一百个穷人准备黑色斗篷,都是雇来走在棺材后面的。我的大人会被安葬在鲁昂大教堂,届时将有各地领主排成长长的队列,用宏大的场面为他送别,一切都将不差分毫地按照他的愿望执行:庄严而高贵,按英国的传统行事。
那一整天我都在写信向所有人通知我丈夫的死讯。我写给我的母亲,告诉她我现在和她一样都是寡妇了:我的大人死了。我还写信给英国国王,给勃艮第公爵,给神圣罗马帝国,给其他国王,给阿拉贡的约兰德。其余时间我都在祈祷。我出席了那天在我们的私人教堂中的每场礼拜,鲁昂大教堂的僧侣们守着我丈夫的遗体日夜不休地照料和祈祷,遗体由四位处于四个方位的骑士守护;这样的守夜只有在火葬之后方才结束。
我等候着,希望上帝能为我指路,我跪着等候,希望自己能明白我丈夫是因为功勋累累才蒙主召唤的,至少他终于去了一个不需要拼死守护的地方。可是我什么也没听见,什么也没看见。甚至连梅露西娜也不曾为他低吟一声哀叹。我想知道自己是否已经失去了预知能力,而镜中那浮光掠影的一瞥就是我从此再不得见的另一个世界的最后影像。
到了晚上,约莫是日落时分,理查德·伍德维尔进了我的房间,问我是想在城堡大厅用晚餐,被家族的男男女女团团包围,还是在自己的房间独自进餐。
我犹豫不决。
“如果你能去大厅,他们会很振奋的。很多人都因失去公爵大人而深深悲痛,他们会很想看见你出现在他们中间,况且你的家族无疑将分崩离析,他们会很想在不得不离开前见你一面的。”
“这个家族会分崩离析?”我傻乎乎地问。
他点头:“毫无疑问,我的夫人。英国朝廷会任命新的法国摄政王,你将会被送回英国宫廷,让他们为你安排另一桩婚事。”
我目瞪口呆地看着他:“我无法想象还要再结一次婚。”
我不太可能再找到一个对我无欲无求,至多不过是瞧瞧我的裸体的丈夫。新丈夫的需求一定远不仅于此,他会对我动粗,而且他几乎毫无疑问会有钱有势,还很年迈。只是这名老人不会让我学习,不会留我独守闺房,他必定想要个儿子,指望我生下他的后代。他会像买一头给公牛配种的小母牛一样买下我。我会像牧场里的小母牛一样尖叫,可他照样会爬到我身上。“真的,我无法忍受再结一次婚了!”
他的微笑满含苦涩。“你和我都要学习如何服侍新主人。”他说,“真够受的。”
我没作声,过了一会儿说:“我会去大厅用餐。你真的觉得大家会喜欢这样吗?”
“他们会的。”他说,“你能自己走去吗?”
我点头。侍女们列队走在我身后,理查德则在我身前开道,走向通往大厅的双扇门。门后传来的声音不如平时那般嘈杂:这个家族正在服丧。护卫们把门打开,我走了进去。所有谈话都在霎时间中断了,沉寂突如其来地降临,接着又是一阵沉重的桌椅挪动声,所有人都站起身来,在我经过时摘帽致意,成百上千的人都在向我这位年轻的公爵遗孀致敬,展示他们对逝者的热爱,还有对丧主的悲伤,以及对我丧夫的同情。我从他们之中走过,听见他们喃喃低语“愿上帝保佑您,夫人”。我一直走到大厅尽头的高台之上,孤身站到高脚桌之后。
“我感谢诸位善良的祝愿。”我对他们说,声音像铃声般在大厅中回响,“公爵大人已经与世长辞,我们都因他的故去而悲伤。你们都会领到下个月的工钱,我会将你们推荐给法国的新摄政王,因为你们都是优秀且值得信赖的仆人。上帝祝福公爵大人,上帝保佑国王。”
“上帝祝福公爵大人,上帝保佑国王!”

“做得好。”我们回私人房间的路上,伍德维尔对我说道,“尤其是工钱那部分。而且你也付得起。大人生前待下人很好,钱库里也有足够的钱支付工资,甚至还有富余的可以给老人们当养老金。你自己也会是个非常富有的女人。”
我在一个小凸窗前站定,望向被夜色笼罩的城镇。一轮椭圆的凸月正在升起,在靛蓝色的天空中散发温暖的黄色光彩。我应该趁月亮渐满时在彭斯赫斯特种植草药,但接着想起自己再也见不到彭斯赫斯特了。“你接下来会怎样呢?”我问道。
他耸耸肩:“我会回加莱,直到朝廷任命新的上尉,然后回英国的老家。我会找到值得尊敬的新主人,效忠于他。也许我会回到法国进行远征,如果国王真的与阿尔马尼亚克人缔结了和约,也许我会到英国朝廷服侍国王。也许我会远赴圣地,当一个十字军骑士。”
“可是我不能再见到你了。”这个念头突然刺痛了我,“你不会在我的家族之中了。我甚至不知道自己会住在哪里,你却可能去任何地方。我们再也不能在一起了。”我看着他,意识到这个事实。“我们再也不能见到对方了。”
“是的,”他说,“我们要在这里分别。也许从今往后再也不能见到彼此了。”
我惊讶得无法呼吸。从此再也见不到他,这个想法太沉重了,重得我几乎无法承受。我发出一声颤抖的笑。“这不可能啊,我每天都会见到你,这样已习以为常了……你总是在这里,我曾经与你并肩散步,一同骑行,与你朝夕相处,已经——已经两年多了?自打我结婚那天起,我就习惯有你……”我停了下来,怕自己听起来太过脆弱,“还有,谁去照顾梅芮?谁能保证她的安全呢?”
“你的新任丈夫?”他提议道。
“我不知道,我无法想象。无法想象你不在身边。还有梅芮……”
“梅芮怎么了?”
“她不喜欢陌生人。”我傻乎乎地说,“她只喜欢你。”
“我的夫人……”
他的声音中满怀着强烈感情,令我安静下来:“怎么?”
他带我走过长廊。在坐在火炉最远端的侍女眼里,我们不过是一起走着商量接下来的几天的安排,就像我们以往一直做的那样,并肩行走,交谈,我们的关系永远都不会改变:一位公爵夫人和她虔诚的骑士。可是这一次,他一直握着我的手,指尖烫得如同正在发烧。这一次他的头离我是这么近,我一直将头扭开。我不能抬头望他,这样的话我们就会碰上对方的嘴唇。
“我不知道未来会将我们带至何方。”他快而低声地说道,“我无从得知你会嫁到何处,也不知道生活将待我如何。只是我不能还没告诉你就让你走——至少对你说一次——我爱你。”
我的呼吸为之一滞:“伍德维尔……”
“我什么也不能给你。我简直一文不名,而你却是法国最高贵的夫人。可是我想要你知道,我爱你,我想要你,第一次看见你的那天我就万劫不复了。”
“我应该……”
“我必须告诉你,你必须知道:我像骑士热爱他的夫人一样满怀荣耀地爱你,我像男人热爱女人一样满怀激情地爱你;此时此刻,在我离开你之前,我想告诉你我爱你,我爱你……”他停下来,绝望地看着我,“我必须要告诉你。”他又说了一遍。
我感到自己好像被炼金术击中一般,变得明亮而温暖。我可以感觉到自己因那些话语而脸红微笑。就在那时我立即知道他说的都是真的,他爱我,就在那时我立即意识到:我也爱他。他已经告诉我了,他说了那些话,我掳住了他的心,他爱我,他爱我,天啊,他爱我。连上帝都知道——可理查德却不晓得——我也爱他。
我们没再说话,钻进走廊尽头的一个小房间,他反手关上门,情难自已地拥我入怀。我朝他扬起头,他吻了我。我的双手从他英俊的脸庞一路抚到宽阔的肩膀,我将他紧紧抱住,近一点,再近一点。我能感受到他肩上的肌肉包裹在短上衣之下,还有他后颈上扎人的短发发梢。
“我想要你。”他对着我的耳朵说,“不是作为公爵夫人,也不是作为占卜者。我想要作为女人的你,我的女人。”
他低头从我长裙领口中露出的肩头上落下亲吻,他亲吻我的锁骨,我的脖颈,一路吻到我的下颌。我将脸埋在他的发间,埋在他的颈窝,他发出一声满含欲望的呻吟,把手指插进我的发巾,把金色的网纱扯了下来,让我的长发纷纷散落,他在其间摩挲自己的脸颊。
“我想要作为一个女人的你,一个普通女人。”他气喘吁吁地重复道,伸手拉扯我的长裙的丝带,“我不想要预知能力,不想要你显赫的家世。我对炼金术、难解之谜和水之女神都不感兴趣。我是一个普通的男人,由最普通的物质造就的英国男人。我不想要探寻难解之谜,我只想要你,作为一个寻常女人的你。我必须拥有你。”
“你会把我带回现实的。”我仰起头,缓缓地说。
他犹豫了,低头看向我的脸。“不是要贬低你的身份。绝不是那样。我想要你保持最真实的自己。我不懂另一个世界的事,也毫不关心。我不关心圣人、鬼怪、女神还有什么贤者之石。我唯一想要的就是和你同床共枕,雅格塔——”我们俩都意识到这是他头一次叫我的名字,“雅格塔,我只想得到你,把你当做一个普普通通的女人,而我则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男人。”
“好啊。”我突然感到一阵欲望的冲动,“好啊。别的我什么也不在乎了。”
他的嘴唇又压上了我的,他伸手拉扯我长裙的领口,解开我的腰带。“把门锁上。”我说,他甩掉上衣,将我拉到怀里。他进入我的时候,我感到一阵灼热的痛苦,接着融化成一种从未感受过的欢愉,令我再不计较那疼痛。可是即使在两人忘我的交融之中,我也清楚知道这是女人的疼痛,我已经成为了一个属于大地与火的女人,不再是属于水和空气的少女了。

“我们得小心点,别怀上孩子。”伍德维尔对我说。我们已经密会整整一周,目眩神迷地沉浸在彼此带来的欲望和欢愉之中。大人的葬礼已经结束,我等着母亲的来信,看她会命令我怎么做。我们终于从爱欲的盲目中清醒了一点,只不过还非常缓慢,开始思考等待着我们的命运将是如何。
“我服过草药。那一晚过后我就服了某种草药。不会有孩子的。我可以保证。”
“我希望你能预见我们俩的命运如何。”他说,“因为我真的无法让你走。”
“嘘。”我让他小心。我的侍女们就在附近边做女红边聊天,不过她们早已习惯理查德·伍德维尔每天都来我的房间了。有很多事情要安排计划,理查德总是随叫随到。
“我是说真的。”他压低声音,“是真的,雅格塔。我无法放你离开。”
“那么你就要抓牢我了。”我答道,把脸藏在文件后忍俊不禁。
“国王会命令你回英国的。”他说,“我总不能绑架你啊。”
我飞快地偷瞧了一眼他愁眉不展的脸。“真的,你应该绑架我算了。”我怂恿道。
“我会想出办法的。”他立下誓言。

那天晚上我取出姑婆留给我的手镯,那个能预知未来的挂满小挂坠的手镯。我取下其中一个,形似小小的结婚戒指,又取下一个像小船的,象征我的英国之旅,然后是一个形似圣波尔城堡的,以防我被召唤回家。我想要把它们分别绑上丝绳,垂进塞纳河最深的水域之中,等月相变化后看看是哪一根会回到我手中。我正要给小挂坠绑上丝绳,突然停了下来,嘲笑自己。我不会这样做的,这是多此一举。
我已经是属于大地的女人了,不再是水做的女孩。我不是少女,我是热恋中的情人。我无意预见未来;我会亲手塑造它,而不是预知它。不需要什么小挂坠告诉我事情会得偿所愿。我向上抛出那个形似结婚戒指的小挂坠,在它掉地前接住了它。这是我的选择。我不需要靠魔法揭示自己的欲望。魔法早已实现了,我坠入了爱河,我与一个属于大地的男人结下了盟约。我不会放开他的。我所要思考的就是怎样才能让我们在一起。
我把手镯搁到一边,抽出一张纸,开始写信给英国国王。
贝德福德公爵遗孀致尊敬的英法之王:
敬爱的大人,亲爱的侄儿,愿您贵体安康。如您所知,先夫在英国给我留下了土地和财产作为遗产,如果您允许,我会回家安排打点自己的事务。我的大人的骑士统领,理查德·伍德维尔爵士,会伴我和我的家族一同前往。静候您的允许。
我把那手镯放进钱包,收回首饰匣中。我不需要魔法来预知前程;我要亲自让它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