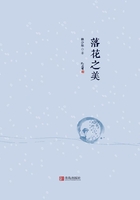
愧对自然
家住麦岛,背靠浮山,清晨爬山几乎成了我白天粉笔灰晚上爬格格生活中唯一的休闲和乐趣。但有两个爬山最佳时节我不得不忍受有山爬不得的痛苦。
一是槐树花盛开的时候。多美的愧树花啊!远望如绿海碧波中的白帆,近观如身披婚纱的少女。我散步的山路上又恰好长着大小许多槐树,细看之下,那一串串玲珑剔透的乳白色小铃铛噙着一颗颗晶莹的露珠,晨风吹来,清香四溢,赏心悦目,沁人心脾,别提有多惬意了!然而不出一两天,她们便惨遭摧残:或枝丫零乱,或骨断皮连,或披头散发,或拦腰折断,地面残枝败叶,一片狼藉——有人大摘特摘槐树花或吃或卖去了。我亲眼见到一个男子爬上树去猛砍树枝,顷刻间树就身首异处,叫他别砍了他也不理。还有一次见一个衣着颇为入时的中年妇女正往树上挥舞镰刀,我忍不住上前劝阻,不料她蛾眉倒立,一字一板地摔过一句:“你这人是不是有病?”得得!眼不见心不烦,只好等槐树花开完了再爬山。
二是金风送爽候鸟南飞时节。爬山路上,鸟儿或三两啁啾树间,或单只惊起草丛,或成群掠过晴空,心头不禁生出难以言喻的欢欣和遐思。然而偏偏有人以网鸟为乐趣。一次正壮着胆子“偷”拆鸟网时突然冒出一个壮汉满脸凶气朝我挥拳头。不用说,论笔头他不是我的对手,论拳头我显然敌不住他。百无一用是书生,赶紧灰溜溜逃下山去。如此这般,只好等鸟飞完了再爬山。
最佳爬山时节却有山爬不成,眼睁睁望山兴叹,滋味真是痛苦。痛苦之余,我开始思忖现代人是不是太傲慢太自私太贪婪太残忍了,是不是有负自然愧对自然。
古人可是打心眼里珍惜和热爱自然风物的。当西方人还一门心思在大理石上捣鼓维纳斯性感而丰腴的裸体的时候,晋齐二谢就已洒脱地吟出“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和“余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的山水佳句了。爱花者,如苏东坡的“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惜鸟者,如陶渊明的“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大气者,如李太白的“阳春召我以烟景,大块假我以文章”,山水诗文,名篇迭出,如繁星在天,琅璨夺目,表现出古人善待自然的博爱情怀和“天人合一”的人文精神。而今人不知何时转而崇尚“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开始向大自然大开杀戒。湖泊是大地的眼睛,而六百里滇池活活被糟蹋成了浑浊发臭的白内障;草原是大地的肌肤,而人们仅仅因为“发菜”与“发财”谐音便将呼伦贝尔大草原挖得体无完肤风沙四起,如今正因“冬虫夏草”可用来滋补身体而在青海高原草场掘地三尺;江河是大地的乳汁,而今长江干流的污染段即已达73%,东坡先生的“卷起千堆雪”成了对白色污染惊心动魄的描摹;森林是涵养乳汁的源泉,而今砍伐的刀斧已向唐古拉山逼近,致使江河雨季浊浪排空樯倾楫摧,旱季河床见底四野嗷嗷待哺;动物是人类的朋友,而今无数飞禽走兽落入人口,有的餐馆甚至把美丽的孔雀关在笼子里任人点杀……
应该说,我们这个民族一向讲知恩图报,却不知何故,唯独对大自然这个无私供养我们的最大恩人恩将仇报!试想,假如天空没有飞鸟只有波音747,地上没有花木只有摩天楼,水中没有游鱼只有塑料瓶,晚间没有星光只有霓虹灯,那将是一个多么乏味而恐怖的世界!
(2004.11.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