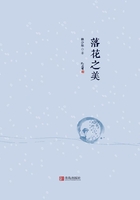
青岛的喜鹊
日前,弟弟从松花江畔送父母来青岛小住。岭南塞北海内海外漂泊半生,从未把父母接来身边。加之弟弟急于回去上班,于是我推开案头杂务,兴冲冲当起了“导游”。身为青岛市民,自然有义务维护青岛美好形象。灰头土脸的地方一概敬而远之,专往前海一线八大关等“花边”地带引导。导得父母和弟弟一副眼睛不够使的样子,一致称赞我“来到天下第一等好地方”。两天“误导”下来,我问他们青岛什么最好,也是因为正巧眼前有喜鹊飞过,母亲和弟弟指着喜鹊说喜鹊最好。母亲说老家那边别说喜鹊,连麻雀都没影了。几天后我去租的房子那里看父母,母亲还是喜滋滋望着草坪上树枝上的喜鹊说喜鹊好。“老家往天上看啥都没有,”母亲说,“以前啥都有。往柳条沟里一钻,扑棱棱飞起好多好多鸟。”
母亲说的情景我也深有记忆。我是东北平原边上的半山区长大的。小时候,天上不但有喜鹊、麻雀,还有乌鸦和春燕,甚至有布谷、有黄鹂、有老鹰。看见小燕子优美的身姿滑进堂屋在梁上筑巢,看见喜鹊落在房后祖父栽的杏树上“喳喳”欢叫,看见麻雀们在河边刚泛绿的柳树间往来嬉闹,即使小孩子心里也充满春天到来的喜悦。“喜鹊登枝”,既是经典的窗花图案,又是寻常的晨夕风景。
其实——也许遗传关系——我也格外喜欢喜鹊。虽然它的叫声算不得婉转,但形象绝对可爱:体态丰满匀称,毛色黑白分明,升空时长尾巴潇洒地一甩,落地行走两脚像弹钢琴,极有抑扬顿挫的韵律美。而往杏树花、樱花、槐树花之间或合欢树上一落,更是风情万种相映生辉,满怀欣喜、一缕乡愁都随之定格在那一瞬间了。我实在想不出人世间还有比这更撩人情思的美妙镜头。
说起来,我是九九年初秋从工作了一二十年的广州跑来青岛的,几个月后广州那所颇有名气的大学率先实行岗位津贴制,随即亮出劝归的“杀手锏”:你的津贴算下来每月可是四千七哟,乃外语系“首富”,立刻回头还为时不晚!你别说,这招还真灵,毕竟当时整个收入才一千挂个小零头,不由我不心动。但少顷我以半开玩笑的语气回敬道:广州清晨能去开满槐树花的山上爬坡吗?晚间能在洒满夕晖的海边散步吗?广州有喜鹊吗?
不知青岛选不选“市鸟”,极想投喜鹊一票。在日本,喜鹊已有“县鸟”之誉——佐贺县的县鸟。说来也怪,喜鹊只在佐贺县这个小县生息,绝不飞出县界。我在与佐贺县相邻的长崎县生活了三年之久,硬是见不到喜鹊。见到最多的是乌鸦。去年在东京,东京乌鸦就更多了,郊区多,城里也多,甚至成群结队飞过银座上空,让我切切实实查出了“黑压压”一词的来源。说实话,清早一出门就有大嘴乌鸦冲你脑门“呱呱”三声,确乎让人扫兴。抛开民间说法不论,即使从美学角度来说,也全然比不上“喜鹊登枝”给人的感受。樱花时节去上野公园,但见白灿灿的樱花树上落了一层黑压压的乌鸦,倒也黑白分明,蔚为壮观,未尝不可以说是赏心悦目。
不过话又说回来,青岛的喜鹊队列中点缀几只乌鸦怕也不坏——就像一群眉清目秀的窈窕淑女之间有两三个魔鬼身段的非洲美女,岂不又多了一番风情?
(2004.6.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