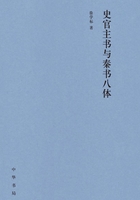
上编 史官主书研究
第一章 史官所指及其内涵
一、史官的界定
金毓黻(1)《中国史学史》:“史学寓乎史籍,史籍撰自史家。语其发生之序,则史家最先,史籍次之,史学居末。而吾国最古之史家,即为史官。盖史籍掌于史官,亦惟史官乃能通乎史学,故考古代之史学,应自史官始。”(2)“史官”是中国古代最早出现的学者群体,中国古学出于史官,现存古代典籍也多撰成于史官,研究中国史学不能不明了史官。
唐刘知几《史通》卷十一《史官建置》云:“盖史之建官,其来尚矣。昔轩辕氏受命,仓颉、沮诵实居其职。至于三代,其数渐繁。”《世本·作篇》《吕氏春秋·先识览》《史记·太史公自序》及《说文解字·序》等,均认为史官产生于黄帝之时。言史官“肇自轩辕”,此固然无直接的材料可以佐证,然从先秦史官体制之发达,史官文化之丰富程度来看,史官起源于西周之前的上古时代,是毋庸置疑的事实,正如梁启超所言:“泰西史官之建置沿革,吾未深考;中国则起源确甚古,其在邃古,如黄帝之史仓颉、沮诵等,虽不必深信,然最迟至殷时必已有史官,则吾侪从现存金文、甲文诸遗迹中可以证明。”(3)不过,需要说明的是,最初之“史”与这种传统意义上的“史官”,并非一回事。
对“史”字构形的辨识,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史”的最初意义及其原始职掌。许慎《说文解字》第三篇下《又部》部云:“史,记事者也。从又持中。中,正也。”认为“史”的构形是“从又持中”,“又”是右手,“中”为中正。王国维《观堂集林》卷六《释史》曰:“古文中正之‘中’字作 、
、 、
、 、
、 、
、 诸形,而伯仲之‘仲’作中,无作
诸形,而伯仲之‘仲’作中,无作 者,唯篆文始作
者,唯篆文始作 者。且中正,无形之物德,非可手持。”王氏此论颇具说服力,“史”之上部所从者并非“中正”之“中”字,“中正”作为一种抽象的观念,也不可能是以手来握持的。“史”字上部究竟为何物之象?这是解开“史”字初义及其原始职掌的关键所在。
者。且中正,无形之物德,非可手持。”王氏此论颇具说服力,“史”之上部所从者并非“中正”之“中”字,“中正”作为一种抽象的观念,也不可能是以手来握持的。“史”字上部究竟为何物之象?这是解开“史”字初义及其原始职掌的关键所在。
戴侗、江永、吴大澂、林义光、阮元、王国维、顾实、李宗侗、劳榦、徐复观诸家,皆以篆书“史”字上部所从之“ ”形为是,对“
”形为是,对“ ”所代表的物象及“史”的初义、职掌等,展开了各自的论述与争鸣,主要观点概括有六(4):一、释“
”所代表的物象及“史”的初义、职掌等,展开了各自的论述与争鸣,主要观点概括有六(4):一、释“ ”为笔,史即持笔之人。如戴侗《六书故》卷十五曰:“史,掌书之官也。秉聿以俟,史之义也。”二、释“
”为笔,史即持笔之人。如戴侗《六书故》卷十五曰:“史,掌书之官也。秉聿以俟,史之义也。”二、释“ ”为簿书,史即掌簿书之人。如江永《周礼疑义举要》卷九曰:“凡官府簿书谓之中,故诸官言治中受中,小司寇断庶民狱讼之中,皆谓簿书,犹今之案卷也,此中字之本义,故掌文书者谓之史,其字从右从中,又者右手,以手持簿书也。”三、释“
”为簿书,史即掌簿书之人。如江永《周礼疑义举要》卷九曰:“凡官府簿书谓之中,故诸官言治中受中,小司寇断庶民狱讼之中,皆谓簿书,犹今之案卷也,此中字之本义,故掌文书者谓之史,其字从右从中,又者右手,以手持簿书也。”三、释“ ”为简册,史即执简记事之人。如吴大澂《说文古籀补》第三曰:“史,记事者也,象手执简形。”四、释“
”为简册,史即执简记事之人。如吴大澂《说文古籀补》第三曰:“史,记事者也,象手执简形。”四、释“ ”为盛算之器,史为持盛算之器者,引申为持书之人。比如,阮元《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卷五曰:“中,射礼所用以实算者,……以手执之,奉中之义。”王国维《观堂集林》卷六《释史》曰:“是中者,盛算之器也……射时舍算,既为史事,而他事用算者,亦史之所掌。算与简策本是一物,又皆为史之所执,则盛算之中,盖亦用以盛简,简之多者,自当编之为篇。若数在十简左右者,盛之于中,其用较便。……然则史字从又持中,义为持书之人。”五、释“
”为盛算之器,史为持盛算之器者,引申为持书之人。比如,阮元《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卷五曰:“中,射礼所用以实算者,……以手执之,奉中之义。”王国维《观堂集林》卷六《释史》曰:“是中者,盛算之器也……射时舍算,既为史事,而他事用算者,亦史之所掌。算与简策本是一物,又皆为史之所执,则盛算之中,盖亦用以盛简,简之多者,自当编之为篇。若数在十简左右者,盛之于中,其用较便。……然则史字从又持中,义为持书之人。”五、释“ ”为弓钻,史为持弓钻钻龟而卜之形,表示卜筮之事。如劳榦在《史字的结构及史官的原始职务》一文中说:“史字是从右持钻,钻是象钻龟而卜之事。”(5)六、释“
”为弓钻,史为持弓钻钻龟而卜之形,表示卜筮之事。如劳榦在《史字的结构及史官的原始职务》一文中说:“史字是从右持钻,钻是象钻龟而卜之事。”(5)六、释“ ”为口诵简文,史即祝祷之人。如徐复观《原史——由宗教通向人文的史学的成立》一文中说:“与祝之从口同。因史告神之辞,须先写在册上。……将笔所写之册,由口告之于神,故右手所执之笔,由手直通向口。”(6)
”为口诵简文,史即祝祷之人。如徐复观《原史——由宗教通向人文的史学的成立》一文中说:“与祝之从口同。因史告神之辞,须先写在册上。……将笔所写之册,由口告之于神,故右手所执之笔,由手直通向口。”(6)
不难发现,以上诸家皆是以后世史官的某一项或几项职能,配合篆书“史”字之形,来推导“ ”所代表物象的。然而,今所见最早的“史”字——甲骨文中的“史”字,通常写作“
”所代表物象的。然而,今所见最早的“史”字——甲骨文中的“史”字,通常写作“ ”“
”“ ”二形,其上部所从者或为“
”二形,其上部所从者或为“ ”,或为“
”,或为“ ”,不尽为篆书“
”,不尽为篆书“ ”一形。其中,从“
”一形。其中,从“ ”之形的存在,是持上述六种观点者所无法解释的。
”之形的存在,是持上述六种观点者所无法解释的。
甲骨文“史”作“ ”者,徐中舒以为其构形是手持武器从事狩猎或作战,所持武器或为丫杈,或为丫杈、棍棒缚以石块做成的锤形物(7)。陈梦家也认为最初之“史为田猎之网,而网上出干者,搏取兽物之具也”(8)。胡厚宣的观点与陈梦家的基本相同:
”者,徐中舒以为其构形是手持武器从事狩猎或作战,所持武器或为丫杈,或为丫杈、棍棒缚以石块做成的锤形物(7)。陈梦家也认为最初之“史为田猎之网,而网上出干者,搏取兽物之具也”(8)。胡厚宣的观点与陈梦家的基本相同:
甲骨文史字作“ ”“
”“ ”,两形通用,如丙78同是“史”字,一作“
”,两形通用,如丙78同是“史”字,一作“ ”,一作“
”,一作“ ”可证。亦或省作“中”,亦有省作“
”可证。亦或省作“中”,亦有省作“ ”者。“丫”即“干”,亦即“单”,为
”者。“丫”即“干”,亦即“单”,为 、
、 、战字所从,乃田猎和战争所用之工具,与卜辞擒之作“
、战字所从,乃田猎和战争所用之工具,与卜辞擒之作“ ”者其意略同。(9)
”者其意略同。(9)
王贵民《说史》一文,对陈、胡二家观点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和论述:
早期的“ ”字所从之“丫”,即是“狩”字“
”字所从之“丫”,即是“狩”字“ ”的田猎工具部分,丫可以是表示干戈的干,也可以是小网长柄的“
”的田猎工具部分,丫可以是表示干戈的干,也可以是小网长柄的“ ”,更可能是原始狩猎刺兽工具的叉,半坡遗址出土骨鱼叉是单刃倒勾,它的发展形式应该是双刃或多刃的,以增强命中杀伤率。它应该是双刃叉这种工具的文字化,
”,更可能是原始狩猎刺兽工具的叉,半坡遗址出土骨鱼叉是单刃倒勾,它的发展形式应该是双刃或多刃的,以增强命中杀伤率。它应该是双刃叉这种工具的文字化, 中的
中的 已是田网的简化,故丫不再是
已是田网的简化,故丫不再是 。捕兽工具需要犀利,故干不如叉。狩猎时代搏兽工具中叉是比较普遍使用的。史字上部偏旁是丫与
。捕兽工具需要犀利,故干不如叉。狩猎时代搏兽工具中叉是比较普遍使用的。史字上部偏旁是丫与 的复合,无非表示田猎工具,甲骨文中又有在叉尖加圆圈者,是文字化以后,不再顾及初形初义的一种增饰。(10)
的复合,无非表示田猎工具,甲骨文中又有在叉尖加圆圈者,是文字化以后,不再顾及初形初义的一种增饰。(10)
徐、陈、胡、王诸家立足于先民生产和生活方式,对“史”字所从之“ ”,“史”之初义及原始职掌的说解,无疑是客观而准确的。“史”之上部为搏击之具,“史”之初义为田猎、作战之人,已为当今学界所普遍接受。故此,从字源上来说,最初之“史”并不能与后世传统意义上的史官发生联系,《说文解字》所言之“记事”并非史官的原始职掌。
”,“史”之初义及原始职掌的说解,无疑是客观而准确的。“史”之上部为搏击之具,“史”之初义为田猎、作战之人,已为当今学界所普遍接受。故此,从字源上来说,最初之“史”并不能与后世传统意义上的史官发生联系,《说文解字》所言之“记事”并非史官的原始职掌。
甲骨文中的“ ”或“
”或“ ”,通常被隶释为“事”“使”“史”三字。隶释为“事”者,有“叶王事”“叶朕事”“我有事”“我亡事”等。王国维《观堂集林》卷六《释史》曰:“殷人卜辞皆以‘史’为‘事’,是尚无‘事’字。”饶宗颐《殷代贞卜人物通考》曰:“徵之豕之卜辞‘叶王事’语,省作‘叶王中’(《戬寿》四六、三,编续五、二二、八及六、二二、一三重)以中为事,是又
”,通常被隶释为“事”“使”“史”三字。隶释为“事”者,有“叶王事”“叶朕事”“我有事”“我亡事”等。王国维《观堂集林》卷六《释史》曰:“殷人卜辞皆以‘史’为‘事’,是尚无‘事’字。”饶宗颐《殷代贞卜人物通考》曰:“徵之豕之卜辞‘叶王事’语,省作‘叶王中’(《戬寿》四六、三,编续五、二二、八及六、二二、一三重)以中为事,是又 、
、 二文并即事字之旁证。”(11)王贵民谓:“在渔猎时代人们的重要生产活动之一是捕获禽兽,故以‘
二文并即事字之旁证。”(11)王贵民谓:“在渔猎时代人们的重要生产活动之一是捕获禽兽,故以‘ ’概括所从之事。”(12)可见,殷人“史”“事”不分,史之用为“事”者,皆取其初义。
’概括所从之事。”(12)可见,殷人“史”“事”不分,史之用为“事”者,皆取其初义。
甲骨文隶释为“使”者,有“使人于画”,“使人于沚”等。胡厚宣以为:“史在卜辞又有用为使者,如言‘使人于画’,‘使人于沚’,‘使人于 ’,‘使人于茜’。画、沚、
’,‘使人于茜’。画、沚、 、茜,皆是地名,使人于某地,亦言因武事而派遣某人使某地之义。……古文字中史、事、使三字不分,史从又持干,或又从斿,象史官奉命出使,所谓‘史乃奉使之义’。”(13)殷商时代,史之用为“使”者,皆为出使之义。
、茜,皆是地名,使人于某地,亦言因武事而派遣某人使某地之义。……古文字中史、事、使三字不分,史从又持干,或又从斿,象史官奉命出使,所谓‘史乃奉使之义’。”(13)殷商时代,史之用为“使”者,皆为出使之义。
甲骨文隶释为“史”者,有“令我史步伐方”“贞在北史亡其获羌”等。此类“史”尽管可以称之为史官,然这一史官却并非后世的文职吏员,而是指武官。胡厚宣《殷代的史为武官说》一文对此论之尤详:“由甲骨文字看来,史官本为武官,并无执笔记事之意。……史官者正是出使的或驻在外地的一种武官。因为史是武官,所以在甲骨卜辞中,常担任征伐之事。如武丁时卜辞或称‘令我史步伐方’。”(14)在殷商时代,史之用为“史官”者,皆为武官。此似已成定论,1980年版的《辞海》及1979年版的《辞源》,均主此说。
可见,至迟在殷商时代,“史”字尚不具备后世史官范畴的任何意义。
据现有文献资料分析,西周之时,“史”已经成为了一种普遍存在的政府文职吏员,传统意义上的史官制度已经发展成熟。然作为史官制度成熟之后的“史”,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其职能也并非一成不变。李宗侗《中国史学史》:
史之初义为史官,而其职权凡三变。总全国一切之教权政权,最初之职务也。盖最古教权与政权原不分,史既掌管一切天人之际的事务,则总理一切政权教权,亦极合理,后渐演变,因政权与教权分离,天人之际属于教权范围,故史官职权缩小,只包括天人之际的事务及其记载而不能参预政权,此第二阶段也。只以著国史为事,此第三阶段。亦即后世对史官之普通观念。(15)
金毓黻亦主张史官职权“三变”说:
凡官之以史名者,既掌文书,复典秘籍,渐以闻见笔之于书,遂以掌书起草之史,而当载笔修史之任。初本以史名官,继则以史名书,而史官之名,乃为载笔修史者所独擅,而向之掌书起草以史名官之辈,转逊谢以为无与,不得不以吏自号矣。史官至此,盖经三变,发展之序,不外是矣。(16)
刘节将中国古代史官分为两种:一种是历史官之史,一种是书记官之史(17)。白寿彝也指出:“从用以称史官的‘史’,到用以称历史记载的‘史’,不知要经过多少年代。”(18)
实际上,就性质而言,李宗侗、金毓黻二家的“三变”与刘节、白寿彝的“两种”之间没有本质性的差别。史官制度成熟之后,最大的变化是专职修史史官的出现,朱希祖《中国史学通论》:
盖后汉之时,尚无历史官专职也。至魏太和中,始置著作郎,隶中书。晋元康初,改隶秘书,专掌史任。梁陈二代,又置撰史学士,历史官之有专职,盖始乎此。由此观之,西周以前,无成家之历史,魏晋以前,无历史之专官,可断言也。(19)
魏晋以后,史官基本上成为了专职修史之官的统称。“史”之义也由“史官”变为了“史书”,如《续后汉书》卷二十八孙权言:“至嗣事以来,省三史诸家兵法,自以为多有所益,……急读《孙子》《六韬》《左传》《国语》及三史。”杜预《春秋左氏传序》中所说的“史”,也尽指“史书”。杜维运《中国史学与世界史学》引巴特菲尔德说:
很多早期的编年史,并非源于恢复既往的动机,……在西方世界以及东方,历史多归功于掌管历法的官吏。在东方(中东,笔者按),历史特别有赖于一类秘书,他们掌管纯为商业性质的记录,最初一点也不是为了绵延历史。(20)
汉以前的中国史官,也如中东的秘书,他们掌管的政务性质的记录,同样也不是为了绵延历史。尽管如此,这些史官所记,经过时间的沉积,便成了旧事和历史,再加整理和增删,则成为了史书,在此背景下,便出现了《尚书》《春秋》《竹书纪年》《左传》等基本上符合后世“史书”标准的历史书,但这并非就意味着汉以前的史官与汉之后的历史官是一回事。
概言之,就“史”之名而言,殷商以前的“史”与西周史官制度成熟之后的“史”,二者是不同的两种概念。当然这只是说殷商以前的史官与西周以后的史官,其“名实”是不统一的,而不是说殷商以前无后来意义上的史官之“实”,如甲骨文中的“作册”与西周的“作册史官”,二者的性质与职能完全相同。两周时代,传统意义上的史官制度发展成熟,并创造了光辉灿烂的诸子文化,奠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秦汉时代,史官制度逐步走向衰退,以至于魏晋以后“史官”之名亦渐为“修史”之官所取代。然而,这并非意味着传统意义上的史官完全退出了历史舞台。实际上,作为文书行政的具体施行者,传统意义上的史官是不可能退出历史舞台的,只不过其名称发生了变化,大多不再以“史”为名罢了。西周至秦汉的史官建制,奠定了中国古代史官制度的基础,史官职能的演变也为中国古代史学的产生和发展开辟了道路。
本书所要研究的,就是从西周到秦汉“史官”之名没有发生变异的这一时间段内的,传统意义上的史官。殷商时代虽有史“名”而非其“实”者,以及汉之后的“修史”之官,皆不在本书的研究范围之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