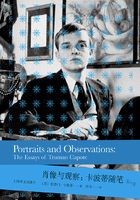
第10章 丰塔纳维奇亚
(1951)
丰塔纳维奇亚,意即古老的喷泉。这就是这座房子的名字。Pace,意为宁静:这个字就刻在门口的石阶上。这里并没有喷泉;而有过的,我想,是一种类似宁静的东西。那是一间玫瑰色的房子,在一个低于海平面的山谷里格外显眼,山谷中长满了杏树和橄榄树。穿过这片水域,在晴朗的日子里,你可以远眺意大利卡拉布里亚半岛的边缘一角。我们的背面是一条碎石路,大多数时候,走在路上的都是些农民,还有他们的驴子和山羊,这条路一直从山的一侧延伸到陶尔米纳镇。住在这里颇有一种坐在飞机上的感觉,又仿佛是轮船在风口浪尖上摇摆:每次放眼窗外,踏上梯田,总会有一种肃穆的感觉,一种悬浮的感觉,就像盘旋于群山之间与海面之上的白鸽。这种广袤无垠将这片景观的细节压缩成为令人倍感亲切的大小——柏树小得如同笔上的羽毛;每一艘由此经过的轮船都能盛放在掌心之上。
破晓之前,慵懒的星星慢吞吞地挪向卧室的窗前,像是一只肥胖的猫头鹰;山间蜿蜒而下的山路上响起了喧闹声,这些小径十分陡峭,时而险峻。那是一户农家正在前往陶尔米纳的集市。不堪重负的驴子跌跌撞撞,驴蹄把路上的岩石踢得四处散落;一路上笑声越来越响,灯笼在摇摆:这些灯笼仿佛是为远方夜间捕鱼的渔夫点亮信号,那些渔夫刚刚还在收网。不久,集市上那些农民和渔民碰面了:他们个子都很小,与日本人差不多,但却很壮实;的确,这种胡桃木般的坚实精壮几乎给人一种生命力旺盛的感觉。如果你问这里的鱼新不新鲜,无花果熟了没有,他们都很善于表演。是的,好极了[32]:他会把你的头按下去闻闻鱼的气味;还会告诉你,这鱼有多么新鲜,眼神里带着一种狂喜和胁迫。我时常被吓得败下阵来;村民可不是这个样子,他们冷冰冰地在那些珠宝大小的番茄中间戳戳点点,闻鱼的气味或是弄伤甜瓜时也从不会犹豫。采购物资、准备餐食走到哪里都是个问题,对此我有所了解;可是在西西里过了几个月,哪怕是最熟练的管家人也会考虑是否该上吊算了——其实也并非如此,是我夸大其词了:那些水果,至少是在它们刚刚成熟的时候,可谓美味无比;鱼的味道也挺不错,当然还有披萨。别人告诉我说,你可以找些能够下肚的肉;我却从没有这么好的运气。同样,蔬菜的可选范围也很小;在冬季,鸡蛋也是件稀罕物。但是当然,真正棘手的事情是我们不会做饭;而且,我恐怕得说,我们的厨子也不会。她是个精力充沛的女孩,长得非常迷人,却有点不合常理:譬如说我们的煤气账单,有时就是个天文数字,那是因为她热衷于将巨大的铅罐用火炉熔化,然后再把熔化了的铅扭成雕刻图案。只要她坚守本行,只做那些简单的西西里菜肴——真的非常简单,非常西西里的菜肴——哎,至少我们就有东西吃了。
不过我还是来说说鸡的事儿吧。不久以前,在西西里度假的塞西尔·比顿到我们家来住。几天以后,他看起来变得有些消瘦:我们明白,要把他调养好,得找出个更合适的办法来。我们就送了一只鸡给他;那只鸡看起来活蹦乱跳的样子,送鸡的是一个农村妇女,有点狡黠,住在山的高处。这是一只巨大的黑色禽类——要我说它一定是很老了。不对,那个女人说,不是老,就是大而已。先把鸡的脖子拧断,然后我们的厨子G就把它放在水里煮。大约十二点钟的样子,她跑过来说,那只鸡还是煮不烂[33]——换句话说,硬得像钉子。我们建议她再试试,然后就坐在阳台上,摆开几个酒杯,准备就在那儿等候。几个小时过去了,几杯酒过后,我跑去厨房,发现G的情况非常危急:她把鸡煮过以后,先是烤,继而是炸,现在呢,绝望之中她正在煮第二遍。尽管没什么别的东西可吃,我们原本也绝不应该把这样的东西端上台面的,因为当它被摆放在我们面前时,我们不得不把视线移至别处:这堆热气腾腾的东西,点睛之笔当属这只可怜的大鸟被拧断的脑袋,它干枯的眼睛瞪着我们,变黑的鸡冠尚未分离。来我们家之前,塞西尔一直跟他的几个朋友待在岛上,那天傍晚,他迫不及待地告知我们,他是非回那帮朋友那儿去不可了。
我们第一次租下丰塔纳维奇亚时——那是在春天,四月——山谷很高,周围有绿色的大麦,蜥蜴在麦秸上竞相爬行。西西里的春天始于一月,此后逐渐汇聚成一捧国王的花束,一座巫师的花园,里面的一切都在竞相绽放:溪水浇灌的薄荷萌发出嫩芽;野玫瑰爬上了枯木枝头;纵然是无情的仙人掌也开出了娇嫩的鲜花。艾略特笔下的四月是气候最恶劣的时节:可这里不是这样。这里就像是埃特纳山顶上的积雪那般明亮。孩子们沿着山坡攀爬,将花瓣装进一个个大袋子里,为圣徒纪念日做着准备;渔民们从这里经过,鱼篓里装着珍珠色的鱼,耳朵后面塞着天竺葵。五月,转眼到了暮春:日照变得更加强烈;你不会忘了非洲离这里只有区区八十英里之遥;秋日的色彩落在整片土地上,宛若古铜色的影子。六月之前,大麦丰收的时节到了。我们怀着一种惆怅的心情聆听镰刀在这片金色的田地里挥舞的声音。等到活干完的时候,我们的房东,也是这片麦田的所有者,为刈麦人举行了一个聚会。这里面只有两个女人——一个是年轻的女孩,坐着在带孩子,另一个是老妇人,是这个女孩的祖母。那个老妇人喜爱跳舞;她打着赤脚,跟一群男人一起舞步旋转——没人能够让她停下来歇息,她在舞曲的中段会冲上前去,一把给自己抓个舞伴。那些轮流拉着手风琴的人,也全都加入到了跳舞的行列,这是西西里乡村的风俗。这是最好的聚会:有跳不完的舞,更有喝不完的酒。后来,我精疲力竭地上床睡觉,这时忽然想起了那个老妇人。在一整天的劳作与一整夜的狂舞以后,她现在就得动身,爬过五英里的山,回到山上的住所。
那是一段通往一片或数片海滩的徒步旅程;这里的海滩有好几处,全都是卵石众多,而其中只有一处——马萨罗——居住的人较多。最引人入胜的是美丽岛,那是一个有人看护的小海湾,里面的海水就像桶里的雨水一样清澈;你只需一路向前,走上一英里半的路程便可以到达;想要再次靠近需要一点技巧。有几次我们是先走到陶尔米纳,再搭乘汽车或者计程车。但大多数时候,我们都是步行。你在三月到圣诞节期间还可以游过去(反正一些壮汉是这么说的),但我坦承,我起初对此并不怎么热衷,直到后来我们买了潜水面罩。面罩有个玻璃透视圆盘,还有呼吸管,可以在你潜水的时候关闭。在岩石间静静地游,你仿佛发现了一个新的视角:在水下的暮色之中,一条发着磷光的鱼向你迫近,近到让你不由一惊;你的影子飘过一片貂皮色的海草;蓝色和银色的水泡从某种长腿沉睡物中升起,那东西躺在一片吹着气泡的海葵丛中,就像是一阵音乐的风在将它们拂动;那些海葵——紫色凝胶长成的爪哇蔓。当我爬上海滩时,感觉上面的世界是那般静止、臃肿。
如果我们不去海滩,那离开住所只有一条别的理由:到陶尔米纳购物,然后在广场上享受一顿美餐。陶尔米纳实际上是纳克索斯岛延伸出来的部分,纳克索斯岛是西西里最早建立的希腊城市,自公元前336年起存在至今。歌德于1787年到此探险,曾经如此描述这里:“我现在就坐在剧院最高处的观众曾经坐过的位置,必须得承认没有任何一位观众在任何一家剧院欣赏过如此令人叹为观止的景致。右手边一侧,在高高的岩石上,城堡直入云霄;往远处看,整座城市就坐落在你的脚下,尽管所有的建筑都建于晚近的年代,而且看上去也很相像,但毋庸置疑,它们代表了一种传统。再往远处,我的目光落在埃特纳火山那一整条长长的山脉之上;接下来在左手边,我一眼可以望到卡塔尼亚的海滩,乃至锡拉库扎[34],而后宽阔的视野被火山冒出的浓烟所阻挡,但那却并不可怖,因为那种气氛带着一种柔化的效果,使它看上去比实际上更加悠远和温和。”据我所知,歌德描述的制高点就在希腊式剧院——时至今日,这座悬崖顶上令人叹为观止的遗迹偶尔还会上演戏剧和音乐会。
陶尔米纳的景致在歌德的描述中可能有些被夸大了;不过这的确是一座奇异的城镇。战争期间,这里曾是德军统帅凯塞林的司令部,因此这里也遭受过同盟国的轰炸,但破坏程度不大。尽管如此,这场战争还是给这座城镇带来了创伤。直到1940年前,除了卡普里以外,这里一直都是法国里维埃拉[35]以南的地中海旅游胜地中最成功的。尽管美国人从不来此地,或者至少不成规模,不过这个地方在英国人和德国人当中还是享有相对不错的口碑。(一个英国人在其1905年出版的《西西里旅行指南》一书中写道:“陶尔米纳充斥着德国人。有些酒店里面有几桌专门就是为德国人开辟的,因为其他国家的人不喜欢和德国人坐在一起。”)如今,德国人根本不可能去旅游;由于外汇管制,英国人也不可能去。去年,圣多梅尼科的入住率从未超过四分之一。这里原本是一所古老的女修道院,十九世纪末期被改建成了一座奢华无比的酒店。大战以前,你必须提前一年预定。今年冬天,或许是为了吸引国际游客,这个城镇使出了最后疯狂的杀手锏——他们开了一家赌场。我祝他们好运:总得有人来买那些堆积在科尔索沿路商店里的手工编织帽、手提包,以及诸如此类的蹩脚货。于我而言,陶尔米纳只要依照它原本的样子就挺适合我的;它具备旅游中心的舒适(有自来水,有提供国外报纸的商店,有能够买到优质马提尼酒的酒吧),但没有游客。
这座城镇不大,夹在两扇城门中间;在第一扇城门——墨西拿港——附近有一座小广场,绿树成荫,还有喷泉和石墙,村子里一些游手好闲的人沿着石墙列成一排,好似电话线上休憩的小鸟。我曾数次步行穿越陶尔米纳,第一次走过这里时,我惊呆了:只见一位老者靠在墙边,穿着一条天鹅绒长裤,裹着一席黑色披风;他的帽子是橄榄色的浅顶软呢帽,折成了一个三角形的冠状,帽子边缘的阴影投在他的脸上,那张脸宽阔、蜡黄,有些像蒙古人。这简直是令人吃惊的戏剧人物造型,真的就是这样,后来仔细一看,我方才意识到,他就是安德烈·纪德[36]。整个春天和初夏,我经常在这里见到他,不是坐在无人察觉的角落,与普通的老人并无二致,就是随意看着那些喷泉,那身披风恰似莎士比亚笔下的那种风格,他看起来是在观察自己在水中的倒影:青年无心,老人无力。[37]
在这些过多的装点之下,陶尔米纳其实就是一座普通的城镇,而这里的人们也有着普通的理想和职业。然而,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尤其是年轻人,具有一种在我看来是酒店服务生的心态,他们将生命奉献在酒店里,他们知道所有的东西都是过眼云烟,所以一定不能太过投入,因为友谊是只有几天光景。这些年轻人可以说是住在“城外”的;他们对外国人很感兴趣,主要倒不是因为有利可图,更多的是因为有机会结识英国人和美国人,他们认为这样能够使他们与众不同;他们当中大多数人天生都有说几种语言的天赋,他们整日在披萨酒馆里和那些游客聊天,彬彬有礼,装腔作势。
这是一个美丽的广场,以一个海岬为中心,从这里可以看到埃特纳火山和大海。托伊撒丁岛上的驴,拖着精心雕刻的货车,正昂首阔步地经过这里,它们的铃铛一路响个不停,货车里面装满了香蕉和橙子。每逢礼拜天的下午,镇里的乐队都会举行音乐会,有些古怪却令人印象深刻,还有摩肩接踵的散步人群;如果我在那里,总是会留心那个屠夫的女儿,她身材健壮,肌肉结实,整个礼拜都在挥舞着杀猪刀,还有另外两个男的,挺凶残的样子;而到了礼拜天,她戴上头饰,抹上香水,穿着两英寸高的高跟鞋,身旁陪伴的是她的未婚夫,一个纤细的男孩,个子还不及她的肩膀,她的身上有一种浪漫,一种得胜的气质,怔得那些搬弄是非的舌头不敢出声:她带着一种傲慢与自信,那正是散步时应有的心态。偶尔,云游到此的艺人会出现在广场上:像山羊一样从大山里来的男孩,演奏着覆盖着皮毛的风笛,旋律就像是高低变换的唱腔,不绝于耳;或者是在春天,会有一个儿童歌手来表演,他每年靠家人的帮助在小岛上巡回演出,他们一家就以此谋生:他的舞台就是树枝,在那里,他的头向后甩着,嗓子发出颤音,唱着让人心碎的高音,他就一直这么唱着,直到声音嘶哑,变成最悲切的低吟。
说到购物,烟草店是我动身去这个国度之前的最后一站。在西西里,所有的烟草商都是些暴躁易怒的家伙。他们的店面通常都是人满为患,但是几乎没有顾客会购买超过三到四包的散装烟:带着一种拮据的庄重,这些饱经沧桑的男人放下几个可怜的里拉,然后仔细地端详着那几根派发给他们的香烟或是细雪茄——烟草店之行看上去是他们一天当中最重要的时刻;或许这就是为什么他们那么不愿意放弃他们在队列中的位置。这里大概有二十种不同的西西里报纸;这些报纸当中,比较好的那些就挂在烟草店的门前。一天下午,我刚刚进城就开始下雨了。严格意义上讲,这场雨并不算大;不过,街道上依旧是空寂无人,直到我差不多走到一家烟草店的时候——人群聚集在此,高声惊呼着报纸头条,报纸在雨中舞动。一些小男孩,光着头,一副三心二意的样子,正站在一起,头凑在一块儿,而一个年长一点的男孩,手指着一张巨幅照片,大声地念着,照片里面的人四肢伸开,倒在一摊血泊中:朱利亚诺,死于卡斯特尔韦特拉诺。可悲啊,可悲啊,可惜啊,遗憾啊,年长者这样说道;年轻人则一言不发,而两个女孩到了店里,出来的时候,手里拿着几份《西西里报》,报纸的头版是一张毙命的绑匪巨幅肖像;这几个女孩把报纸护好,以免淋湿,她们手拉着手,一步一滑地在泛着光的大街上走着。
转眼到了八月;太阳还没升起,我们就已感受到了它的存在。很奇怪,在这个空旷的山头上,白天比晚上还要凉爽,因为通常情况下,不期而至的微风会把海水吹走;而太阳下山的时候,风又调转了方向,朝着海水的方向吹去,那是吹往南边希腊和非洲的方向。这个季节,属于无声的绿叶,属于流星,属于红月,也是大蛾出没和蜥蜴夏眠的季节。无花果裂开了,李子丰满了,杏仁也变硬了。一天早晨,我醒来后,在杏树林里听见了竹竿击物的声音。山谷中,山脚下,上百名农民,以家庭为单位劳作,正把杏仁敲落树下,再从地上拾起,收在一块儿;他们还对着歌,一人领唱,众人附和,歌声像是摩尔音乐和弗拉门戈舞曲,他们的歌没有起始也没有终结,然而却包含着劳作、热情与丰收的元素。这一周以来,他们一直在忙着收获,每天的放歌都会达到一种有失理性的程度。我没法去想它;我的心中感受到这样一种压倒一切的过盛的生命力。最终,在最后这段疯狂的日子里,这炽热而美好的歌声仿佛是从海上传来,从杏树的根里传来;你就好像迷失在回音阵阵的洞穴里,而当夜幕降临,万籁俱寂,即便此刻,我也能够在沉睡的边缘听到那些歌声,纵然你竭力想把它拒之门外,但它似乎依然想要讲述一个令人怜悯而痛苦的故事,想要把一些可怕的事情向你告知。
在丰塔纳维奇亚,并没有太多人造访我们;对于那些临时访客来说,这段路未免太远,日子就这么一天天地过去,没人敲我们的门,除了那个卖冰激凌的小男孩。小男孩一头金发,头脑机灵,虽然只有十一岁,却有着一副学者风范。他的姑姑年轻貌美,肯定可以算得上是我认识的最具吸引力的女孩之一,我也经常和这个小男孩聊起她的事。我想知道,为什么他的姑姑A就没人追求呢?为什么她老是单独行动,从不参加舞会或者周日的散步呢?那个卖冰激凌的小男孩说,那是因为他的姑姑瞧不上本地男人,所以她总是闷闷不乐,一心只想着去美国。或许是吧。但是我自己倒是觉得这可能是因为她自家的男人寸步不离地看护着她,以至于没人敢和她接近。西西里的男人对于他们的女人能做或是不能做什么有着很大的话语权;苍天在上,女人们自己也似乎喜欢这样。譬如说我们的厨子G,她今年十九岁,有个不比她大多少的哥哥。一天早上,她看起来嘴唇裂了,眼圈也黑了,胳膊上有被刀划伤的疤痕,从头到脚,都有瘀伤。这简直是太不可思议了;她早该进医院了。G露出不太自然的微笑说道,好吧,是她的哥哥打了她;他们吵架了,因为他觉得她去海滩去得太频繁了。当然,我们认为这个反对的理由有点奇怪;她是什么时候去的海滩——夜里吗?我劝她不要在意她哥哥的话,他的行为太过野蛮,太过龌龊。而她的回答是,事实上,我应该管好自己的事;她说她哥哥是个好人。“他人长得好看,交了很多朋友——只是对我野蛮。”即便如此,我还是到我们的房东那里告状,说应当告诫她的哥哥,我们不能容忍他的妹妹回来工作的时候是这副模样。他看上去有些不解:我为什么要责怪她的哥哥?话说回来,哥哥有权管教妹妹。当我跟那个卖冰激凌的小男孩说到这件事的时候,他也赞同房东的说法,而且一本正经地说,如果他也有个妹妹不听他的话,他也同样会教训她一顿的。八月的一个傍晚,此时的月亮大得出奇,我和那个卖冰激凌的男孩进行了一次短暂却惊悚的对话。他问,你对狼人怎么看?你天黑了害怕出门吗?事实上,我那天刚刚听过一个关于狼人的恐怖故事:一个深夜走路回家的男孩,自称是被一个嚎叫的动物袭击了,那是个四脚着地的人。可我笑了起来。你不相信有狼人,对吧?哦,我相信。“陶尔米纳曾经有过许多的狼人,”他说着,灰色的眼睛镇定地望着我;然后,轻蔑地耸了耸肩,“现在只剩下两三只了。”
就这样,秋天来了,就在这样的时刻到来,手鼓似的风,幽灵般的烟雾在黄色的树林里穿梭。这是葡萄丰收的好年景;空气中弥漫着芳香,那是葡萄的味道,它们落在满地落叶的松软土地上——新酒的原料。六点钟,星星探出了头;此刻坐在露台上喝一杯鸡尾酒,还不算太冷,明亮的星光下,我望着羊群从牧场下山,绵羊们个个长着一张巴斯特·基顿[38]的脸,山羊们成群移动时发出拉拽干柴的声音。昨天有人给我们带来了一货车的木头。所以我也不用担心冬天来临:还有什么比坐在火堆前静候春天的到来更让人值得期盼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