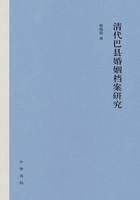
第三节 巴县婚姻档案的研究现状
近年来,地方档案和文献的价值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尤其是清代地方县级政权档案成为了研究的热点。就四川而言,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巴县档案、南部档案、冕宁档案,学界关注度高,研究成果丰硕。其中,巴县档案和南部档案都获得了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的立项建设,在研究的广度和深度方面进一步加强。2011年,以吴佩林教授为首席专家申报的“清代南部县衙档案整理与研究”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立项(批准号:11&ZD093),该课题是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与南充市档案馆联合申报的,被视为校(院)馆合作的典型。2016年,四川大学陈廷湘教授领衔申报的课题“清代巴县衙门档案整理与研究”也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立项(批准号:16ZDA126)。除国家社科重大项目之外,近几年立项的与巴县档案有关的其他类别的项目也比较多。其中,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主要有:西南科技大学廖斌主持的“清代四川地区刑事司法制度的变迁与演进——以巴县司法档案为例”(2007年),四川大学谯珊主持的“控制与整合:清代重庆城市管理研究”(2009年),西南政法大学梁勇主持的“移民、国家与地方权势——以清代巴县为例”(2011年),张晓霞主持的“清代巴县婚姻档案研究”(2013年),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龚义龙主持的“清代巴蜀移民社会研究”(2013年),四川大学周琳主持的“清代州县档案中的市场、商人与商业制度研究”(2014年);省部级以上项目主要有:西南政法大学梁勇主持的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清代移民社会地方基层制度研究——以巴县客长制为中心”(2007年),湖州师范学院史玉华主持的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清代州县财政与基层社会——以巴县为例”(2007年),中国政法大学李青主持的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清代档案与民事诉讼制度”(2008年),太原师范学院陈亚平主持的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18—19世纪重庆商人的实践历史研究:以巴县档案为中心的考察”(2010年),广东惠州学院魏顺光主持的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清代中期坟产争讼问题研究——基于巴县档案为中心的考察”(2011年),西南政法大学刘熠主持的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清末底层兴学与社会变迁——以四川省为考察对象”(2013年),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傅裕主持的重庆市社科规划项目“基于巴县档案的会馆研究”(2014年)。海外的还有京都大学名誉教授夫马进主持的日本学术振兴会资助项目“‘巴縣檔案’を中心として見た清代中國社會と訴訟·裁判——中國社會像の再檢討”。
专门以巴县档案为中心的学术会议很少,主要是一些有关地方档案与文献、古代史、法律史、文化史、社会史等领域的学术研讨会,也有学者提交与巴县档案有关的论文进行讨论。比如:2012年以来西华师范大学、曲阜师范大学先后举办的四届地方档案与文献研究学术研讨会,2012年11月在海南海口举办的中国法律史学会学术年会,2013年8月成都市龙泉驿区人民政府主办的龙泉驿百年契约文化学术研讨会,2013年10月在四川成都召开的第二届巴蜀文化与湖湘文化高层论坛,2015年10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国优秀传统法文化与国家治理学术研讨会暨庆祝研究院(所/中心)成立三十周年并中国法制史专业委员会年会,2019年4月河南大学法学院主办的中世纪与近代早期法律治理与国家形成国际论坛等等学术会议,都有学者提交与巴县档案相关的论文。日本同志社大学文学部成立了巴县档案读书会,该读书会从2010年7月起基本每月举办一次,一直持续至2015年8月。在此期间,主要围绕乾隆朝和同治朝的巴县档案缩微胶片,各自选择史料细读并研讨。[34]
通过知网“文献”(包含期刊论文、报纸论文、硕博论文)进行检索,检索截止时间:2020年1月31日;检索项:主题,检索词:“巴县档案”或含“巴县;档案”(精确匹配),共获得文献总数212篇。[35]在这212篇文献中,可以看出对巴县档案进行研究的文献分布时间呈现出先冷后热的态势。2000年之前40多年的时间共发表论文28篇,其中1958年—1980年3篇,1981年—1990年13篇,1991年—2000年12篇;2000年至2019年的19年时间相关论文数量急剧增加,共有184篇,其中2001年—2010年56篇,2011年—2019年128篇。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2000年之前学界对巴县档案的关注度不够,2000年之后对巴县档案的研究呈愈来愈热的势头,尤其在最近的10年体现得更为明显。这个趋势与整个学界对地方档案与文献关注程度的变化是一致的。随着“眼光向下”研究范式的流行,再加上如巴县档案、南部档案、冕宁档案、孔府档案、宝坻档案、清水江文书、徽州文书等越来越多的地方档案与文献被大家所熟知,其作为“第一手史料”的价值和功用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为学界对基层社会的深入研究提供了可能。
就中国知网收录的相关论文来看,2000年之前的28篇论文作者主要是四川省内的专家学者,集中分布在四川省档案馆、四川大学历史系,而四川以外的学者对巴县档案的关注度还不高,研究成果较少,这与巴县档案的保存与流转是密不可分的。如前所述,四川大学历史系和四川省档案馆先后承担了对巴县档案的保存和整理工作,对巴县档案进行研究有地利与资料之便利。但需要注意的是,美国学者早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就认识到巴县档案的重要价值,纷纷到四川省档案馆查阅巴县档案,开展相关研究。1985年至2006年,到四川省档案馆利用巴县档案的外国利用者共1977人次,查阅档案139232卷次,复印67245页。[36]泽林早在1986年发表了利用巴县档案进行研究的论文;白瑞德1994年完成博士论文,2000年出版专著;上个世纪90年代,唐泽靖彦在四川省档案馆查阅巴县档案长达半年之久;苏成捷1994年完成博士论文,2002年出版专著;美国北卡罗来纳州州立大学历史系教授欧中坦主要致力于清代法制史与法律史的研究,分别于1993年、1994年、1996年三次到四川省档案馆查阅巴县档案;美国密苏里大学教授魏达维为研究清代家族的分家问题,于1995年到四川省档案馆查阅巴县档案。[37]之后还有很多的美国中青年学者,如白莎、戴史翠等一直都在利用巴县档案进行研究。从中可以看出,美国学者对巴县档案关注早,研究成果丰硕,其中又尤以黄宗智教授为核心的加州大学洛杉矶校区中国法律史研究群最为集中,代表人物主要有黄宗智、白凯、白瑞德、苏成捷、唐泽靖彦。
就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研究所涉及的范围和领域非常广泛,主要可以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是有关巴县档案文本的文献学、档案学及其他相关研究,另一部分是利用巴县档案进行的具体问题研究,主要包含基层社会治理、农业生产和土地关系、工商业、司法、社会文化生活以及教育等方面的研究。[38]
目前有关婚姻方面的研究成果,不胜枚举。其中,有关婚姻史方面的著作主要有:芬兰著名的社会学家E·A·韦斯特马克的《人类婚姻史》。此书在列举大量事实的基础上,结合各派学者的论点和论据,对人类婚姻史进行了深入而细致的研究。[39]该书于1891年在伦敦用英文出版,先后被译成多种文本,并被西方学术界奉为社会科学的经典之作,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也曾多次提及。尽管此书出版至今已有100多年的时间,但其中的很多具体观点仍然具有很强的学术意义,值得深入研读。陈顾远的《中国古代婚姻史》(商务印书馆1925年版)和《中国婚姻史》(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被称为“婚姻史领域的担纲之作”。尤陈俊在《法学家陈顾远笔下的〈中国婚姻史〉》一文中对此书有如下的评述:“距其初版之日七十多年以后,细读陈顾远所著的《中国婚姻史》一书,窃以为,此书依然不愧为中国婚姻史研究领域中的经典之作”,但他也同时提到了此书的时代局限性主要体现在资料方面。该书在资料上主要依靠正史并辅以一些笔记述闻类史料,因此其关注点主要集中在各朝社会的中上层,而对帝制中国时期社会下层的情形稍嫌叙述薄弱。就婚律而言,对这些法律规范的真实运作情形,未能再利用更多的资料进行深入分析。[40]陈鹏的《中国婚姻史稿》上起春秋,下至明清,对我国封建社会婚姻法制的起源、演变与发展进行了非常细致而深入的论述,内容非常丰富,资料也非常详实。[41]我国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安徽师范大学陈怀荃教授评价说,像这样的婚姻法制专史,到目前为止,在我国学术界,尚属不可多得的力作。[42]
以上有关婚姻史的著作,论述的时间范围和地域范围都很广,并不局限于某一个特殊的年代,也不专指某一个特定的地方。[43]专门对清代婚姻关系进行研究的主要有郭松义、定宜庄、王跃生、钱泳宏、吴正茂等人的著作。[44]这些著作大都利用了第一历史档案馆刑科题本中的婚姻家庭命案档案。刑科题本档案并不局限于某地,而是全国各地相关命案的汇集,对于了解全国宏观层面的婚姻冲突及与婚姻和家庭相关的其他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如果要深入了解某地的婚姻家庭情况和更为详细具体的地方实际状况,则还需要利用当地的微观材料。
以南部档案的研究状况为例,近年以妇女婚姻为主题的期刊论文较多,[45]著作主要有如下两部:赵娓妮的《审断与衿恤:以晚清南部县婚姻类案件为中心》,[46]以南部档案中涉及婚姻关系的案件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对“悔婚”“买休卖休”“奸情”三类案件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讨论。经过研究,赵娓妮认为,律例并不是州县案件裁断的唯一依据,也不是最高依据,知县在审断实践中最为明显的特点是“从轻处断”。吴佩林在《清代南部县衙档案研究》第四编“清代南部县之婚姻与社会研究”中,以南部档案为主要研究对象,对南部县的婚姻常态、南部县婚姻秩序中有违伦理的婚姻行为(以嫁卖生妻为例)、南部县的婚姻“问题”及基层社会和官方对“问题”的应对进行了分析,并阐释了官与民、法律与习俗、中央与地方的互动关系。[47]
目前,国内学者以巴县婚姻档案为主要支撑材料的研究成果主要有如下一些:梁勇根据巴县档案的卖妻案件记录,认为清代巴县的丈夫并不能随意卖妻,如果不经过妻子娘家同意将妻子嫁卖,就会被妻子娘家追问、斥责,一旦告到衙门,地方官会对卖妻人进行惩罚。[48]张志军也对巴县档案中的嫁卖类别和原因进行了探讨,认为清代巴县的县官是反对嫁卖妻子的。[49]陈翔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对巴县婚姻档案中的庚帖、婚书和喜课进行了释读和分析,展示出巴县档案的“民间性”。[50]吴佩林主要运用巴县档案和南部档案,对清末新政时期四川官制婚书推行的背景、意图、实际效果以及失败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和研究。[51]台湾政治大学李清瑞以巴县档案的拐案记录为中心,辅以中央档案中的拐案记载、地方县衙的审判制度和地方档案中的非拐案记录等资料,集中剖析了清代乾隆年间四川拐卖妇女的案件及所反映出来的各种社会问题。[52]杨毅丰以巴县档案为基础,对四川妇女改嫁原因、特点以及由此而引起的财产纠纷进行了论述。[53]高钊对咸丰朝巴县婚姻离异的类型进行了探讨,提出基层长官判案时并不一定与中央律法条规一致,具有较强的灵活性。[54]刘艳丽以巴县档案、徽州文书等材料为中心,对清代妇女的法律地位进行了探析,认为清代妇女的地位依然非常卑微。[55]周彦冰对清代巴县妇女尤其是已婚妇女在家庭中的权益和地位进行了分析。[56]刘欢欢以巴县档案和南部档案为基本材料,对清代下层妇女离家出走现象进行了专门考察。[57]周琳、唐悦对乾隆末年的一桩离婚案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探讨,主要涉及到该案中的女主角秦氏与丈夫徐以仁离婚的故事。[58]
美国学者对婚姻与妇女的问题关注早,研究也很深入,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黄宗智、白凯、苏成捷等人的成果,均利用了大量巴县档案。其中,黄宗智《清代以来民事法律的表达与实践》(北京:法律出版社,2014年)三卷本之《法典、习俗与司法实践:清代与民国的比较》中对清代妇女婚姻奸情进行论述,其中用到了从巴县和宝坻县搜集的131件清代婚姻奸情类档案。白凯《中国的妇女与财产:960—1949》(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使用了1760年代至1850年代的巴县档案,以及宝坻县档案、台湾地区淡水分府新竹县档案、江苏太湖厅档案等5个不同司法辖区的档案。苏成捷利用巴县档案对性、妇女、婚姻等问题进行研究,专著《中华帝国晚期的性、法律和社会》使用巴县档案500件,在学术界获得极高的评价。他还专门对清代底层社会的一妻多夫婚姻尤其是“招夫养夫”现象和卖妻交易进行了研究,认为不管是一妻多夫还是卖妻,都是贫穷所引发的一种生存策略。[59]日本学者也对清代巴县档案中的妇女诉讼问题有所研究。日本关西学院大学文学部水越知以同治朝巴县档案为中心,对清末的夫妇诉讼与离婚问题进行了探讨。[60]日本东京外国语大学臼井佐知子以巴县档案、徽州文书、太湖厅(理明府)档案、顺天府档案为基本材料,对清代妇女诉讼涉及到的范围进行了分析,认为“妇女作为原告的案例,主要集中在承继、家产、夫妻纠纷和债务等方面”。[61]
巴县档案数量浩大,在研究某一个具体问题时,很难做到穷尽所有档案,而基于部分档案得出的研究结论可能并不是非常客观,甚至还会存在盲人摸象的情况。有学者提出这样的担忧:对同一问题的研究可能会因为研究者所收集的资料并不重叠而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这个担忧是有一定道理的,这种现象也是有可能存在的。如前所述,巴县婚姻档案共有6000余卷,其中的案例涉及到婚姻的方方面面,是研究清代巴县婚姻关系及其相关问题的第一手史料。2010年,四川省档案馆选送的“清代四川巴县档案中的民俗档案文献”成功入选《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这份民俗档案就是巴县婚姻档案中测算结婚吉期的“喜课”。可见,巴县婚姻档案具有很强的民间性,特色明显,值得进行深入全面的研究。而现有的以巴县婚姻档案为中心的研究成果,大都利用巴县档案从某一个方面对婚姻和妇女问题进行论述,或关注嫁卖生妻,或关注离异改嫁,或集中对妇女拐卖问题进行探讨,还有一些领域没有涉及或者涉及很少,缺少系统全面的研究成果。为了能更加深入系统地对巴县婚姻档案进行研究,并尽量避免出现资料不全所带来的弊端,本书对6000余卷巴县婚姻档案进行了系统的阅读与梳理。在此基础上,从形式和内容两大方面进行论述和研究。第一章至第四章主要从巴县婚姻档案的文种、语言与称谓、官代书戳记与画押以及巴县婚姻档案所呈现的抱告制度与诉讼实态进行分析和论述,第五章至第十章主要对巴县婚姻档案的内容进行具体探讨,分为童养婚档案研究、退悔婚档案研究、嫁卖生妻档案研究、孀妇再嫁档案研究、犯奸档案研究、卖娼档案研究等六个方面。
[1] 巴县,老县名,重庆主城区的古称,北周武成三年(561)始称巴县。1995年撤县建区,巴县改为巴南区,巴县至此消失。清代重庆府隶属四川省,故称巴县为“四川巴县”,1997年中央把重庆市划为独立的直辖市,不再隶属四川省。文中提到的“四川巴县”特指清代的四川和巴县,“巴县档案”也特指清代的巴县档案。
[2] 关于清代巴县档案的称谓,迄今并不统一,主要有“清代巴县县衙档案”“四川巴县清代文书档案”“清代四川巴县档案”“清代巴县档案”几种,文中简称为“巴县档案”。
[3] 关于巴县档案的起始时间,有多种说法。栾成显在《明清地方文书档案遗存述略》一文中提到,巴县档案的时间跨度是乾隆元年(1736)至宣统三年(1911)。《四川省档案馆指南》(四川省档案馆编,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2001年)就有两种说法:第18页提到巴县县府全宗的起始时间是乾隆十七年(1752),而第19页又提到清代巴县档案上自康熙九年(1671)。认为巴县档案起始于乾隆十七年的还有杨林,见杨林:《关于巴县档案起始时间》,《历史档案》1990年第3期,第135页。认为巴县档案起始于康熙九年的还有陈代荣和吴佩林。见陈代荣:《巴县档案今昔》,《档案工作》1984年第4期;吴佩林:《清代县域民事纠纷与法律秩序考察》,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5页。张仲仁则认为巴县档案起始时间为乾隆二十二年(1757),见张仲仁:《一批宝贵的档案“开花结果”了》,《档案工作》1958年第4期。
[4] 此数据来源于四川省档案馆主编的一系列档案汇编,主要见于:四川省档案馆编:《四川省档案馆指南》,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2001年,第19页;四川省档案馆、四川大学历史系主编:《清代乾嘉道巴县档案选编》(上册),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89年,序言;四川省档案馆编:《清代巴县档案整理初编·司法卷·嘉庆朝》,成都: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18年,序言。但也有学者提出不同的观点:陈代荣认为,巴县档案共有110023卷,见陈代荣:《巴县档案今昔》,《档案工作》1984年第4期;吴佩林对四川省档案馆馆内案卷数进行统计之后发现,巴县档案现存数量共计114865卷,见吴佩林:《清代县域民事纠纷与法律秩序考察》,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5页。
[5] 耘耕:《一块待开垦的清代法律史料园地》,《现代法学》1991年第3期。
[6] 张仲仁:《一批宝贵的档案“开花结果”了》,《档案工作》1958年第4期。
[7] 赵彦昌、苏亚云:《巴县档案整理与研究述评》,载赵彦昌主编:《中国档案研究》(第五辑),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2018年。
[8] 这11个大类并不是巴县档案形成时的最初分类体系,而是当年四川大学历史系进行整理的结果。当时的整理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仓促进行的,打乱了原有按房进行分类的来源体系,改用事由原则即案卷内容进行分类。这对档案本身来说是一场浩劫,因为档案原本的历史联系被打乱,同一来源的档案被人为分割开来,损失很大,也给现有的管理和利用带来了诸多的不便。但在当时的情况之下,能够将巴县档案进行抢救并集中保管起来,也不得不说是后人之福了。
[9] 伍仕谦:《一座内容丰富的文献宝库——巴县档案》,《文献》1979年第1期。
[10] 四川省档案馆编:《四川省档案馆指南》,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2001年,第26页。
[11] 祖晓敏:《近二十年来明清婚姻问题研究述评》,《安徽冶金科技职业学院学报》2005年第2期。
[12] 黄宗智曾经提到,戴炎辉整理淡新档案时所用的分类体系,是将通奸和妇女拐卖案归入刑事案件的。中国内地的档案工作者并没有用现代的法律范畴来整理巴县档案,只是按照其内容进行归类。他本人也将这两类案件都归入婚姻的范畴。见[美]黄宗智:《清代的法律、社会与文化:民法的表达与实践》,北京:法律出版社,2014年,第194页。本书将这两类案件也归入婚姻档案的范围,分别在“犯奸档案研究”和“嫁卖生妻档案研究”两章进行讨论,原因有二:第一,通奸案和妇女拐卖案本就与婚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类案件发生的背景与嫁卖生妻、孀妇再嫁等案件发生的男多女少、性别比例失调的社会背景相同;第二,现存巴县档案的分类体系中,妇女是单独的一个类别,其中绝大多数案件与婚姻有关,当然也包括通奸案和妇女拐卖案。
[13] 四川省档案馆编:《四川省档案馆指南》,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2001年,第19页。目前缩微胶卷已经不能对外出售。
[14] 关于巴县档案的保存状况,四川省档案馆陈翔也曾提到:“巴县档案素以数量众多闻名,但这并不意味着巴县档案卷卷都是完整的。抗战时期,巴县档案藏于重庆市樵坪关帝庙,无人看守,乞丐常以档案当引火之用,损失不小。因此,巴县档案中有许多残卷,无头无尾,难于索解,被同仁戏称为‘天书’。”见陈翔:《庚帖、喜课与民间婚姻——四川省档案馆所藏巴县婚姻纠纷档案释读》,《中国档案》2008年第7期。
[15] 吴铮强发现龙泉司法档案中存在屡票不案的情况,出现这种情况最主要的原因不是多次堂审,而是差役票传不到、两造反复催呈所致。他认为,凡县官认为诉讼内容有虚构嫌疑而勉强受理并签票传讯的案件,在呈词上的批语就会表现出较为消极的态度,而这种消极态度势必影响到差役的态度。见吴铮强:《龙泉司法档案所见晚清屡票不案现象研究》,《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黄宗智对巴县档案、宝坻档案、淡新档案研究的结果表明,在绝大多数情况之下,诉讼记录在正式开庭之前即已中止,即绝大多数案件并没有进行到堂审这一个环节,主要原因是堂审之前诉讼当事人之间已经通过各种方式自行解决了争端,或者当事人和官府并没有对此案件进行积极追理,以至于在告状之后并无下文。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受贿的衙役故意拖延或者作弊,报称某方失踪或者因病无法到案参加堂审等等。黄宗智对巴县308个案件进行了统计,真正由法庭审决的只有31.8%,民间解决的17.2%,记录不完整的高达49.4%。见[美]黄宗智:《清代的法律、社会与文化:民法的表达与实践》,北京:法律出版社,2014年,第109页,第156页。
[16] 巴县档案大多数案卷有两个卷皮,一是后人整理档案时给案卷加的卷皮(简称“新卷皮”),一般按照“告状人”+“告状事由”撰写标题,并在标题后面标注档案形成的时间,而且大多会在告状人姓名之前加上“X里X甲”等籍贯和住址信息,目前档案馆给利用者提供利用的案卷目录使用的就是这个标题。另一个卷皮是巴县档案形成之时由巴县县衙的立卷归档部门制作的最原始的卷皮(简称“原始卷皮”),但并不是所有的案卷都有此项内容。缺失原始卷皮的案卷,应该是卷皮已经丢失或者因破损残缺而不可辨认。以道光时期一个案卷为例,这个案卷的原始卷皮有如下信息“署巴县正堂杨,一件为殴逐叩验事,据李世凤告曾三卷,刑房呈,智里四甲,差(略),结,道光十三年二月十九日立”。原始卷皮是当时形成的,审案的知县、案件是结还是息,承办的部门、办案的差役等方面都有体现,相对项目更为全面,只不过作为标题一部分的事由表述比较简单,大都直接采用告状人的四字或八字硃语,比如本标题中使用的就是“殴逐叩验”四字硃语。如果不看案卷内容,可能无法明白其具体要表述的内容。此卷新卷皮上含有如下信息“司法智里四甲李世凤告婿曾三屡滋嫌凌殴伤遂回案,道光十三年三月”,“司法”是巴县档案重新整理后新加的类别,标题中的事由要比原始标题详细一些,是整理者根据告状内容按照今人的习惯重新调整后的表述。不过因为标题撰写者水平参差不齐,部分新标题也存在诸多问题,比如关键人名写错,标题不能反映案卷内容等等。利用者在利用档案的时候,不能只看新标题,应该将新旧标题结合使用,方能获得更为全面和准确的信息。
[17] 表面上看起来此处唐何氏两次告状,但实际上首状并非唐何氏本人所呈,而是其长子唐开亮窃母亲之名所具,所以唐何氏在明白真相之后告状,将事情的原委阐述清楚,请求知县将儿子窃名所具之首状注销。知县张在首状中批“候唤讯察究”,实际上就是受理了案件,唐何氏说明缘由之后,知县张又在其告状后批“前词已准唤讯,既系窃名,候集案讯究”,依然准予受理,故才有了后面的供词等相关材料。
[18] 《巴县档案》6-4-5748,咸丰十一年十一月十四日。
[19] 浙江龙泉档案中甚至出现了一个案件的档案散存在22个案卷的情况。
[20] 吴佩林:《地方档案整理的“龙泉经验”》,《光明日报》2019年11月14日。
[21] 黄存勋:《清朝地方档案浅议》,《四川档案》1985年第1期。
[22] 黄存勋:《清朝地方档案浅议》,《四川档案》1985年第1期。
[23] 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张我德先生在1982年5月30日四川省档案学会成立大会暨第一次档案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中也提到了这个问题,他说:“文件自然还是官吏们站在封建统治阶级立场上写下来的,但是许多基本事实他们总不能完全抹煞,所以这一大批档案实在是很可贵的。”
[24] 雷荣广、姚乐野:《清代文书纲要》,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6页。
[25] 此段文字是张我德先生于1982年5月30日在四川省档案学会成立大会暨第一次档案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重点谈到清代巴县档案的价值。
[26] 里赞在《晚清州县诉讼中的审断问题——侧重四川南部县的实践》一书中也对此作了评述。他举例说,刘衡在其《理讼十条》中表示:“状不轻准,准则必审。审则断,不许和息也。”然而,将此段话拿到巴县档案或者南部档案中去对照就会发现,事实并非如此。大量的档案并没有批词或者判词,说明“审不一定断”;而相当多的案例也表明,案件已经开始审理,如果有人请息,知县一般都会批准销案。这说明,官箴中的记载并不一定就是实际情况,不可轻信。
[27] 郭松义:《伦理与生活——清代的婚姻关系》,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211页。
[28] 根据里赞的研究,在南部档案光绪年间54件有明确判词的案件中,严格依律而断的仅有3件,占比为5%。见里赞:《晚清州县诉讼中的审断问题——侧重四川南部县的实践》,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年,第123页。这种法律表达与司法实践之间的差异在巴县档案中也有非常明显的体现。
[29] 张晓蓓:《清代婚姻制度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3年,第7页。
[30] 黄静嘉:《中国法制史论述丛稿》,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303页。
[31] 张晓霞:《契约文书中的女性——以龙泉驿百年契约文书和清代巴县婚姻档案为中心》,《兰州学刊》2014年第8期。
[32] 关于女性在契约中的角色以及女性作为主体所签订契约的效力问题,各地也有不同的习惯。巴县档案和龙泉驿契约文书中显示有相当多的女性在契约文书中以立约者的身份出现,丝毫不影响这些契约的效力。但也有一些地方对女性所签订的契约并不认同。比如甘肃省平凉县,凡是买卖不动产的契约,一般以男子之名为主,寡妇则用其子或孙之名,否则并不会产生效力,因此而涉讼的情况颇多。见前南京国民政府司法行政部编:《民事习惯调查报告录》,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839页。
[33] 早婚现象主要在一些较为偏远的农村地区存在,相关报道频频见诸于媒体。根据腾讯网纪实图片故事栏目《活着》的相关报道,在云南西南边陲地区,早婚现象非常普遍。只在一个村寨中,就能看到数个背着孩子的少女。有些女孩嫁人时甚至才12岁,由于不到法定年龄,他们不能领结婚证,婚姻没有法律效力。这些少男少女们用青涩的“爱情”经营起家庭,更像“过家家”,却又现实地孕育着下一代生命。其中的小节只有13岁,却已结婚将近1年,怀孕6个月;16岁的小彩已经当了两个月的妈妈,其丈夫小明也只有17岁;16岁的小梅结婚一年,怀孕9个月;小丽17岁,结婚3年;小容16岁,小勇20岁,他们结婚1年,孩子10个月大;16岁的小美结婚2年,大女儿2岁,小儿子1岁,她和丈夫是小学同班同学,六年级开始恋爱,结婚后辍学。见腾讯网《活着》栏目,2014年11月20日。
[34] [日]小野达哉著,杜金译:《〈巴县档案〉读书会研讨词汇集》,《中国古代法律文献研究》2018年第1期。
[35] 需要说明的是,还有一些论文集也会刊载巴县档案的研究论文,如:《四川清代档案研究》(李仕根主编,成都: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04年),《从诉讼档案出发:中国的法律、社会与文化》([美]黄宗智、尤成俊主编,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年),《地方档案与文献研究》(吴佩林、蔡东洲主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2016年),《明清法律运作中的权力与文化》(邱澎生、陈熙远主编,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等等。此处统计的只是知网收录的数据。
[36] 张晓霞、黄存勋:《清代巴县档案整理研究的回顾与思考》,《档案学通讯》2013年第2期。
[37] 朱兰:《“老外”眼中的巴县档案》,《四川档案》1998年第3期。
[38] 对巴县档案研究成果的回顾与总结,可见张晓霞、黄存勋:《清代巴县档案整理研究的回顾与思考》,《档案学通讯》2013年第2期;赵彦昌、苏亚云:《巴县档案整理与研究述评》,载赵彦昌主编:《中国档案研究》(第五辑),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2018年。
[39] [芬兰]E·A·韦斯特马克著,李彬、李毅夫、欧阳觉亚译:《人类婚姻史》(第一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35页。
[40] 尤陈俊:《法学家陈顾远笔下的〈中国婚姻史〉》,载陈顾远《中国婚姻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240页。
[41] 陈鹏:《中国婚姻史稿》,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
[42] 陈怀荃:《陈鹏〈中国婚姻史稿〉评介》,《安徽师大学报》1991年第4期。
[43] 除此处介绍的几部著作之外,其他有关婚姻、家庭、妇女的研究成果,还有常建华:《婚姻内外的古代女性》,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乡土重建》,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汪玢玲:《中国婚姻史》,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年;赵凤喈:《中国妇女在法律上之地位》,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4年;陶希圣:《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外一种:婚姻与家族》,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孙晓:《中国婚姻史》,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16年。此外还有国外学者如[美]伊沛霞、[美]白凯、[美]曼素思、[法]朱丽娅·克里斯蒂娃等人的著作。具体可参见吴佩林、毛立平、褚艳红等论著中有关婚姻、妇女的学术史回顾和述评。
[44] 郭松义:《伦理与生活:清代的婚姻关系》,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郭松义、定宜庄:《清代民间婚书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王跃生:《十八世纪中国婚姻家庭研究:建立在1781—1791年个案基础上的分析》,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年;王跃生:《清代中期婚姻冲突透析》,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钱泳宏:《清代“家庭暴力”研究:夫妻相犯的法律》,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吴正茂:《清代妇女改嫁法律问题研究》,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5年。
[45] 以南部档案为支撑进行婚姻和妇女等相关问题研究的论文成果主要有:赵娓妮:《晚清知县对婚姻讼案之审断——晚清四川南部县档案与〈樊山政书〉的互考》,《中国法学》2007年第6期;吴佩林:《〈南部档案〉所见清代民间社会的“嫁卖生妻”》,《清史研究》2010年第3期;吴佩林:《清代四川南部县民事诉讼中的妇女与抱告制度——以清代四川〈南部档案〉为中心》,载[美]黄宗智主编:《中国乡村研究》(第八辑),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年;毛立平:《“妇愚无知”:嘉道时期民事案件审理中的县官与下层妇女》,《清史研究》2012年第3期;毛立平:《清代下层妇女与娘家的关系——以南部档案为中心的研究》,载吴佩林、蔡东洲主编:《地方档案与文献研究》(第一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240—267页;毛立平:《档案与性别——从〈南部县衙门档案〉看州县司法档案中女性形象的建构》,《北京社会科学》2015年第2期;雍晓夏:《父权体系与经济因素交互影响下的地方婚姻——论吴佩林清代南部县之婚姻〈与社会研究〉的史学价值》,《四川文理学院学报》2015年第2期;李彦峰:《清代“招夫养子”与“带产入赘”的利益诉求考察——以〈南部档案〉婚契文约为例》,《长江师范学院学报》2015年第5期;吴志忠、刘金霞:《〈南部档案〉所见的川北城乡婚俗》,《四川档案》2015年第6期。
[46] 赵娓妮:《审断与衿恤:以晚清南部县婚姻类案件为中心》,北京:法律出版社,2013年。
[47] 蔡东洲等著:《清代南部县衙档案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508页。
[48] 梁勇:《妻可卖否?——以几份卖妻文书为中心的考察》,《寻根》2006年第5期。
[49] 张志军:《何以嫁卖?——从乾嘉道巴县36份嫁卖案例说起》,《西华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3期。
[50] 陈翔:《庚帖、喜课与民间婚姻——四川省档案馆所藏巴县婚姻纠纷档案释读》,《中国档案》2008年第7期。
[51] 吴佩林:《清末新政时期官制婚书之推行——以四川为例》,《历史研究》2011年第5期。
[52] 李清瑞:《乾隆年间四川拐卖妇人案件的社会分析——以巴县档案为中心的研究(1752—1795)》,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11年。
[53] 杨毅丰:《巴县档案所见清代四川妇女改嫁判例》,《历史档案》2014年第3期。
[54] 高钊:《咸丰朝巴县地区婚姻离异现象研究——以〈清代四川巴县衙门咸丰朝档案选编〉为中心》,《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14年第6期。
[55] 刘艳丽:《浅谈清代妇女社会地位——以清代巴县档案为视角的考察》,《商品与质量》2012年S6期。
[56] 周彦冰:《清代巴县妇女的权利研究》,广西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5年。
[57] 刘欢欢:《清代下层妇女离家出走现象考察——基于巴县、南部县档案的研究》,中国人民大学硕士论文,2015年。
[58] 周琳、唐悦:《秦氏的悲情与野心——乾隆末年一桩离婚案中的底层妇女》,载里赞、刘昕杰主编:《法律史评论》(第十一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
[59] [美]苏成捷:《帝制中国晚期的性、法律与社会》,斯坦福大学出版社,2002年(Sex,Law,and Socie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性工作:作为生存策略的清代一妻多夫现象》,载[美]黄宗智、尤成俊主编:《从诉讼档案出发:中国的法律、社会与文化》,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年;《清代县衙的卖妻案件审判:以272件巴县、南部与宝坻县案子为例证》,载邱澎生、陈熙远编:《明清法律运作中的权力与文化》,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
[60] [日]水越知著,海丹译:《清代后期的夫妇诉讼与离婚——以同治年〈巴县档案〉为中心的研究》,载周东平、朱腾主编:《法律史译评》(第五卷),上海:中西书局,2017年。
[61] [日]臼井佐知子:《从诉讼文书来看清代妇女涉讼问题》,载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编:《徽学》(第九卷),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1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