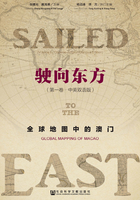
上编 综合研究
“亚洲”概念的传入及其在中国的反响
董少新[1]
我不明白为何三个名字,而且是三个女性的名字,被用于称呼本为一体的一块大陆。
——希罗多德
欧、亚、非三大洲的理论起源于古希腊。在欧洲中世纪,这一理论体系被置于天主教神学背景中加以阐释,例如在流行于中世纪的 T-O世界地图中,耶路撒冷位于中心,三大洲被标示为诺亚的三个儿子 Shem,Ham和 Japheth的领地。在大航海时代,欧洲航海家找到了前往印度和远东的新航路,“发现”了新大陆;同时,欧洲关于亚洲是一个单独的大洲的观念也被强化。但是,正如希罗多德所说,为什么要将实为一体的一片大陆划分为三个部分并赋予不同的名称呢?答案或许是,欧洲需要一个“他者”以构建自我的认同。
中国人从不知道自己的国家属于一个被称为亚洲的大陆,直到1584年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神父在肇庆绘制了首张世界地图《山海舆地图》,中国人才被告知,中国是五大洲之一亚洲的一部分。通过利玛窦、艾儒略、傅汎际、南怀仁等欧洲天主教传教士,包括亚洲观念在内的西方地理学知识在明末清初被介绍到中国。
西方地理学深刻地改变了中国传统的天下观,但欧洲的亚洲观念在明末清初中国思想界并未产生重大影响,直到晚晴时期,徐继畲、魏源、何秋涛等著名学者在他们的书中接受了亚洲学说,欧洲的亚洲观念才在中国流行开来。晚清时期,面对西方列强,中国需要重新思考其传统的天下观,并构建包括本国在内的区域认同;亚洲观有助于这一构建,而欧洲则相应地被视为“他者”。
在被称为亚洲的这片陆地上,一直存在多元文化、不同宗教以及多种认同。因此,这块陆地无论从什么角度,都不宜被视为一个单独的大洲。从古至今,亚洲就是一个被构建出来的概念,并被习惯性沿用着。那么在当今全球化的时代,我们仍需要亚洲这一观念吗?
1.前言
教科书上写着,世界分为七大洲,包括亚洲、欧洲、非洲、北美洲、南美洲、大洋洲和南极洲。但仔细观察地球仪,我们发现亚、欧、非三洲构成一块绵延而广袤的大陆。从地理学角度而言,欧洲是欧亚大陆西北部的一个半岛。或许有人说,三大洲的分法是基于文化的差异,但这并不符合文化地理学的准则,因为我们知道,与欧洲相反,亚洲各地区的文化差异巨大,可谓五彩缤纷,例如南亚的印度教、西亚的伊斯兰教、东南亚的佛教和东亚的儒家文化,等等。既然三大洲的分法与区域的文化边界不相符合,那么我们又为何要将这一片大陆人为地分成三个大洲呢?
实际上,早在2400多年前,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已提出这样的质疑,他说道:“我不明白为何三个名字,而且是三个女性的名字,被用于称呼本为一体的一块大陆。”[2]希罗多德努力探究这三个名字的起源,但仍无法弄清楚。这一问题至今仍存争议,但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古希腊人在向整个地中海地区殖民扩张与贸易的时期,已经用亚细亚和利比亚来称呼东方和南方的地带,而自认为是欧洲人。这或许在某种程度上,与古代中国人称呼周边部族为戎、狄、蛮、夷,并自称华夏相类似。这是古人理解外部世界、构建自我认同的一个途径。
将“旧大陆”分为欧、亚、非三大洲的理论是欧洲人的发明,以便将欧洲与其他区域区隔开来。三大洲的边界及欧洲人的亚洲观念随着时代的不同也不断变化。在古希腊迈锡尼时代以前,少数文献记载了一些来自一个被称为亚洲的区域的女奴,但这里主要指的是安纳托利亚,即后来的小亚细亚。在那个世代,欧洲主要指的是希腊,而利比亚是埃及以西的一小片区域。公元前6世纪至前5世纪,亚、欧边界位于高加索山脉的里奥尼河,随着希腊化时代地理学的发展,这一古代地域观念被修订,亚、欧边界被认为是在顿河。罗马地理学家托勒密继承了古希腊的三大洲理论,并将红海视为亚、非边界,将顿河入海口往北至未知区域一线作为亚、欧分界线。托勒密的亚洲一直延伸到远东,与今日之亚洲范围较为接近。
中世纪至18世纪,欧洲对大陆的划分仍延续托勒密的思想,而亚、欧边界为爱琴海、达达尼尔海峡、马尔马拉海、博斯普鲁斯海峡、黑海,刻赤海峡,亚速海和顿河一线。中世纪欧洲地理学在天主教神学的阴影下停滞不前,一个典型的例子是 T-O世界地图的出现。T代表地中海、尼罗河和顿河,将整个大陆分为亚、非、欧三大洲;O则代表环绕大地的海洋。耶路撒冷一般被置于地图的中央,由于太阳从东方升起,因此伊甸园一般被认为地处亚洲,即地图的上方。三大洲被视为是诺亚的三个儿子 Shem,Japheth和 Ham的领地。
在大航海时代,欧洲的地理学和地图绘制学发生了重大变革。欧洲航海家找到了前往印度和远东的新航路,并“发现”了新大陆。经过两个世纪的航海探险活动,世界上绝大部分地方都留下了欧洲人的足迹,16世纪的世界地图已大体呈现出整个世界的面貌。同时,亚洲被视为欧洲最重要的“他者”,亚洲作为一个单独的大洲的观念在欧洲人思想中得到了强化。尽管越来越多的欧洲地区成为独立的民族国家,但他们仍需要保留欧洲身份认同,特别是在面对非洲人、印度人和远东人民的时候。例如在18世纪,沙俄操纵了亚、欧边界的修订,以便在地理和文化意义上保留其欧洲身份。1730年,瑞典地理学家 Philip Johan von Strahlenberg发表了新的地图,以乌拉尔山脉取代顿河作为亚、欧边界。
至19世纪中叶,对于亚、欧边界仍有三种不同观点。其一是沿着顿河、伏尔加-顿河运河和伏尔加河,其二是沿着库马-马内奇河洼地至里海、乌拉尔河,其三则完全弃用顿河,采用高加索山脉分水岭至里海一线。直到1860年代以后,地理学家仍对这一问题争论不休,Douglas Freshfield认为高加索山脊最适合作为亚、欧分界线,大多数苏联地理学家赞同这一观点,因此在20世纪高加索山脉成为亚、欧两大洲的标准界线。现代亚、欧分界线是爱琴海、达达尼尔海峡、博斯普鲁斯海峡、黑海、高加索山脉分水岭、里海北部、乌拉尔山脉,大多数地图都是如此划分的[3]。
从古到今,亚、欧、非三大洲的理论,尤其是亚洲的观念,一直是一个典型的欧洲概念。这个概念是由欧洲人提出、解释、讨论、界定并传播的。不同的欧洲地理学家、哲学家、政治家和神学家根据各自的需要赋予亚洲不同的内涵,或以不同的边界划分欧、亚二洲。例如,埃及属于中东而非亚洲,尽管中东是亚洲的一部分。但在亚洲概念形成的整个过程中,几乎所有生活在被称为亚洲的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完全是缺席的。无论中国人、日本人、朝鲜人、越南人还是其他所谓亚洲的民族,在近代以前都不曾知道自己是亚洲人。在他们自己看来,他们各自的文化存在巨大的差异性,因而与古代欧洲的观点不同。他们不自称为亚洲人,而是被称为亚洲人。而事实上,从来不存在一个以“亚洲人”为名的人类群体。
16世纪后期,包括亚洲观在内的欧洲五大洲观念被介绍到中国。中国有其传统的世界观,即天下观。本文讨论两种世界观的相遇,尤其是中国人对欧洲的亚洲观念的反响。
2.亚洲概念的传入
天主教传教士是16~18世纪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主要媒介。他们带来欧洲的知识,也将中国的信息传回欧洲。作为几乎唯一的中欧间文化传播媒介,传教士可以决定向中国介绍什么样的欧洲知识,以及应该将什么样的中国信息传回欧洲。欧洲的中国印象和中国对欧洲的印象便是由这些传教士塑造的,尽管这种印象并不总是反映实际情况。
传教士(尤其是耶稣会士)在向中国传播欧洲地理学知识方面表现得尤为积极,这主要有两方面原因:首先,中国文人士大夫对认识外部世界有浓厚的兴趣,因此介绍欧洲地理学知识成为传教士结交中国精英阶层的重要方式,而获得中国精英阶层的友谊对在中国传教至关重要;其次,由于中国人不愿意向野蛮人学习任何东西,传教士需要向中国人证明他们来自拥有高度文明的地区,而不是来自野蛮人的地区,以使中国人愿意接受天主教。
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在广东肇庆安顿下来后,在住所的墙壁上悬挂了一幅用欧洲文字标注的世界地图。根据近年的研究,利玛窦所悬挂的地图很可能是欧洲地理学家 Abraham Ortelius(1527~1598)或 Gerardus Mercator(1512~1594)的作品。来访的客人对此图充满好奇,并希望获得一份有中文标注的复本,于是利玛窦绘制了《山海舆地图》。利玛窦在该图上加入了一些天主教义,以利传教;而且利玛窦对欧洲的世界地图做了调整,将中国置于地图的中央,以迎合中国人对世界的想象。尽管此图远非完美,但却在中国文人士大夫中广为流传,并为利玛窦带来了很高的声誉。不幸的是,此图没有任何一个复本保存至今,但我们可以推测,在这张地图中,利玛窦已经介绍了包括亚洲观念在内的西方地理学中的大洲理论。
从那以后,利玛窦在其他几个居住过的地方,如南昌、南京和北京,均绘制过多幅世界地图。无论是在南昌绘制的《舆地山海全图》(1596)还是在南京绘制的《山海舆地全图》(1600),我们今天都无法看到了。保存至今的则有利玛窦绘制于北京的《坤舆万国全图》(1602)。在这幅地图上,利玛窦简要介绍了五个大洲的名称和边界。
以地势分舆地为五大州:曰欧逻巴,曰利未亚,曰亚细亚,曰南北亚墨利加,曰墨瓦腊泥加。若欧逻巴者,南至地中海,北至卧兰的亚及冰海,东至大乃河、墨何的湖、大海,西至大西洋。若利未亚者,南至大浪山,北至地中海,东至西红海、仙劳冷祖山岛,西至河折亚诺沧。即此州只以圣地之下微路与亚细亚相联,其余全为四海所围。若亚细亚者,南至苏门答腊、吕宋等岛,北至新曾白蜡及北海,东至日本岛、大明海,西至大乃河、墨何的湖、大海、西红海、小西洋。若亚墨利加者,全为四海所围,南北以微地相联。若墨瓦腊泥加者,尽在南方,惟见南极出地,而北极恒藏焉,其界未审何如,故未订定之,惟其北边与大、小爪哇及墨瓦腊泥峡为境也。其各州之界当以五色别之,令其便览。[4]
利玛窦的介绍很简短,此后来华的耶稣会士,如艾儒略(Giulio Aleni,1582~1591)、傅汎际(Francisco Furtado,1589~1563)、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1623~1688)等,则有更为详细的介绍。艾儒略在《职方外纪》中为每一个大洲都撰写了概说,其中《亚细亚总说》云:
亚细亚者,天下一大州也。人类肇生之地,圣贤首出之乡。其地西起那多理亚,离福岛六十二度;东至亚尼俺峡,离一百八十度;南起爪哇,在赤道南十二度;北至冰海,在赤道北七十二度。所容国土不啻百余,其大者首推中国。此外曰鞑而靼,曰回回,曰印弟亚,曰莫卧尔,曰百儿西亚,曰度儿格,曰如德亚,并此州鉅邦也。海中有鉅岛,曰则意兰,曰苏门答剌,曰爪哇,曰渤泥,曰吕宋,曰马路古,更有地中海诸岛,亦属此州界内。中国则居其东南,自古帝王立极,圣哲递兴,声名文物、礼乐衣冠之美,与夫山川土俗、物产人民之富庶,远近所共宗。……其距大西洋,路几九万,开辟未始相通,但海外传闻,尊称之为大知纳。近百年以来,西舶往来贸迁,始辟其途。而又耶稣会中诸士,幸复遍历观光,益习中华风土,今欲揄扬万一,则《一统志》诸书,旧已详尽。至中华朝贡属国,如鞑鞑、西番、女直、朝鲜、琉球、安南、暹罗、真腊之类,具悉《一统志》中,亦不复赘。[5]
这里,以中国为宗的远近诸国,包括中国的朝贡国乃至西域各国,均位于亚洲,而欧洲诸国(传教士称其为大西洋诸国)并不包括在内。欧罗巴属于另一个大陆,拥有与中国同样高度的文明,直到耶稣会士来到以后中国才知道其存在。传教士的这一思想对中国传统的天下观产生了颠覆性的冲击。依照传统的天下观,中国位于世界的中心,距离中国越远的区域,文明程度越低,也更为野蛮。耶稣会士承认中国是一个文明中心,但他们告诉中国人,中国仅是亚洲的中心,此外还存在另外一个中心,即泰西(欧洲),传教士正是从那里来中国的。
然而,根据传教士的说法,在亚洲还有一个国家,即如德亚,甚至比中国更为重要,艾儒略写道:
亚细亚之西,近地中海,有名邦,曰如德亚。此天主开辟以后,肇生人类之邦。天下诸国载籍上古事迹,近者千年,远者三四千年,而多茫昧不明,或异同无据。惟如德亚史书,自初生人类至今,将六千年,世代相传,及分散时候,万事万物,造作原始,悉记无讹,诸邦推为宗国。地甚丰厚,人烟稠密,是天主生人最初赐此沃壤。[6]
艾儒略对如德亚的介绍甚为详细,主要是因为如德亚在天主教义中具有独特地位。耶稣会士在所介绍的地理学知识中加入宗教内容是很自然的事情,艾儒略《万国图小引》(1648)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写道:
造物主化成十二重天,而火气水土四行,从轻至重,渐次相裹。……然天下万方,总分为五大州,曰亚细亚,曰欧逻巴,曰利未亚,曰亚墨利加,曰墨瓦蜡泥加。又此各州中,分大小无算之国,小图不能尽笔也。兹不过述其大约云耳。噫!五州之大,万国之众,其于上天不过圈中之一点也,吾所居之邦,又五州之一点也,吾之所驻足,又大邦之一点也。今我比天为何如乎?我比天地之大主又何如乎?则我正似点中之一点,而无处可觅我矣。顾我身之在天地,虽为甚微,而一点灵才,为造物主所赋,自能包括天地,而明天地万物之真主,所谓人身小天地也。[7]
最后一句表明耶稣会士用儒家术语和思想解释天主教教义,或者换句话说,他们赋予儒家思想表述以天主教的含义。
傅汎际在《寰有诠》中写道:
人类皆繇亚当,实在亚细亚境。但亚当所生之人,既能流通亚细亚、利未亚、欧逻巴之万国,何谓不能通于亚墨利加与墨曷蜡尼加之远也?陆路虽艰,航海有法。天主既为人而造地,必命天神,取此人以至彼地。
当圣徒在世时,亚细亚、利未亚、欧逻巴皆被耶稣之教。此三大域,乃全地之贵分,故虽未及通教四远,亦谓流通全地云。[8]
这样,尽管中国位于亚洲的最东部,但亦应该接受天主教,而这也正是传教士自欧洲来到中国的原因。
在欧洲地理学传入之前,佛教世界观早已被介绍到中国。佛教将世界分为四大部洲,包括北俱卢洲、东胜神洲、西牛贺洲和南瞻部洲。但耶稣会抨击这一佛教观念,例如利玛窦写道:
各国繁伙难悉,大约各州俱有百余国……释氏谓中国在南瞻部洲,并计须弥山出入地数,其谬可知也。[9]
讹传谬说者何?所谓四天下、三十三天、三千大千者,即是也。四天下、三十三天,其语颇有故。盖今西国地理家,分大地为五大洲。其中一洲,近弘治年间始得之,以前无有,止于四洲。故元世祖时,西域札马鲁丁献《大地圆体图》,亦止四洲,载《元史》,可考也。四洲之中,独亚细亚、欧逻巴两地相连最广。其中最多高山,故指亚细亚之西境一高山,为昆仑亦可,或为须弥、为妙高,皆可。此四天下之说所自来也。[10]
利玛窦虽批判佛教四大部洲之说,但亦从中找出相似之处,以利西说在华之传播,并认为佛教四大部洲源自欧洲的四大洲之说。
明末清初天主教传教士通过介绍包括大洲观念的欧洲地理学知识,向中国人展示了一种新的世界观。他们试图构建一个两极化的世界,欧洲和中国是世界的两大文明中心,构成两极,而其他国家和地区则是中国和欧洲的附庸。中国传统的天下观受到这种新的世界观的冲击,但并未彻底崩塌,因为尽管中国不再是整个世界的中心,但仍是亚洲的中心。中国传统的天下观被新的亚洲观取代,因为中国传统的四裔诸国、诸地区均位于亚洲。欧洲和亚洲均有圣人出现,但在亚洲,圣人仅出现在如德亚和中国。同时,欧洲不属于中国的四裔,而是一个拥有与中国同样高度文明的区域。传教士试图扫清中国人接受天主教的心理障碍。在其所介绍的地理学知识中加入天主教内容,以及反对佛教的世界观,均是为了在中国传教。但在面对新来的欧洲地理学及其亚洲观念时,中国人却有多种不同的反响。
3.明末清初中国人对西方亚洲观念的回应
欧洲的五大洲说,尤其是利玛窦《坤舆万国全图》和艾儒略《职方外纪》中所介绍的五洲学说,在明末清初被许多书提到或征引,例如《明史》《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广东通志》《皇清文献通考》,等等。可见,欧洲地理学知识在中国学界产生了反响。如传入中国的其他西学知识一样,中国人对西方亚洲观念的回应可以分为三种:接受、拒绝和存疑。
欧洲地理学中的大洲说与亚洲观,对中国人而言是全新的。直到17世纪中叶,还没有中国人到达过西欧和美洲。中国人从前不知道这些地方,因此也无从判断新传入的地理学知识的真伪,故对其存疑是中国人的主流态度。
明末江西地理学家章潢(1527~1608)在其《图书编》中收入了利玛窦的《地球图说》和《舆地山海全图》。尽管章潢书中的这幅世界地图并非利玛窦地图的完整摹本,但他把各大洲的名字清楚地标在上面,并评论说:“此图即太西所画。彼谓皆其所亲历者,且谓地象圆球,是或一道也。”[11]但传统中国的天下观和佛教的世界观也被收入《图书编》中,因此我们可以说章潢仅仅是将各种地理学理论汇集在一起,以便其他学者可以比较并判断哪种理论更为合理。周于漆《三才实义》(1680)亦收入一幅利玛窦世界地图(《舆地图》),[12]在回应西方地理学知识方面,《图书编》和《三才实义》可归为一类,即存此一说,以广异闻。
在清初,对五洲说持存疑态度仍为主流,这一点可以从官修史志中得到印证。《明史》写道:
万历时其国人利玛窦至京师,为《万国全图》,言天下有五大州,第一曰亚细亚洲……其所言风俗物产多夸,且有《职方外纪》诸书在,不具述。[13]
《明会要》也这样评论利玛窦世界地图及其五洲说:
意大里亚国,居大西洋中,自古不通中国。万历时,其国人利玛窦至京师,为《万国全图》,言天下有五大洲:第一曰亚细亚洲,中凡百余国,而中国居其一;第二曰欧罗巴洲,中凡七十余国,而意大里亚居其一;第三曰利未亚洲,亦百余国;第四曰亚墨利加洲,地更大,以境土相连,分为南北二洲;最后得墨瓦腊泥加洲,为第五。其说荒渺莫考。[14]
《四库全书总目》也持类似的观点:
(《职方外纪》)所纪皆绝域风土,为自古舆图所不载,故曰《职方外纪》。其说分天下为五大州。一曰亚细亚洲……前冠以《万国全图》,后附以《四海总说》。所述多奇异,不可究诘,似不免多所夸饰。然天地之大,何所不有。录而存之,亦足以广异闻也。[15]
不少学者持同样的态度,例如当时的文人顾景星写道:“利玛窦言天九重,日月五星各居一重,二十八宿、六等之星在第二重;地五大洲,中国则五大洲中亚细亚洲百分之一耳。其说又无所究竟也。”[16]
对五大洲说持存疑态度的学者,大多数无与传教士直接而密切的接触,也无法证明这一学说的正确性,因此采取存疑态度也就可以理解了。另一个可能性是,他们不愿意承认一个强大他者(欧洲)的存在,以及中国的天下的式微,因此不愿意接受五洲学说。例如梁辀的《乾坤万国全图古今人物事迹》,[17]尽管综合利用了利玛窦地图中的一些知识,但从风格和形制上看仍是典型的中国传统广舆图,展示的是中国的天下观,且没有标注各大洲的名字。另一个例子是曹君义的《天下九边分野人迹路程全图》(1644),[18]在这幅图中,中国及其四裔居于当中,占据整个地图一半以上的面积,而其他四大洲则被画得很小;虽然标注了其他四洲的名字,但没有标出亚细亚洲的名字。这是一幅以中国天下观为基础、吸收了一些欧洲地理学知识的世界地图。曹君义似乎接受了其他四大洲存在的事实,但不愿意接受亚洲的观念。
曾积极推动传教士世界地图及其他地理学著作的出版或为其作序的文人士大夫,例如王泮、王应麟、吴中明、郭子章、冯应京、李之藻、徐光启等,或可被认为接受了欧洲的五大洲学说,或至少不反对这一学说。他们大多数对天主教持友好态度,而其中一些人甚至领洗入教。下面我选择其中几位曾评论过欧洲的亚洲观念的学者,略加讨论。
中国士大夫教徒李应试(1602年领洗,教名保禄)曾出版过利玛窦的世界地图,名为《两仪玄览图》(1603)。他在为此图撰写的序言中说:
无论国朝二百余年,即三代以继今之父老,蔑闻欧罗巴何,亦蔑闻地球何。往哲以鸡卵喻两仪,所憾言而未尽。逮西方人自欧罗巴浮桴八万里,以其国人数千年历大地图说,为中土先达,厥绩伟欤。……然西方人声音文字与中土殊,殊而能同,盖心同理同,其学且周孔一辙,公卿大夫日接而雅敬之。[19]
“东海西海,心同理同”是中国文人接受西学的重要理念基础之一,也被用于接受欧洲地理学知识。
士大夫冯应京(1555~1606)对西学甚为仰慕,在去世前几乎领洗入教。在他为《两仪玄览图》撰写的序言中,完全赞同欧洲的五大洲学说,而且注意到传教士绘制世界地图目的在于传教,但这与接受欧洲地理学知识并不矛盾,他写道:
西泰子舆图,凡三受梓,递增国土,而兹刻最后,乃最详。……周职方氏掌天下之图,四夷、八蛮、七闽、九貉、五戎、六狄止尔。延及我明,多方砥属,东南际海若朝鲜、暹罗、爪哇凡十有七国,西南夷若婆罗、满剌加凡二十九国,其由天方通者又十有六国,西域则泥剌、朵甘凡七国,其由哈密通者又三十有八国,北虏种类繁伙,佥受羁縻,视古声教为尤盛,视此图仅五分之一耳。所称无远弗届,是耶?非耶?……圣人立极绥猷,代天以仁万国,夫亦顺人心以利导,而吾徒顾瞻环宇,效法前修,各以心之精神,明道淑世,薪火相传,曷知其尽。即如中国圣人之教,西士固未前闻,而其所传乾方先圣之书,吾亦未之前闻,乃兹交相发明,交相裨益。惟是六合一家,心心相印,故东渐西被不爽耳。……西泰子有云:神之接物,司记者受之,司明者辨之,司爱者处之,要归事上帝为公父,联万国为兄弟。是乃绘此坤舆之意与![20]
冯应京在他的著作《月令广义》中翻刻了一份利玛窦地图(《山海舆地全图》),并收入一篇吴中明为利玛窦世界地图撰写的序。冯应京的这个地图又被收入王圻的《三才图会》和游艺的《天经或问》。亚细亚洲的名称被清楚地标注在该图上。冯应京还将利玛窦赠予的两半球图出版,尽管这两幅图已逸,但在程百二《方舆胜略》(1610)和潘光祖《舆图备考》中保留有刻绘本。程百二的书中还列有一个长表,将每个大洲中的每个国家的经纬度罗列出来,该表可能是一个中国学者根据《职方外纪》和传教士世界地图而列。[21]
另一位中国教徒士大夫瞿式榖(1607年领洗,教名玛窦)不仅接受了欧洲的五大洲说,而且用此学说抨击中国传统的天下观与夷夏观。他在为艾儒略《职方外纪》写的序中,这样阐述他的观点:
尝试按图而论,中国居亚细亚十之一,亚细亚又居天下五之一。则自赤县神州而外,如赤县神州者,且十之九,而戋戋持此一方,胥天下而尽斥为蛮貉,得无纷井蛙之诮乎?
且夷夏何尝之有?其人而忠信焉,明哲焉,元元本本焉,虽远在殊方,诸夏也!若夫汶汶焉,汩汩焉,寡廉鲜耻焉,虽近于比肩,戎狄也。其可以地律人、以华夏律地,而轻为訾诋哉![22]
“西学中源”说是中国学者接受西学的另一个重要基础。当一种新的知识被介绍至中国,中国学者通常会从中国古代知识中寻找其渊源,这是一个常见的历史现象。面对欧洲的五大洲学说,李之藻、郭子章、王英明、熊明遇、方孔炤、方以智(孔炤子)、揭宣(以智弟子)等中国学者认为,这一学说源自古代中国的地理学理论。作为利玛窦《山海舆地全图》的出版者,郭子章认为利玛窦世界地图及其五大洲学说与中国古书《河图·括地象》、《山海经》尤其是邹衍、大禹的九州理论相合,他写道:
予读《周礼》,职方氏掌天下之图,辨邦国、都鄙、四夷、八蛮、百越、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与财用,辨九州岛之国使贯利,以为宇内之地穷于斯矣。既阅《河图·括地象》,则云,夏禹所治九州岛四海,内地东西二万八千里,南北二万六千里;若八极之广,东西二亿三万三千里,南北二亿三万一千五百里。《山海经》所载禹九州岛道里,与《括地象》同。而海外四经,大荒四经,意即八极之广也。驺衍以为儒者所谓中国者,于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禹序九州岛之中国,名曰赤县神州,中国外如赤县神州者九,乃名九州岛,有大瀛海环其外,实天地之际焉。利先生之图说……闇与《括地象》、《山海经》合,岂非驺子一确证邪?[23]
揭宣以艾儒略世界地图为基础,绘制过两幅地图,即《大地圆球五州全图》和《亚细亚一大州图》。他不仅接受了这些西方知识,而且还认为这些知识源自元代天文学家郭守敬(1231~1316)的理论,只不过西方学说更为详尽,“其说始于郭守敬,而详于西氏”。[24]
艾儒略在福建学界更有影响,在很多地方学者写给他的诗歌中,“五州”概念常被提及,例如:
三山林叔学:“地界沧溟争昼夜,学窥衡管折丝毫。五州形胜披图狭,八万舟车计路劳。”
三山陈宏己:“图开五大州,一一为我指。”
晋江蔡国铤:“地轴圆球自利君,年来西学又奇闻。周天日表图中见,二极星枢眼底分。宛转金声开八面,依微绿字起三坟。生身我亦欧逻氏,此日定交在水云。”
晋安陈耀:“西域产畸人,汗漫游中国。五州小于点,万里轻如翼。裴束欧罗云,飡供大田稷。”
莆中林泂:“先生居在欧逻都,西渡沧溟引舳舻。道阐天人隳众义,教翻佛老契吾儒。五洲阅历风涛幻,十诫皈依识力俱。谁说殊方辙轨异,繇来冶铸一洪炉。”
温陵黄鸣晋:“五大部州归一统,欧逻巴国应昌期。”[25]
在清代中叶,李光地、阮元等高级官员和著名学者也基本上接受欧洲的五大洲说,例如李光地在其《榕村集》中写道:
周游环匝,初无定位,其名有亚细亚、欧罗巴、利未亚、亚墨利加四大洲。今之九州岛及四夷之地,皆亚细亚国土也。其所记亲历各州,风土山川,寥廓荒忽,虽不可尽信,然其实测晷景,见诸施行者,颇为信而有征,其理盖不可诬。[26]
阮元在其编纂的《广东通志》中记载:
明泰西利玛窦入中国,进万国图,分天下为五大州。一曰亚细亚,二曰欧逻巴,三曰利未亚,四曰亚墨利加,五曰墨泥加。艾儒略、南怀仁之徒,皆祖述其说。中国居亚细亚之中。若东之朝鲜、日本、琉球,西之小西洋、小吕宋、如德亚,南之暹罗,北之俄罗斯、红孩儿、廓尔喀、痕都斯坦诸国,皆亚细亚也。[27]
由于这些官员和学者或者位高权重,或者为学界领袖,因此通过他们,欧洲的五大洲学说得到了更为广泛的传播。在明末清初,亦有一些学者反对西方的五大洲学说。根据传教士的理论,中国比以前缩小很多,这使这些学者极为不安。《皇清文献通考》的作者就不同意艾儒略《职方外纪》中的五洲观点,认为南极洲仅千余里却被视为一大洲,而中国地广万里却只构成亚洲的一部分,这是极为不合理的。其云:
至意达里亚人所称天下为五大洲,盖沿于战国邹衍裨海之说,第敢以中土为五洲之一,又名之曰亚细(亚)洲,而据其所称第五洲曰墨瓦腊泥加洲者,乃以其臣墨瓦兰辗转经年,忽得海峡,亘千余里,因首开此区,故名之曰墨瓦兰泥加洲。夫以千余里之地,名之为一洲,而以中国数万里之地为一洲,以矛刺盾,妄谬不攻自破矣。又其所自述彼国风土物情政教,反有非中华所及者。虽荒远狉獉,水土奇异,人性质朴,似或有之,而即彼所称五洲之说,语涉诞诳,则诸如此类,亦疑为剿说![28]
浙江秀水人张雍敬认为,所谓的五洲说是夸诞之辞,与固有天下观念不合,故不可信:
西说五大洲,曰欧罗巴,曰利未亚,曰亚细亚,曰南北亚墨利加,曰墨瓦腊泥加。吾不知海外另有天地,抑同此天地也。今以天道观之,日月星辰,其变占多应于中国,而春秋冬夏、四炁和均,亦仅太行以南、衡岳以北耳。则九州岛之内,岭南多暑,朔地多寒,其气候且不能尽得天地之正,又何论乎海外!故海国虽多,而与万古神圣相传、广土众民、声名文物之天下,必不可同年而语也。彼为是说者,徒以耳目之所不能及,世亦无从致诘耳。今中国南交北朔、东海西域,固可考而知。若南逾瘴海,至苏吉丹、澎湖岛,北至骨利干、铁勒,此外则不可穷。夫其不可穷,即其穷处。……南北既有可穷,东西不当独远。其动称去中国几万里,或以水陆纡回之故,或故为夸诞之辞,殆未足信也。[29]
另一位名叫璱耽的民间学者更是通过翻阅传统的小学著述,认为“亚细亚”意即“次小次”,是西方人有意贬低中国,甚至宣称凡是见到用这个术语的书,便会扔到地上用脚踩踏,见平步清《霞外攈屑》:
璱耽幼时侍其父远历西洋,周知夷诡。利玛窦《万国全图》,中国为亚细亚洲,而以西洋为欧逻巴洲。欧逻巴不知何解,以太西推之,亦必夸大之语。若亚者,《尔雅·释诂》云次也,《说文解字》云丑也,《增韵》云少也;细者,《说文解字》云微也,《玉篇》云少也。亚细亚为西语,华语则次小次洲也。其辱中国极矣。……明人甘受利玛窦之侮嫚,而不之觉,曾无一人悟其奸者,何耶!璱耽每见世人文字有称引泰西欧逻巴、亚细亚者,辄怒掷蹴踏之,不复视。[30]
著名学者黄宗羲还曾写过一首诗《明司天汤若望日晷歌》,批判西方的五洲说,同时抨击天主教,诗云:
吾闻五洲之说颇荒诞,芋区瓜畴界莫侵。
亚细亚洲居第一,神州赤县细弗任。
渊原将无出驺衍,存而不论戒狂淫。
何物邪酥老教长,西行夸大传天心。[31]
西方地理学,尤其是五大洲的观念,扩大了中国人的视野,并对中国传统的天下观产生严重冲击。传教士希望构建一个欧、亚两极世界观以代替中国的天下观,其中亚洲大体上相当于以中国为中心的传统天下。传教士不希望被中国人视为野蛮人,尽力通过传播西学去获取中国人的尊敬,以便使中国人消除接受西方天主教的心理障碍。大多数传教士自称他们来自欧罗巴或大西洋,而不是明确说自己来自欧洲的哪个国家或地区。他们希望中国人产生一种印象,认为他们来自一个统一的区域,并希望中国人也能够同样视这个区域为一个平等的他者,就如他们视中国为其最重要的他者一样。
在明末清初,中国文人、士大夫、学者对新来的西学知识有不同的回应,其中主流的观点,主要来自官修史志的作者们。他们对西方的五大洲学说采取了存疑的态度,而且对中国失去世界文明中心地位感到十分忧虑。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尽管他们对西方传来的地理知识已经有所了解,但仍按照中国传统舆地图的形式绘制世界地图。多数接受西方五大洲学说的文人士大夫对传教士都很友善,甚至入教。通过欧洲地理学知识,他们认识到中国不是整个世界的中心,而仅仅是亚洲的中心;世界比中国传统的天下要大得多;他们首次知道了欧洲、美洲和南极洲的存在,并了解到欧洲是另一个拥有与中国同样高度文明的中心。其中有的学者,例如瞿式榖,甚至用欧洲五大洲学说来激烈地批判天下观。尽管有部分学者强烈排斥五大洲学说,其中包括黄宗羲这样的大学者,但他们的态度似乎不是主流,且影响不大。
4.清中晚期对欧洲亚洲观的回应——以魏源《释五大洲》为中心
清代中晚期中西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化。贸易冲突不断,欧洲的坚船利炮游弋于中国沿海,致使东西方关系更为紧张。中国的天下观和朝贡体系在西方的冲击下崩塌,代之以近代世界观和条约体系。天主教传教士不再是中西文化交流的唯一媒介,新教传教士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且出国亲自观察外部世界的中国人也越来越多。在晚清(尤其是在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以后),更多的西方知识也从日本被引进到中国。
更多西方地理学知识通过不同途径传入中国,五大洲说(或者七大洲,将美洲分为南美洲和北美洲,再加上大洋洲)被作为一种常识而被普遍接受。由于与西方列强的战争连续遭到挫败,并被迫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中国开始认识到西方代表了另一种文化,其科学技术水平高于东方的任何地区。传统的天下观已无意义,中国不得不承认并接受西方作为其强大的他者。
来自西方的持续压力迫使中国学者开始主动研究西方地理学,涌现出一批近代地理学著作,例如林则徐(1785~1850)《四洲志》(1841)、魏源(1794~1857)《海国图志》(1842~1852)、梁廷枏(1796~1861)《海国四说》(1846)、徐继畲(1795~1873)《瀛环志略》(1849)、何秋涛(1824~1862)《朔方备乘》(约1858),等等。这些著作的出现,表明中国人开始将目光投射到了整个世界。他们接受了西方的世界观及大洲理论,介绍五大洲中每一个国家的地理位置、文化、军事、外交、政治、物产、人民、贸易等各个方面。这些著述的编撰形式多少与艾儒略《职方外纪》相类,但更为详细。还有大量其他著述,无论是官修还是私撰,经常涉及世界地理和大洲理论,例如贺长龄、魏源《清经世文编》(1826)、杞庐主人《时务通考》(1897)等。本节简要讨论魏源的五大洲观念,因为他的观念在晚清具有代表性,也有更为广泛的影响。
在林则徐的建议下,魏源完成了《海国图志》的编撰。该书被视为中国地理学划时代的巨著,因为它是中国学者编撰的最重要的近代地理学著作,使中国人得以详细地了解外部世界。魏源参考的资料很广泛,包括中国传统的文献,天主教和新教传教士以中文撰写的地理学著作,以及来自外国人的其他信息。魏源的目的是使中国人能够“师夷长技以制夷”。该书按照五大洲的体系编撰,但魏源对西方的大洲理论有自己的理解和阐释,其思想在《海国图志》卷七十四《释五大洲》中可以清楚地看到。[32]
上文提到,利玛窦曾批判佛教的四大部洲学说,而魏源正是在佛教的这一学说框架下接受西方五大洲学说的。他认为大洲应以大洋为区隔,并被大洋环绕,而不能用海、河、山、地峡等作为大洲的分界线。所以欧、亚、非大陆应该被视为一个大洲,而不是三个大洲,同样美洲也不能以巴拿马地峡为界分为南北两大洲。这样,欧洲人所谓的五大洲,其实只是佛教中的两大部洲:欧、亚、非大陆为南瞻部洲,而美洲为西牛贺洲。第三大洲北俱卢洲位于北冰洋,欧洲人从未到达那里,因此不知道其存在;第四大洲东胜神洲即西人所谓的南极洲,尽管西人曾到过那里,但并未与当地人有交流(魏源不知道南极洲为无人区),因此不了解那里。
根据佛经记载,南瞻部洲有四主,东人主、南象主、北马主、西宝主。魏源据此认为,中国位于东方,为人主;印度位于南方,为象主;蒙古和哈萨克位于北方,为马主;欧罗巴位于西方,为宝主。而且在南瞻部洲中,以亚细亚为尊,因为所有圣人,包括耶稣、穆罕默德、佛陀和孔子,均诞生于亚细亚。魏源认为欧罗巴有害于中华,因为英吉利向中国贩卖鸦片,但美洲有利于中华,因为中国从那里获得白银。
魏源对五大洲的评论在晚清甚有影响。王韬(1828~1871)、俞樾(1821~1907)等著名学者均赞同其观点。王韬《瓮牖余谈》据魏源的思想,认为地球仅有两大洲:
地球中大半为水,小半为地。地分五大洲,一曰亚细亚,二曰欧萝巴,三曰阿非利加,此东半球也。四曰南亚墨利加,五曰北亚墨利加,此西半球也。以全地大势观之,南北亚墨利加与东土三洲不相连属,而其开辟实在三百六十余年之前,前此未知有其地者也。然参之梵典,则已早分大地为四大洲,特以梵典之四大洲非即泰西舆地家所言之五大洲也。《说文》水中可居曰州,后人乃加水旁,曰洲。邹衍《谈天》裨海所环曰神州。释典论地,则咸海所画为四洲。是洲者,四面皆水之名。今亚细亚与欧罗巴,一土相连,似未可遽区为二。其欧罗巴、阿非利加之山,皆发脉葱岭,迤逦而西,入于海。其中隔一红海及地中海,面有苏夷士颈地相属,则三洲似实一土也。惟南北亚墨利加,则别为一大洲,亦不得以中央地狭判而为二也。……魏源曰:今之亚细亚、欧罗巴、阿非利加,即佛经之西牛贺洲也。至北具卢洲,则隔于北冰海,西舶无绕北海而归之事。东神胜洲则阻于南冰海,西舶虽能至南极左右覩其地,而不能遇其人。此虽创说,是非无见,设西国好事者环南北极而一觅之,或有二大洲在,未可知也。[33]
俞樾在《湖楼笔谈》中写道:
《尔雅》所载四极四荒之名,实莫知其所在,古时必有纪载,学者不能言之矣。《史记》载驺衍之说,以为中国名曰赤县神州,中国外如赤县神州者九,乃所谓九州岛也,于是有裨海环之,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环其外。当时斥为怪迂,莫信其说。《汉志》有《邹子》四十九篇,《邹子终始》五十六篇,后世无传焉。佛氏书入中国,乃有四大部洲之说,更为学士大夫所不道。然自泰西诸邦交乎中国,海上往来捷于飙轮,于是始有五大洲之名,曰欧罗巴,曰利未亚,曰阿细亚,曰南北亚墨利加,曰墨瓦蜡泥加。至近时,魏氏《海国图志》则谓阿细亚、欧罗巴、利未亚此三洲者,共为释典之东胜神州,北具卢洲,则阻于南北冰海,更无从问津矣。茫茫海宇,虽西士如墨瓦兰者,尚不能周知,大雄氏之法力,真不可思议。乃邹衍在战国时,先有大九州岛之说,博览宏识,更出大雄氏上。呜呼!先秦诸子若邹衍者,其圣矣乎![34]
尽管俞樾以西学称颂中国古代学者,仍不免于“西学中源”思想的影响,但赞同魏源对西方五大洲说的接受模式。也有学者不赞同魏源的观点,而认为应该完全接受西方的五大洲学说,例如张维屏(1780~1859)。他写道:
地有四大洲:南瞻部洲,东毘提河洲,西瞿陀尼洲,北拘卢洲(《大唐西域记》)。南瞻部洲,西牛货洲,东胜神洲,北具卢洲(《海国图志》)。地有五大洲:亚细亚洲,欧罗巴洲,利未亚洲,亚墨利加洲,墨瓦蜡泥加洲(《明史》引利玛窦之言,《皇清通考》、《职方外纪》并同)。魏氏(源)曰:佛经所谓四大洲,西人止得其二,亚细亚、欧罗巴、利未亚共为南瞻部洲也;墨利加则西牛货洲也。此外必有二洲(《海国图志》)。老渔曰:魏默深以释典东神胜洲、北具卢洲为在利玛窦所云五大洲之外,言之凿凿,余不能无疑。墨利加洲,明以前尚未通西洋,唐代之人何由知之。《西域记》叙云:海中可居者,大略有四洲。是唐时已明有此四洲,岂至今反不知二洲所在?且西洋人能通自古未通之墨利加洲,岂唐人已知之洲而西洋人反不知者?然则二洲即在五洲之内,至墨利加洲,多产金银,默深,遂以此为西牛货洲之证。余谓音随译转,货字似未可据也。(《老渔闲话》)[35]
当然,张维屏的观点后来成为主流,到了19世纪末,中国人已不再需要从古代知识或佛教中寻找接受西学的依据了。
至20世纪,西方的大洲观念已被作为一种真理和常识而广泛接受。中国与西方成为竞争对手,在中国人的心目中,西方总是他们的比较对象和参照物,此后几乎没有中国学者再尝试反思亚洲的概念。
5.结语
本文首先简要追溯了大洲及亚洲概念在欧洲的起源和发展,然后讨论了西方五大洲学说的传入,以及明清时期中国对该学说的回应。但这并非此文的本意。我的主要目的是想反思亚洲这个概念,而本文只是第一步。
亚洲不仅仅是一个地理概念。从古到今,它都是一个为不同目的而被构建出来的概念,并成为一个惯用语,具有多重含义。它是一个文化的、宗教的、政治的、种族的、身份认同的概念,但它首先是一个欧洲概念。它起源于古希腊,并发展于欧洲。数千年以来,这片广袤的陆地被称为亚洲,但居住于其中的人们并不自认为是亚洲人。他们有着自己的世界观,例如中国的天下、佛教的部洲等。在16~19世纪,西方的五大洲学说的传入开阔了中国人的视域,并最终导致了中国天下观的崩溃,但并非所有中国人都赞同这一观念,它只是引起中国人对世界的重新思考。
现在,亚洲作为一个术语被广泛用于体育、政治、媒体、经济等领域,但它并非一个很好用的概念。例如,在被分在同一小组的时候,中国足球队不得不远赴约旦参加一场世界杯预选赛。这个例子还只是说明了空间距离所带来的不便,而实际上,在被称为亚洲的这片大陆上,存在着多元文化、多种宗教以及不同的认同。因此无论从什么意义上看,它都不适合被视为一个大洲。
近年来,有学者尝试书写一部亚洲史。美国学者罗兹·墨菲(Rhoads Murphey)的《亚洲史》是第一部亚洲通史,也是最有名的一部(顺便提一句,这片大陆上的人们不仅被西方人称为亚洲人,其第一部全面性的通史也是由一个西方学者书写的)。我们已经有国别史、区域史、地方史和全球史,现在我们又有了一个大洲的历史。但如果亚洲是一个欧洲人构建出来的概念,那么“亚洲史”呢?如果说历史书写具有认同的功能,那么“亚洲史”代表着或者要构建什么样的认同呢?如果“亚洲史”仅仅是亚洲不同区域及其相互关系的历史,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去写一部亚欧非史呢?

图版一:托勒密的世界地图

图版二:T-O世界地图,Guntherus Ziner 1472

图版三:利玛窦在北京所绘《坤舆万国全图》(1602)

图版四:艾儒略《万国全图》

图版五:章潢《图书编》中的《舆地山海全图》(本图扫描自黄时鉴、龚缨晏《利玛窦世界地图研究》,第13页。)

图版六:梁辀《乾坤万国全图古今人物事迹》

图版七:曹君义《天下九边分野人迹路程全图》

图版八:冯应京《月令广义》中的《山海舆地全图》(扫描自黄时鉴、龚缨晏《利玛窦世界地图研究》,第23页。)

图版九:王圻《三才图绘》中的《山海舆地全图》(扫描自黄时鉴、龚缨晏《利玛窦世界地图研究》,第23页。)

图版十:程百二《山海舆地图》(扫描自黄时鉴、龚缨晏《利玛窦世界地图研究》,第38页。)

图版十一:熊明遇《坤舆万国全图》(扫描自黄时鉴、龚缨晏《利玛窦世界地图研究》,第51页。)

图版十二:揭宣《五州全图》《亚细亚图》(扫描自黄时鉴、龚缨晏《利玛窦世界地图研究》,第108页。)
[1] 董少新,教授,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副院长。
[2] The History of Herodotus,Book IV.
[3] 以上内容多处参考了英文维基百科中“亚洲”“大洲”“亚欧边界”“T-O地图”等词条。
[4] 利玛窦:《坤舆万国全图》,载朱维铮主编《利玛窦中文著译集》,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74~175页。
[5] 艾儒略:《职方外纪》卷一,谢方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第32~33页。
[6] 艾儒略:《职方外纪》卷一,第52页。
[7] 艾儒略:《万国图小引》,布雷顿斯国立图书馆藏品,见黄时鉴《黄时鉴文集》第三册《东海西海》,彩图16,上海:中西书局,2011年。
[8] 傅汎际译义、李之藻达辞《寰有诠》(1628)卷六,法国国家图书馆 Chinois 3384,第52页。
[9] 《坤舆万国全图》,载朱维铮主编《利玛窦中文著译集》,第175页。
[10] 利玛窦:《复莲池大和尚〈竹窗天说〉四端》,载朱维铮主编《利玛窦中文著译集》,第666页。
[11] 章潢:《图书编》卷二十九,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44~46页。
[12] 参见黄时鉴、龚缨晏《利玛窦世界地图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18~19页。
[13] 张廷玉:《明史》卷三百二十六列传第二百十四“意大里亚传”,武英殿刻本,第17~21页。
[14] 龙文彬:《明会要》卷七十九外蕃三,清光绪十三年永怀堂刻本,第11页。
[15] 《四库全书总目》卷七十一史部二十七,武英殿刻本,第17~18页。
[16] 顾景星:《白茅堂集》卷三十,康熙刻本,第43页。
[17] 曹婉如等编《中国古代地图集》(明代),北京:文物出版社,1994年,图145。
[18] 曹婉如等编《中国古代地图集》(明代),图146。
[19] 李应试:《两仪玄览图》,引自黄时鉴、龚缨晏《利玛窦世界地图研究》,第171页。
[20] 冯应京:《舆地图叙》,引自黄时鉴、龚缨晏《利玛窦世界地图研究》,第171~172页。
[21] 参见黄时鉴、龚缨晏《利玛窦世界地图研究》,第37~41、53页。
[22] 瞿式榖:《职方外纪小言》,见艾儒略《职方外纪》,谢方校释本,第9~10页。
[23] 郭子章:《山海舆地全图序》,引自黄时鉴、龚缨晏《利玛窦世界地图研究》,第175页。
[24] 揭宣:《旋玑遗述》卷二,“地圆”,引自黄时鉴、龚缨晏《利玛窦世界地图研究》,第108页。
[25] 《熙朝崇正集》,吴相湘主编《天主教东传文献》,台北:学生书局,1965年,第652~653、661~662、671、684~685页。
[26] 李光地:《榕村集》卷五,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3页。
[27] 阮元:《(道光)广东通志》卷三百三十列传六十三,道光二年刻本,第61~62页。
[28] 《皇清文献通考》卷二九八,四裔,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6~17页。
[29] 张敬雍:《定历玉衡》卷三,《续修四库全书》景印复旦大学图书馆藏本,转引自黄时鉴、龚缨晏《利玛窦世界地图研究》,第97页。
[30] 平步清:《霞外攈屑》卷二执香峪话“莲鬓阁集”,民国六年刻香雪崦丛书本,第53~54页。
[31] 全祖望:《鲒埼亭诗集》卷二,四部丛刊景清抄本,第2~3页。
[32] 魏源:《海国图志》卷七十四,光绪二年魏光寿平庆泾固道署刻本,第1~10页。
[33] 王韬:《瓮牖余谈》卷四“论地球仅得两大洲”,光绪元年申报馆本,第10~11页。
[34] 俞樾:《湖楼笔谈》七,光绪二十五年刻春在堂全书本,第18页。
[35] 张维屏:《国朝诗人征略二编》卷四十七,道光二十二年刻本,第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