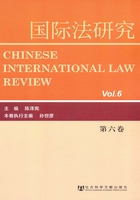
二 人权国际合作义务的法律效力——弱强制性
从规范层面来讲,以《联合国宪章》第56条和《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2条第1款为代表的义务性规则,给相关主体(如联合国和国家)施加了在履行人权条约义务方面开展国际合作的法律义务。但是,无论是《联合国宪章》,还是国际人权条约都没有明确规定人权国际合作义务的具体内容和实现方式。特别是,上述法律文件中“合作”与“援助”的内涵与外延都不甚清晰,相关国际人权机构也没有或者也不愿对之作出明确的界定。不仅如此,一些有关人权国际合作义务的条款还使用“基于自愿同意的国际合作”“认识到……国际接触与合作的好处”等软化人权国际合作义务强制力的措辞。这些情况导致人权国际合作义务并不具备一般法律义务所应有的刚性和强度,从而呈现出弱强制性。根据国际人权软法规范所产生的人权国际合作义务,其强制色彩则更弱。因为,各国不必因此承担实在法意义上的法律义务,它们在国际关系上只负有开展人权国际合作的道德义务或政策压力。
正因为如此,在实践中,各国在履行人权国际合作义务时,具有较大的自由裁量空间。尽管《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23条对该公约第2条第1款所规定的“国际援助和合作”作出了较为具体的列举,如签订公约、提出建议、进行技术援助以及为磋商和研究的目的同有关政府共同召开区域会议和技术会议等,但是,对于许多国家而言,这仍然是不确定的。不仅如此,《儿童权利公约》(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the Child)[17]第4条在后半段更是明确规定,为更好地实现儿童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缔约国应竭尽国内资源的最大限度的能力,并可视情况需要开展国际合作。可见,开展国际合作只是一种为实现人权所必要的义务,缔约国可以根据自身需要选择履行人权国际合作义务的方式和途径。
人权国际合作义务内涵与外延的不确定性导致当前人权国际合作的实现机制,如协商制定国际人权标准、参与国际人权机构的活动、开展经济和技术援助、进行双边或多边人权对话、召开国际会议等都没有强制效力,并且有赖于多元主体的自愿参与。首先,尽管从国际人权公约的措辞来看,开展人权国际合作的义务主体是国家,[18]但是,没有哪一个国际人权条约规定缔约国有义务必须参与所有国际人权机构的活动或者发达国家有义务对发展中国家进行经济或技术援助。其次,除联合国及其部分专门机构根据其组织章程承担开展人权国际合作义务之外,[19]绝大部分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并没有基于其组织章程或其他法律规范所规定的开展人权国际合作的强制性义务。例如,虽然根据《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22条的规定,经济社会理事会可以提请从事技术援助的其他联合国机构和它们的辅助机构,以及有关的专门机构对缔约国履行义务的任何事情予以注意,但这并不是一种法律义务的措辞和表述;联合国专门机构,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根据其与联合国签订的关系协定要考虑联合国的决议和建议意见,从而可能在业务活动中关注人权问题并与联合国合作,但这也不是一种强制性义务。因此,一般情况下,非国家行为体,特别是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等民间力量参与人权国际合作并不是基于一种法律义务,而是基于促进国际人权保障事业的现实考虑和其自身的宗旨与目标定位。可见,当前人权国际合作的诸多实践形态,多是特定历史、特定环境的产物,它的形式、内容及效果均受到参与人权国际合作的相关主体的意志及实际情况的制约。
或许正因为如此,有些西方学者认为,《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2条第1款只包含一种较弱的国家承诺,在义务履行方面是一种软法规范。[20]我们认为这种观点值得商榷。尽管人权国际合作义务因为规范不明而体现弱强制性,但这并不表明这种法律义务的来源是一种软法规范。基于《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2条第1款以及其他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人权文件所产生的人权国际合作义务,本质上是一种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条约义务。对此,阿尔斯顿和奎恩教授就公允地评论道:“很难说公约施加了要求某一特定国家提供某一特定形式的国际援助的法律义务,但是不能因此就断定相关的规定是无意义的。在实施特定权利的情况下,依据公约第2条第1款开展国际合作义务是强制性的。”[21]
值得指出的是,虽然国家开展国际合作与寻求国际援助,特别是经济和技术援助的方式是任择性的,但是,这并不表明相关国家在实现国内人权的过程中可以斟酌不采取此种途径,从而“卸掉”此种义务。正如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多次在一般性意见中强调的,如果一个国家声称由于它无力控制的原因而无法履行义务,则有责任证明这种情况,并且证明它已经寻求国际合作与援助支持,但未能成功。[22]因此,对缺乏足够国内资源的国家而言,寻求国际合作与援助是基于履行国际人权公约义务所要求的法律义务,至少是在证明该国履行义务的行为是否符合条约规定时的强制性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