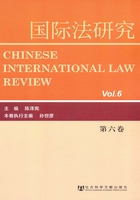
二 案件调查、起诉及审判期间的管辖权和可受理性质疑
同是涉及可受理性与管辖权问题,规约第18条与第19条的适用范围存在较大差别。第18条主要规定情势调查启动之初接受有关国家就可受理性问题的质疑,而第19条主要处理具体犯罪嫌疑人或被告已经确定之后“案件”的管辖权和可受理性问题。同时,与第18条仅限于检察官基于自行调查权和缔约国提交之情势启动的调查不同,第19条也适用于检察官启动的对安理会提交之情势的调查。不仅如此,第19条并非只规定了法院有义务对管辖权问题进行主动确定,对可受理性问题可以主动予以断定,而且还规定,除有关的国家可以提出管辖权和可受理性质疑外,被告人或者已经成为逮捕和法庭传唤对象的人也可以提出质疑。此外,与第18条规定只有检察官有权请求预审分庭作出可受理性的初步裁决不同,第19条规定有权提出质疑的主体在确认指控前也有权直接向预审分庭提出可受理性和管辖权质疑。
(一)法院确定管辖权与可受理性问题的义务
规约第19条第1款规定:“本法院应确定对收到的任何案件具有管辖权。本法院可以依照第十七条,自行断定案件的可受理性问题。”从中可以看出,对于可受理性与管辖权问题,规约在19条中对法院提出了不同于第18条规定的义务要求。因此,我们不妨结合第18条的规定,就不同调查阶段法院对可受理性问题与管辖权问题是否有义务主动或被动或可以主动进行判断作一简短的比较和分析。规约第18条规定,在情势调查阶段,法院负有被动地确定可受理性问题的义务。当有关国家对法院可受理性问题提出质疑,检察官可提请预审分庭对可受理性问题进行裁定,此时的裁定是法院应当经由申请而被动作出,至于法院是否有义务或者可以主动对可受理性进行断定,本条款并未涉及。同时,第18条对管辖权质疑问题也未有规定。虽然根据对管辖权的管辖权原则,在调查和起诉的任何阶段,国际刑事法院的确有义务对有关管辖权质疑的问题作出确定与否的决定,并且确定管辖权问题是法院开展一切司法活动的根本前提,管辖权问题不解决,调查行动和后续的诉讼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但是,由于情势的调查正处于初期阶段,有些情势经过检察官调查之后未必会进入具体案件调查和起诉程序,如果此时有关国家并未对管辖权问题提出质疑,规约却规定法院有义务主动或可以主动对其自身(根据规约第34条包括检察官办公室在内)的管辖权问题进行确定,那么必然会不利于检察官办公室调查行动的开展,进而严重影响法院的工作效率。[11]至于如果有关国家对管辖权问题提出了质疑,规约是否应当要求法院有义务被动地对管辖权问题作出裁定问题,上文已有讨论,此处不再赘述。
与规约第18条的规定刚好相反,规约第19条第1款规定的是,法院对“具体案件”的管辖权和可受理性问题,均规定有权主动进行判断,而无须等到此类质疑被提出,只不过对管辖权是有义务“应当予以确定”,对可受理性则是可以“自行断定”。有观点认为,根据对管辖权的管辖原则,“此处如此规定没有必要”。[12]然而,事实上,本条款的规定与对管辖权的管辖权原则并不矛盾,因为它只是更进一步明确和强调了法院在此方面承担的义务。这点不难理解,既然检察官的工作已从泛泛而指的情势进入针对具体案件的调查与起诉阶段,那么规约对案件应当具备的法定条件自然比对情势的要求更高,因而规定法院应当主动确定案件的管辖权,在规约中明确此项义务并无不妥。当然,倘若此时有关国家或个人对此提出质疑,法院更有义务被动地予以确定,这也是第19条第2款所规定的内容。至于可受理性问题,在具体案件调查和起诉阶段,根据第1款的要求,法院可以“自行断定”,即意味着可以主动而为之,如果此时有关国家或个人也对此提出质疑,法院自然也应当被动地予以判断。由上可知,与第18条仅要求法院对情势调查阶段可受理性质疑的被动回应相比,规约第19条第1款中对管辖权与可受理性问题为法院设定了更灵活的权力与义务。
(二)可提出质疑的主体与处理程序
《罗马规约》第19条除第1款对法院处理管辖权与可受理性问题时的权力和义务进行了规定,在接下来的数款中也对可以提出质疑的主体以及质疑的受理、次数、处理程序等方面的要素进行了逐一的规定。
与规约第18条将对可受理性提出质疑的主体仅限定为有关国家不同,第19条第2款明确规定,可以提出质疑的主体包括以下三类:一是被告人或根据第58条已对其发出逮捕证或出庭传票的人;二是对案件具有管辖权的国家,以正在或已经调查或起诉该案件为理由提出质疑;三是根据第12条需要其接受本法院管辖权的国家,也就是作出声明接受法院管辖权的非缔约国。这三类主体可以根据第17条所述理由,对案件的可受理性提出质疑,也可以对本法院的管辖权提出质疑。
虽然规约允许相关主体对案件的管辖权和可受理性这两个问题提出相关质疑,但是此项质疑权的行使条件与范围并非没有限制。规约第19条第4款首先对提出质疑的时间和次数进行了规定,对于上述提出质疑的任何人或国家,只可以对某一个案件的可受理性或本法院的管辖权提出一次质疑,并且这项质疑应在审判开始前或开始时提出。在特殊情况下,法院可以允许多次提出质疑,或在审判开始后提出质疑。在审判开始时,或经法院同意,在其后对某一案件的可受理性提出的质疑,只可以根据第17条第1款第3项有关“一罪不二审”原则的规定提出。对质疑次数进行限定,主要是为了节省法院的开支和提高法院的工作效能。关于提出质疑的时间,一般要求应在审判开始前或开始时提出,第5款明确要求,对于管辖权或者可受理性提出质疑的国家应尽早提出质疑。虽然对此进行限定的目的在于,保障法院能尽早对管辖权和可受理性问题予以确定,有利于之后法院各机关采取相应的法律行动,但是究竟何为“尽早”,规约或《程序和证据规则》均未明确规定,从而也无法对有关主体故意拖延至开庭审理后提出质疑的行为进行规制。[13]值得一提的是,根据第18条第7款的规定在情势调查阶段提出过可受理性质疑的国家,在预审分庭对此作出过裁决的情况下,那么原则上就没有权利在案件调查阶段再提出可受理性质疑;如果这些国家质疑预审分庭根据第18条作出的裁定,那么只能以掌握进一步的重要事实或情况发生重大变化的理由,根据第19条对案件的可受理性再次提出质疑。
对于管辖权和可受理性的质疑具体由法院哪个机关负责受理问题,规约和《程序和证据规则》对此按照不同诉讼阶段进行了不同的规定。在确认指控以前,对某一案件可受理性的质疑或对法院管辖权的质疑,应提交预审分庭。在确认指控以后,应提交审判分庭。对于就管辖权或可受理性问题作出的裁判,可以依照第82条向上诉分庭提出上诉;如果在已确认指控但尚未组成或指定审判分庭期间,对法院管辖权或案件可受理性提出的质疑,应提交院长会议;在依照《程序和证据规则》第130条组成或指定审判分庭后,院长会议应立即将质疑移送审判分庭(《程序和证据规则》第60条)。
对法院管辖权或案件可受理性的质疑,无论是由被告人、犯罪嫌疑人和有关国家提出,还是由检察官就此提出的裁决申请,或是各分庭依照第19条第1款规定依职权进行确定,法院在程序上应当如何处理呢?《程序和证据规则》第58条对此进行了规定,预审分庭或者审判分庭“应决定应循程序,并可以酌情采取措施以适当进行诉讼。分庭可以举行听讯。如果不会造成不当延迟,分庭可以在确认或审判程序中一并审理提出的质疑或问题,但在这种情况下,分庭应先行审理并裁判提出的质疑或问题。法院应将收到的被告人、犯罪嫌疑人和有关国家提出请求书或申请书转发检察官,有关国家提出请求书或申请书还应提交被告人、犯罪嫌疑人,并应允许他们在分庭所定时限内对请求或申请提出书面意见”。同时,如果一案的管辖权和可受理性均受到质疑,《程序和证据规则》还规定,“法院应先裁定有关管辖权的质疑或问题,再裁定有关可受理性的质疑或问题”,以强调管辖权的质疑是法院首先要解决的根本性问题,没有这个前提,法院无法考虑其他相关的问题。
在保障有关主体有权提出相关质疑的同时,《罗马规约》第19条第3款还进一步确认:“在关于管辖权或可受理性问题的程序中,根据第十三条提交情势的各方及被害人均可以向本法院提出意见。”这些有权提出意见的主体包括提交情势的缔约国、安理会以及被害人。为了保障这一程序性权利,《程序和证据规则》第59条规定,国际刑事法院书记官长应将根据第19条第1款、第2款和第3款就管辖权或可受理性提出的任何问题或质疑,告知根据第13条提交情势的各方以及已就案件同法院联系的被害人或其法律代理人。书记官长应向上述各方提供关于质疑本法院管辖权或案件可受理性理由的摘要,但采用的方式应符合法院在资料的保密、人员的保护和证据的保全方面的义务。上述收到资料的各方可以在主管分庭认为适当的时限内,向该分庭提出书面意见。
(三)检察官处理相关质疑问题的权力与义务
对于有关主体向法院提出的管辖权或可受理性质疑,《罗马规约》为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设定了作出质疑裁决期间应当遵守的法律义务,也赋予了其必要的调查和起诉权力。也就是说,提出管辖权或可受理性质疑在法律上对检察官会产生的效果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1.暂停调查的义务
第19条第7款规定:“如果质疑系由第二款第2项或第3项所述国家提出,在本法院依照第十七条作出断定以前,检察官应暂停调查。”根据此条款的要求,检察官在一定情况下应当暂停对案件的调查。只是在检察官履行这一暂停调查义务之前,必须满足如下三方面的适用条件:首先,质疑必须是“由第二款第2项或第3项所述国家”,也就是“对案件具有管辖权的国家”和“根据第十二条需要其接受本法院管辖权的国家”提出的质疑,如果是“被告人或根据第五十八条已对其发出逮捕证或出庭传票的人”提出的质疑,那么检察官就没有暂停调查的义务。从中可以看出,国家提出的质疑比个人提出的可受理性质疑法律效果更明显。其次,有关国家提出的质疑必须是针对可受理性的质疑,因为《罗马规约》第17条只是规定“可受理性问题”,因此如果有关国家仅仅提出管辖权质疑,那么检察官也没有暂停调查的义务。最后,检察官暂停调查的时间点是有关国家提出可受理性质疑之后,法院依照第17条作出裁决之前。
那么这个暂停调查义务与第18条检察官等候一国调查义务之间有何区别呢?这两个义务都是由具有管辖权的国家提出可受理性质疑引起的,都实际导致检察官调查的暂停。两者的暂停调查最显著的区别是处于调查不同的阶段,第18条是情势调查阶段的可受理性质疑,因而检察官等候国内调查实际就是暂停对情势的调查,而第19条是案件调查和起诉阶段的暂停调查,因此检察官暂停的是对案件的调查(实际还包括起诉)。由于暂停调查的“情势”和“案件”存在差别,因此从暂停的效果上说,第18条的暂停调查意味着这个情势调查的暂停,而第19条的暂停调查只是暂停有关国家提出了质疑的个别案件的调查,检察官对于同一个情势中其他案件的调查仍然可以继续,除非有关国家也对这些案件的可受理性同时提出了质疑。
2.检察官在暂停调查期间的权力
提出管辖权和可受理性质疑不影响检察官在此之前采取的任何行动,或本法院在此以前发出的任何命令或逮捕证的有效性(第19条第9款),但是,在检察官依据第19条履行暂停调查义务后,其必然可能面临根据第18条暂停调查后遭遇的同样问题,即由于暂停调查可能丧失特殊的调查机会和证据的收集,在案件调查阶段,还可能导致错失抓捕犯罪嫌疑人的时机。为此,第19条第8款又进一步规定,暂停调查后,在法院正式作出裁定之前,检察官可以请求法院授权从事某些调查性活动。那么,在此期间,检察官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可以进行哪些特殊的调查行为呢?
首先,检察官可以请求法院授权“采取第十八条第六款所述一类的必要调查步骤”。这就意味着,如果出现取得重要证据的独特机会,或者面对证据日后极可能无法获得的情况,检察官可以请预审分庭或审判分庭作为例外,授权采取必要调查步骤,对此种证据进行保全。由于检察官可以授权采取的调查行动是“第十八条第六款所述一类”的必要调查步骤,因此调查步骤并不以第18条第6款规定的内容为限,对于其他跟其类似的必要调查步骤,检察官也可以请求法院授权采取。
其次,检察官可以请求法院授权检察官“录取证人的陈述或证言,或完成在质疑提出前已开始的证据收集和审查工作”。这就意味着在暂停调查期间,只要经过法院授权,检察官仍然可以随时录取证人的陈述和证言;而对于证据收集和审查工作,只有在有关国家提出质疑之前已经开始的,才可以继续进行直到完成。这样有利于保障检察官录取证人陈述和证言的工作基本不会受到有关国家提出的可受理性质疑的影响,也可以使这种质疑对已经开始的证据收集工作的影响降到最低,并减少可能极其昂贵的调查成本和对被害人和证人的干扰。
第三,检察官还可以请求法院授权其“与有关各国合作,防止已被检察官根据第五十八条请求对其发出逮捕证的人潜逃”。这个规定主要是为了确保已经对其发出逮捕证的人不会因为暂停调查而潜逃,使检察官在暂停调查期间仍然可以通过与各国合作,逮捕已经发出逮捕证的人。不过这只能限于对已经发出逮捕证的人,检察官在暂停调查期间无法对将来可能被签发逮捕证的人采取措施,也无法申请新的逮捕证。
此外,第19条第11款规定了检察官在暂停调查期间与有关国家的资料交流问题。该条款确认,如果检察官考虑到第17条所述的事项,决定等候一项调查,检察官可以请有关国家向其提供关于调查程序的资料。根据有关国家的请求,这些资料应予保密。检察官之后决定进行调查时,应通报其曾等候调查的国家。这条规定与第18条第5款的规定比较类似,不过两者也存在一定的区别,两者不仅在调查所处的阶段方面不同,在强制力方面也存在很大不同。例如,第18条第5款规定,“检察官可以要求有关国家定期向检察官通报其调查的进展和其后的任何起诉。缔约国应无不当延误地对这方面的要求作出答复”,这表明这是一种检察官的权力以及缔约国的义务;但根据第19条第11款检察官只是“请有关国家向其提供关于调查程序的资料”,虽然资料的范围可能要宽于前者,但这并不是一项检察官的权力,而是其寻求其他国家帮助的一种请求而已。当然,对于检察官提供协助的请求,根据《罗马规约》的要求,缔约国也有义务提供这种合作,只是此项义务的强度并没有第18条第5款那么明显。而且从字面含义看,该条款的内涵似乎并不限于面临可受理性质疑后导致暂停调查的情况,它还包含检察官发现具有不符合第17条的情况因而自愿暂停调查的情形。[14]这也是该条款与第18条第5款的一个显著区别。
3.请求复议权
第19条第10款还规定了检察官在应对可受理性质疑方面享有的另一项权力,那就是对法院作出不可受理裁决提请复议的权力。该条款规定:“如果本法院根据第十七条决定某一案件不可受理,检察官在确信发现的新事实否定原来根据第十七条认定案件不可受理的依据时,可以请求复议上述决定。”这种情况主要发生在法院对不可受理性决定已经生效之后的情况。如果不可受理性决定还没有生效,检察官可以提出上诉。《罗马规约》第82条规定,对于“关于管辖权或可受理性的裁判”,当事双方(包括检察官)均可提出上诉。《程序和证据规则》第154条第1款规定,对于这种裁判的上诉,检察官应在接到关于裁判的通知之日起五日以内提出。根据第19条第10款规定,在法院有关可受理性的裁决生效后,如果发现了案件的新事实,并且确信发现的新事实足以否定法院原来根据第17条认定案件不可受理的依据,那么检察官可以向法院提出复议上述裁判的申请。显然,与上诉程序不同,复议提出并没有时间限制,但它需要以上述特定理由为启动条件。
复议申请应当向作出生效裁判的分庭提出,如果作出生效裁判的是预审分庭或审判分庭,就应该向预审分庭或审判分庭提出,如果作出生效裁判的是上诉分庭,则应向上诉分庭提出。对于预审分庭或审判分庭就检察官的复议申请所作出的裁定,检察官应当可以提出上诉,因为这种裁定仍然属于《罗马规约》第82条规定的“关于管辖权或可受理性的裁判”。在《程序和证据规则》第62条中规定,根据第19条第2款提出可受理性质疑的国家,其质疑导致第19条第10款所规定的不可受理决定的,应获得关于检察官复议请求的通报,并有机会在所定时限内提出意见。这主要是为了保障这些国家的参与权。不过,《程序和证据规则》第62条并没有规定,可能提出质疑的被告人或犯罪嫌疑人是否有获得检察官有关复议申请通报的权利。法院关于可受理性的裁定既可能因有关国家的质疑行为所致,也可能是被告人或者犯罪嫌疑人提出质疑的结果。在由被告人或者犯罪嫌疑人提出质疑并导致法院作出不可受理裁定的情况下,检察官的复议也与之存在直接利害关系,因此规约似乎并无充足的理由让检察官只是通报有关国家,而不通报这些利害关系人。
第19条第10款只是规定了检察官在法院对不可受理性决定已经生效之后的复议权利,但并没有规定,如果法院作出不具有管辖权的决定,在其生效之后检察官是否也享有这种复议权利。从这种有选择性的规定来看,可以很自然推导出的结论是,检察官并不能请求对管辖权的决定进行复议。[15]尽管如此,但有人认为,如果检察官在法院对管辖权作出决定之后发现了一些原来没有发现并且也不可能发现的信息(如一个不愿合作的国家掩藏了证据),检察官应该可以根据第19条第3款有关“检察官可以请法院就管辖权或可受理性问题作出裁定”的规定申请裁定,因为该条款并没有对检察官提出这种裁定申请的实践和次数作出限制。[16]然而,这种观点其实也存在一定的问题,因为如果按照这种解释,第19条第10款规定的检察官复议申请程序就根本没有必要,检察官对于法院不可受理的决定同样可以根据第19条第3款再次提出裁定申请。由此可见,检察官根据第19条应当无法请求对法院关于管辖权的生效决定进行复议。当然,如果在管辖权方面出现如第19条第10款规定的同样情形,如发现新的重要事实,对此应如何处理,仍然有待于法院将来的实践予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