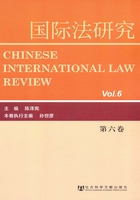
一 情势调查期间的可受理性质疑
《罗马规约》第18条的规定有多重目的。首先,它强调缔约国在调查和起诉属于国际刑事法院管辖范围内的犯罪方面具有首要责任和权利,因此体现了《罗马规约》确立的补充性管辖原则这一基本原则。其次,第18条也使有关国家在检察官开始进行情势调查的早期阶段即有机会向国际刑事法院提出可受理性质疑,从而可以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补充性管辖原则进行监督。第三,它通过预审分庭的监督确保检察官能够负责任地行使其自由裁量权。第四,预审分庭在调查这么早的阶段即介入也有助于保护检察官不受某些国家可能提出的轻率或基于政治偏见进行调查的指责。[2]与第19条同时赋予国家和个人对案件的可受理性和管辖权质疑权利不同,第18条只是允许有关国家在检察官启动情势调查的初步阶段对于某些情势的可受理性问题提出质疑。
(一)可以提出可受理性质疑的情势范围
对于情势调查阶段可以提出可受理性质疑的情势范围,第18条只是限于“已依照第十三条第1项提交本法院”的情势,以及检察官“根据第十三条第3项和第十五条开始调查”的情势。第13条第1项规定,“缔约国依照第十四条规定,向检察官提交显示一项或多项犯罪已经发生的情势”,而第13条第3项和第15条都是指检察官“可以自行根据有关本法院管辖权内的犯罪的资料开始调查”。因此,就第18条规定可以提出可受理性质疑的情势而言,仅仅包含缔约国提交之情势以及检察官通过自行调查权启动的情势。只有对这两类情势有管辖权的国家在收到检察官的通报一个月内,才“可以通知本法院,对于可能构成第五条所述犯罪,而且与国家通报所提供的资料有关的犯罪行为,该国正在或已经对本国国民或在其管辖权内的其他人进行调查”,并且可以要求检察官等候其调查。
很显然,第18条并没有规定有关国家可以对检察官启动调查的联合国安理会根据第13条第2项规定向检察官提出的情势提出可受理性质疑的权利。这说明,第18条并不适用于安理会提交的情势,因此对于安理会提交的情势,有关国家没有权利在检察官启动情势调查的初步阶段即提出可受理性质疑。这种规定也说明,安理会提交的情势在情势调查阶段具有不受有关国家提出的可受理性质疑的特权。这种特权主要来自《联合国宪章》第7章有关安理会在处理国际和平和安全的事项上享有特权的规定。安理会根据《联合国宪章》第7章向检察官提交情势说明这种情势已经事关国际和平和安全,因此所有的国家也有义务遵守安理会作出的这种情势提交决定,检察官基于这种提交作出的情势调查决定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安理会提交情势行为的自然延伸,因此第18条不赋予有关国家对安理会提交之情势提出质疑的权利有其合理之处。
然而,如同缔约国提交的情势以及检察官自行调查启动的情势一样,安理会提交的情势同样会存在有关国家“正在或已经对本国国民或在其管辖权内的其他人进行调查”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不允许这些国家在这个阶段提出合法性质疑是否意味着国际刑事法院对安理会提交的情势就不适用补充性管辖原则?答案无疑是否定的。因为根据《罗马规约》的规定,无论检察官启动调查的情势来源于何种方式,都必须符合规约第17条规定的可受理性条件,检察官只有在判定接受初步审查的情势符合该可受理性条件的前提下,才会启动对有关情势(包括安理会提交之情势)的调查。不仅如此,规约第19条还规定对于对案件具有管辖权的国家对于法院正在调查或起诉的案件(包括安理会提交之情势中的案件)可提出可受理性和管辖权质疑。由此可见,规约第18条不赋予有关国家在情势调查阶段提出可受理性质疑的权利的主要原因并不在于安理会提交的情势在可受理性问题上有什么特殊性。从根本上说,原因还是在于安理会提交的情势以及第18条的特殊规定。安理会提交情势就意味着它事关世界和平和安全,因此对其进行调查具有至关重要性和紧迫性,如果在启动情势调查的初步阶段就赋予有关国家提出可受理性质疑的权利,那么检察官一般情况下就必须按照规定等候该国的调查,并且只有在决定等候之日起六个月后,或在由于该国不愿意或不能够切实进行调查,情况发生重大变化的任何时候,才可以由检察官进行复议。这种做法显然与安理会提交之情势的至关重要性和紧迫性不太相适应,而允许检察官在启动此类情势的调查后不受打扰地进行调查工作显然更加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和安全。当调查进入针对特定犯罪事件和犯罪嫌疑人的案件调查阶段之后,有关国家针对安理会提交之情势中的具体案件提出的质疑则并不会出现第18条情势调查阶段提出质疑可能导致的全面暂停对情势调查的后果,毕竟它只能引发检察官对情势中某个具体个案的暂停调查。这也是规约第18条未赋予有关国家对安理会提交之情势提出可受理性质疑权利,第19条却赋予其此类权利的很大一个原因所在。
此外,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规约第18条并没有提到《罗马规约》第12条第3款规定向国际刑事法院提出表示接受国际刑事法院对发生在其境内或者由本国国民所犯的有关犯罪行使管辖权的声明这种情形。有学者认为,非缔约国的这种声明实际也是一种情势提交,并且与缔约国和安理会的情势提交一样都只是让检察官注意到可能引发调查程序的一些事实。[3]《检察官办公室条例》第25条也把非缔约国的这种声明视为引发办公室对情势初步审查和评估的三个来源之一,然而,这并不表明它在法律效果上就等同于安理会或缔约国的情势提交,事实上它只是表明该国自愿接受国际刑事法院对有关国际犯罪的管辖,在情势初步审查方面引发的法律效果更像是缔约国或者非缔约国提交一般犯罪资料和信息的行为。作出这种论断的第一个理由是,根据规约第12条规定,非缔约国提交接受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声明只是国际刑事法院“行使管辖权的先决条件”,这种情形未规定在第13条有关提交情势的规定中本身就说明其不等于提交情势;其次,第53条只是确认缔约国和安理会可以就检察官作出的不予调查的初步审查决定向预审分庭提出复核请求,提交上述声明的非缔约国并不享有这项权利。还有一个可以证明的事实是,对于科特迪瓦政府两次提交的自愿接受管辖声明,检察官都只是将它们视为法院可以行使管辖权的基础,而没有将其视为一种类似于缔约国那样的情势提交行为,因为最后在对该情势进行初步审查后检察官并没有像对缔约国或安理会提交的情势进行初步审查后直接作出调查决定一样行动,而是向预审分庭申请启动自行调查授权申请。从检察官对科特迪瓦的司法实践也可以看出,非缔约国提交接受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声明最后引发有关情势调查的情形在性质上就属于第18条规定的检察官通过自行调查权启动情势调查的情况。
(二)情势调查期间检察官对可受理性质疑的应对措施
1.检察官决定调查后的通报义务
检察官对缔约国提交的情势作出启动调查的决定,或者根据规约第13条第3项和第15条获得预审分庭对其自行调查的授权之后,检察官办公室面临的首要任务是,将该项决定或授权通报所有缔约国以及对有关犯罪具有管辖权的国家。规约第18条第1款规定:“在一项情势已依照第十三条第1项提交本法院,而且检察官认为有合理根据开始调查时,或在检察官根据第十三条第3项和第十五条开始调查时,检察官应通报所有缔约国,及通报根据所得到的资料考虑,通常对有关犯罪行使管辖权的国家。”这种通报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向所有缔约国通报检察官即将开展的调查行为,既可以让缔约国对检察官办公室即将开展的调查工作有所了解,也允许所有缔约国有机会向法院提出可受理性质疑,并提醒在将来的调查和起诉过程中,相关缔约国应向检察官办公室以及国际刑事法院其他内部机构提供相关合作与协助;二是通报对于准备调查的情势可能具有管辖权的国家,告知其可以根据《罗马规约》有关规定,就情势可受理性问题向国际刑事法院提出质疑,从而避免出现违反补充性管辖原则和“一罪不二审”原则的情形。根据该条规定,检察官通报的对象包括所有缔约国以及通常对有关犯罪具有管辖权的国家,其中对有关犯罪具有管辖权的国家至少应包括犯罪发生地国以及犯罪嫌疑人的国籍国。但是,如果对这一通报要求进行广义的解释,可以说所有国家都将得到通知,因为根据普遍管辖原则,所有国家通常都可能对这些犯罪具有管辖权。[4]当然,根据该条款规定,只有对于检察官基于自行调查权和缔约国提交之情势启动的调查,检察官才负有这种通报义务。而对于检察官对安理会提交之情势启动的调查,并不受制于这个程序。因此,在情势调查阶段,有关国家无权对情势的可受理性问题提出质疑,检察官也无须对此进行回应。
同时,检察官在向这些国家通报过程中,可以灵活决定通报的方式及其内容,这在规约第18条也有所规定:“检察官可以在保密的基础上通报上述国家。如果检察官认为有必要保护个人、防止毁灭证据或防止潜逃,可以限制向国家提供的资料的范围。”对此,《程序和证据规则》第52条对于检察官提供资料的内容设置了进一步的义务,它要求检察官在不违背上述限制的情况下,将关于可能构成规约第5条所述犯罪的行为包含在通报之内,并且向缔约国和其他具有管辖权的国家提供充分资料,使其足以判断本国是否再对相同情势进行调查。受通报的国家如果认为检察官提供的资料不够充分,也可以请检察官提供补充资料,以便确定是否存在重复性调查的问题。不过受通报国这种寻求补充资料的行为,并不能影响受通报国根据第18条第2款规定,在一个月的期限内对检察官通报给予回应,同时检察官也应对该受通报国提出的补充资料的要求迅速作出回复;对于预审分庭基于检察官申请作出的裁定,有关国家也可以根据第82条向上诉分庭提出上诉。
2.检察官决定是否等候国内调查
规约第18条第2款规定:“在收到上述通报一个月内,有关国家可以通报本法院,对于可能构成第五条所述犯罪,而且与国家通报所提供的资料有关的犯罪行为,该国正在或已经对本国国民或在其管辖权内的其他人进行调查。根据该国的要求,检察官应等候该国对有关的人的调查,除非预审分庭根据检察官的申请,决定授权进行调查。”此条款授权受通报国在收到检察官通报的一个月内,可以以该国正在或已经对可能属于检察官调查范围的本国国民,或在其管辖权内的其他人进行调查为由提出可受理性质疑。对于这种质疑,检察官可以作出选择:一种是根据该国要求,决定等候该国对有关的人进行调查;另一种是可以选择直接将该问题交由预审分庭裁决,由后者决定检察官是推迟调查还是继续进行。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这个条款规定有关国家对于这个阶段可受理性的质疑可以通报“本法院”(因而可能包括预审分庭),但预审分庭并没有义务直接对它们提出的可受理性质疑作出裁决。根据该条款,只有检察官可以请求预审分庭对有关可受理性问题作出裁决。这一点与后面第19条规定的可受理性质疑和裁决有所不同。由此也可以看出,在情势调查阶段,检察官在应对可受理性质疑方面享有较多的自主权,这一点也与下文将谈到的案件调查阶段检察官在此方面的权力有所不同。
《程序和证据规则》第53条要求,一国根据第18条第2款要求检察官等候调查时,应书面提出要求,并参照第18条第2款提供有关国内调查的资料。如果检察官认为其提供的资料不充分,也可以请该国提供补充资料。如果有关国家基于各种原因拒绝提供充分的资料,或者对检察官提供补充资料的请求不予回应,而现有资料又不足以判断有关国家国内调查和起诉的性质时,检察官也可以直接请求预审分庭作出裁决。《程序和证据规则》第55条规定,预审分庭应当决定应循程序,并可以采取相应措施以适当进行诉讼,包括举行听讯;预审分庭应审查检察官的申请及依照第18条第2款要求等候调查的国家提出的任何意见,并应考虑第17条列举的因素,对是否授权进行调查作出决定;预审分庭在作出决定后,应将决定及作出决定的根据尽快通报检察官和要求等候调查的国家。当然,对预审分庭作出的裁定,有关国家或检察官可以根据第82条的规定向上诉分庭提出中间上诉(interlocutory appeal)。
3.检察官等候国内调查期间的权力
如果检察官决定等候一国调查的决定,或者预审分庭作出此类裁定,那么检察官必须等候有关国家的国内调查。为了确保检察官决定调查的情势得到有效调查,避免有罪不罚情况的出现,第18条也授权检察官可以对有关国家是否能够和愿意对有关犯罪进行调查予以监督和定期评估。第18条第3款确认:“检察官等候一国调查的决定,在决定等候之日起六个月后,或在由于该国不愿意或不能够切实进行调查,情况发生重大变化的任何时候,可以由检察官复议。”第5款又规定:“如果检察官根据第二款等候调查,检察官可以要求有关国家定期向检察官通报其调查的进展和其后的任何起诉。缔约国应无不当拖延地对这方面的要求作出答复。”从常理上说,如果缔约国对检察官定期通报要求不作答复或者答复存在不当拖延情况,检察官就可以据此判断该国存在不愿意或不能够进行切实调查的问题。该条款只是规定了“缔约国”应无不当拖延地对检察官相关的要求作出答复,而未要求对情势具有管辖权的非缔约国履行此类义务,因为根据国际法,《罗马规约》无权对非缔约国设定义务。尽管如此,但倘若非缔约国对检察官定期通报的要求不予回应或者答复存在不当拖延,这也并不妨碍检察官作出认定该非缔约国不愿意或不能够进行切实调查的判断。如果在等候国内调查期间,检察官认为该国不愿意或不能够切实进行调查,检察官仍然可以根据第18条第2款申请预审分庭裁决。
在等候国内调查期间,检察官还有一项特别的调查权力。第18条第6款规定:“在预审分庭作出裁定以前,或在检察官根据本条等候调查后的任何时间,如果出现取得重要证据的独特机会,或者面对证据日后极可能无法获得的情况,检察官可以请预审分庭作为例外,授权采取必要调查步骤,保全这种证据。”规约对此予以特别规定的原因,主要是为了防止出现因检察官等候国内调查而给未来可能进行的调查带来严重不利的影响,诸如可能丧失获得某些重要证据的独特机会,证据可能被销毁或灭失,这些不利的影响既可能是因为有关国家阻碍行为而造成的,也可能是由于自然和社会方面的其他原因所引起的。不过,无论如何,此项权力仅在例外情况下,经由预审分庭的授权方能予以行使。对此,《程序和证据规则》第57条专门进行了规定,检察官在第18条第6款规定的情况下向预审分庭提出的申请,应在检察官单方参与的非公开庭上审理,预审分庭应从速对申请作出裁定。
(三)情势调查期间可否对管辖权提出质疑
虽然《罗马规约》第18条规定了在部分情势调查启动之初,检察官和预审分庭应如何应对有关国家提出的对情势可受理性的质疑,但是该条并未涉及有关国家是否可以就情势的管辖权问题提出质疑。这说明第18条规定的程序适用于检察官对一个情势进行调查之初,在这个阶段,法院没有义务确定法院对检察官将要调查或正在调查的情势有无管辖权,法院只能确定检察官是否可受理对一项情势的调查。[5]然而,有关国家在收到检察官发出的调查通报时,如果认为国际刑事法院不具有管辖权,会很自然将管辖权与可受理性问题一并向预审分庭提出质疑,那么在此阶段,有关国家有没有提出管辖权质疑的权利,以及检察官和预审分庭是否具有审查这种质疑的义务呢?《罗马规约》第18条对此问题没有作出规定,第19条却特别规定了“质疑法院的管辖权或案件的可受理性”问题,其中第1款规定,“本法院应确定对收到的任何案件具有管辖权”。从该条规定的主要内容看,它主要涉及具体“案件”调查和起诉期间如何应对对管辖权和受理性的质疑问题。这里的“收到的任何案件”意味这里的“案件”应该不是第13条、第14条和第18条规定的“情势”,而应该是“情势”调查已经得出的某些结果:具体的个人已经被确定作为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甚至逮捕令或者出庭传票已经签发,因此根据这个规定,法院没有义务主动对检察官调查之情势的管辖权问题作出决定。[6]对于第19条的“案件”,预审分庭在其解释中也确认其是不同于“情势”的具有确定指控对象和犯罪的情形,[7]因此断定第19条的管辖权质疑规定只是适用于“案件”调查和起诉阶段而不适用于更早的情势调查阶段不无道理。
对于上述理解,有观点认为,从严格意义上说,《罗马规约》并没有必要在第19条对法院设置“应当确定案件的管辖权”这项义务。[8]其理由在于,对于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权问题,可以从国际刑事司法机构以往的司法实践中找到一般性解释。前南国际刑事法庭在对“塔迪奇案”有关管辖权中间上诉的裁判中认为,确认法庭自身的管辖权是任何司法或仲裁法庭本身所附属或固有的权力(incidental or inherent jurisdiction),这就是对管辖权的管辖权(jurisdiction to determine its own jurisdiction)。[9]如果检察官的调查行为完全超出了法院的管辖范围(如调查的情势发生在《罗马规约》生效之前,并且在生效之前已经结束),那么预审分庭可以根据法院固有的权力,对检察官调查行为是否具有管辖权进行判断。[10]换而言之,根据上述原则,如果有国家对法院管辖权提出质疑,法院都有权力也有义务对之作出确定与否的决定,无论是在情势调查阶段还是案件调查阶段。当然,对国际刑事法院是否认可对法院管辖权的管辖权这一原则,《罗马规约》规定得不甚明确,因此,法院在情势调查阶段应如何处理管辖权质疑问题,尚有待于预审分庭和上诉分庭在将来的实践中予以解决。